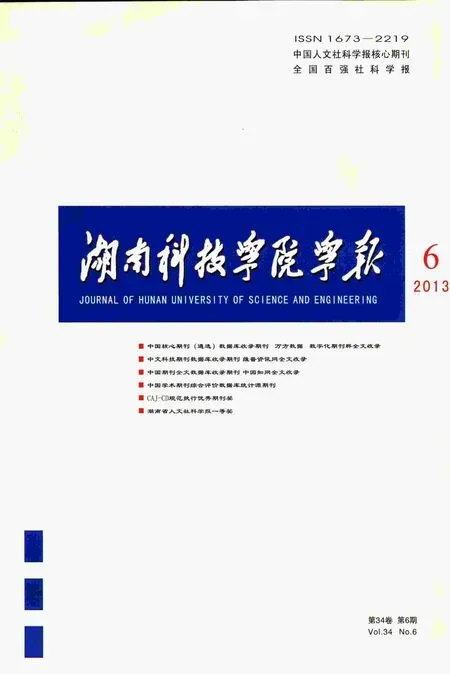发展中国家腐败制控机制探究
王金平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一 引 言
腐败制控机制就是一个国家在反腐败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手段机制的总和。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一直十分严重,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与进步。本文所探讨的“发展中国家”既包括当下仍然属于发展中的国家,也包括那些在20世纪60、70年代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今已成为新兴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即“曾经的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这些国家不仅通过经济发展,而且也通过政治发展,包括持续有效的反腐倡廉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初步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在对腐败制控机制进行探索,有的成效显著,有的却收效甚微,分析其探索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腐败制控机制
贪污腐败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构成严重威胁,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各种腐败制控机制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腐败制控机制带有着明显的传统色彩。
(一)发动运动,大张旗鼓反对腐败
运动式反腐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做法。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反腐败斗争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运动式反腐。亚洲的韩国等亦是如此。二战后,韩国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依靠吃苦耐劳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腐败所造成的痛苦之中。韩国各届政府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清除腐败现象,其中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开展反腐败运动。1961年朴正熙上台执政以后,一方面严厉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败运动。上台伊始就发起了“政治净化运动”,惩办了一批前政府的贪官污吏和其他违法乱纪分子。接着又开展了“庶政刷新”运动。庶政刷新运动的宗旨是“消除公务员社会的所有腐败现象,开展有效、明朗的服务行政,恢复国民的信赖;在加强行政效率的同时把运动升华为消除整个社会腐败现象的社会净化运动和提高国民价值观,树立健全的国民精神的精神改革运动”。1992年8月金泳三上任后雷厉风行的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运动,率先公布个人财产,修改选举法和公职人员的伦理法,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倡导节俭,整肃官场陋习,针对政界、军界要员进行了全面道德重建,并把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推上了审判台,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不流血革命”。虽然金泳三反腐败不遗余力,但都是以治标不治本的行政手段(被人指责为“清算政治”)为主,没有动摇颓相初露的韩国政治经济根基。结果是,反腐败运动虽然轰轰烈烈,而腐败则“树欲静,而风不止”,金泳三像消防队员,疲于奔命,最后自己的阁僚、秘书乃至儿子也在旧体制的诱惑下,卷入了“官商勾结”的腐败浪潮之中。
韩国的这种运动式反腐的特点和结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运动式反腐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对腐败分子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在短期内可以有效地制止腐败的滋长蔓延,但由于没有涉及到根本的制度问题,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贪污腐败不可避免的还会卷土重来。在巨大的权力、金钱诱惑下,在缺乏刚性的监督制约下,执政者及其亲信很快必将走向腐化。运动式反腐往往回避已经暴露的体制问题,靠人治色彩浓厚的政客手段,可以得势一时,但终究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命运。
(二)执政者率先垂范,高调反腐
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制控机制无不打上最高执政者鲜明个性的烙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在掌握政权之后,往往都高调反腐、率先垂范,以反腐败作为树立威信、建构合法性的突破口,同时,也期望能够以此消除腐败,建设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1986年1月,以穆塞维尼为首的“国家抵抗运动”开始执政乌干达,执政伊始就明确表示视腐败为以往遗传下来的罪恶之一,是阻止乌干达进步的最主要障碍。穆塞韦尼总统带头垂范,清正廉洁,因而在乌干达人民中树立了较高威望。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执政 8个月后就建立政府检察长办公室(IGG),专司反腐败工作,在政府机构中引入责任制度,为所有公务员建立行为准则,鼓励公众揭发检举腐败现象,强调舆论监督等,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腐败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状况。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1986年上台以后,很注意为政清廉。针对当时菲律宾贪污受贿现象严重,尤其在马科斯统治后期贪污受贿泛滥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控制腐败的措施。1986年6月,阿基诺夫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内阁成员出国履行公务时,必须严格控制开支,任何部长都不得订购头等舱机票,不得住豪华旅馆。阿基诺夫人上台后首次出访美国时,不乘专机只乘普通班机,随身携带两只箱子,同马科斯夫人出访美国时仅衣箱就有200个,形成鲜明对比。1989年7月9日晨,阿基诺夫人乘菲律宾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西德访问,3天后,她又乘民航班机前往法国。菲律宾驻西德大使解释说,总统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约,因为国事访问一向耗资不少。”她还坚决反对她的直系亲属参政。因此有的报纸称她是“清廉的化身”。科·阿基诺夫人虽然自身廉洁,但对待政府官员和亲属的贪污舞弊行为却心慈手软,所以一些反贪污的政令只能停留于纸上谈兵,贪官污吏变本加厉有恃无恐,最终贪污腐化的猖獗,断送了科·阿基诺的政权。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依靠最高领导者的率先垂范形成的人格魅力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人治式的反腐败行为,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三)激进式变革,制度移植性反腐
在发展中国家反腐败的实践中,还有一种反腐败方式就是进行激进变革,一成不变地移植国外制度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全社会全面推行民主化、公开化、自由化进程,以期能够清除腐败现象。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做法的结果却形成了社会治理系统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由于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对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反叛心理,而突如其来的社会政治开放,把他们从封闭、专制下解放出来,他们一下子茫然无措,以致无法适应而处于“失重”状态,并且又缺乏法制规范,在不知法、不守法、不适应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缺乏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导致社会失控、政局动荡。另一方面,由于旧制度、旧组织的迅速解体,新制度新组织的仓促建立,造成人治和法治的简单迭加,这两种体制内在排斥和消耗,形成了大量的权力管控真空,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的滋生,而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又要求政治上层对社会进行强化控制,但强化控制的结果,又回到个人的专制和腐败的“历史回归”上。
激进式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如果超出了社会政治制度整合和系统所能容纳的限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不但不能反腐败,反而被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二战后相继独立的许多非洲国家基本上继承了宗主国的政治模式,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但由于这种照搬过来的议会民主制并不符合当时非洲的国情,非洲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部族势力比较强大,人民也缺乏基本的公民意识,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党往往成为部族势力的载体,腐败油然而生。虽然许多国家也建立了相当多的预防腐败惩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反腐机构,但都难以发挥其作用,只是流于形式、遮人眼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与非洲也大同小异。可见不考虑本国国情,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反腐模式,最终只能导致国家动荡,腐败猖獗,社会落后。
三 发展中国家探索腐败制控机制的经验教训
发展中国家在腐败制控机制上的探索,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留下了值得我们总结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总体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是一种人治性的而非法治性制度性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是短期性非持续性的。实践证明,反腐败靠法治比人治更为可靠,靠制度比靠领导更为有效与长久。
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在腐败制控机制上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最高领导者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只是反腐倡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乌干达、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最高领导者本人虽然能保持廉洁,率先垂范,但却对手下的高级官员、亲戚朋友的腐败行为不敢、不能或不忍心惩罚,致使腐败照样滋生蔓延。虽然领导者个人获得了清廉的好名声,但整个国家和人民却深陷于腐败造成的痛苦之中,最后人民忍无可忍,起而反对,导致最高领导人的下台。另一方面,领导者必须廉洁自律,这是反对腐败的必要条件,领导者的道德水准是健康社会、健康政府的基础。如果领导者自己都带头贪污腐化、巧取豪夺、穷奢极欲、贪赃枉法,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因为领导者本人就是最大的腐败分子。领导者除了自己必须清廉公正、严于律己之外,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的亲朋和所属的政党,决不能有丝毫的腐败行为,更不能对他们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纵容放任。必须始终从严教育、从严管理,绝不许越雷池半步。如果出了问题,要大义灭亲,严加惩处,不能因心慈手软而放虎归山,搞下不为例。否则,放过的也许才几个人,但损害的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崩溃的是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败坏的是整个社会风气。除此之外,最高领导者还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与腐败行分子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正如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杨温明所说,作为高层政府官员特别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切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愿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反腐败国际主席彼得·艾根也认为:如果领导者缺乏政治意志和坚定信心,在反腐败方面是不可能进行立法和行政上的改革的。如果领导者在反腐败时虎头蛇尾,或者雷声大雨点小,也是难以清除腐败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的发展中国家领导者一边高喊反腐败口号,一边却大肆腐败;一边严打苍蝇式的小腐败,一边却纵容老虎式的大腐败;一边对人民信誓旦旦,一边却肆意妄为。甚至有的领导者还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打压持不同政见者,排斥异己,搞家族政治、家族腐败。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玩火自焚。
其次,发展中国家腐败制控机制的探索证明人治性的反腐倡廉不能撼动体制性腐败的根基。反腐败运动在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人民群众的素质还比较低,而反腐败斗争又错综复杂、腐败势力相当强大时,广泛发动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大张旗鼓的反腐败运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如果在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完善以后,还不断地依靠发动各种运动来反腐败,就说明其政治体制还缺乏健全和正常的“预警”和“纠偏”机制,不能在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中把其中的腐败与弊端予以矫正,说明了现行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严重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否则,随着问题、弊端的逐步堆积,日积月累,最后只能靠某种偶然事件,如某个铁碗人物的上台、某个社会事件的爆发为契机,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腐败问题与腐败份子进行“爆发性”的大清洗。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运动。一场政治反腐败运动过后,不论其荡涤污垢的效果有多大,如果仍未建立起稳定、有效、正常的“纠偏”机制,对于腐败问题不能进行正常的“疏导”与清除,就只能等待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的“爆发性”解决。进一步说,反腐败运动是政治体制缺乏稳定性的表现,是一种政治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一种“稚嫩”表现。只有建立一整套防治腐败的严密体制,才能使腐败在整体上处于可控状态,使腐败不至于泛滥成灾,危害国家人民,甚至亡党亡国。
最后,引进和借鉴国外反腐败制度和经验决不能生吞活剥,不考虑国情,照搬照抄。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指出,腐败是“软政权”下的产物,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在一个“软政权”的国家中,松弛和随意可以为那些掌握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所利用来谋个人私利。一方面软政权提供的可大量利用的机会当然只供上等阶层任意享用;另一方面即使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常常找到这样的机会来谋些小利。为什么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形成软政权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引进其他国家的制度时,没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照搬照抄,虽然各种制度、各种机构都建立起来了,但都只是聋子的耳朵——纯属摆设,甚至成为某些阴谋家、野心家争名夺利的工具。实践证明外国的好经验、制度要学习借鉴,但必须建立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辨证地“扬弃”,才能使之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1]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3]刘明波.外国监察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何增科.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