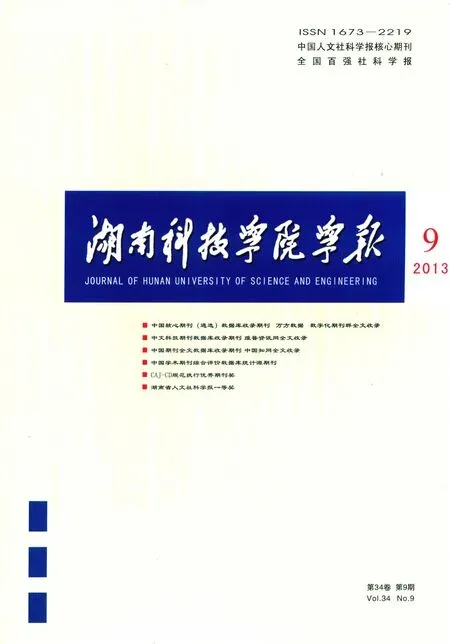凌鹰新乡土散文的审美视界
刘忠华
(湖南科技学院 图书馆,湖南 永州 425199)
一个雨过天晴的初夏的黄昏,我坐在草地上轻轻地嗅着那些久违而又熟悉的泥土与青草的气息,心底突然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恋情绪。我知道这种情绪来自于我相识了20余年的老友凌鹰的那些新乡土散文,因为我最近刚刚读完他近几年创作的一系列新乡土散文,心里一直就想为他那些文字写点自己的感悟,可又总是被一些杂务给拖延下来。何况,凌鹰的散文,也确实能让他的阅读者生出许多颖悟来。这个下午对泥土最直接的亲近,让我做出一个断然的决定,要对凌鹰的一系列新乡土散文做一个理性的梳理。
一
读完凌鹰的新乡土散文,我的脑海里随即浮现出了一个多彩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是凌鹰以他精妙的笔触和诗意的抒写,所描绘和展现的是他独有的世界。在这里,凌鹰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他对潇湘大地这一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感悟,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表达着他对神奇秀美的潇湘故土的深情守望,抒发着他对这片古老大地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忧思。
曹凌霞《乡土世界”的符号学阐释——以乡土散文为例》曾以乡土散文为例,从符号学的角度阐释了乡土世界的三重符号学意义,认为它包括了“土性乡土”、“文化乡土”和“神性乡土”,乡土散文所呈现的乡土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符号世界。此论对于我们理解乡土散文有一定的美学意义。在这里,我也试图将凌鹰的新乡土散文所呈现的世界分为“土性乡土”、“文化乡土”和“神性乡土”,并称之为“三重世界”。在我看来,这“三重世界”其实也是凌鹰新乡土散文的审美视界,或者说审美维度。他就是从这三个维度,去观照他的乡土世界,并将之言说成散文的。
乡土散文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其笔下的乡土世界正是建构在他赖以生、赖以长的以故土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土性’乡土”实际上就是一种以作家出生的自然村社为主体,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自足的乡土现实世界或者说生活世界。这里是一个俗世社会,更是一个重情义的世界。在这里,事物自然生长,又自然消亡;在这里,一颦一笑千金重,一草一木皆关情。这个世界本真自然,又那么顺其自然。我们常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井”。这口“井”,实际上就是作家自小生活的故土世界。这个我们甫一出生就触摸到的最初的世界,滋养了一个人最初也是最真的灵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始终被这种故土情结所牵挂、所纠缠。凌鹰的乡土,就是生他养他的晓塘冲村。这是一个偏僻、自然环境有些恶劣,但是却宁静、祥和、温暖的小村,仿佛一头老水牛静静地跪卧在某座岭下。日头从东岭爬起,又从西山落下,会在某个时段给它留下一些光怪斑驳的影子,但不会影响它的心情。它淡定,从容,悠闲,偶尔还会有些孤独。这些深深烙上了农耕时代印痕的乡土元素,同样会烙在一个乡土作家的心灵深处。表面看来,凌鹰的故乡晓塘冲与湘南许许多多的村庄无异。但是,通过凌鹰的“土性”视角的透视,并将其记忆中的“土性”深入挖掘,就再现了一个不一般的“晓塘冲”:《坼田》、《草籽》、《车水》、《田埂》、《稗子》、《扯秧》、《老井》、《守水》、《积肥》、《打禾》、《禾屋》、《池塘》、《赶花》等13篇短文,组成了凌鹰的《与水稻相关的往事》。这些“往事”,不动声色地讲述了那些业已远去却犹记忆如新的独特的“农事”经历:作家和他的乡民们一起,在贫瘠的土地上,用最原始的工具劳作,一年四季,做着与“水稻”相关的农活。这些个人经历犹如岁月淘洗后的蚌壳或者瓷片,明亮而又尖锐,让久离乡土的我们眼前一亮,又那么不经意地戳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疼痛。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缩影,也是作家向我们展现的一个真实的乡土世界。在这些篇什中,个人尤喜《坼田》、《车水》、《稗子》、《老井》、《守水》、《积肥》、《禾屋》、《赶花》。其中《坼田》、《守水》、《积肥》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农民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而《稗子》、《老井》、《禾屋》等,不再停留在对乡村平常物、景、事的摹写,还倾注了作家对乡民们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土性”乡土世界品格的颂扬。“稗子”虽是“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意义的异类植物”,却从另一面启发了乡人“对于某种生灵的价值的本质认定”,培养了他们朴素的价值观;“老井”以她甘甜的清泉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乡人,从而受到乡人的喜爱和珍视。而当家家户户有了压水井,老井没有利用价值了,“没有了孩子的吸吮”,老井也就像一个妇人一样“断了奶了”,最后“成了一口枯井”。这老井的命运,仿佛就是一个乡村妇女人生命运的缩写。当她青春不再、垂垂老矣,留给我们的,是她“麻木而又坚韧”的背影。“禾屋”则见证了一段特殊岁月中“淳朴和本分往往都是被饥饿消解的,道德往往让位于生存的事实”,并引发了作家的反思:“任何生灵似乎都具有对曾经的生存空间无法忘怀的记忆。” 《车水》一文,于平和的叙事之中,更是抒写了一个怀春少年对于异性之美的追忆与怀恋:“那白光早就把我喂饱了,喂大了,把我从一个少年喂成了一个男人”,但是“那个车水的月夜却在我的心里一直没有老去,一直鲜活而又甜润着”。《赶花》更是将农村男女青年对爱情的向往与“追赶”作了心照不宣的描述:“人工授粉也不一定就要一男一女,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都可以”,并赞叹“这隐喻充满了人性的光芒”,因为“我后来听说过他们中有人在悄悄恋爱了”。尽管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结出金黄的稻子”,但是却可以见出一种人的本性的追求。所有这些真情抒写,应该说都是乡村生活的常态的真实反应,这个“土性”乡土世界正是现实乡村生活世界中乡景乡情、乡风乡韵的真实写照。
上述散文以不同的场景从“面”上对晓塘冲作了“蒙太奇”似的全景扫描,让我们获得了“晓塘冲”这一“土性”乡土的整体认知。正是在这些近乎碎片化的局部的小型叙事中,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一个”真实的乡土世界。而《父亲是一条鱼》则是从一个“点”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生活在晓塘冲的老一辈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深入透视。父亲像世世代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一样,敬畏于天,匍匐于地,靠天吃饭,土里刨食,水中淘金,忍辱负重,自甘贫贱,从不知道投机取巧,只知道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最基本的生活尊严——父亲就像他饲养的一条鱼——赤裸、赤贫、赤诚,永远活在水里,活在他亲人的心田里。在真切自然的表述中,凌鹰写出了对艰辛生活的体察,对深沉父爱的感悟。
从乡野自然万物及其生长状态,到乡村农民及其生存现实,这些无一不是乡村生活的自然常态,也无一不是作家的真情书写,隐隐流淌着作家真诚的主体情韵。这些散文是对故乡生活的感怀与追忆。作家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情深意长地向我们诉说着他童年的生活世界,童年的心灵场景,以及童年的生存幻想。同时,也寄寓着作家对待人生与自然生态和谐依存的一种乡土化的审美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凌鹰并没有以诗意化的描写屏蔽乡村生活的困顿与艰辛、闭塞与贫穷。恰恰相反,他从那些卑微的、毫不起眼的事物如草籽、田埂、稗子、稻花、禾屋及生存环境中,发现了朴素的价值观和人生哲理。这一点,应当说是他也是新乡土散文作家们对于前人的超越。
二
如果说“‘土性’乡土”所呈现的更多的是物质的或者以物质为基础所构成的自然的世界,那么“文化乡土”所表现的则是文化视野中非物质的乡村世界。在西方,“文化”一词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后来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其实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等。这些要素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乡土文化,是乡土生活方式的文化记录和价值取向,是乡土世界赖以安身立命的本真存在。文化中蕴含着一个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因此,对文化的观照与记录,也是作家一种身份的寻找与认同。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乡土散文作家对乡土文化的观照,一般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作家以自己的主体意识回归乡土,重视对乡土精神的挖掘,以质朴的乡村世界传统伦理(尤其是乡村社会美好的人情、人性、人味等人类基本精神价值)对抗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从乡村生活寻找远去的诗意与人生哲理。二是将地域文化色彩如民风民俗、人文地理和历史事实等,融入到乡土世界的描绘中。或者直接记叙地方特有的文化遗存,以展现某种地域精神。凌鹰的新乡土散文中有一部分是记录永州地方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的《民间朵花》,就是他精心撷取的流传在他的故乡的三个地方戏曲:祁剧、渔鼓和小调。在这些散文中,凌鹰以“在场”的方式,介入叙述,生动地再现了一幕幕戏剧情景和生活场景,巧妙地将艺术与生活、历史与现实、个人境遇与时代变迁揉合起来,仿佛让我们穿越时空,置身于以“晓塘冲”为舞台的现场,和劳动归来的村民们一起,观赏那些古朴而又透着米酒香味的祁腔祁调与祁剧祁乐,领略这些民间艺术古拙独特的瑰丽与魅力。“晓塘冲”也就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的生存空间。这里地处僻远,文化传统悠久,封闭自足。在这样一个乡土世界中,乡民们自弹自唱,自娱其乐,终致成曲成调。它们如山涧潺潺溪流,轻灵,跳动,沾着草叶上晶莹的露珠和山野清脆的鸟鸣,带着山茶花的芳香,从历史的那边起来,不事雕琢,气韵生动,犹如一幅幅浅浅淡淡的水墨画。画里蕴含着的,就是乡民们那种对再苦再累的生活的热爱,以及不屈服于命运的质朴与坚韧,乐观与豁达。当然,世事变迁,这些优秀的“民间植物”也在时代大潮中雨打风吹,逐渐凋零,走向沉寂。作者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中,表达了一种深情的眷念与无奈。这种眷念与无奈,其实也是作家对渐渐寂然的地域文化奇葩的无可奈何的挽歌。在这几篇文化散文中,作家尽可能地开掘乡土文化中的美德与力量,体现出一种质朴、凝重而又温婉的阴柔之美,这也是凌鹰散文的基调。
三
一方面是如“禾屋”、“池塘”等乡土场景为代表的乡土现实世界的坍塌与消亡,一方面又是如“祁剧”、“渔鼓”和“小调”等民间优秀文化的寂然凋零。不管是“‘土性’乡土”还是“文化乡土”,都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着消解。物非人也非,乡土作家再也回不到那个山清水秀、自然和乐的记忆中的乡村社会去了。那么,重构一个以土性乡土为原点、以文化乡土为内核的“另一个”乡土世界,就成了当下乡土作家的寻梦之旅,我们不妨称之为“精神还乡之旅”。这种精神追寻,其内驱力是“恋土情结”,其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则是作家对自己情感和理想世界的孜孜以求。在这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还有赖于作家所秉持的近似于宗教般的虔诚的对于生活和文学的崇高信仰。
不知是凌鹰有意挑选,还是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在他发给我的这些散文中,除了上述已论及的之外,我认真梳理了一下其余篇什,发现了其中一条有趣的脉络:
《湘江源头考》:表面是质疑和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实质上“是对一条大河文化根脉的寻找和探源”,我视它为对潇湘精神之源的寻根。
《天堂马车》:“我”在城市中的迷茫,在通往“天堂”(实际上就是作家的精神家园)的途中的无所依傍;“我”左冲右突,期待着通往“天堂”的“马车”。母亲为“我”装的那壶家乡的井水和英国画家康斯太勃的画作《干草车》给我激励和指引。
《屋檐》“渴望屋檐”其实就是渴望“找到自己的归属”。城市没有屋檐,乡村的屋檐让人感到一种温情与呵护。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让漂泊在城市的乡下人无所适从,只有回到乡村,站在乡村的屋檐下,才能让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庇护之所,才能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
《房间》:叙写寻找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停靠的栖息之所的辗转与艰难。走过不同的城市,呆过不同的房间,唯有永州——这个成就了柳宗元和怀素的文化之乡,才勉强找到一间安放自己疲惫灵魂的房间。
《放牧流水》和《跟霍贝玛回家》:从“时间”之维,叙述探寻精神家园之旅。精神旅途中探寻者的内心是孤独的,他需要寻找知音,寻找旅伴。这知音,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诗经》,一个是十六世纪的荷兰画家霍贝玛。尽管年代不同,地域也不同,但是“通往灵魂家园的路都是相通的”。
《对一条河流的狂想》(和《从塔希提岛到巴州岛的距离》:从“空间”之维,叙述探寻精神家园之旅。一个是东方,湖南江华瑶族“对自己祖先的艰难寻觅和追逐”途中的艰辛与生生不息,同时也让作家的内心“渐渐地开始明亮”;一个是西方,荷兰画家高更的精神家园“塔希提岛”,让作家豁然开朗。“塔希提岛”与相隔万里的湖南永州的巴州岛,“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小岛,其实有一种很隐秘的关联的。” 不仅“通往灵魂家园的路都是相通的”,而且灵魂家园也是相似的。值得注意的是,两文都一虚一实,前者既有现实的瑶山大峡谷,也有美国作曲家科洛非的交响乐《大峡谷》;后者有现实中的巴州岛,也有根据画家高更经历和画作描述的想象中的塔希提岛。现实与艺术虚实相交,很好地描绘了作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同时,借助于音乐与绘画,进一步烘托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不再是停留在“桃花源”似的村庄层面,而是作家更高更美的追求与向往——充满艺术气氛的、喧哗中的宁静与和谐的圣殿!最后,在完成了精神家园的探寻与描绘之后,作家借高更的画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发出了人生的终极追问,进一步引发我们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思考,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与创作的一种新的追求。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散文甚至有某些形而上的意义。它们复活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世界的细腻感觉和对生命的深刻体悟,让那些民间的生活细节和心灵镜像重新得以呈现。
我不知道上述这种臆测是否准确。但是,以我对凌鹰人生境遇的了解,这其中确实包含了他作为编外人员大半辈子四处漂泊的人生况味:无所依傍,焦虑压抑,尴尬无奈,同时内心又充满了积极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栖息之所。人生际遇如此,作家的乡土散文创作也大抵如此:他沿着“自然世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一路探寻,从自然地理的“晓塘冲”出发,穿过人文地理的“晓塘冲”,最后又回到以“晓塘冲”为核心的精神家园——诗画潇湘,从而建构起自己特有的心灵栖息之地。可见,凌鹰新乡土散文中的三重世界,并非孤立的,而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整体。凌鹰就是以这种三重视界,去审视他的乡土,最终完成他对自己乡土世界的构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凌鹰的新乡土散文创作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美学意义。在这种独特的审美视界中,凌鹰的散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作家蕴藉厚重的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以及他崇尚自然、崇尚民间、崇尚和谐的审美追求。他以“晓塘冲”作为观察世界的起点,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养育他的故土之上,并以浓郁的乡土性、地域性文化特色,标定自己的存在,同时不忘“仰望星空”,将深邃而忧郁的目光掠过屋檐,掠过大峡谷,掠过巴州岛和塔希提岛,投向蔚蓝天空的云朵之上。我们希望他能永远坚持着这一份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假以时日,他的散文必然会独树一帜,蔚成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