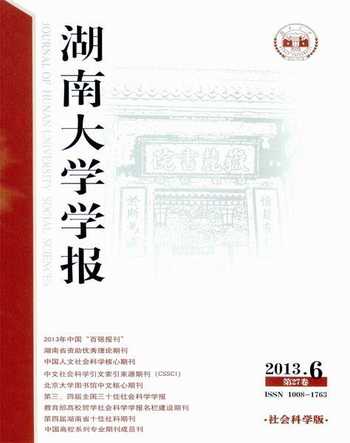最深处是歉疚和忏悔——论《秦腔》中的引生和白雪*
刘继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系,北京 100089)
《秦腔》是一部大著,需要长时间细密、深入的研究,刚出版不久,评论家白烨即认为:“这部书写出来是真正可以当枕头的书,可以终其一生死而无憾。对于评论和阅读来讲可能是最有持久性和耐久性的一部书。需要我们今后不断阅读不断解读。”①参见《<秦腔>北京研讨会: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http://book.sina.com.cn,2005年05月30日12:13新浪读书。这五六年来,随着它获得第一届“红楼梦文学奖”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的文学奖项,学术界的关注逐渐加大。
理解《秦腔》重要的一点,是在贾平凹的写作中特别注重的个人“心迹”。贾平凹曾说:“中国文坛向来崇尚史诗,我更喜欢心迹。”[1](P98)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两位长篇小说作家贾平凹和莫言,追求的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贾平凹以《废都》、《高老庄》、《秦腔》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大致可看成自传式写作,即使是看似与作家毫无关系的《病相报告》等,也掺杂着不少个人的癖好、情趣和情绪;而莫言以《红高粱系列》、《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完全是虚构性写作,即使是以自己姑姑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新作《蛙》,也基本上与作家个人情感寄托无甚关系。《秦腔》是一部细密扎实的乡土写作,时时浸透着贾平凹自己的情感印痕,就像当年的《废都》是“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了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2](P527)一样,贾平凹这样说《秦腔》:“它是我的宣泄,一种说话,不写出就觉得郁闷和难受,就像一个人在他的父母去世时没有去奔丧而永远气堵、揪心,耿耿于怀。”[3]这一点,在对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主人公白雪的描绘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一 引生不是真正的参与者
理解《秦腔》,首先回避不了对引生的理解。小说大部分内容是由疯子引生叙述的,只是偶尔会出现引生之外作者的全知叙事。
在直至目前的《秦腔》研究中,陈思和教授的研究集中而独到。2005年第1、2期《收获》杂志刊完《秦腔》,尚未出版单行本时,由陈思和教授主持、贾平凹参会的《秦腔》研讨会即于2005年3月25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是学术界最早对于《秦腔》的集中探讨。2006年7月26——27日,香港浸会大学举办首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评选,《秦腔》获得首届大奖时,陈思和教授是评委之一。2006年,陈思和教授在三次阅读《秦腔》之后,发表了《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和《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两篇共2万5千字的论文,[4]充分肯定了《秦腔》几乎完全以细节和场景支撑小说的独特现实主义艺术的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充分阐述了《秦腔》的价值。但是陈思和教授的两篇论文中,关于引生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发人所未发,新奇而突兀:
很显然,夏风只是《废都》中庄之蝶圈子里的一个废人,白雪与夏风的离婚是必然的。虽然没有明说,但引生与白雪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可以确定,小说里每次写到引生遭遇夏风总是落荒而逃,但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引生说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夏风回来。”充满了自信的语气中,预示了全书爱情故事的结局。[5](P104)
从全篇的结构而言,引生与白雪的爱情故事仍然是主线,[6](P110)从普通男女的情欲出发,走向纯粹精神性的疯狂爱恋,最终在秦腔的精神层面上结合为有情人,是白雪与引生这一对民间精灵的伟大爱情故事。[6](P123)在陈思和教授的解读中,十分肯定地将引生和白雪理解为真正的恋人,整部小说的主线是白雪和引生的爱情故事。怎么理解这些问题,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对引生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作用的理解。或者说,贾平凹设置这个人物、选择这种叙述视角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疯子引生视角的引入,是对传统的中国乡土叙事中根深蒂固的启蒙姿态的颠覆:“一方面,他以一个疯疯痴痴的非理性的形象彻底颠覆了启蒙叙事传统中理性的正人君子式的叙事者形象,可以说,‘疯子’的定位正是对叙事者身份的有效回避。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全知性’的‘疯言疯语’烛照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系统的虚假性。”[7]
在一些研究《秦腔》的论文中,都提及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和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疯子”引生的设置,并非贾平凹独创。也有学者对这几个白痴类人物进行了区别:“福克纳那个白痴的视点是为了表现理性不能看穿的真相,为了进入潜意识的深度,揭示人性和心理的复杂性。阿来的那个白痴,几乎从来就不痴,头脑比正常人还清醒。贾平凹的这个疯癫的引生却是看到生活的散乱,看到那些毫无历史感也没有深度的生活碎片。”[8]陈思和教授的论文《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一文,也论及引生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和《尘埃落定》中傻子形象的对比。
这些论及引生的论文,或多或少都存在理论先行、过于抽象归纳之处,没有涉及来自贾平凹在《秦腔》创作五六年之前的《我是农民》一书中关于“引生”的重要交代:
人窝里,我看到了邻村的引生。他是个疯子,过两天清醒了,过两天又疯癫,而且是个自残了生殖器的人。……那一个晚上,父子俩脚蹬脚地睡着,又为请媒人的一份钱争执开来,争执到鸡叫了三遍。引生毕竟是孝子,觉得不能再怨父亲,要生气就生气自己身上长了个东西,没有这东西也就没那么多焦躁、急迫和烦恼,便摸黑用剃头刀将那根东西割了。割了,蹬醒已睡着的老父,说:“我把××割了!”老父说:“今年不行了,明年养个猪,年终媳妇就有了……”他说:“我不要媳妇,我把××割了!”老父说:“睡吧睡吧,胡说些啥?!”他说:“我真的把××割了,就撂在炕下。”……[9](P89)
这一段文字,和《秦腔》第46页中描述引生割掉生殖器时的语言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可以确认,引生这一人物,在作家的安排中,既非为了回避启蒙叙事,也不是为了虚构一个文学中的痴傻形象来建构某一特殊的文学世界,和所谓“阉割美学”的距离更远。他来自贾平凹故乡的真实生活。这也是《秦腔》这部大作内含丰富魅力的一个方面。由此,我也感觉到,研究《秦腔》的学者,一方面充分肯定《秦腔》这种完全以细节客观呈现、真实还原生活、不表露作家主观意见的写法,但是在对《秦腔》进行研究和解读之时,又总是陷入抽象的“宏大叙事”之中,很难从生活实感和普通人情物理的角度进行品味、解读。
但是,引生又不是来自《秦腔》中清风街的原型棣花街,而是棣花街的“邻村”。这一点也至为重要。引生既来自故乡生活,但又没有直接参与真实的棣花街日常生活,即使从这个由现实到作品的转换情形来看,引生在《秦腔》中,可能也不会是承担主要生活实感和实体性情绪体验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清风街的生活,他是一个不时夹杂着、交混着客观观察和主观激情的见证者。他不同于清风街上那些真实地过着自己独有的一份日子的村民,他是一个活在自己内心、又时刻对清风街上每一个人保持高度关注的旁观者。引生是小说主要的叙述者,但他的存在,完全是依附着白雪而取得自身存在的理由。
这一点,从较为普遍的中外文学中痴傻类文学形象来看,也是自然的,痴傻类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实体性场景和情节的中心人物,他们的任务并非是为了直接参与行动,而往往是一个视角最为独特的见证者。仅从这一点来看,前述陈思和教授所说的:“引生与白雪的爱情故事仍然是主线”、“最终在秦腔的精神层面上结合为有情人,是白雪与引生这一对民间精灵的伟大爱情故事”的论点,是难以站住脚的。
在陈思和教授的论证中,特别关注了引生自宫前偷窥新婚的白雪在太阳照射下洗衣服的一段,认为“这一段描写非常奇特,给人一种光亮耀眼的效果。”然后推延至古代民族史诗和民间传说中“太阳照射而产子的传说”,认为:“贾平凹在《秦腔》里描写包含了太阳神话的原型,而以引生对白雪的强烈思念和欲望——牡丹花的感情交流——太阳光的直射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起源过程。”[6]强烈暗示夏风和白雪的孩子牡丹其实是引生和白雪的孩子!得出这样的结论,难免求之过深,有过度阐释之嫌。2000年,陈思和教授撰就煌煌大文《凤凰鳄鱼吸血鬼——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10]文中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对白先勇《孽子》作出的分析,是一次高难度、典范性的学术工作,直至现在都难以超越,但是这里对《秦腔》所做的原型批评,则显得牵强。
二 白雪的美、无辜和悲伤
小说第一句话,是引生的独白:“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紧接着还让三踅说了一句:“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11](P1)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第一句话往往凝结着作家漫长的构思,这样一部近46万字的长篇,这样的开头,是否意味着贾平凹写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心迹”呢?
在既有的对《秦腔》的解读中,孙新峰的研究也值得关注。他最先发表的是与人合写的论文《〈秦腔〉:贾平凹在自责中对前妻的追念》[12],明确将白雪与贾平凹前妻韩俊芳对等起来,细致梳理了贾平凹与韩俊芳恋爱婚姻的一些材料,论证白雪就是韩俊芳,夏风和引生都是以贾平凹为原型的。这样,《秦腔》主要是对前妻的追念,是作家的懊悔和自责。之后,他又发表过两篇论文《〈秦腔〉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文化意义》[13]、《怪胎女婴:解读<秦腔>作品的一把钥匙》[14],孙新峰是陕西人,对于贾平凹的生活非常熟悉,对于《秦腔》里面的生活也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他的《秦腔》研究主要是传记研究角度,对于注重在创作中表露自己“心迹”的贾平凹来说,自有许多精彩发现。[15]《秦腔》内涵作家的自责和忏悔,但完全将引生等同于贾平凹,白雪等同于韩俊芳,也未免拘泥。孙新峰同样忽略了引生这个人物的真实原型。而且,在他的论文中,也完全赞同陈思和从太阳照射产子的民间传说推演而出的牡丹是引生和白雪之子的论证和结论。两位学者也都引用了引生的心理活动:“我甚至还这么想,思念白雪念得太厉害了,会不会就是她怀孕了呢?难道这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以此印证、加强太阳照射产子推论的正确性。这样的思路,是成问题的,并且也是在一些《秦腔》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将“疯子”引生的每一句话,都视为有微言大义而细加深究。引生疯狂地爱白雪,自己又时而清醒时而疯狂,上述心理活动的产生,无非表现爱之炽烈、疯狂而已。如果引生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那他还是疯子么?如果在阅读时时刻想着引生某一言行的象征意义,还能真正接受贾平凹“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么?贾平凹真有必要写一个比哲人还睿智深刻、比正常人在思维、逻辑和心理上更可信赖的疯子引生么?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其实很难真正接受生活无尽的偶然和枝枝蔓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一双寻求“规律”的眼打量作品。从这个角度看,白娥玩弄引生的场景,评论家很难将它归纳到哪个结论之中,却是小说自身拥有的妙趣和天然。
引生既有现实原型,是一个真正的疯子,言行中就不时会有《我是农民》中提及的那个邻村疯子引生的身影,他不能被视为作家贾平凹的一个化身,他本身也是故乡生活构成的一部分。但是,在小说引生的刻画中,确实又寄托了不少贾平凹的思考和主观情绪。贾平凹其实很难以客观的方式来写引生,在引生的言语行为中,不时寄寓自己的情绪和判断。比如引生经常看见这个那个头上别人看不见的火焰,其火焰之强或弱的区分,其实就是作家对于笔下那些自己无比熟悉的现实中农民原型的气质或性格的一种判断。这是写作的自由和方便,也是写作本身对于作家来说是发泄胸中块垒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引生的存在,是为了印证白雪的美、无辜和悲伤。夏风和白雪自由恋爱而结婚,但书里没有任何两人相亲相爱的描绘,从新婚到离婚,夏风对白雪总是平淡、冷漠的,这种写法不符合生活常识,也不符合贾平凹的婚恋经历。这是事过多年之后的一种安排,极力突出夏风对于白雪的伤害,也就开脱了现实中造成离婚状况时韩俊芳的责任,同时通过引生的炽烈、疯狂之爱,衬托出白雪的美,进一步加深着自己对于前妻的歉疚和对自己的谴责。正像现实生活中贾平凹非常喜欢听秦腔,平时也常“哼唱两句秦腔”,[16](P50)夏风却一直特烦秦腔,也不理解秦腔对于父亲和白雪的意义,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动因。在这部密实书写故乡的作品中,这种从现实到文学的转换,最深层的内容,就是这种深深的歉疚和忏悔。
引生是一个见证者,白雪才是《秦腔》中真正最为重要的主人公,有关白雪的一切,几乎都由引生之眼呈现出来。由引生集中呈现出来的,是白雪的美、无辜和悲伤。
在最初的解读中,有论者认为:白雪没有为引生的痴情感动,而是“攀上”了夏风这个在省城工作的“高枝”,夏风和白雪,“一个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个则带有传统农村社会的迂腐与守旧。因而当这两个事实上属于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青年男女结合在一起时,他们婚后所生下来的其实必然是没有肛门的怪胎。”[16](P59)这里的“必然”式思维,对于《秦腔》这部试图还原故乡生活之作,“必然”会是一种伤害。在《秦腔》的写作中,夏风对白雪很冷漠,却并未对白雪有任何人格上的贬低,细读全书,对于白雪的“挑剔”,其实只有两处:第一处是白雪和二婶聊天时,二婶问白雪:“……白雪你高中毕业?”白雪说:“没毕业。我不配你夏风了!”[11](P64)第二处是夏风和白雪就工作调动的一次吵架:“夏风说:‘在县上工作长了,思维就是小县城思维,再这样呆下去,你以为你演戏就是艺术呀,以为艺术就高贵呀,只能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俗,难登大雅之堂!’白雪说:‘我本来就是小人,就是俗人,鸡就住在鸡窝里,我飞不上你的梧桐树么!’哭得更厉害,嘤嘤地出了声。”[11](P298)高中没有毕业和“小县城思维”,是白雪仅有的“缺点”,但是,读者谁又会真的认同这里白雪的自我贬低和夏风的批评呢?一方面通过引生这个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的疯子,夸张地、无保留地高唱“白雪诗赞”,另一方面,即使是刻画夏风的冷漠和薄情,小说也时时注意回避对于白雪人格的贬低,这是《秦腔》在描绘白雪这个人物时的分寸感,笔端是带着温情、带着歉意的。
白雪的悲哀,不单来自和夏风婚姻的不幸福,也不单来自自己挚爱的秦腔的衰败,更深的,是内心的落寞、深深的悲苦和孤独。
第一,引生的爱,是疯狂的,并非能打动白雪,也并非能增加白雪的荣耀。正是引生的疯狂引发了白雪的早产,这种爱的疯狂,带来了白雪的耻辱和灾难。白雪完全只是随顺自己博大的同情,对引生没有更多的反感而已,她和引生之间也从未有过任何情感的交流,“民间精灵的伟大爱情故事”,何从谈起!
第二,三踅巴不得是战乱,可以强奸白雪。夏风拥有了白雪,却是那样冷酷和不耐烦。
引生真挚而疯狂地爱着白雪,也总是试图让白雪感知这种爱,我们的研究过多地从小说整体寓意和引生的角度,阐发“阉割美学”的深意,但是从白雪这方面来说,这个爱着自己的人,尽管也数次暗暗地手淫,却是生殖器被割掉的男人。这种永远不会真正实现灵肉一致的所谓“爱情”,对白雪不也是一种一生的羞辱、一种一生的巨大空虚、凄苦和不公平么?
第三,几乎所有论者都从未引起过重视的,是小说中关于百盛的简短文字。百盛是白雪在县剧团里善吹箫的同事,白雪总是搭乘他的摩托回家:
直到白雪订了婚,白雪是和百盛真的夜里坐在山梁上吹过一次萧,天上的星星都眨眼,而蝴蝶并没有飞。白雪说:“你吹牛,哪儿有蝴蝶?”百盛说:“你不是个大蝴蝶吗?”就在那个晚上,百盛将这只萧送给了她。这只萧白雪一直挂在自己的房中。百盛死去了,这只萧还挂在白雪的房中。夏风并不知道这萧的来历,白雪也不愿告诉他,他还问她会吹吗,她说不会吹,夜半里等着它自鸣哩。[11](P376)
“那个晚上”,在小说的交代里是极其简短的,却也是含蓄的、浪漫、暧昧的。后来白雪去送还这只箫时,看见百盛的遗像,“心里还在说着,门外一只黑色的蝴蝶就飞进来,落在相框上,翅膀闪了闪,便一动不动地伏着。白雪打了个冷噤,腿发软,身子靠住了柜。”[11](P379)百盛在小说中就出现过这么一次,但我们由此感知夏风和白雪婚姻中的最为隐秘之处,夏风的初恋是金莲,金莲此刻却是满脸雀斑的人妻、并和上善有婚外情,白雪在婚前,和百盛拥有那个浪漫、暧昧的夜晚。诗人冯至1923年写出抒情长诗《吹箫人的故事》,箫似乎总是和凄美爱情联系在一起。白雪的“冷噤”,就是白雪在情感生活中压在心底深处的凄苦和悲伤。
引生在追随县剧团下乡时,见到过一个白雪的戏迷,“人长得怪难看的,说话都咬文嚼字,口袋上插了个钢笔”,正是这个戏迷写下了700余字的“白雪诗赞”,引生为这一篇诗赞感染和陶醉,一遍遍背诵和表演。[11]这个丑陋的戏迷,何尝不也是当年的青年贾平凹的化身。此刻这个迷狂的引生,又何尝不是多年后贾平凹想时光倒流成为的当年理想的“贾平凹”!我在阅读这700余字文绉绉的“白雪诗赞”时,总是感慨万千,这一段长篇诗赞文字,和小说总体情节场景的铺展,真是没有多大关系啊,不知有多少读者会轻易略过它们!但是作家写下这一段文字,又得耗费多少心力,得有多大的耐心,得调动多少悔恨和痛苦的情感啊!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文字,有时恰恰透露着作家的真实“心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秦腔》整部作品,其实也就是一个长篇的“白雪诗赞”。
三 余 论
最后,还有必要再回到文章开始处论及的“心迹”。
在阅读贾平凹作品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即他对两位著名女作家的理解和敬重。他有三篇广为流传的散文《哭三毛》、《再哭三毛》和《读张爱玲》,充分肯定了两位女作家的才情和天才。此外,在很多零星的文章及段落中,也一再涉及对于三毛和张爱玲的理解。阅读和推敲《秦腔》之后,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些内容,细细一想,这里也有和《秦腔》创作深层相通的地方。三毛所有散文都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最深体验到的情感。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像贾平凹一样,更多来自小说创作,因而没有三毛这么明显的亲身经历的内容,但她几乎所有的小说,写的仍然只是自己观察到同时也正体验着的生活,几乎没有像莫言那样整体性虚构的作品。张爱玲1973年写作的散文《谈看书》里有一句:“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在张爱玲去世后,她的亲弟弟张子静专门写了一本《我的姊姊张爱玲》回忆她,其中第九章《故事——〈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的开始,就特意引用了张爱玲《谈看书》这篇长篇散文的上述段落,显示出作为弟弟对于姊姊作品中“传记性”深刻的理解。张子静还言及:“一般的读者,读她的作品大多欣赏她讲得故事,她流利的文字和独特的写作技巧。我读她的作品,则在欣赏之外还旁观她心灵的变化——如她所说:‘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这是她1945年7月21日与李香兰、金雄白、陈彬苏座谈时说的话)。”[17]P96正因为张爱玲创作强烈的“传记性”,因之她的亲弟弟才会较之“一般读者”,更愿意从其创作中“旁观她心灵的变化”。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张子静才会在《金锁记》和《花凋》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与张爱玲毫无瓜葛的作品里面,读出张爱玲心中深深的哀伤。
张爱玲创作中的这种“传记性”,这种“心灵的变化”,也正与贾平凹自己看重的“心迹”息息相通。或许正是在这种深层的对于创作理解相通的层面,使得他对从未谋面过的两位天才型女作家保持着强烈的关注、理解和敬重吧?也正是在这个层面,标示出贾平凹三十余年的创作中最为重要、最为独特最为动人之处。在这个日渐世俗化、功利化的当下社会,一个作家,始终不渝地倾听自己内心深处、过往的岁月深处的真实回声,构成了当代文坛最为动人的风景。在《秦腔》这部以故乡、以父老乡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中,这种“心迹”的因素更见浓重,正是极其自然的。它通过真实却又疯狂的引生,自由地表达了作家自己对于故乡人事不漏痕迹的关注和评价,更通过对白雪这一美好形象毫无保留的刻画、兼之以对夏风与原型贾平凹自己性格及爱好等的区别取舍等微妙的处理,深刻地却隐晦地传达出作家自己现实生活中对前妻的深深怀念、歉疚和忏悔,这一段“心迹”,正是“一般读者”所难以见到、却构成作品最为动人心弦的心灵诗章!
总的来说,阅读《秦腔》,最让我们动心的,不是乡土的衰落。西部乡村的衰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清晰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见惯不怪的现实,如果说《秦腔》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揭示了这一点,恰恰是对《秦腔》意义的窄化。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在当代中国,既缺乏真正认知复杂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更不具备解决现实困境的真实力量;让我们揪心的,也不会是秦腔的衰败,秦腔的衰败在小说中之所以是令人唏嘘的,仅仅只是因为秦腔是白雪的生命寄托!让我们久久动容的,是白雪菩萨般惊人的美!是白雪的无辜、白雪深深的凄苦、孤独和悲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秦腔》成为50岁时的贾平凹必须要耐烦写出的作品,是他的生命、他的心灵稍稍得以安宁的寄托。阅读和评价《秦腔》,必须探讨在很难看见的文本深层,浸透着、饱含着作家个人在这种乡土衰落进程中的忧思和感怀,饱含着作家个人内心深处的歉疚和怅惘,对岁月逝去的深沉追怀。
[1]孙建喜.危崖上的贾平凹[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2]贾平凹.废都[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3]贾平凹.《秦腔》台湾版序[J].美文(上半月),2006,(11):5.
[4]陈思和.当代小说阅读五种[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陈思和.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A].当代小说阅读五种[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陈思和.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A].当代小说阅读五种[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7]吴义勤.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秦腔》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6,(4):74-82.
[8]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J].当代作家评论,2006,(3):4-17.
[9]贾平凹.我是农民[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
[10]陈思和.凤凰鳄鱼吸血鬼——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A].谈龙谈虎[C].桂林:广西师范学出版社,2001:233-239.
[11]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2]孙新峰,席超.《秦腔》:贾平凹在自责中对前妻的追念[J].商洛学院学报,2007,(6):99-104.
[13]孙新峰.《秦腔》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文化意义[J].商洛学院学报,2009,(2):22-29.
[14]孙新峰.怪胎女婴:解读《秦腔》作品的一把钥匙[J].当代文坛,2009,(3):119-123.
[15]吴涛.中原文化根源性的解构与重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4):128-131.
[16]王建民.《秦腔》大合唱[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17]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