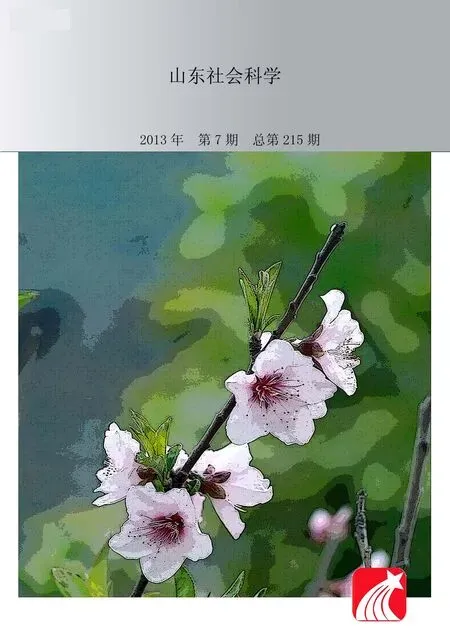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李冬木
(佛教大学 文学部,日本 京都 603-8301)
一、《国民性十论》的话语背景及其作者
原书日文名称与中文汉字相同:《国民性十论》。日本明治四十(1907)年十二月,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作者芳贺矢一(Haga Yaichi,1867—1927)。
出版机构“富山房”,由实业家坂本嘉治马(Sakamoto Kajima,1866—1938)于明治十九(1886)年在东京神田神保町创立,是日本近代,即从“明治”(1868—1912)到“大正”(1912—1926)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主要以出版国民教育方面的书籍著称。“(自创立起),尔来五十余年,专心斯业之发展,竭诚尽力刊行于教学有益书籍,出版《大日本地名辞书》、《大言海》、《汉文大系》、《大日本国语辞典》、《日本家庭大百科事汇》、《佛教大辞汇》、《国民百科大辞典》、《富山房大英和辞典》等辞典以及普通图书、教科书合计三千余点,举划时代之事功而广为国民所知者”。注株式会社冨山房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会社概要。参见该公司网站:http://www.fuzambo-intl.com/?main_page=companyinfo.——现今子公司“株式会社富山房国际”引先人之言,虽未免自夸,却也大抵符合实际。日本国会图书馆现存富山房出版物约950种,仅明治时代出版的就占了630余种,除单行本外,还有各种文库,如“名著文库”、“袖珍名著文库”、“新型袖珍名著文库”、“世界哲学文库”、“女子自修文库”等,各种“全书”,如“普通学全书”、“普通学问答全书”、“言文一致普通学全书”等;而进入“昭和”(1926—1989)以来最著名的是“富山房百科文库”,从战前一直出到战后,共出了100种。就“明治时代”而言,富山房虽不及另一出版巨擘博文馆——大桥佐平(Ohashi Sahei,1836—1901)于明治二十(1887)年创立于东京本乡区弓町,仅明治时代就出版图书3970种[注]参见拙文《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上)》,《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7号,1998,第271页。——却也完全称得上出版同业当中的重镇了。富山房明治出版物中,同期就有不少中译本,值得关心近代出版的朋友注意。
顾名思义,《国民性十论》是一本讨论“国民性”问题的专著。如果说世界上“再没有哪国国民像日本这样喜欢讨论自己的国民性”,而且讨论国民性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的话,[注]南博『日本人論——明治から今日まで』まえがき(前言),岩波书店,1994年10月。那么《国民性十论》则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历来受到很高评价,影响至今。[注]参见久松潜一『「日本人論」解題』,富山房百科文庫,1977。近年来的畅销书、藤原正彦(Fujiwara Masahiko,1943—)的《国家品格》[注]『国家の品格』,新潮社「新潮新書141」,2005年。在内容上也显然留有前者的痕迹。
“国民性”问题在日本一直是一个与近代民族国家相生相伴的问题。作为一个概念,Nationality从明治时代一开始就被接受,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在《明六杂志》就被叫做“人民之性质”[注]参见『明六雑誌』第三十号所载中村正直「人民ノ性質ヲ改造スル説」(改造人民之性质说)。明治十二(1879)年出版的『英華和訳辞典』(プロシャイト原作、敬宇中村正直校正、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著)既以「ジンミンノセイシツ,jin-min no seishitsu」即「人民ノ性質」(人民之性质)来注释英文Nationality(国民性)了。和“国民风气”,[注]参见『明六雑誌』第三十二号所载西周「国民気風論」(国民风气论)。其原标题「国民気風」旁边标注日语片假名「ナシオナルケレクトル」,即英文National Character(国民气质,国民性)之音读。在“国粹保存主义”的明治20年代被叫做“国粹”,[注]参见志贺重昂「『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議を告白す』(告白《日本人》所怀抱之旨义),『日本人』第二号,明治二十一(1888)年四月十八日。明治30年代又是“日本主义”[注]参见高山樗牛「日本主義を賛す」(赞日本主义),『太陽』3巻13号,明治三十七(1897)年六月二十日。的代名词,“国民性”一词是在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当中开始被使用并且“定型”。日本两战两胜,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竞争场中的一员,在引起西方“黄祸论”恐慌的同时,也带来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空前高涨,“国民性”一词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最早以该词作为文章题目的是文艺评论家纲岛梁川(Tsunashima Ryosen,1873—1907)的《国民性与文学》,[注]「国民性と文学」,本文参阅底本为『明治文学全集46·新島襄·植村正久·清沢満之·綱島梁川集』(武田清子、吉田久一編,筑摩書房、1977年10月)。发表在《早稻田文学》明治三十一(1898)年五月号上,该文使用“国民性”一词达48次,一举将这一词汇“定型”。而最早将“国民性”一词用于书名的则正是10年后出版的这本《国民性十论》。此后,自鲁迅留学日本的时代起,“国民性”作为一个词汇开始进入汉语语境,从而也将这一思想观念一举在留日学生当中展现开来。顺附一句,作为一个引进的外来词,“国民性”一词几乎不见于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出版的基本辞书(74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和12卷本《现代汉语大辞典》这类巨型工具书除外),却又在研究论文、各类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其在当今话语中的主要“载体”是“鲁迅”。——以上与“国民性思想史”相关的各个要点之详细情形,请参阅笔者的相关研究。[注]李冬木:《“国民性”一词在中国》,(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論集』第91号,2007年;《“国民性”一词在日本》,(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論集』第92号,2008年。(中国)二文同时刊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芳贺矢一出生于日本福井县福井市一个神官家庭,其父任多家神社的“宫司”(神社之最高神官)。在福井、东京读小学,在宫城读中学后,18岁入“东京大学预备门”(相当于高中),23岁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国文科,4年后毕业。历任中学、师范学校和高中教员后,明治三十二(1899)年33岁时被任命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副教授)兼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翌年奉命赴德国留学,主攻“文学史研究”,同船者有后来成为日本近代文豪的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1867—1916)。一年半后的1902年——也就是鲁迅留学日本的那一年——芳贺矢一学成回国,不久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履职到大正十一(1922)年退休。[注]参见久松潜一编「芳賀矢一年譜」,収入『明治文学全集』44巻,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1978)年。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如果按现在的理解,近代国民国家离不开作为其“想像的共同体”[注]Benedict Anderson语,参见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之基础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注]胡适语,参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的话,那么芳贺矢一对日本语言和文学所作的整理和研究,其“近代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他是公认的首次将德国“文献学”(philologie)导入到日本“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以“日本文献学”规定“国学”,并通过确立这一新的方法论,将传统“国学”转换生成为一门近代学问。明治三十七(1904)年一月发表在《国学院杂志》上的《何谓国学?》一文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开创性思路,不仅为他留学之前的工作找到了一个“激活”点,亦为此后的工作确立了崭新的学理起点,呈现广博而深入之大观。“据《国语与国文学》(十四卷四号【1937年4月——引者注】)特辑《芳贺博士与明治大正之国文学》所载讲义题目,关于日本文学史的题目有《日本文学史》、《国文学史(奈良朝平安朝)》、《国文学史(室町时代)》、《国文学思想史》、《以解题为主的国文学史)》、《和歌史》、《日本汉文学史》、《镰仓室町时代小说史》、《国民传说史》、《明治文学史》等;作品研究有《源氏物语之研究》、《战记物语之研究》、《古事记之研究》、《谣曲之研究》、《历史物语之研究》;文学概论有《文学概论》、《日本诗歌学》、《日本文献学》、《国学史》、《国学入门》、《国学初步》等;在国语学方面有《国文法概说》、《国语助动词之研究》、《文法论》、《国语与国民性》等。在‘演习’课上,还讲过《古今集》、《大镜》、《源氏物语》、《古事记》、《风土记》、《神月催马乐》及其他多种作品,大正六年【1917年——引者注】还讲过《欧美的日本文研究》。”[注]久松潜一『解題芳賀矢一』,『明治文学全集』44巻,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1978)年,第428页。由此可知芳贺矢一对包括“国语”和“文学”在内的日本近代“国学”推进面之广。就内容的关联性而言,《国民性十论》一书不仅集中了上述大跨度研究和教学的问题指向——日本的国民性,也出色地体现出以上述实践为依托的“顺手拈来”的文笔功力。芳贺矢一死后,由其子芳贺檀和弟子们所编辑整理的《芳贺矢一遗著》可示其在研究方面留下的业绩:《日本文献学》、《文法论》、《历史物语》、《国语与国民性》、《日本汉文学史》。[注]『芳賀矢一遺著』二卷,富山房,1928年。而日本国学院大学1982—1992年出版的《芳贺矢一选集》7卷,应该是包括编辑和校勘在内的现今所存最新的收集和整理。[注]芳賀矢一選集編集委員会編『芳賀矢一選集』,国学院大学,東京,1982-1992。第1巻『国学編』、第2巻『国文学史編』、第3巻『国文学篇』、第4巻『国語·国文典編』、第5巻『日本漢文学史編』、第6巻『国民性·国民文化編』、第7巻『雑編·資料編』。
二、《国民性十论》的写作特点和内容
《国民性十论》是芳贺矢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虽然关于日本的国民性,他后来又相继写了《日本人》(1912)、《战争与国民性》(1916)和《日本精神》(1917),但不论取得的成就还是对后来的影响,都远不及《国民性十论》。书中的部分内容虽来自他应邀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连续讲演,却完整保留了其著称于当时的富于“雄辩”的以书面语讲演[注]小野田翠雨『現代名士の演説振り——速記者の見たる』(现代名士演说风范——速记者所见),『明治文学全集』96巻,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二(1967)年,第366-367页。的文体特点。除此之外,与同时期同类著作相比,该书的写作和内容特点仍十分明显。前面提到,在日本近代思想史当中,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1894—1895)到“日俄战争”(1904—1905),恰好是日本“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而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明治日本”的“国民性论”正式确立的时期。日本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出现的志贺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的《日本风景论》(1894)、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o,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1894,1908)、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o,1862—1933)的《武士道》(1899)和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1913)的《茶之心》(1906)作为“‘富国强兵——‘日清’‘日俄’高扬期’”的“日本人论”代表作来加以探讨。[注]船曳建夫『「日本人論」再考』,講談社,2010年。具体请参照该书第二章,第50-80页。但作者完全“屏蔽”了同一时期更具代表性《国民性十论》,干脆没提。就拿这4本书来说,或“地理”,或“代表”人物,或“武士道”,或“茶”,都是分别从不同侧面来描述和肯定日本的价值即“国民性”的尝试,虽然各有成就,却还并不是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综合而系统的描述和阐释。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4本书的读者设定。除了志贺重昴用“汉文调”的日语写作外,其余3本当初都是以英文写作并出版的。[注]《代表的日本人》原题Japan and The Japanese,明治二十七(1894)年由日本民友社出版,明治四十一(1908)年再从前书选出部分章节,改题为Representative Men of Japan,由日本觉醒社书店出版,而铃木俊郎的日译本很久以后的昭和二十三(1948)年才由岩波书店出版;《武士道》原题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1900年在美国费城出版(许多研究者将出版年写作“1899”,不确),明治四十一(1908)年才有丁未出版社出版的樱井鸥村的日译本;《茶之书》原题THE BOOK OF TEA,1906年在美国纽约出版,昭和四(1929)年才有岩波书店出版的冈村博的日译本。也就是说,从写作动机来看,这些书主要还不是写给普通日本人看的,除第一本面向本国知识分子诉诸“地理优越”外,后面的三本都是写给外国人看的,目的是寻求与世界的对话,向西方介绍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日本人”。
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与上述著作的最大不同,不仅在于它是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面向普通日本人来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文本,更在于它还是不见比于同类的、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作为经历“日清”“日俄”两战两胜之后,日本人开始重新“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的一本“国民教材”,该书的写作方法和目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或宗教,或语言,或美术,或文艺来论述民族的异同,致力于发挥民族特性”,[注]参见《国民性十论·序言》。建立“自知之明”。[注]参见《国民性十论·结语》。
全书分十章讨论日本国民性:(一)忠君爱国;(二)崇祖先,重家名;(三)讲现实,重实际;(四)爱草木,喜自然;(五)乐天洒脱;(六)淡泊潇洒;(七)纤丽纤巧;(八)清净洁白;(九)礼节礼法;(十)温和宽恕。其虽然并不回避国民“美德”中“隐藏的缺点”,但主要是讨论优点,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第一、二章可视为全书之“纲”,核心观点是日本自古“万世一系”,天皇、皇室与国民之关系无类见于屡屡发生“革命”、改朝换代的东西各国,因此“忠君爱国”便是“早在有史以前就已成为浸透我民族脑髓之箴言”,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情感;“西洋的社会单位是个人,个人相聚而组织为国家”,而在日本“国家是家的集合”,这种集合的最高体现是皇室,“我皇室乃国家之中心”。其余八章,可看做此“纲”所举之“目”,分别从不同侧面来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描述和阐释,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的确可堪称为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的尝试。而这也正是其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日本人“自己写自己”的书,除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外,其他有影响的还并不多见。而关于日本及日本人的论述,从通常引用的情况看,最常见的恐怕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求其次者,或许“赖肖尔”的《日本人》也可算上一本。这两本书都出自美国人之手,其所呈现的当然是“美国滤镜”下的“日本”。芳贺矢一的这一本虽然很“古老”,却或许有助于读者去丰富自己思考“日本”的材料。
三、关于本书中的“支那”
同日本明治时代的其他出版物一样,“中国”在书中被称作“支那”。关于这个问题,特作一下说明: “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最早见于佛教经典,据说用来表示“秦”字的发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以前普遍以“支那”称呼中国,因这一称呼在甲午战争后逐渐带有贬义,招致中国人的强烈反感和批评,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已经终止使用,在我国的出版物中也多将旧文献中的“支那”改为“中国”。事实上,“支那”(不是“中国”)在本书中是作者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由此可感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日本知识界对所谓“支那”怀有怎样的心像。
在日本明治话语,尤其是涉及到“国民性”的话语中,“支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像在后来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所看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贬斥和“惩膺”的对象。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那”一直是日本“审时度势”的重要参照。例如《明六杂志》作为“国名和地名”使用“支那”一词的频度,比其他任何国名和地名出现得都要多,即使是当时作为主要学习对象国的“英国”和作为本国的“日本”都无法与之相比。[注]参见「『明六杂志』語彙総索引」,高野繁男、日向敏彦監修、編集,大空社,1998年。这是因为“支那”作为“他者”,还并不完全独立于“日本”之外,而往往是包含在“日本”之内,因此拿西洋各国来比照“支那”也就往往意味着比照自身,对“支那”的反省和批判也正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这一点可以从西周的《百一新论》对儒教思想的批判中看到,也可以在中村正直(Nakamura Masanao,1832—1891)为“支那”辩护的《支那不可辱论》(1875)[注]「支那不可辱論」,『明六杂志』第三十五号,明治八(1875)年四月。中看到,更可以在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1834—1901)《劝学篇》(1872)、《文明论之概略》(1877)中看到,甚至可以在专门主张日本的“国粹”,“以图民性之发扬”[注]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生松敬三編『日本人論』,富山房,昭和五十二(1977)年,第17、34页。该书初版为明治二十四(1891)年政教社版。的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1891)中看到——书中以日本人了解“支那文化”远远胜过“好学之欧人”为荣,并以“向全世界传播”“支那文明”为“日本人的任务”。[注]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生松敬三編『日本人論』,富山房,昭和五十二(1977)年,第17、34页。该书初版为明治二十四(1891)年政教社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来的所谓“脱亚”[注]语见明治十八(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社説「脱亜論」,一般认为该社论出自福泽谕吉之手。事实上,“脱亚”作为一种思想早在在此之前福泽谕吉就表述过,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都可清楚地看到,主要是指摆脱儒教思想的束缚。也正是要将“支那”作为“他者”从自身当中剔除的文化上的结论。在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当中,“支那”所扮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无法从自身完全剔除的“他者”的角色,除第十章以“吃人”做比较的材料所显现的“贬损”倾向外,“支那”在全书中大抵处在与“印度”和“西洋”相同的参照位置上,总体还是在阐述日本从前在引进“支那”和“印度”文化后如何使这两种文化适合自己的需要。
四、周作人与《国民性十论》
《国民性十论》不仅是鲁迅的目睹书,更是周作人的目睹书,该书至少有助于解读与周氏兄弟相关,却因年代久远和异域(中国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悬而未决的若干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最具代表性的《鲁迅年谱》[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四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作人年谱》[注]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还查不到“《国民性十论》”这本书,更不要说对周氏兄弟与该书的关系展开研究。就笔者阅读所限,中国学者最早在关于周作人的论文中谈到“芳贺矢一”的,或许是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赵京华研究员1997年向日本一桥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注]「一橋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論文。論文題目:周作人と日本文化、著者:趙京華(Zhao,JingHua)、論文審査委員:木山英雄、落合一泰、菊田正信、田崎宣義。1997」。笔者所见该论文得自赵京华先生本人。,只可惜尚未见正式出版。
芳贺矢一在当时是知名学者,《朝日新闻》自1892年7月12日至1941年1月10日的相关报道、介绍和广告等有337条;《读卖新闻》自1898年12月3日至1937年4月22日相关数亦达186条。“文学博士芳贺矢一新著《国民性十论》”,作为“青年必读之书、国民必读之书”[注]《国民性十论》广告词,『東京朝日新聞』日刊,明治40(1907)年12月22日。也是当年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自1907年底初版截止到1911年,在短短四年间就再版过八次。[注]本稿所依据底本为明治四十四(1911)年九月十五日发行第八版。报纸上的广告更是频繁出现,而且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注]《朝日新闻》延续到昭和10(1935)年1月3日;《读卖新闻》延续到同年1月1日。甚至还有与该书出版相关的“趣闻轶事”,比如《读卖新闻》就报道说,由于不修边幅的芳贺矢一先生做新西服“差钱”,西服店老板就让他用《国民性十论》的稿费来抵偿。[注]「芳賀矢一博士の洋服代「国民性十論」原稿料から差し引くユニークな店/東京」(芳贺矢一博士的西服制装费从〈国民性十论〉的稿费里扣除——东京特色西服店),『読売新聞』1908年6月11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性十论》引起周氏兄弟的注意便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兄弟俩是谁先知道并且注意到芳贺矢一的呢?回答应该是乃兄周树人即鲁迅。其根据是,就在《国民性十论》出版引起社会反响并给芳贺矢一带来巨大名声时,鲁迅已经是在日本有5年半多留学经历的“老留学生”了,他对于与自己所关心的“国民性”相关的社会动态当然不会视之等闲,此其一;其二,通过北冈正子教授的研究可知,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后不久就进了“独逸语专修学校”,从1906年3月初到1909年8月回国,鲁迅一直是作为这所学校的学生度过了自己的后一半留学生活,一边学德语,一边从事他的“文艺运动”,而在此期间该校特聘芳贺矢一担任“国语”(即日本语文)教学的兼课教师。[注]参见北岡正子『魯迅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第一章〈文芸運動〉をたすけたドイツ語——独逸語専修学校での学習」,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3月20日。关于芳贺矢一任“国语”兼课教员,请参看该书第29页,注(30)。从上述两点来推测,即便还不能马上断言鲁迅与芳贺矢一有着直接的接触,也不妨认为“芳贺矢一”应该是鲁迅身边的一个不能无视的存在。不论从社会名声还是从著作进而是从课堂教学来讲,芳贺矢一都不可能不成为鲁迅关注的阅读对象。相比之下,1906年9月才跟随鲁迅到东京的周作人,留学时间短,又不大谙日语,在当时倒不一定对《国民性十论》有怎样的兴趣,而且即便有兴趣也未必读得了,他后来开始认真读这本书,有很大的可能是受了乃兄的推荐或建议。比如说匆匆拉弟弟回国谋事,尤其预想还要讲“日本”,总要有些参考书才好,鲁迅应该比当时的周作人更具备判断《国民性十论》是一本合适参考书的能力,他应该比周作人更清楚该书可做日本文学的入门指南。而从周作人后来的实践来看,其所体现的也正是这一思路。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关于这本书最早留下文字记录的却是周作人。据《周作人日记》,他购得《国民性十论》是1912年10月5日[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501-502页。,大约一年半后的1914年5月14日有购入相关参考资料和同月17日“阅国民性十论”的记录,而大约又过了一年四个多月之后的1915年9月“廿二日”,亦有“晚,阅《国民性十论》”的记录。[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740-741页。而周作人与该书的关系,恐怕在其1918年3月26日的日记中最能体现出来:“廿六日……得廿二日乔风寄日本文学史国民性十论各一本”[注]《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740-741页。——周作人前一年,即1917年因鲁迅的介绍进北京大学工作,同年4月1日由绍兴抵北京,与鲁迅同住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注]前出《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121、131页。——由此可知《日本文学史》和《国民性十论》这两本有关日本文学和国民性的书是跟着周作人走的。不仅如此,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做了可堪称为他的“日本研究小店”[注]《〈过去的工作〉跋》(1945),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6页。挂牌开张的著名讲演,即《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4月17日写作,5月20日至6月1日在杂志上连载[注]前出《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121、131页。),其中就有与《国民性十论》观点上的明确关联(后述)。与此同时,鲁迅也在周作人收到《国民性十论》的翌月即1918年4月开始动笔写《狂人日记》,并将其发表在5月出版发行的《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其在主题意像上出现接下来所要谈的与前者的关联,殆并非偶然吧。
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谈过,截止到1923年他们兄弟失和以前的这一段,周氏兄弟所阅、所购、所藏之书均不妨视为他们相互之间潜在的“目睹书目”。[注]拙文《鲁迅与日本书》,《读书》2011年9期。兄弟之间共享一书,或谁看谁的书都很正常。《国民性十论》恐怕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例。这本书对周氏兄弟两个人的影响都很大。鲁迅曾经说过,“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33页。如果说这里的“小说”可以置换为一般所指“文学”或“文艺”的话,那么《国民性十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范本。前面提到,在这部书中,芳贺矢一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国文学”学者的本领,也显示了作为“文献学”学者的功底,用以论证的例证材料多达数百条,主要取自日本神话传说、和歌、俳句、狂言、物语以及日语语言方面,再辅以史记、佛经、禅语、笔记等类,以此推出“由文化史的观点而展开来的前所未见的翔实的国民性论”。[注]南博『日本人論——明治から今日まで』,岩波书店,1994年10月,第46页。这一点应该看做是对周氏兄弟的共同影响。
尤其是对周作人。在周作人收藏的一千四百多种日本书[注]拙文《鲁迅与日本书》,《读书》2011年9期。当中,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对他的“日本研究”来说,无疑非常重要。事实上,这本书是他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此后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也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周作人在多篇文章中都援引或提到芳贺矢一,如《游日本杂感》(1919)、《日本的诗歌》(1921)、《关于〈狂言十番〉》(1926)、《〈狂言十番〉附记》(1926)、《日本管窥》(1935)、《元元唱和集》(1940)、《〈日本狂言选〉后记》(1955)等。而且也不断地购入芳贺矢一的书,继1912年《国民性十论》之后,目前已知购入的还有《新式辞典》(1922—购入年,下同)、《国文学史十讲》(1923)、《日本趣味十种》(1925)、《谣曲五十番》(1926)、《狂言五十番》(1926)、《月雪花》(1933)、《芳贺矢一遗著》(富山房,1928出版,购入年不详)。[注]在《元元唱和集》(《中国文艺》3卷2期,1940年10月)中有言“据芳贺矢一《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汉文学史》非单行本,收入《芳贺矢一遗著》,1928年由富山房出版。总体而言,在由“文学”而“国民性”的大前提下,周作人所受影响主要在日本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方面,包括通过“学术与艺文”[注]参见《亲日派》(1920),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621页。《日本管窥之三》(1936),出处同前,第37-46页。看取日本国民性的视角。这里不妨试举几例。
周作人自称他的“谈日本的事情”始于1918年5月发表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该文在五四时期亦属名篇,核心观点是阐述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创造的模拟”或“模仿”,而这一观点不仅是基于对芳贺矢一所言“模仿这个词有语病。模仿当中没有精神存在,就好像猴子学人”(第三章“讲现实,重实际”)的理解,也是一种具体展开。
又如,从1925年开始翻译《〈古事记〉中的恋爱故事》,[注]载《语丝》第9期。到1926年《汉译〈古事记〉神代卷》,[注]载《语丝》第67期。再到1963年出版《古事记》全译本,[注]日本安万侣著,周启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可以说《古事记》的翻译是在周作人生涯中持续近40年的大工程,但看重其作为“神话传说”的文学价值,而不看重其作为史书价值的观点却始终未变,虽然周作人在这中间又援引过很多日本学者的观点,但看重“神话”而不看重“历史”的基本观点,最早还是来自芳贺矢一:“试观日本神话。我不称之为上代的历史,而不恤称之为神话。”(第一章“忠君爱国”)
再如,翻译日本狂言也是可与翻译《古事记》相匹敌的大工程,从1926年译《狂言十番》[注]周作人译:《狂言十番》,北新书局1926年版。到1955年《日本狂言选》,[注]周启明译:《日本狂言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前后也经历了近30年,总共译出24篇,皆可谓日本狂言之代表作,由中可“见日本狂言之一斑”。[注]周启明:《〈日本狂言选〉后记》,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第365页。这24篇当中有15篇译自芳贺矢一的校本,占了大半:《狂言十番》译自后者校本《狂言二十番》6篇,《日本狂言选》译自后者校本《狂言五十番》9篇。而最早与“芳贺矢一”及其校本相遇还是周作人在东京为“学日本语”而寻找“教科书”的时代:
那时富山房书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库”里,有一本芳贺矢一编的《狂言二十番》,和宫崎三昧编的《落语选》,再加上三教书院的“袖珍文库”里的《俳风柳樽》初二编共十二卷,这四册小书讲价钱一总还不到一元日金,但作为我的教科书却已经尽够了。[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八七 学日本语续”,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作为文学“教科书”,芳贺矢一显然给周作人留下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启蒙”痕迹。这与芳贺矢一在当时的“出版量”以及廉价易求的“文库本”直接有关。日本国会图书馆现藏署名“芳贺矢一”出版物42种,由富山房出版的有24种,属富山房文库版的有7种:《狂言二十番》(袖珍名著文库第7,明治三十六〔1903〕年)、《谣曲二十番》(同名文库第14,出版年同前)、《平治物语》(同名文库第41,明治四十四〔1911〕年)、《保元物语》(名著文库,卷40,出版年同前)、《川柳选》(同名文库,卷50,大正元(1912)年)、《狂言五十番》(新型袖珍名著文库,第9,大正十五〔1926〕年)、《谣曲五十番》(同名文库,第8,出版年同前)。这些书与周作人的关系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而尤为重要的是,芳贺矢一把他对各种体裁的日本文学作品的校订和研究成果,以一种堪称“综合”的形式体现在了《国民性十论》当中。对周作人来说,这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大纲”式教本——虽然“有了教本,这参考书却是不得了”[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八七 学日本语续”,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为消化“教本”让他没少花功夫。
此外,周作人在对日本诗歌的介绍当中,芳贺矢一留下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做具体展开,只要拿周作人在《日本的诗歌》(1921)、《一茶的诗》(1921)、《日本的小诗》(1923)、《日本的讽刺诗》(1923)等篇中对日本诗歌特点、体裁及发展流变的叙述与本书的内容对照比较,便可一目了然。
当然,对《国民性十论》的观点,周作人也并非全盘接受,至少就关于日本“国民性”的意义而言,周作人所作取舍十分明显。总体来看,周作人对书中阐述的“忠君爱国”和“武士道”这两条颇不以为然(《游日本杂感》1919、《日本的人情美》1925、《日本管窥》1935)。虽然周作人认为确认“万世一系”这一事实本身对于了解日本的“重要性”,而且像芳贺矢一那样介绍过臣民中很少有人“觊觎皇位”的例子(《日本管窥》),虽然周作人在把对日本文化的解释由“学术与艺文”扩大到“武士文化”时,也像芳贺矢——样举了武士对待战死的武士头颅的例子,以示“武士之情”(《日本管窥之三》1936),但对这两点都有前提限制,关于前者,认为“忠孝”非日本所固有,关于后者,意在强调“武士之情”当中的“忠恕”成分。而他对《国民性十论》所做评价是“除几篇颂扬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说几种国民性的优点,如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等,都很确当。这是国民性的背景,是秀丽的山水景色,种种优美的艺术制作,便是国民性的表现。我想所谓东方文明的里面,只这美术是永久的永久的荣光,印度中国日本无不如此”。[注]周作人:《游日本杂感》,《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刊。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第7页。
还应该指出的是,越到后来,周作人也就越感到“日本”带给他的问题,而“芳贺矢一”自然也包括在其中。例如,1935年周作人指出:“日本在他的西邻有个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国文化里发现一点不惬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给支那,便是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如佐藤隆三在他新著《狸考》中也说日本童话《滴沰山》(Kachikachi yama)里狸与兔的行为残酷非日本民族所有,必定是从支那传来的。这种说法我是不想学,也并不想辩驳,虽然这些资料并不是没有。”[注]知堂:《日本管窥》,《国文周报》12卷18期,1935年5月,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第26页。其实这个例子周作人早就知道,因为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第十章“温和宽恕”里讲过,“这恐怕不是日本固有的神话”,而是“和支那一带的传说交织转化而来的”,由此可知,周作人从当初就是“不想学”的。
到了写《日本管窥之四》的1937年,年轻时由芳贺矢一所获得通过文艺或文化来观察日本“国民性”的想法已经彻底发生动摇,现实中的“日本”令周作人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我们平时喜谈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注]原载《国文周报》14卷25期,1937年6月,署名知堂,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第56页。这意味着他的“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注]《〈过去的工作〉跋》(1945),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版,第176页。——就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观察而言,或许正可谓自“芳贺矢一”始,至“芳贺矢一”终吧。
五、鲁迅与《国民性十论》
笔者曾撰文探讨鲁迅《狂人日记》“吃人”这一主题意象的生成问题,认为其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密切相关,是从这一言说当中获得的一个“母题”。为确证这一观点,笔者主要着手两项工作,一项是对明治时代以来的“食人”言说展开全面调查和梳理,另一项是在该言说整体当中找到与鲁迅的具体“接点”,在这一过程中,芳贺矢一和他的《国民性十论》“浮出水面”,因此,“鲁迅与《国民性十论》”这一题目也就自然包括在了上述研究课题中。论文题目为《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文学评论》2012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详细内容请读者参阅这篇文章,这里只述大略。
与周作人相比,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方面。具体而言,鲁迅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的国民性,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
在鲁迅文本中没有留下有关“芳贺矢一”的记载,不过,不提不记不等于没读没受影响。事实上,在“鲁迅目睹书”当中,他少提甚至不提却又受到很深影响的例子的确不在少数。[注]请参阅拙文《鲁迅与日本书》,以及笔者关于《支那人气质》和“丘浅次郎”研究的相关论文。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也属于这种情况,只不过问题集中在关于“食人”事实的告知上。具体请参阅第十章“温和宽恕”,芳贺矢一在该章中举了12个中国旧文献中记载的“吃人”的事例,其中《资治通鉴》4例,《辍耕录》8例。笔者以为,正是这些事例将中国历史上“吃人”的事实暗示给了鲁迅。其推查过程如下:
《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这就是说,虽然史书上多有“食人”事实的记载,但在《狂人日记》发表的当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事实,也更少有人由此而意识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鲁迅是“知者尚寥寥”当中的“知者”,他告诉许寿裳自己是“偶阅《通鉴》”而“乃悟”的。按照这一说法,《资治通鉴》对于“食人”事实的告知便构成了《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直接契机,对作品的主题萌发有着关键性影响。
鲁迅读的到底是哪一种版本的《资治通鉴》,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在鲁迅藏书目录中未见《资治通鉴》。[注]参阅《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编,1957年;《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中岛长文编刊,宇治市木幡御藏山,私版300部,1986年。《鲁迅全集》中提到的“《资治通鉴》”,都是作为书名,而并没涉及到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的“食人”记载,因此,单凭鲁迅文本,目前还并不能了解到究竟是“偶阅”到的哪些“食人”事实令他“乃悟”。
不排除鲁迅确实直接“偶阅”《资治通鉴》文本这一可能性,也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即鲁迅当时“偶阅”到的还有可能是《国民性十论》所提到的4个例子而并非《资治通鉴》本身,或者还不妨进一步说,由《国民性十论》当中的“《资治通鉴》”而过度到阅读《资治通鉴》原本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正如上面所说,在鲁迅文本中还找不到他实际阅读《资治通鉴》的证据。
另外,芳贺矢一援引8个例子的另一文献、陶宗仪的《辍耕录》,在鲁迅文本中也有两次被提到,[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鲁迅全集》第9卷,第57页。《古籍序跋集:第三分》,第10卷,第94页。只不过都是作为文学史料,而不是作为“食人”史料引用的。除了“从日本堀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翻译过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philippe,1874—1909)《食人人种的话》[注]参见《〈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和作为“神魔小说”资料的文学作品“食人”例子外,鲁迅在文章中只举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上“吃人”的例子,那就是在《抄靶子》当中所提到的“两脚羊”:“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2005年版注释内容相同)对此作出订正,说这不是黄巢事迹,并指出材源:“鲁迅引用此语,当出自南宋庄季裕《鸡肋编》”。[注]收入《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第205页。这一订正和指出原始材源都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照抄了《鸡肋编》中的这个例子,这让芳贺矢一也在读《辍耕录》时看到并且引用到书中:“宋代金狄之乱时,盗贼官兵居民交交相食,当时隐语把老瘦男子叫‘饶把火’,把妇女孩子叫‘不慕羊’,小儿则称做‘和骨烂’,一般又叫‘两脚羊’,实可谓惊人之至。”私以为,鲁迅关于“两脚羊”的模糊记忆,不一定直接来自《鸡肋编》或《辍耕录》,而更有可能是芳贺矢一的这一文本给他留下的。
截止到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为止,中国近代并无关于“吃人”的研究史,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后才开始做他那著名的“吃人”考证,也只列出8例。[注]参见《吃人与礼教》,《新青年》六卷六号,1919年11月1日。调查结果表明,“食人”这一话题和研究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展开的。《国民性十论》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却因其第十章内容而与明治思想史当中的“食人”言说构成关联,其之于鲁迅的意义,是促成鲁迅在“异域”的维度上重新审视母国,并且获得一种对既往阅读、记忆以及身边正在发生的现实故事的“激活”,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个“悟”。
总之,即使只把话题限定在“周氏兄弟”的范围,也可略知《国民性十论》对于中国五四以后的思想和文学有着不小的意义。
2012年3月15日于大阪千里
【附识】
本文是为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中译本所做的导读(略有改动),翻译此书的直接动机,缘于在检证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时所阅文献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发现:芳贺矢一著《国民性十论》不仅是鲁迅的目睹书,更是周作人的目睹书,于是,“《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便作为一个问题浮出。对其检证的结论之一,便是作为一个译本,该书至少有助于解读与周氏兄弟相关,却因年代久远和异域(中国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悬而未决的若干问题。这是我们为商务印书馆“日本学术文库”提供这一中译本的缘由所在。
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新的解读。通过调查和翻译,检证并确认两者关系的存在,不论对周氏兄弟的研究来说,还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发现,因为截止到2012年1月笔者发表《明治时代的“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同年1期)为止,“芳贺矢一”和“《国民性十论》”作为两个固有名词还几乎不为上述研究界所知,更不要说引起注意。论文发表后,引发了各种不同意见,如果把反对的意见做一个归纳,那么大致都指向一点,即否定《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存在关系。对此值得反思的是论文本身恐有言不达意之处,或许应做出更充分的论证才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篇导读乃至整个中译本便都是不可或缺的补充了。这样,此后的反对意见才或许可信,因为至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连原书都没看,更不自己动手去找证或反证的资料,就能断言“事实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哪怕是丝毫的关系”,或“不能成立”之类。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