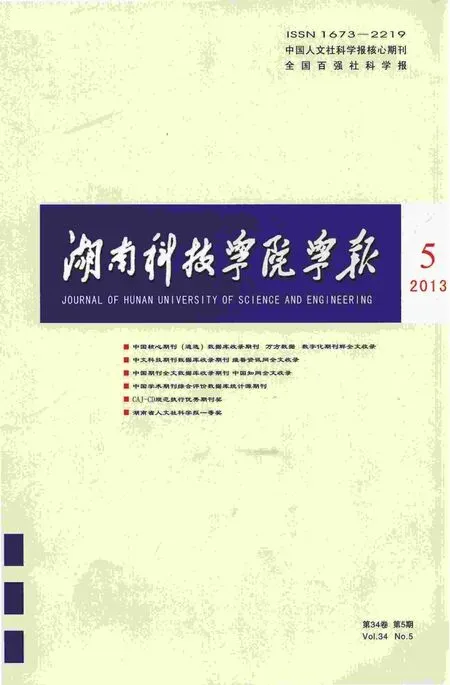由现存指向未来:布洛赫哲学人本主义逻辑探析
李纯斌
(湖南化工职院 思政课部,湖南 株洲 412004)
作为20世纪文化批判思潮的重要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既影响着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对二战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学说以独特的术语、观点和表达方式体现着对人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独特贡献。
一 布洛赫哲学研究旨趣的偏向
生于德国莱茵河畔路德维希港城(Ludwigshafen)一个普通犹太家庭的布洛赫是20世纪德国具有独创性的著名哲学家。他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生活、斗争、思考和写作,即使 到晚年双目失明,仍然挥动笔的武器,写作不止,直到最后一息。他用一系列熠熠闪光的著作使哲学贫乏时代的形而上学重新给出了真理与现实之间深刻的认知方式。
布洛赫一生与很多学界大师泰斗们接触和交流过。早在十七八岁时,布洛赫就与李普斯(Theodor Lipps)、哈特曼( Eduard von Hartmann) 、 文 德 尔 班 ( Wilhelm Windelband,)、马赫(Ernst Mach)等书信来往。后来,在慕尼黑大学期间,布洛赫师从李普斯学习,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Husserl)和舍勒(Scheler)交往。在乌兹堡大学期间,他师从当时在实验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最有权威的学者屈尔佩(Oswald Külpe),并受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在柏林学习期间,他师从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席美尔(Georg Simmel),并结识了韦伯、雅斯贝尔斯和卢卡奇等。
在这众多名家里,他深入研究的主要是胡塞尔、克尔凯郭尔、韦伯、屈尔佩、尼采、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反映了面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文化危机,深刻体现在人的物化与异化、技术世界对人的统治、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遗忘等系列方面,作为哲学家的思考,布洛赫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的许多观点,确立了他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研究旨趣。在系统的哲学研究中,他不主张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角度来研究哲学史,他依据动态思维和静态思维把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分作为两大类:一类是代表动态思维的过程哲学家,主要代表有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者、莱布尼茨、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一类是固守静态思维的静止的机械思想家,主要是埃利亚学派、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法国启蒙思想家、英法唯物主义者等。他偏向并推崇过程哲学家,因为这些思想家的观念更接近希望、可能性、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等思想。其中,他特别注重研究康德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谢林的神秘主义的天启哲学、黑格尔负载历史感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他期望以此研究理论能唤醒人内在的乌托邦冲动,使人变成自觉的希望的主体,以超越现代人的文化困境。
布洛赫的思想体系及学术观点博大而深奥,他的哲学体系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精神与各种哲学流派的观点。在西方传统文化格局中他不是偏重于希腊理性主义,而是偏重以人被拯救为目的的希伯来精神以及与此相关或相类似的以救世主义为宗旨的文化精神。布洛赫对历史上各种乌托邦主义文化思潮或理论构想非常感兴趣。20年代初发表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他非常赞赏闵采尔通过基督救世主义的激进的启录的神示而推进的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社会变革。在乌兹堡大学期间,学习过哲学、物理学、音乐、卡巴拉(Cabbala)和犹太神秘主义,其中卡巴拉(Cabbala)和犹太神秘主义给了布洛赫乌托邦精神的因子。这种犹太神秘主义宣传一些神秘图像、数字以及希伯来文字母的排列,释放神力,解救犹太人的苦难。布洛赫对犹太教的兴趣不在于它的具体的宗教含义和内容,而在于其中所包含的以人的拯救为核心的救世主义文化精神。此外,布洛赫还涉猎各种救世主义和末世学。诸如他研究诺斯替教义,发掘其教义的救人在于赐人以智慧,使人知道如何从肉体桎梏下解放出来。很显然,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社会普遍的物化现象和文化危机,面对人类各种异己力量的压迫与统治现状,布洛赫反复挖掘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偏重价值,即人的拯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对西方历史上以理性逻辑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并不感兴趣,而是对各种以上帝的救赎为核心的救世主义文化精神倍加关注。
这是他善于博采与综合各种哲学流派和学术思潮的表现,在这里,他不是随意的将各种文化精神或哲学观点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他的博采与综合是有着前后一致的价值原则,即服从于人的解放和人的拯救这一根本的人本主义逻辑主题。
二 布洛赫哲学理论剖析
(一)理论的始基:尚未
布洛赫哲学是由“尚未”(Noch-Nicht)概念为基础进行构建的,换言之,他的哲学的枢机是“尚未”。“尚未”(Noch-Nicht),其直接意义是“尚不是,还没有,还不是,”等。在布洛赫这里,尚未是指目前尚未存在或尚未生成,但面向未来正在生成、可能存在或应该存在的东西,一种开放性的过程;或者说“尚未”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生成的,它是乌托邦哲学概念之母源。
布洛赫的尚未概念认为,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已完成的或按某种超人的力量或规律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是依据人的超越性的、对象化的活动而正在生成的过程,这是一个向未来开放、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超越性过程。同时,人也不是某种给定的存在物,不能用某种具体的物或概念来规范和把握人的本质,人按其本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一个不断凭借对象化活动创造世界也自我创造的过程,一个不断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不断生成、不断超越的过程。布洛赫的尚未概念认为,经验世界、世界经验是明确的以物质表达的方式方法,这种物质包容了一切,都具体落实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框架内、落实在因果性和目的性的转换范畴内,以及落实在自然和历史等区域范畴内。现实中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创新的真实潜能。一方面,任何一种实际的世界状况都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可能性作为真实的其基础是物质的可能性又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或愿望。在这里,这种“尚未”哲学成了战胜现存的希望,只要现实不是封闭的,潜藏着的希望因素一旦遇到时机就将实现自身。除此之外,尚未这一概念还引申出了一系列其他概念:乌托邦、希望、真实的可能性、过程、物质、直行道、宗教遗产、世界的人道化等。
(二)对世界的人道化构想
布洛赫构建希望哲学,高扬乌托邦精神作为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的存在其主旨是“使世界人道化”。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呈现了典型的工具理性世界现象,社会处于深深的文化焦虑当中,反抗、批判、拯救,在这里,布洛赫想尽力寻找一种世俗的或神学的哲学,以使弥赛亚冲动具体化。“在马克思之前,人类更多关注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是现存的世界而不是将来的世界。例如,在柏拉图看来,经验世界是变幻的现象,只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宇宙是由理念按照逻辑秩序构成的善的理念是最高理念,即逻各斯,它是一切理念的来源,是宇宙的目的。因此,所谓知识就是回忆,无非是说,真正的知识不是关于经验世界的,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1]P226-227
布洛赫批判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以及启蒙以来的科学主义,因为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否定了康德的“物自体”观念,严格在直接给定的感性直觉界限内思考知识的可能性,对任何越过这个界限去思考绝对的思想都横加指责。同时,布洛赫认为科学主义是死者埋葬死的东西,因为科学追求的世界排除了主体的体验和世界中的神秘的暗示、精神的因素,使现实进入预先设定好的图式、结构和规律中,这是一种窒息了的内在性,机械论的绝对枉然。在布洛赫这里,落脚点是世界的人道化。因此,布洛赫认为希望呈现为弥散状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下的黑暗中,人与上帝沟通的内在之路,不是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而是要走向康德的实践理性,找到理论理性的界限,拥抱自然中的暗示、神话和乌托邦的因素,动员出它的可能的革命力量和实践内涵。从《乌托邦精神》中的“自我遭遇”到《希望原理》中的“具体的人性”,布洛赫实现了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向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concrete utopia)”的转变,乌托邦哲学要求除却人间之恶,重建家园。布洛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给出了能够实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形式的没有超验超越的乌托邦。这“是指这样一种未来的状况:人在那里达到现在还在躲着他的本质,它指人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在那里,人不再是单纯的现象,而是由于认识到他自己的人性而成为某种本质的活生生的东西”[2]P242。
尽管人的生命有着超验性的视域,但是这种超验作为具体的乌托邦就不再包含任何超验性了。布洛赫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寒流”和“暖流”的结合,包括着由客观冷静的经济分析和精神道德的倾向或“乌托邦过剩”两方面组成。“其实,从柏拉图一直到费尔巴哈,理念世界与现实物质世界都是抽象地对立的,他们的哲学被布洛赫认为是抽象的、静态的、沉思的知识,而马克思却试图沟通这两个对立世界,实现可能与现实的统一,从现实出发,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进入自由王国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把知识概念带到一个本质上不再指向已生成物,而是指向正在到来的趋势的世界;于是它第一次把未来带入了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把握。”[1]P226在布洛赫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热流”,缺乏伦理学,忽视主体性,具有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倾向,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因此他主张把乌托邦精神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主体精神在认识和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布洛赫哲学便要集中在“热流”上,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布洛赫看来,弥赛亚的实现却是靠人自身的力量,在这里人既是旅行者,又是指南针,人是乌托邦的主体。“唯有面向未来的、具体的、真正的希望才能为人类造福,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也只有把希望变成实际行动,主观同客观相结合,人才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在改造世界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理想、虽然在梦想实现的时候,必然会有所失望,而与此同时,希望依然保持着,没有因实现而终结”。[1]P262在布洛赫这里,由于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人的尊严就在于不断追求尚未存在的一切,人依据客观实在的可能性而实现自己的本质,消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或二元分裂,使社会化了的人同经过人中介了的自然相结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把世界创建成富有新奇性、可能性、创造性的人类家园。这是乌托邦形而上学的内在超越的诠释:乌托邦不是空想、虚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是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规划(即乌托邦)才能体现人的本质;主体—客体的同一性预先存在于主体的经验中,以象征性的意图在世界中实现这种同一性;当然,在布洛赫这里,这种解释不是神的救赎而是人的自我救赎,哲学的任务是唤醒生活,唤醒人内在的乌托邦冲动、乌托邦激情或乌托邦精神,以超越不合理的现存世界,使人真正成为乌托邦的主体。因此,布洛赫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关于人的自我理解,并更好地理解世界。
(三)拯救主体
首先在布洛赫看来,构建乌托邦主体得从哲学的系统研究中去寻找。布洛赫非常重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从而去合理构建起人的主体性。布洛赫重视康德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学中,分别从认识领域、实践领域等不同角度建构个体主体性思想,他关于人的认识对象是人自己确立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人是有目的的、意志是自由自律的等观点,把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自觉的主体性问题摆到理论探讨的中心位置。可以说,康德的全部理性批判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布洛赫重视他对希望的论述,他认为,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可以发现希望的形而上学基础,真正把人建构成希望的主体。对于谢林,布洛赫很关注他晚年的神秘主义的天启哲学或称内在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中谢林属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中介环节,相比较他的绝对哲学(完成了康德哲学中个体主体性向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表现形态的整体主体性的转折),布洛赫更感兴趣他晚年神秘主义的天启哲学或称内在哲学。在这里,谢林从人的存在角度探讨了自由问题。他认为人的真正自由既包括行善的自由,也包括行恶的自由,当非理性冲动控制理智时,人就从美德堕落为邪恶。这种从理性和非理性发生的内在冲突来揭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思想,对布洛赫影响深远。对于黑格尔的哲学,布洛赫不赞成他哲学的泛理性化和泛逻辑主义化,那种以绝对观念吞没个体主体性的做法。但是布洛赫看重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尤其是构成这一历史感的核心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想。他认为黑格尔的中心思想是:实在(绝对理念)是一个主体—客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主体外化出客体,然后又扬起客体的外在性与给定性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布洛赫进行了汲取,他认为这是扬弃了传统哲学所固守的主体客体的僵硬二元对立,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最终促使布洛赫在在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中能合理建构起人的主体性。
其次,乌托邦主体的地位,是来表征历史运动的内在的、本质的维度,即不断否定和超越现存、不断指向未来的维度,这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至关重要。“因此,当下是黑暗的,我们无法真正地体验当下的瞬间,而只能通过存在的解蔽和乌托邦之光的发现来走向本真的世界。”[3]P202
布洛赫认为,思想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停留在一个要终止的世界上,而是要像康德那样把世界变成一个没有岸的海洋。布洛赫使无限通达了他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体。在这里,乌托邦主体不是理论上的反思主体,不是笛卡尔的“我思”,而是实践意义上的“我们”(We)。乌托邦实践是通过弥赛亚经验领悟我们(We)的“共在”。在布洛赫这里,弥赛亚主义不是重新复活一个他者的世界,作为救赎而存在的弥赛亚,它与我们这个世界有着沟通,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启示。对布洛赫来说,人的主体性存在本来是隐匿起来的,它只是躺在最深的阴影里,对自身而言它是隐匿者,它处在一个道德的形而上学的隐匿者当中。很明显,乌托邦意识匮乏的时代必然使人的精神衰退、灵魂麻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现实化和世俗化,在逃避面对面的内涵丰富的交往世界而使“虚拟实在”短暂地弥合了人们的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但是这不能消解人们的精神困惑和苦闷。因此唤醒人内在的乌托邦冲动和乌托邦精神,使人真正成为乌托邦的主体,“那样,希望就不会失望,希望就会转为可能,人们心中的理想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2]P242,才能超越不合理的现存世界。
(四)乌托邦精神
在布洛赫这里,人的生存是被各种各样激情与渴望驱使的,希望则是人的各种激情和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希望是人所特有的,是所有精神情绪中最富有人性的,它使人向往美好的未来,向往人类自由的王国。人类是不能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就没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功,就归于死亡。”[4](P474)它使人的生存直接指向未来,使人们不满足于和不屈从于当前的现实,是生活在未来、内在于未来思维、内在于社会存在,从而使人能够创造性地开创自己的未来。
这种由对未来的幻想所激发的改造现状的欲望被布洛赫称为“乌托邦精神”,人不是某种给定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一个不断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不断生成、不断超越的过程;它表明这不是一种具体的观念,而是对未来经验保持开放,它也没有忽视个体的利益。
在布洛赫看来,一方面,乌托邦精神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现实的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世界,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把我们下降成为动物,使我们丧失了乌托邦精神,因此这种批判渴望新生活,敢于向旧的价值秩序和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另一方面,乌托邦精神体现了对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和向往,世界是“可能获得拯救的实验室”,乌托邦是人和物质内在所固有的动力,“希望如何可能?布洛赫认为,人并不是有限的,是包含着许多可能性的,而要实现这些可能性,要想走向成功,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希望的态度,唤醒人类尚未这种潜在能力,从而实现这种潜在的可能性”[1](P233)。它反对一切未完成的东西。因此,乌托邦远远超出了社会乌托邦的范围,“社会乌托邦只是一个侧面而已,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建筑、地理探险、绘画、文学以及音乐中的乌托邦,当然也包括宗教里的乌托邦”[5](P103-104)。
[1]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