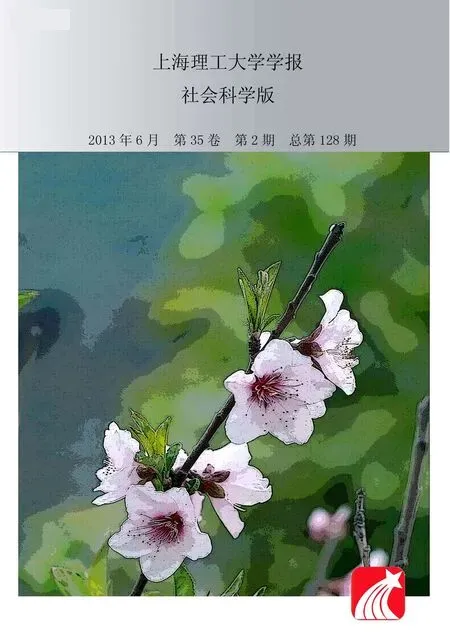《所罗门之歌》主题探索
贾兴蓉
(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成都 612222)
《所罗门之歌》主题探索
贾兴蓉
(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成都 612222)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女作家,其获奖作品《所罗门之歌》蕴涵丰富,思想深刻。本研究旨在从黑人传统文化和人物分析着手,运用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异化理论和圣经学说解构与阐释小说主题及意义:“飞翔”―――黑人文化回归和传承。进而阐述黑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美国非裔少数族群生存的重要性和建构独立、多元、层次丰富的黑人文化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回归和超越的真正含义及关键所在。
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存在主义;异化;追寻;黑人文化
在当代世界文坛占重要地位的托尼·莫里森是世界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她的写作主要聚焦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命运、精神世界和他们的人生体验,并将其作为自身文学创作的主题。托尼·莫里森曾阐述道:“对于黑人存在问题的思考是理解我们国家文学的关键,……人们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或伪造的非裔黑人的存在是形成这种‘美国性’的关键。”[1]她对非裔美国人命_运的_关注,其作品展现的勇气、个性、观点、力度和优美等特质给她带来辉煌的学术成就,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赢得了世界声誉。
1978年获美国文学研究院和全国书评会奖,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第三部长篇小说,是美国文学史上非裔美国文学的一次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是作家立身于美国文坛的代表作。《所罗门之歌》,比起稍后名声大噪的《宠儿》,更完美地展现了莫里森所背负的非裔美国人的民族历史和现实责任。书中沉重而宏大的黑人史诗般的叙述使她展现出不亚于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天才。她文笔优美,犹如“诗般璀灿”,充满了黑人传统文化特有的暗喻与神秘。评论家们说她的写法“如史诗般宏大、古老、久远、神秘”,叙事“娓娓诉说,哀而不伤”。无疑,该作品奠定了她在美国小说界的地位,使她成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所罗门之歌》一书以主人公奶娃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麦肯·戴德一家三代的人身遭遇为契机,生动地阐述了美国19世纪末“南部重建”后的“镀金时代”直至上世纪62年代,黑人从种族主义色彩厚重的南部移居到工商业氛围浓郁的北部时,所遭遇到的尖锐的生活矛盾和严酷的生存考验。显而易见,莫里森旨在通过这部作品强调黑人自我身份的确立和族群完整心理的建构与黑人文化及其传承之密不可分。无疑,“托尼·莫里森笔下的黑人世界,无论是现实生活或者古老传说,作者带给广大美国黑人的始终是他们的历史渊源,一幕又一幕,历历在目。”[2]3
就题材而论,《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莫里森却独辟蹊径,在并不复杂的情节上采用独特的艺术手法―――美国黑人传统文化中的“飞翔神话”表述对黑人真实历史的寻觅。“黑人会飞”的神话对于黑人族群是一种心理上的拯救力量,体现了黑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家”的渴望。这正如莫里森所说“我想使用黑人的民间故事,也就是带有魔力和迷信的那部分。黑人相信魔力,那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飞翔’是《所罗门之歌》中主要的暗喻……”[3]
本文旨在借主人公奶娃的成长经历阐释《所罗门之歌》蕴涵的主题及其含义―――“飞翔”―――黑人文化回归。以奶娃人生的痛苦历练,揭示种族主义歧视给黑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和文化错位,强调黑人文化对于黑人生存之重要性,以及建构个性独立、色彩斑斓、层次丰富的黑人文化之必要。论述黑人民族的自信、自立和自豪,是非裔美国人族群得以成功立足于以(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民族之林的关键。回归黑人性,在种族平等与和睦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多民族的融合,形成大一统意义上的美利坚民族,这不仅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初衷,也是她的全部小说的生命根基和归宿。
一、历史的印记―――人与事物之命名
《所罗门之歌》中人的姓氏,事物的名称都充满了象征和暗示,寓意深远。名字是一个人或事物存在的象征。名字的失落则喻意自我存在和身份的丧失及文化的消亡。奶娃一家三代姓氏的失而复得即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黑人街道的命名斗争和“林肯天堂”农场的命名,就是借事物的命名方式,以讽刺性内涵反映了黑白种族之间的矛盾。在非洲原生态文化中,无论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川大地、河流,抑或人的姓名均被看作是灵魂的“表达方式”。一个人应“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名字。这个名字会是在他诞生时以爱心和严肃的态度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是个玩笑,也不是个假名,也不是给奴隶打上的烙印标记”[4]22。因此,选择并保持人的姓名神圣而庄严,而它的丧失则被看作是亵渎神灵,冒犯上苍之大不敬。在美国南部蓄奴时代,当黑奴一家人被极不人道地强制拆散拍卖时,其姓氏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抹掉。从非洲承接的黑人真实姓名的留存与否至关重要,姓氏既是其身份的象征,更是其家族传承的印记和保持自己非裔祖籍及血缘续接的关键。没有姓名就没有根。奶娃的姑母派拉特由此日夜佩带着刻有自己名字的耳坠,她父亲手写下的名字作为她出身的印记,通过小盒做成的耳坠和她的身体紧紧相连,这暗喻人的姓名与身体之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令人酸楚不已的是,姑母派拉特耳坠里留存的名字并非其传承的家族姓氏,而是目不识丁的父亲仅靠字形的主观印象而信手所写:“他妹妹出生时,母亲死于分娩。父亲为此方寸已乱,就挑了一组他看着挺有劲和挺神气的字母,……用那种文盲抄书的办法,抄在一张褐色的纸上。”[5]17-18父亲选出的名字:“Pilate”恰好“像是杀害基督的彼拉多”。[5]17-18而此时,父亲内心想的却是相同发音的另一词:“pilot”(像个船只的领水员)[5]17-18。为此,作者寓意深刻地暗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强势介入影响下,表面上黑人顺从地接受了其误导的思维定式,而内心却对自身存在的象征―――姓名―――根的呼唤永远不会消失。父亲时刻向往着心中的“领航员”会带领自己“飞翔”到故土,寻得自由,寻得自己的根,寻得血脉传承的象征―――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族名字。这也是说,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名字的失落即身份的丧失,名字的失而复得则意味着自我的重生。对此莫里森曾阐述道:“如果你来自非洲,你的名字就消逝了。这尤其成问题。因为那不仅仅是你的名字,而是你的家族,你的部落。当你死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失去了名字,你怎样和你的祖辈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的伤疤。”[6]
与姑母相反,奶娃一开始就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姓名。他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名字麦肯·戴德源自一个白人的错误。北方的胜利宣告黑奴制度被废除。解放了的奶娃祖父去登记:“可办公桌后边那人喝醉了。他问他出生在哪里。爸爸说在‘麦肯’。然后又问他的父亲叫什么。爸爸说:‘死了’(英文为dead,音为戴德)”。就这样在他名字那个栏目里那蠢货写上了‘戴德’逗号,‘麦肯’。”[5]61奶娃,故事的主角之一,这位莫里森创作的众多作品里唯一的年轻男主角,却被赋以“奶娃”这一婴儿气息浓重的绰号。在此,压抑与冷漠,充满暴力的畸形家庭关系所导致的令人窒息的情感;病态的母爱―――恋母情结的另类表达―――跃然纸上。“奶娃”或“戴德”的荒谬称呼,却成了正式称谓。两个名字,一个象征着病态的母爱,另一个表面是白人的“误导”,实际上暗喻对黑人的蔑视,是黑人卑微地位的证明和象征。奶娃的姓“戴德”还形象地表达了其生存困境:暮气沉沉,了无生机的生活现状。甥女哈加尔及好友吉他对他的追杀,再加上平时姑母派拉特的黑人宗教及非洲神秘文化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驱使奶娃孤身南下,开始了他的南方寻梦之旅,也正是这一旅程使他得到净化,最后才从精神上断了“奶”,走向成熟。当奶娃踏上故土寻找父辈流失的金子时,他开始了对真实姓名的追寻。为了重返父亲发现金子的山洞,他探访故人瑟斯并从她口里意外地了解到先祖的真实姓名:吉克和辛。顺着线索他寻到沙里玛,从一群小孩的咏唱中他首次听到了完整的所罗门之歌―――关于他祖先和家史的歌:“吉克是所罗门的独子/……把婴儿留在一个白人的家里/……二十一个孩子,最小的叫吉克!”[5]312,从而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得知祖父母的真实姓名后,又得知姑母一直带在身边的是祖父的骨殖,便和姑母一起将他葬在故乡所罗门高地。奶娃终于寻回并继承了家族的真实姓名,而这也意味着自己将永远和祖辈联系在一起。此时,奶娃更深刻地领悟到名字的重要意义,它是身份的象征和“历史的印记”。
在非洲传统文化和美国社会生活中,“姓氏”不仅具有传世意义和宗教色彩,更是获得人的尊严和自由之象征。无疑,“姓氏”的背后蕴含着黑人的历史,它是人肉体消亡之后历史和文化之留存的重要载体。“姓名”不仅能帮助黑人找到并确定自己的种族身份,而且还能够帮助黑人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源和精神领地。这也反证了:人如果脱离维系其存在的先祖文化之象征―――姓氏,“脱离本民族,脱离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信仰,就离弃了自己存在的根基。”[7]其结果只能是抛弃真实的自我、身份,抛弃信仰,背信弃义,毁掉自己。而且,书中的戴德、派拉特、所罗门、奶娃、林肯天堂等姓氏和名称无不体现出莫里森的深刻寓意,姓氏名称在这里不仅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线索,而且在反映小说主题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评论界所说: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8]。
二、雅歌如诉―――“所罗门”在歌唱
历史上的所罗门(Solomon)又称所罗门王,即纪元前12世纪以色列国王,大卫王之子,以其财富和智慧著称。“所罗门之歌”(The Song of Solomon)源于圣经旧约中的雅歌。据记载为上古时(公元前3世纪)所罗门王所作。它来自希伯来语“Sir has sirim”意为最美之歌,英文为“the Song of Songs”或“Song of Solomon”。整部诗也可视为诗剧,作者借诗中的独白、对白,以诗的语言表达了丈夫和妻子,男女恋人之间的真挚而炽烈的爱。而宗教释意则别有深意,“圣经视男女之间的爱情和结合乃是上帝在创造周内赠给人类的礼物,是一美丽而崇高的情操。”故它常被用以喻为上帝对人的爱,是完善和纯洁的爱之象征。全诗真挚、热烈,有渴望,更饱含追寻和向往。莫里森将“雅歌”诗名重新赋予自己的作品,寓意深刻,富有哲理。笔者以为,在北美大陆(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氛围下,莫里森以“雅歌”为她的作品命名,是想喻指其隐含的宗教寓意―――“雅歌是传达更深灵意的载体或渠道”。借诗中喻指的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来暗喻非裔黑人对自身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坚守与追寻同样真挚而炽烈。仔细品味雅歌首节诗中意蕴的“黑即是美”:“Women of Jerusalem,I am dark but beautiful,/dark as the desert tens of Kedar,/but beautiful as the draperies in Solomon’s palace.”(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哪,/我虽然黝黑,却是秀美,/黝黑似基达沙漠中的帐篷,/却秀美如所罗门宫中的帐幔。)[9]635就能领悟到莫里森的深刻寓意―――一种对自身种族命运,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精神的追索与坚守、挚爱与深情。并希冀以此来突破美国黑人在黑白文化冲突中的心灵困境。
奶娃在南方故土寻金旅行中,虽未能找到渴求
的“真金”却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是被掳掠的非裔黑奴―――“会飞的所罗门”的后裔。而且,悟出了“所罗门之歌”的蕴意。在一个被当地人称为“沙理玛”(Shalimar)的小镇,他意外了解到那里所有人都姓“所罗门”,并由此领悟到“Shalimar”乃是“Solomon”的谐音。该镇实应理解为“所罗门镇”。而自己的祖先“所罗门”在蓄奴制度时代就留传下抛弃家人逃离奴隶制度的“飞翔”传说:“欧,所罗门,不要把我丢下/(所罗门飞了,所罗门去了)/所罗门穿过天空,所罗门回了老家。”[9]313相较雅歌开篇即存相似的诗句“Take me w ith you,and we’ll run away”,“愿你把我带走/让我们飞奔。”[9]635再联想到故事开端,在奶娃出生前一天,美国经济大萧条高峰时期一位非裔保险代理人史密斯从慈善医院屋顶自杀―――“飞翔”时,姑妈派拉特以宏亮的女低音吟唱的黑人灵歌:“啊甜哥飞去了,/甜大哥走掉了,/甜大哥掠过天空,/甜大哥回家了。”[5]4圣经的“所罗门之歌”和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虽都是人类的追寻之歌,蕴意各有不同,但追寻中却经历了相同的炽热和悲怆,挚爱与深情。尤其是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的追寻,“即那充满耻辱、痛苦甚至也包含了喜悦的死亡的旅程―――‘飞翔’,踏上归乡的自由之路”[12]。读罢它,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主人公奶娃在归程中的经历,其间融入的大量传说、神话、宗教仪式及童谣,无不表达了朴素的人生哲理,“歌唱”了厚重的黑人历史文化意蕴。“所罗门之歌”对于用文学重塑黑人历史,重建黑人文化传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飞翔―――求索中的“幻象”
《所罗门之歌》中的“飞翔”暗示的是“精神的重生”,即哲学意义上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是生存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缝隙中的黑人族群渴望自由的寓意表达。对“飞翔”寓意的充分运用也体现出作者对美国社会往昔和现实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精髓的“广博领悟”。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以麦肯·戴德祖孙三代的不同人生际遇来隐喻迄今黑人对种族出路的思考和探寻,并以此表明小说的立意;美国黑人“虽身处险境”却“超越现实”,怀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全力以赴展开对民族获救出路的探寻。而这样的求索,实际上体现的是持不同世界观的黑人,为摆脱困境,寻求自救做出的人生抉择。不同的抉择必然导致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局。
回顾上世纪中叶“哈莱姆文艺复兴”第二次高潮的领军人物黑人作家拉尔夫·埃利森在论述人性到底是什么,人的自我、身份在哪里等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人的本质属性命题时,他对黑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深入而经典的思考。他写道:“一般来讲,黑人以三种不同的方式面对他们的命运:通过希望和黑人宗教的感情净化的作用,他们能够扮演白人为他们规定的角色,并能永远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他们能够把对于歧视黑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满埋在心里,同时努力寻求通往中产阶级的路,因此,有意无意地变成压迫他们黑人兄弟的白人的同伙;或者,他们抵制眼前的现实,采取犯罪的态度,与白人展开一场无休止的心理战,这一心理战常常引发为暴力。”[11]387
奶娃的祖父老麦肯·戴德和外祖父福斯特大夫可被视为持第一种人生观―――“飞翔模式”的人。两者都是美国内战后获解放的前黑奴。成为自由人后,他们顺从地接受白人社会的安排,天真地视美国为一个机会均等、人权有保障的民主国家,相信“成功将最终降临那些勤劳的人,有节制的人,诚实的人和有教养的人……信守契约义务以及不可侵犯的人。”[12]554相信靠诚实肯干,自己的美国梦一定会实现。前者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与家人开创了“林肯天堂”农庄。十六年之后“他就有了全门图尔县最好的农庄之一。”[5]239后者则靠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成为城里著名的黑人医生,其声望和成功使他居住的街道被黑人骄傲地誉为“医生街”。然而两者的人生结局都以悲剧告终。祖父老麦肯因他的财富和快乐的人生招致白人忌恨,最后为保护家产不幸被白人“把他打到空中五英尺高”[5]41,肆意枪杀在“林肯天堂”农庄的土地上。外祖父福斯特大夫虽然医术精湛,但却因肤色招致白人阶层的歧视而被拒绝接纳和承认,最后抑郁而亡。
奶娃的父亲麦肯·戴德是持第二种人生观的黑人,从父亲的被害麦肯悟出了自己的人生哲理:黑人要从精神上、物质上重新获解放,夺回被掠夺的财富,就得顺应白人的主流文化及意识形态,放弃自身民族特质,遵奉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在此,莫里森揭示的是美国黑人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人的普遍意义上的生存危机―――“人的自身存在及随之的自我异化”,从而阐明战后美国黑人因其特殊的双重社会身分―――既是美国人更是黑人―――所遭遇的社会冲突和精神危机。人的存在及异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也常是现代派小说的基本主题。为消除这一危机,重建西方精神文化的可靠根基,现象学的存在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思想方法,并对此作出了启发性的尝试。加缪指出:“荒诞指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现代人被抛在这种处境中无处可逃。”[13]131萨特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内容是自我选择。”[13]152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则指人的自我丧失,人的本质意义上的被异化。“掌握财产,用你掌握的财产再去掌握别人的财产,这样你就可以掌握你自己,也就可以掌握别人了。”[5]56麦肯·戴德就这样以人的本质意义上的被异化―――“追逐金钱”的方式,践行已然被异化的人生观。生活中他精明老到,善于把握商机,对自己的同胞更是以无情而出名。“要是你想不出什么办法给我交租钱的话,反正他们是得到街上去的。”[5]22-21黑人老奶奶对他的评价客观而中肯“开买卖的黑鬼看着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5]22。如此理财,再加上二战商机,小麦肯成了北卡罗莱那州商誉良好的成功人士,拥有两栋住宅楼产权的青年黑人房地产商。成为富翁后,麦肯更加抵制自己的黑人性,与黑人社区的穷黑人断绝了交往,甚至自己的亲妹妹也不例外。他从父辈汲取的教训是,为避免招致白人的嫉恨,在白人面前必须谦卑。长期的异化必然导致心理扭曲,他终于从心灵上“漂白”自己,“有意无意地变成压迫他们黑人兄弟的白人的同伙”[11]387。是他持的价值观―――对金钱的贪婪与崇拜,使他良心逐渐泯灭,成了唯利是图、丧失黑人性、已然被异化的遭本民族唾弃的人。
奶娃的青年伙伴吉他则代表了黑人青年中对白人主流文化及社会持憎恨态度,主张“以暴抗暴”的激进主义人生观的黑人。现实中他们目睹黑人虽获解放已百年,但迄今仍处境艰难,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等苦难不断,这直接促其踏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与麦肯相似,童年时吉他的父亲惨死在唯利是图的白人老板的工厂里,而人命赔偿金仅有微不足道的42美元。生活重压下母亲弃家出走,祖孙三人陷入生存绝境。是家庭悲剧催生了吉他对白人的仇恨心理,并认为白人不会对黑人施仁慈。这种儿童成长期仇恨心理的“心灵内化”成年后外化为强烈的复仇欲望,直接驱使吉他加入以报复白人为目的的“七日”极端主义组织。仇恨心理和私欲驱使吉他“心理分裂,人格变态”,在疯狂地仇杀白人后,吉他因个人私利竟开枪射杀自己的黑人同胞―――好友奶娃和长辈派拉特,彻底异化为一个毫无人性的冷酷职业杀手。
通过以上三种飞翔模式,莫里森概括了自蓄奴制度被废除至22世纪62年代百余年间非裔美国人为探索种族出路所作的常态性努力。但对这样的飞翔能否助黑人摆脱困境,作者的回应是否定的。莫里森论述道,美国社会种族问题核心和两难处境是“如何避免自我憎恨式的融入白人主流文化和完全反对白人的民族主义。”[14]莫里森塑造的人物小麦肯和吉他恰好是美国黑人怎样对待白人文化及社会的两个极端的范例。莫里森分析了黑人在探索种族出路屡屡受挫的原因时,以上述人物的悲剧性结局隐喻了自己的理性反思,认为迄今美国黑人仍在探寻生存和发展的可行之路,第一代解放了的黑人迫切希望改变自身处境,但对白人主流文化和价值建构理解过于简单,未能对其主流价值观做理性批判就盲目追随,直至被愚弄和欺骗。这表明如果黑人全面接受白人主流价值观,“只谋求经济出路”,结局会是悲剧性的。这不仅不能自救,反而是黑人性的丧失,掉进民族虚无主义的陷阱里。对吉他的“以暴抗暴”方式,莫里森也持否定态度,上世纪62年代,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指出“黑人革命的目的在于实现种族平等而不是独立”[15]。在白人为主流社会的条件下,白人掌握主要的社会资源和权利,黑人要想以少数族裔的力量与主流社会作不理性的抗争,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片面强调民族分离主义,更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会导致整个国家动荡,民族矛盾冲突不断,莫里森以书中人物奶娃和派拉特的求索否定了吉他式的黑人运动的偏激行为。
四、飞翔―――回归或超越
能深刻体现小说主题的莫不如贯穿全书的“飞翔神话”所包含的寓意。神话是人类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和领悟,是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原始民众的生活体验、故事和传说。莫里森在创作《所罗门之歌》时不仅借用了“黑人会飞”的神话,还从现代意义上重新诠释了这个神话,即黑人作为少数族裔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获救出路的探寻。小说中父亲小麦肯、吉他与姑姑派拉特各自的人生搏击,本身就象征着其灵魂的堕落与升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飞翔”模式。不同的“模式”对奶娃的成长起着全然相反的作用,而奶娃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飞翔”―――重铸新的黑灵魂。
派拉特,美国黑人文化的坚守者,无疑代表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民族意识觉醒的“新黑人”。其对“飞翔模式”―――民族精神自由、解放的追寻,是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展现的。派拉特长期被迫生活在社会底层,亲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民族文化的侵蚀、冲击,因而对它持警惕、排斥态度。她高举民族意识,坚守自身信念,坚持传统文化复兴之路。派拉特的选择是有深刻内在原因的,早年,她父亲、哥哥在“林肯天堂”劳作。她的“自我”和谐而自然,成为“自然之女,没有母亲,她被自然所抚育,成了独特的领路人”[16]。父亲的被谋杀,及随后逃亡中的尖锐的价值观冲突,使兄妹各自踏上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派拉特为寻亲独自南行,踏上寻根的道路。她历尽艰辛终于回到黑人的第二故乡―――弗吉利亚。就在此,她寻得自己黑人民族文化的根,成了非裔黑人文化的坚守者。派拉特命运多舛,因天生无肚脐并遭嘲讽与讥笑,甚至失去婚姻。生活艰辛迫使她北上寻找失散的哥哥。此时,富有的哥哥却将她拒之门外。是贫困的黑人社区收留了她一家,她随后以酿贩私酒开黑市买卖艰难谋生。派拉特蔑视金钱,崇尚自然纯朴的生活。身处都市却固守南方乡村黑人的生活方式,连火炉也是三块砖垒成,甚至电灯、自来水等乃至白人社会的礼仪与文明均拒绝吸纳。她试图与女儿、外孙女一道营造现代版的世外桃源来抵御现代都市文明。现实却以讥讽性悖论呈现。外孙女哈格尔对白人为主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崇拜与狂热,导致了她的不断受挫、失败,最终抑郁而亡。这证明派拉特的坚守在一定层面上是不成功的,她停留在过去,固守传统,坚持黑人文化,希望以此消弭种族歧视,抵御白人强势文化的侵袭。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这种靠恢复往昔的与世隔绝,来回避本民族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依社会学观点,无疑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坚守和现实的荒谬绝伦。正如莫里森寓意的:“回归,固守只是消极的回避和一种无奈,就像一杯烈酒,只能使人倒下,而不能使人腾飞。”[17]
小说中奶娃“新黑灵魂”的诞生,阐释的是一种崭新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传承观,即在文化传承的根基上“飞翔”。这与派拉特的“飞翔”模式―――坚持传统文化复兴的传承观,都有着划时代意义。上世纪32年代,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论述:“改变黑人的现实处境,仅仅去改变法律和现行的体制还不够,必须来一场对整个社会的重建,来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12]569凭此思想,莫里森以《所罗门之歌》中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对现实世界作了有益的探索。她以小说中的奶娃重铸“新黑灵魂”的历程,阐述了自己对当代非裔美国人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以奶娃的求索历程,折射出这样的观点:文化遗产既可使黑人获得民族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而且,文化遗产本身还蕴涵着民族精神和民族魂魄。
传统寻宝和青年成长等叙事模式,历来用以表现启示性或探索性文学主题。《所罗门之歌》正是以奶娃的人生历程来反映崭新的“飞翔”模式―――“新黑灵魂”诞生的探索性主题,其核心是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无论是父亲小麦肯、奶娃、派拉特、还是伙伴吉他,他们各自鲜明的,甚至尖锐对立的人生经历都促使奶娃不断反思。父亲小麦肯原本天性善良,为了替祖父复仇,重振家业,父亲选择了金钱至上的道路;姑妈派拉特目睹祖父保卫家产而惨遭枪杀,后又眼见哥哥的拜金主义导致他良心泯灭,从而内心蔑视金钱,踏上回归自然,重返传统之路;伙伴吉他善良淳朴,是家庭悲剧使他看透了白人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以及都市社会中的伪善性,这驱使他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奶娃起初因家庭富有,无生计之忧,整日浑浑噩噩。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渐意识到确立人生目标,掌握个人命运的重要性。自我意识的复苏标志着奶娃开始思考、探索人生的意义。当然,上述人物的价值观的不足与冲突曾使他疑虑重重,然而,他们价值观内核的潜在合理性,又为其潜意识中的“飞翔”做了思想准备,回故乡南方寻金成了其世界观变革的关键。首先,追寻姑姑当年的足迹,可以获得“南方黑人的魔力”,其次,找到藏金,从此摆脱父亲的控制,经济上获得独立,这也是思想独立的前提。临行前他认为主流社会的思想观念,坐拥豪宅名车,身着名牌西服,获有令人仰慕的社会地位,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等都是成功的标志,人生目的和意义就在于上述目标的实现。但在寻金历险中,奶娃经历的生与死,特别是“沙理玛”镇和南方山区森林的考验,促成他完成价值观的革命性蜕变。奶娃刚到南方时,由于他的虚假派头和中产阶级的优越感,惹恼了当地青年,冲突在所难免,打斗中奶娃的西装被撕破毁坏,这既象征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黑人文化传统击成碎片,同时预兆黑人文化意识已进入其思考内核,潜意识中的黑人文化已被唤醒。后来在狩猎中,奶娃丢弃华丽西服,换上当地黑人肮脏的猎装,换装象征着他抛弃了原来崇尚的物质财富及虚荣心,经历了疲乏不堪的森林狩猎后,奶娃顿悟自己的“我只能分享你的幸福,不能承担你的痛苦”[5]284的人生观是何等的自私,麻木不仁。当奶娃逃脱吉他的截杀,重返猎人群后,终于彻底褪下伪装,摒弃了恐惧,真正融入黑人族群中,并以参与者、分享者的身份融入其中。分享猎物“狸猫心脏”这一古老的仪式,象征奶娃已成为当地部族的一员,标志着奶娃已彻底摒弃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正以崭新的视角看待本民族的过去,评价和理解族群的现在和未来。磨难中,他还体悟到“人人都要黑人的命”隐喻要学会“在险境中生存”。对黑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要具有在任何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能忍受一切的毅力,这也是黑人精神核心之一。家史的发掘,所罗门家族姓氏的屈辱与荣耀,促使奶娃领悟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即继承黑人文化遗产,探求族裔振兴的民族主义道路,而小说结尾正暗含这种隐喻。待祖父被埋在所罗门高地,接着姑姑也被枪杀后,奶娃从所罗门跳台飞身一跃:“吉他,你想要我的命……,拿去吧……”[5]347他终于成为“黑飞人”,在故土自由“飞翔”。
奶娃“新黑灵魂”的诞生表明,黑人民族文化遗产和思想的传承,可以帮助非裔个人和族群确立家族和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获得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文化遗产本身蕴含的民族精神能产生民族凝聚力,是捍卫本民族的精神和主体意识免遭侵蚀,防止被白人价值观完全征服和同化的前提和条件。书中,莫利森倡导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民族主义道路的同时,还以派拉特失败的传承方式暗示“回归传统要适度”。现实中,派拉特的“回归传统”,是不符合时代进步趋势的,因此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之路更要避免复旧。要以包容、自信、开放、发展的态度来吸收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潮流。这就是莫利森提倡的“取之于过去,用之于未来”的黑人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也即莫里森的重视黑人文化遗产的理性思考,和力图从本质上寻求拯救黑人民族的良方。1981年2月,托尼·莫利森在采访中说道:“我们现在处境危急,要么完全割断未来,死守原地―――这就等于,好比把我们自己全部消灭……要么我们假装不知道有什么过去,只顾盲目往前走,去追求那个我们以为就是快乐的东西……。理想的情况是取之于过去,用之于未来的,这并不改变过去或者未来―――而是在两者之间择其善者而从之罢了。”[18]222而《所罗门之歌》正是这种理性思维的范本,让人们读之深思。
[1]Morrison T.Playing in the Dark[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4-6.
[2]斯图尔·艾伦.诺贝尔文学授奖词[M]∥章汝雯.托尼·莫里森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226.
[3]David L M.Toni Morrison’s Fiction[M].New York:Garlang Publishing,Inc.,1997:112-127.
[4]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5]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229.
[6]托·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尼·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1):24-28.
[7]雷建国.埃利森《六月庆典》主题探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12,37(3):89-93.
[8]斯图尔·艾伦.“授奖词”[M]∥赵平凡.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受奖演说卷(下).徐望藩,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9]基督教会.中英对照圣经(和合本)[M].北京:中国基督教两会,2225:9.
[12]张艳清.“所有上帝的孩子都得到了翅膀”―――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飞行”文化母题探索[J].理论界,2225(11):166-167.
[11]李宣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下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222.
[12]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讲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1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4]泰勒·格里思(Danille T G.).托尼·莫里森访谈录[M].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9:122 -133.
[15]钱满素.美国当代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4.
[16]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2-96.
[17]吴康茹.回归还是超越―――解读托尼·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的主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21(2):79-87.
[18]查尔斯·鲁亚斯.美国作家访谈录[G].粟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The Exploration on the Motifs of Song of Solomon
Jia Xingrong
(College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00,China)
Toni Morrison is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female w riter who w ins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The w inning novel Song of Solomon is rich in content and profound thought.From black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aracter analysis,this article aims to utilize the theories ofmodern socialism and existentialism,dissimilating theory and the doctrine of biblical deconstruction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me of the novel:“Flying”―the return and inheritance of black culture.Furthermore,it elaborates the importance of black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to African-American minority’s survival 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multiple,and rich black culture.Meantime,the thesis points out the truemeaning and key point of the retur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novel.
ToniMorrison;Song of Solomon;existentialism;dissimilating;pursue;black culture
I 126.4
A
1229-895X(2213)22-2142-27
2213-24-16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SC11WY228)
贾兴蓉(1962-),女,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评论。E-mail:jia_x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