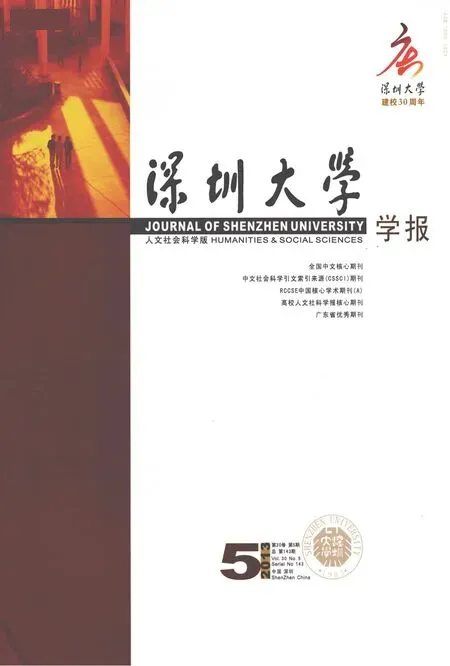文化安全背景下的国民消费宗教研究
陈振旺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在文化帝国主义时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不再是攻城略地或输出产品,而是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实现新的商业利润,以奢侈品为代表的符号消费、符号经济便是主要手段之一,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对文化帝国主义如此表述:“文化帝国主义,带有明确的目标,如通过含有文化价值商品的跨国销售而实现全球性文化支配。”[1]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变得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渗透力更强[2]。李理、黄丹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即指西方各国(主要指美国)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商品的跨国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这些产品从表面上看提供的主要是信息和服务,但在深层精神结构上却在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消灭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全球文化趋同,并威胁到民族国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3]符号消费跨越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蕴涵着生产者所处民族文化体系的价值理念等意识形态内容。文化帝国主义时代的符号经济、符号消费和价值观输出,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渠道体系中掌握强势的话语权,使得全球性文化消费体现出不平衡、不平等特点,严重威胁他国国家文化安全。
消费是一面镜子,可以影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理想,符号消费在中国之所以引起忧思,重要原因之一是符号消费遭遇“中国特色”,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全民疯狂和崇拜,中国国民符号消费在国际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呈现出异样的景观,折射出的正是国人所景仰且孜孜以求的功利性生存境界。在消费图腾逻辑的支配下,国民理想主义情怀每况愈下,纷纷将符号化商品的占有作为达到幸福的途径,沉醉于短暂的感官快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迷失人生航向。这种境界实际显示为宗教性超越感的阙如,对于信仰缺失、精神迷惘的芸芸众生,商业化的符号图腾是短暂的心灵救赎。符号消费之所以能成为当代国民的新图腾,其背后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传统文化磁场的延续和辐射
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我国的正统思想,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渗透到国人灵魂深处,儒家文化不仅仅从思想上影响民众的消费观念,更是从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方面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模式。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基石的儒学,其原则是“行为与地位一致”。例如中国古代服饰在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通过上层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礼制教化,服饰中的符号逐渐成为各种意义的象征,用来明辨等级地位,区分尊卑贵贱。服饰符号与象征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等级森严和文化垄断。《后汉书·舆服志》中的“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和《新书·服疑》中的“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都清楚地表明,在阶级社会中,服饰作为一种符号,成为等级贵贱的象征。而在当下,“中国消费者在奢侈品的购买动机方面存在着很强的物质主义和地位消费倾向,这跟中国长期以来的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有关,消费就是寻找差异化符号,东方人奢侈品消费热既是由于自身对奢侈品的内部驱动因素所致,但同时也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4]。例如Richins在调查中发现,中国消费者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倾向,在这样一种等级观念支配下,奢侈品作为一种社会工具的作用远超过其他功能。Redding(1983)认为,仅仅试图通过西方消费模型来解释处于独特的儒家文化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行为,是很不完善的。与西方国家相比,国民奢侈品消费不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是为了攀比和炫富。普遍对奢侈品消费迸发出强烈的渴望,并将此作为自身归属与认同的一个表现,表征出中国当今社会的种种畸形现象。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奢侈品消费背后是中国儒家等级消费观的世俗化,折射了中国当代国民进行符号消费的深层动机。儒家思想要求人们遵循礼制的规定,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不对欲望加以遏制,就很容易对统治者构成威胁,于是统治者要求人们安于天命,用礼制来规范社会成员的消费观念及其消费行为。即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消费方式,被统治阶层不得超越统治阶层,消费是一个社会阶层身份地位的代表。因此自先秦时代以来,礼制的消费观一直压抑在人们的消费观,等级消费观的不可逾越在社会成员中根深蒂固。Markus&Kitayama(1991)认为:“对社会等级制度的高度认可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5],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日常生活仪式中的等级消费观念的不可逾越性开始慢慢转变,固定化的等级消费观逐渐被革除。虽然代表身份和阶层的观念依旧存在,但是消费的等级不再是统治阶层依据礼制的主观划分,下层阶级也能开始与上层社会的人们攀比消费,甚至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进行模仿,并接受上层社会的消费观念,以期达到与他们外在的、表面的平等。中国自古以来等级分明,儒家礼乐观念深入人心,因而中国人对等级制度高度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国民奢侈品消费盛行的内在文化机制。Wong&Ahuvia(1998)的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消费行为体现出很强的等级性,很多物品带有社会等级观念的色彩,被人们赋予特权和地位的象征。”[6]
二、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破灭和消费宗教的慰籍
奢侈品,就是一门宗教,这是当下中国的一面镜子。正如英国TIMES报道的那样,整个伦敦都是中国人在排队购买奢侈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全球知名战略咨询机构贝恩资本日前在上海发布 《201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幅为30%,毕马威与汇丰的研究报告都认为,中国2012年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占据全球份额的28%,创历史新高”[7]。中国人将以国内外庞大的购买力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消费奢侈品实力国家。然而,奢侈品消费,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种种缩影,它根源于人们的精神缺失与迷茫。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的背后,看到人们渴望得到慰藉的灵魂,而这预示着人类社会的“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根本无法存在,人类的物欲是不可消除的,而这种物欲的流行已然成为当代国民符号消费重要的社会病根。建国之初的民众对曾经的集体(国家)精神认同是一种“乌托邦”。在那个假想“乌托邦”社会中生活的一代人,在精神上对国家和集体有强烈的认同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消费文化的逐渐渗透,人们对虚幻的国家乌托邦信念开始动摇,甚至放弃。国家集体乌托邦最终破灭,原因在于其最终没有兑现对民众的物质基础承诺,那种所谓的乌托邦混淆了理想与事实之间的分界,把虚幻等同于现实。然而事实是乌托邦最终没有兑现承诺,于是清醒后的人们打破了乌托邦。改革开放后随着消费社会的日益形成,人们本能地被裹挟到汹涌的物质大潮中,放弃精神追求和思想深度锤炼,转向无所不在的符号化的物品,由此获得安全和满足感。对物质与金钱的狂热追求成为当代文化的一大奇观,伴随着当下物质生活近乎炫目的表象,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缺失,人们越来越困惑于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寻找身份的焦虑之中,焦虑,是当下国民的普遍症状。奢侈品昂贵且稀有,经典且独特,成为人们定义自身身份、划分所属社会阶层的重要工具。日常生活中身份感的缺失使国民内心深处渴望认同与归属,具有划分社会阶层功能的符号化商品恰如其分地成为普罗大众消费模仿上层社会的手段。因此,国民对符号图腾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摆脱与日俱增的焦虑、空虚、忧伤等等被社会边缘化带来的恐惧感。
符号消费其实是对人们各种幻象的满足,将符号化商品的消费与自身价值衡量混为一谈,表面看起来振振有词的消费选择,其实是虚幻和荒谬。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在验证马尔库塞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人们在这种缺乏使命感、崇高感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缺乏思想深度、毫无精神追求、丧失批判力的单向度的个体。“当代国民很少再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安身之道,而将物质占有和消费作为达到幸福的捷径,忘却人生的意义,失去主体的思想,遮蔽人性的光辉。”[8]精神空虚导致物质欲望高涨,而大众媒介掩盖下的符号图腾消费,成为当代国民最好的自我安慰方式。符号消费让原本漂泊的灵魂更是走向罪恶的道德深渊。精神缺失,文化迷茫,乃至乌托邦的彻底破灭,使得当代国民的生活重新回归纸醉金迷。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提升,而精神生活反而“沙漠化”,符号消费影射了整个社会心理和个体精神世界沦陷的危机。肖鹰认为,“技术的无限扩张,导致了商业的扩张,商业的普遍化导致了自我的沉沦。诗意被技术与商业的片面性所扼杀,代替诗意生活的是一种渴求欲望满足的生活,无主体的制作代替了艺术的创造。因此,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也就成为欲望的奴隶”[9]。“物欲症”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人们在豪华奢侈的购物场所中,犹如孤独漂泊在琳琅满目商品景观中的灵魂,欲望被赤裸裸地激活,人们离理想信念越来越远,离审美越来越远。
三、全球化陷阱下的文化迷茫
消费文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成为现实的同时,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表达了对全球文化同质化、单一化的深刻忧虑。特别是伴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的盛行,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都有被整合进一个全球性商业文化体系中来的可能。”[10]当下消费文化借助现代商业传播系统席卷全球,几乎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欧美等发达国家有计划、有谋略地将其产品及其背后文化和精神意义塑造成为美好世界的象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进行隐蔽性渗透(Rosnow,1988)。 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曝光说:美国为了完成战略目标,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和操纵了文化冷战,而一些闻名全球的作家和艺术家则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文化冷战的工具。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来填补这个空缺,为了本国目标的实现,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1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因此,当代全球化文化传播具有强烈的不平等、不对称特征。
张殿元教授指出:“跨文化传播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空间,但时下强势国家的单向度传播对弱势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文化的同质化趋势对维护各弱小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持多元的文化趣味和思想价值构成了挑战,最终使文化的开放性、丰富性和创造性面临着潜在的威胁。”[11]正如爱德华·赫尔曼(Edward·Herman)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Mchesney)所说,那些研究全球化的人漏掉了一个关键点:“即在当今世界主要的入侵是模式的灌输。其次重要的是商业网的发展、巩固和集中以及和全球体系的日益融合,再加上这些进程逐渐对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影响。”[12]建国以来,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国民自我意识长期被束缚。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文艺思想发展空前活跃,国外各种思潮也纷至沓来,国民自我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反思历史,甚至怀疑过去、反叛传统意识形态。诗人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个人”,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但是,伴随国门洞开,商品经济和全球化的大潮奔腾而至,全球化浪潮把还没弄清楚自我意识的人们裹挟到商品经济大潮和没有边际的世界体系之中,几乎没有喘息之机,“下海”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炙热名词,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同步的,是快速的物质欲望膨胀。在这样一个从所未有的时代,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并存,且朝夕变化,人们只有快速改变自己才能适应变化的周遭。这带来国民整体性的信仰和精神缺失,内心交织着失落、焦虑和恐惧,虚伪浮华潜滋暗长,思想没有深度,易被煽动和利用,信仰缺失。“全球化在给我们经济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本土文化遭遇巨大冲击,文化主体性逐步丧失。文化自卑感使个体失去精神存在的根基,使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和自我独立的同时,沦为丧失生存根基的无家可归的漂泊者。”[13]精神世界的迷茫,导致当代国民迷恋商品符号带来的虚幻快感与幸福。
四、文化帝国主义的消费宗教渗透
1948年,汉斯·摩根索在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随后,“西方社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战后西方文化的反思中形成了对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论,即文化帝国主义论断,其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14]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一开始便具有批判性,其最初是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大国文化输出的批判。如前文所述,符号消费是一个深谋远略的系统化操控活动,国际新帝国主义通过所谓国际分工、版权付费和品牌保护,同时通过传媒输入消费宗教,谋求对经济、文化后进国家的经济控制,以此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剥削,赚取巨额利润。产生当代国民符号消费迷狂症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帝国主义无时无刻的消费宗教灌输,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种表面自愿平等的交易背后,是帝国主义操控世界舆论和文化话语权来灌输消费宗教的本质。因此,对帝国主义的消费宗教灌输的揭露,是解读当代国民符号消费拜物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符号消费在中国的盛行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合谋。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文化上的占领和控制实际上并不是指向单纯的文化而是指向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改造或者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传播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物欲症在中国的流行,符号消费已融合了“商品拜物教”的内在意义,在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导向下,商品的象征价值和符号意义被不断放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二战以来,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以高技术为手段,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品为载体,借助于发达的大众媒介,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使接受国渐受影响并认可、推行其价值观念,从思想上、文化上瓦解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以使帝国主义达到在政治、经济、外交的目的。”[15]消费宗教通过广告、媒体、电影和体育运动无时无刻地向全球推广,各种文化艺术活动都成为传播渠道,媒介的内涵不断被外延,如同麦克卢汉所说,环境亦是冷媒介。在消费文化扩张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一直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因此文化帝国主义也被视为“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上世纪50年代以来,跨国传播媒介日趋高度集中和垄断,形成信息在全球的单向流通,造成信息传播的严重不对称,世界文化丰富性和多元性不断被挑战。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今社会之存在,主要体现为两种现象:政治体系现象与经济体系现象。文化决不是孤立的,他必然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体现出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追求的不是以领土掠夺和殖民征服为目标的传统殖民帝国,而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控制的非正式帝国”[16]。
其次,符号消费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宗教灌输方式。符号消费成为当下人类最高形式的宗教,对商品符号的崇拜,是一种内心物质欲膨胀狂热病症的外化。大众媒体赋予商品符号象征意义,构造虚拟世界,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传输给每个消费者,使其成为当代人认同和归属的对象,广告教育使得大众成为拜物教徒。广告虚拟的符号化的物质世界似乎成为富有阶层能够抓得住的救命绳,视为内心精神家园的“海市蜃楼”,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寄托。商品符号世界如同宗教理想国度,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消费宗教的洗礼,人们紧紧追随的时尚犹如耶稣般高高在上,大众虔诚地接受影视明星、超级模特儿等“领潮者”们的时尚“传教”和“洗礼”,然后疯狂地模仿,享受所谓的奢华并不断地追求更多的“名不副实”的时尚符号,以LV、GUCCI包为例,从本身的制作来看,产品只是普通的材料而已,单从使用价值而言,它也是一个收纳物品的容器,纵使材料的稀少,售价也无须高达几万乃至数十万。然而,作为现代消费宗教的狂热信徒,中国的富有阶层渴望这样的奢侈品,渴望奢侈品带来的精神感受,新帝国主义利用这一点开始对奢侈品进行灌输。这些奢侈品消费者就像“基督徒”,离开了奢侈品,仿佛离开了他们心中的上帝和圣经。新帝国主义的消费宗教意识灌输,让最富有的阶层对诸如此类的符号消费狂热不已。
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普遍缺失,物质丰裕灵魂缺席的国民沉浸于填补灵魂空白的新宗教—商品符码。当代人悲哀地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虚,不再把生命赋予纯粹的精神领域,而是转向无所不在的物质。符号化的商品充当了救赎者的角色,将消费者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现代人就是沉溺在这样一个“符号拜物”的世界里,相信只有通过消费这些符号意义,尤其是能够彰显身份的差异化符号,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商品拜物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是一种消费意识形态,它营造了一种消费需求的“虚假意识”。文化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历时和现实优势,垄断了消费宗教的产品供给并占据产业链的最高端,这形同中世纪的教会,完全垄断了圣经的供给一样,人们虔诚地拜倒在这座符号供给的大殿前,并自愿倾囊购买这些“免罪符”。因此,当国民认为符号图腾能带来精神享受之时,符号消费便成为新帝国主义消费宗教灌输消费意识的手段,符号成为消费者的“救命符”,国民为此乐此不疲,达到了宗教的狂热,毋庸置疑,这种狂热已是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如同人类社会的宗教,与理性和思辨相悖,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因为信,所以信。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21.
[2]李彦文.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J].东岳论丛,2007,(3):162-164.
[3]李理,黄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102.
[4]陈宪.中国奢侈品消费行为分析:从儒家文化影响的角度[J].市场营销导刊,2007,(1):42-45.
[5]Markus&Kitayama.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 and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91,98(2):224-253.
[6]Wong N Y&Ahuvia A C.Personal taste and family face:luxury consumption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societies[J].Psychology&Marketing,1998,15(5):423-441.
[7]布鲁诺·兰纳.2012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 [R].上海:Bain Company,2012.
[8]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31-39.
[9]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18.
[10]李理,黄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102.
[11]张殿元.文化宰制辨析:一种广告传播的视角[J].人文杂志,2005,(6):157-160.
[12]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42.
[13]肖鹰.存在与艺术:自我的现代命运[J].哲学研究,1996,(6):41-49.
[14]雷文彪.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三重解读[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25-27
[15]洪晓楠,邱金英.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概念辨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51-54.
[16]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