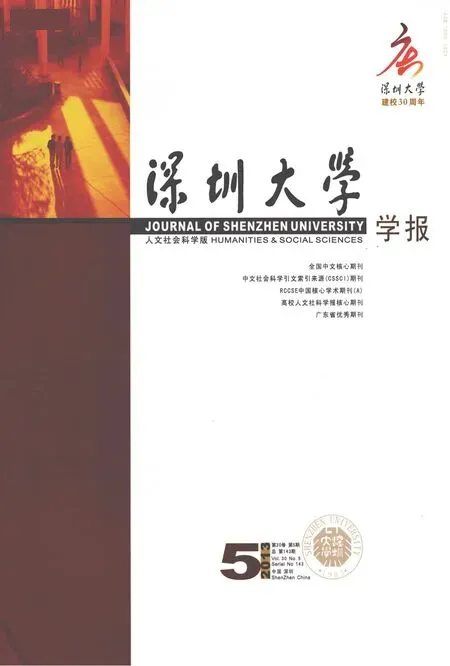非虚构文学的价值与出路——对深圳文学的反思与批判
汤奇云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深圳文学:新的生存批判叙事
就像外国人看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是一个戏剧性的崛起一样,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版图内,深圳文学也同样是一个戏剧性的崛起。无论是从作家的人数、出版和发表作品的数量,还是从文学的影响程度和文学书写话题的独特性上来讲,深圳文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存在。不仅深圳异常发达的“打工文学”引发了全国文坛对“底层写作”的大讨论;而且,深圳大学曹征路的小说《那儿》、《问苍茫》相继在中国文坛“炸响”后,曹征路就被尊为中国“新左派”文学的“圣手”,被评论界认为是目前中国以文学干预现实、反思现实最深刻的作家。人们似乎又看到了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所呈现的文学干预现实所产生的荣光。2011年,《人民文学》也由此打出了“非虚构”文学的旗号,目的在于引导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向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格的回归。
深圳文学也确实有着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品格。但与我国5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学议论国家政治变革对人的社会生存态度的影响不同,深圳文学关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形成的社会转型期间个体生存的耻辱与苦痛,并力图揭示这一普遍的精神“苦痛”的社会根源,如官僚腐败、钱权勾结、资本家的冷血、户口与暂住证制度所造成的人的等级划分,等等。从事这种“苦痛书写”的深圳作家,跟其他的深圳人一样,都是来自于内地各省的“移民”。他们本来就都是带着内地原有的文学书写范式和思想资源而来的。但是,我们只要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与内地作家多取材于历史(主要是从晚清到“文革”)不同,深圳文学多取材于作家们当下的现实生存。他们似乎不愿做宏大历史的反思者或评判者,而更愿做现实生存的愤激的批判者。
应该说,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以非常不情愿的姿态,走向所谓“边缘化”以来,准个体虚构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主义写作等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文学时尚,而整个深圳文学却保有着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干预性品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新的社会生存而写作,或者用张未民先生的判断:“这是一种生存中的写作”①。显然,正是这个被称之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城市的全新社会构成,以及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所规定的生存方式,扭转了作家们的美学价值取向,并引发了文学创作题材的群体性转向——走向现实和功利。因此,对深圳文学的认知与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更有助于人们正确辨识中国当代文坛某些惑人的论调。
多年来,文坛流行着文学边缘化论调,也充斥着对“伪”现代性文学话语的时尚追逐,实际上是部分人在现代文学精神受到创伤后的某种矫情的自艾自怨。正像五四新文学一直在批判性地审视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一样,中国当代文学其实一直在严密地监测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陷阱,并在这种监测中显示着自身的价值,尽管带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深圳文学就是这一文学品质的赓续者。
众所周知,自从设立经济特区而立市以来,深圳这个城市就按照资本的逻辑,通过不断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园和兴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形式在急剧扩张和膨胀。深圳也在按照资本的逻辑在不断重组和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化空间。深圳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先来的还是后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每天都在这一逻辑轨道上生存,每天都在呼吸着这种资本化时代的文化空气。如果人们还能够认同深圳是一个现代都市,那它绝对是全然不同于北京、上海等仰仗政治权力或西方殖民势力发展起来的老牌都市社会的。
作家们的神经本应该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富于想像的。但是,对于这些从内地体制社会来到这型城市社会里求生存的深圳作家们来说,这份敏感与想像似乎用不着了,他们只要把自身的那份新的城市生存体验写出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原本对现代城市的想像与对现实生存的感受之间的巨大落差,已经足够产生他们的文本所需要的文学性了。
因此,深圳文坛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当深圳号召作家们要打造合乎深圳这座城市的现代气派与身份的“新都市文学”时,深圳的一个街道文学杂志则执拗地打出了要书写“新城市文学”的旗号。因为在这部分作家看来,深圳只是从一片农田里新冒出的由无数工业园连接起来的一座物质化城市空间而已。而从农村社会到这个所谓的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就有足够多的新奇人事供他们书写和记录了。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律师执业者,自己出钱办杂志办文学网站,再把自己在职业生存中碰到的令人惊绝的司法故事,“批发”给其他作家来书写的现象。
如果说新的职业生存和新的身份生存,是深圳这个新型城市社会的生存真相;那么正是这种独特的城市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催生了深圳的也是目前中国最发达的行业文学和打工文学。大学教授写高校,南翔就写过《博士点》,曹征路也写过《南方麻雀》;银行职员写银行,谢宏就写过《信贷项目经理》;职业经理写股市操盘手,丁力也写过《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导游写旅游行业,央歌写过《来的都是客》;做过城管局工作人员的李季彬写过《城市游击》和《城关局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个城市所拥有的千奇百怪的职业,都能够在文学中找到其对应性的书写。打工仔们没有深圳户口与编制,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来源,也意味着他们在新的社会阶层组合中社会身份的卑微。他们往往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各个行业与角落。他们卖保险,做地产中介,搞物流物业,上工厂流水线,乃至身不由己地涉足色情行业。也恰恰是这些成为作家的打工仔们,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中国当代社会深度的潜望镜。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写出了各行各业的黑幕,也写出了打工生存的梦想、苦痛与失落,血泪与颤叫,如戴斌的《深南大道》、《压米》。《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等刊物,多年来一直在大量刊登这些行业文学和身份文学的代表作品,如打工作家王十月和萧向风的作品。
这些行业文学和身份文学所呈现出的 “新城市”景观,就远不同于老舍、王朔、徐坤之于北京的嘲讽化市民想像,更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王安忆、卫慧之于上海的现代时尚书写。在曹征路笔下,深圳是一个嘈杂而血肉飞溅的工场,老工会主席因替工友们维权未果,愧疚难当,而躺倒在巨大的蒸汽锤之下(《那儿》);本土的老村长则因看不惯资本之舞的血腥与残忍,而自我放逐于一个荒凉的海岛上(《问苍茫》);在吴亚丁的笔下,深圳是一个出租之城,年轻的叶蝉(研究生)们和陈旎(空姐)们同居、租住在出租屋里,同时他们也在出租着自己的智慧与美貌,当其人生资本消散殆尽时,他们便再一次收拾好自己的行囊,无奈地让渡着自己的人生乃至于这个城市(《出租之城》)。总之,这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城市的“过客”(央歌《来的都是客》)②。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就象那玻璃缸里的不断游动的金鱼貌合神离(谢宏《貌合神离》)。而楼外搵工失意的“苦瓜们”、“土豆们”,或“对着太阳撒尿”,或大脚踹向垃圾箱,嘴里却在嘟囔着:“长这么丑,我容易么?”(戴斌《长这么丑,我容易么》);或在心中幽怨地念叨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我们不是一人类》)。更有网络作家则不无偏激地以《天堂往左,深圳向右》为题来书写他们的深圳印象。一部分打工作家开始对这原本充满无限羡艳与诱惑的新城市生存产生了 “过敏症”(谢湘南诗集《我的过敏史》),而纷纷转向对家乡的温情怀念的书写(卫鸦《被记忆敲打的黄昏》、《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被红土串起的记忆》,孙向学《二傻》、《天堂凹》),像他们的前辈沈从文一样,间接地表达了对这新的城市生存的批判。
显然,深圳作家面对这座城市,一直在做着一种立足于自身的社会生存位置与感受的不无情绪化的批判性书写。如果说,北京叙事在以一种老住民的身份,嘲讽着笑看着调侃着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世事风云与人间变幻;上海叙事在以一种主人的身份享受着追逐着这座摩登城市的现代与新奇;那么,深圳叙事则是在以这座城市的“过客”的身份怨恨着、批判着这座城市大工场。“过客”,是深圳人的文学影像;批判,是深圳叙事的美学品格;怨恨,是深圳文学的主流情调。
特定的社会场域,蕴酿了特定的社会情绪;独特的社会情绪,又规定了文学的美学品格追求取向。文学的现实规定性这一定律,至少在深圳这三十多年文学书写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能够解释一些内地评论家在解读深圳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困惑:为什么深圳这些作家在享受着现代化的好处的同时,却在干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的勾当?深圳这座令世界都产生惊艳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派 “先锋文学”?深圳的这种“怨恨文学”不是我们一直所熟悉的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吗?
二、身份叙事:批判美学的局限
深圳文学确实具有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巴尔扎克式和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而是一种对新的现实生存的不适应及其社会情绪的记录与写实。因为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风俗人情有着深入的分析,而鲁迅则对五四前后的文化与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透彻的识解。
对深圳作家而言,人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号召“要回到现实”、“回到生活”。深圳文学几乎就是匍匐在当下现实生存地面,呼吸在工厂流水线上,呼吸在大街小巷里,呼吸在出租屋里和写字楼里。当下《人民文学》和《文艺争鸣》正在倡导创造“非虚构”文学,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一直就在做着典型的非虚构文学。因为这种新的城市生存体验的沉重,根本就不容许他们去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大部分年轻作家的文学写作技术也限制了其对虚构的运用空间。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只有表达、倾诉乃至宣泄。因此,当9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走向政治“边缘化”,纷纷投入叙事技术探索,走向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反叛,从事着对人的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唤醒的时候,深圳文学却自然而然,同时也是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对当下生存感受的叙写上。文学的针对性,在深圳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那便是完成对新的社会生存的批判。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整个中国文学搏击在“存在”和“话语”的虚空中,从而导致文风乃至文体走向阴性化或软体化(当然是以“个体化写作”名义出场的)的时候,深圳文学尽管缺乏写作技术的精致,却集体性地表现出一种久违的刚健与硬朗色彩。这种不无刚健与硬朗的文学,尽管不是那种能够抚摸或慰藉心灵的文学,却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力度,以文字担当起社会道义的力量。这种“铁笔担道义”的良知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传统品质。
正如任何外来客都有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一样,而深圳文学所散发的出于社会道义的批判力量,恰恰就是来源于这座城市的集体性的 “过客”意识(有文学习作者甚至就以“过客”为其笔名)。这种“过客”意识也就是作为这座城市移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而存在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非主人”的身份出场,甚至总是在以“客者”的身份来自说自话。一张深圳身份证,一本深圳户口簿,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文化身份意识,因为连一些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先来者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深圳人历来就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因此,深圳作家也是在以一种“他者”身份,怯弱而警惕地打量这座城市的一切人事。他们不可能像北京作家一样,以这座城市的老住民身份底气十足乃至油嘴滑舌地嘲弄人间的荒诞;也不可能像上海作家那样,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现代城市生存的优雅与美好。所以,这才有吴君的概叹:“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也才有吴亚丁的对住在出租屋里的岩桐的孤独与寂寞的咀嚼,盼望着在黑夜有人来叩响自己的窗户(《谁在黑暗中敲打我的窗》)。
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作为一个依据政治权力和资本市场重新组建的移民城市,所有的深圳人都被重新纳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文化空间里,也被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客者”;而只有权力和资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如何应对这两位新的主人(因为权力主体和资本主体总是在不停地更换),才是他们眼下生存现实中的第一要义。他们既要讨好这两位新主人以适应生存,同时也更讨厌这两位主子的冷血性的待客之道。因此,我们也应看到,深圳作家的这种暧昧态度,极大地损伤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往往当他们得到了这两位主人的“赏识”时,于是他们会觉得,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女人是漂亮的,城市是摩登的。有时甚至还会幻觉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了,为自己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而当他们的青春与智慧在租赁行为中得以终结,于是他们会对这两位主人大吐忧怨的口水,甚至破口大骂,骂他们冷血无情,骂他们没有人情味。
这种写作心态的摇摆,从现有的这些写深圳的街道、酒楼、咖啡馆、KTV歌厅和出租屋、工厂、故乡这两类场景的文本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证明。写前者时,文本的人物有时甚至会借着酒意或面向情人的爱意,径直地喊出 “我爱这座城市”(如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写后者时,老板和当权者则成了心怀鬼胎的恶魔,自身生存苦难的制造者,唯有回到“美好的故乡”(其实也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才能逃出这“地狱”之城,如卫鸦的《天籁之音》,就让一个哑巴唱出了《茉莉花》这首歌。因此,深圳文学对新都市生存的批判,仍然只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道德批判,尚未达到立足于现代性的批判起点。
尽管目前对现代性的内涵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乃至莫衷一是,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确:现代性指涉的是人的现代性。它基本要求的是,当人们面临着现代社会的物化生存和理性生存之时,人作为生存的主体,必须饱有其自身强大而独立的生命意志。对于这种新的城市生存与社会关系,作家们不仅要有现代人文精神上的崇高识别,更要有现代社会学知识层面上的认知与反思,和哲学层面上的遐思与体认。只有作家对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的认知的问题得到解决,作家的书写立场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如果作家们依然立足于既定的社会文化身份,而仅仅在题材或词令技巧层面下功夫,文学的问题,尤其是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因为文学的现代性的一项基本指标是,文本叙事中或者文本中的人物的思想与意识,应该体现出应对现代社会的这种物化生存与理性生存的清醒的认识与态度,而远不是按照原有的社会生活理念去猎获新社会里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么简单。显然,这更需要作家对新社会中的人与事,有更深入的观察、更精细的思考与选择。
有人曾经简单地做过这样的逻辑推理:现代性社会必然产生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必然派生出现代性文学。因此,先锋城市就必然会诞生出先锋文学,新都会就必然会产生新都市文学。然而深圳的文学事实证明,这只是理论家们一厢情愿的一场春梦。
其实,无论是人们立足于什么样的身份来写作,其文学书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其情绪的偏狭性和美学的局限性。过去的阶级身份和当下正时髦的性别身份,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无不证明这一点。或许,这些社会文化身份所代表的书写立场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变种罢了。
当然,立足于身份书写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一是立足于不同身份的写作,确实为作家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新的发现;二是人的社会文化身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规定性,作家也一样。带着这种现实身份的规定性来写作,也似乎使文学天然地具有了现实主义美学色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审美自觉性和情怀的超越性追求便终止了,文学的批判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当人们反诘这些制造批判文学的深圳作家:“这座城市又没有关门,既然你觉得深圳这么不好,故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作家们就只能面临一种无言以对的尴尬。
因此,新的社会生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对象,而文学自身的超越必须依赖作家这一主体的成长与强大。毕竟文学是由作家写出来的。
三、超越传统:非虚构文学的出路
显然,由于深圳是一个由人口不足三万的小渔村,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而成长为今日的一个拥有千余万人口的大都会,因此,深圳文学无疑具有移民文学性质,因而也就带有一种阿客琉斯的脚踵式的先天性缺陷——以“客者”的身份与立场来书写。在这里,我们及时地对自己所钟爱的深圳文学作出这种批判性的反思,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她克服这一缺陷,超越传统的身份写作,立足现代人文知识者的立场,才有可能使这支业已成型的文学军团饱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况且,深圳移民文学与世界发达地区的移民文学相比,还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深圳移民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内地移民。即使有个别作家属于土生土长(如谢宏),他们也与这些移民作家有着几乎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甚至生存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是同一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属于“文化移民”,是从旧观念时代迁移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移民。他们共同成为了这新的大都会社会生存的第一代文学言说者。他们是不可能象米兰·昆德拉们一样,是在与一个已有的现代都市文学言说进行碰撞、修正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超越性写作的。如果他们继续死守着手中的文学乡村牧笛,那么我们就永远只能从这座城市的上空听到那种哀怨的笛音,也永远无法回答社会对这种“苦痛文学”的反诘。
细读深圳当下的文本,人们不难发现,这支由内地移民作家组成的文学军团,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潜意识、记忆和语言里。他们与当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发生了一种新的断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更为现代的精神与文明。他们绝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化”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在抒发着他们的乡愁与诅咒。他们热衷于关于这座城市新颖离奇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这个新的城市社会作为分析和思考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这个社会就成为移民们脑海中的一个“被说明”之物,成为文学中无主题性的背景。也就是说,作家们原本想要揭示的这座城市、这个社会的精气神往往落了空。
由于这些移民作家们继承的是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观念,而在对人的生存与欲望、历史与知识、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上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从而导致在他们的创作中,对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心理、语言与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还缺乏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他们只能遵循资本时代的注重效率的文化逻辑,以量取胜,不断重复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的老歌。
好在有些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决定重写或改写自己的“非虚构”故事。这说明我的上述观察与判断没有走偏。所以,实事求是地说,“非虚构”文学不可能真正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文学经验。因为我们还看不到他们在写作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文学思维方式,所以在作品中存在着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达的之间的错位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昆德拉在批评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说:他枯燥的心灵掩盖在看起来情感汪洋肆意的风格背后[1]。我觉得这句话很能切中“非虚构”文学的软肋。
当下的这种“非虚构”文学,很明显地呈现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倾向是,媚俗式地采用传统的文学言说方式,粗暴地改编或剪裁着我们的现实,让文学仅仅成为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经验与认知;另一种倾向是,专注于个体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偏执,也成为了“非虚构”文学的一种美学风格,也成为吆喝世人的一种手段。
对深圳作家而言,要创造真正立足于新的都市生存的“新都市文学”,就不仅要超越他们原本所熟悉的社会生存身份书写,还必须要在人文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体认与文学言说途径等方面,作出一种面向自身文学传统的全方位的超越。说白了,就是要求作家们完成在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等方面的超越,以建立自己独特的体认人生的哲学支点和表达时代的文学语言。
因此,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应该具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政治生存或社会生存背后所游荡的情感的伤痕。只有超越这种集体性的身份写作,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真正能动人心魂的文学才会出现,我们的文学星云也才能获得永久的灿烂。而对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文化移民作家(实质上恐怕是一些文化的 “遗老遗少”)来说,可能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是吸同一个文学胞衣里的血而长大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成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价值的实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不仅仅是现实的记录,也不只是自我虚空的表白,而应该是当下现实中鲜活而健全生命的自由呈现。
注:
①这是张未民先生在一次关于深圳“打工文学”的座谈会上谈到的。他在主编《文艺争鸣》时,曾竭力呼应“非虚构文学”这一主张。
②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办,其中一句迎宾标语为“来了就是深圳人”,被张贴于深圳的大街小巷里。该标语与“来的都是客”,在潜意识层面也形成了一种逻辑同构关系。
[1]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