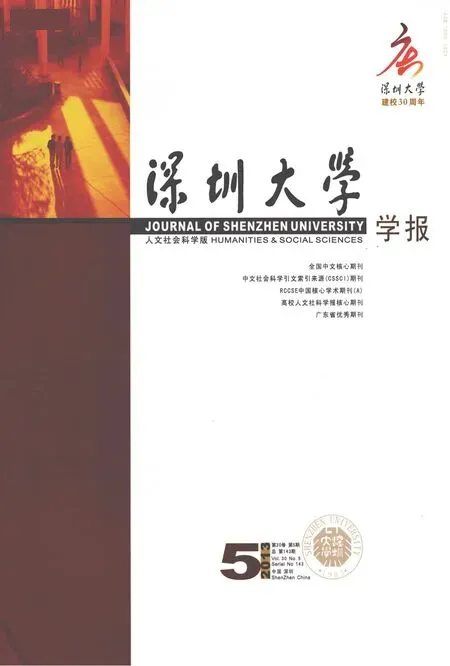湛若水关于儒道之别的观点述略——以《非老子》为中心
黎业明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60)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为雨,后定今名。广东增城县甘泉都(今增城市新塘镇)人,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四月间,当时隐居南海西樵山的湛若水,完成了《非老子》一书的撰作。湛若水撰作《非老子》,主要是针对王道(1487—1547年,字纯甫,号顺渠,山东武城人)《老子亿》的。作为湛若水的弟子,王道认为儒道之间并无区别,而且在其《老子亿》中,或“以圣经贤传之言附会其说,并称二圣;或援孔以入老,或推老以附孔”[1]。王道这种混淆儒道之间区别的做法,无论是对儒学还是对湛若水本人,都是一种猛烈的冲击。正如湛若水的另一弟子冼桂奇说,“注《老子》者多矣,未有如王纯甫拟老子于孔圣者。虽然,王子未知道,不足怪也;独怪其出于门下,非惟于师道无所发明,反贻名教之累也。此书传于天下,将必有追咎者矣。”[2]难怪,湛若水要与这时已经过世的王道划清界线,不再认王道为自己的弟子,并且号召门徒要对王道“鸣鼓而攻之”①;难怪,湛若水自己要“忘其年之耋耄,词而非之”[1],要撰作《非老子》一书。
《非老子》是湛若水集中批评《老子》、讨论儒道之别的最重要的著作。但是,人们对于湛若水的这部著作并不是很重视,相关的研究不多。限于见闻,所得见者,只有台湾的张佑珍先生所撰《江门道统与〈非老子〉》一文[3]。显然,对于湛若水的《非老子》,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大体上说,湛若水撰作《非老子》,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证实《老子》根本不是老聃的作品,二是要辨明儒道之间的区别。在这里,我们仅就湛若水在《非老子》中关于儒道之间区别的观点略加分析论述。
一
在《非老子》中,对于儒道之间区别的问题,湛若水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其中最为湛若水所重视和强调的,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儒家与道家所理解的“道”的问题,二是儒家与道家所说的“自然”问题。
道是儒家与道家都特别重视的概念。在《老子》书中,道更被人看成是一个核心概念。在道的问题上,湛若水认为,儒家与道家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在《老子》那里,道与器是分离的,是虚远而飘渺的;在儒家那里,道与器是一体的,是平易而近实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非曰:《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上下精粗皆具矣,何其直截明白也。老子此言周遮支离,欲求高远无名,已不识道,反又晦焉。盖下一“道”字即是名矣,岂名外又有无名之名耶?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非曰:《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同一形字,只上下之间耳。老子以无名、有名分天地万物,与《易》相反矣。况以道观天地万物,则天地亦一物耶
《老子》书的开头,便将道与名区分为“常道”与非“常道”、“常名”与非“常名”,并将“常道”、“常名”说成是不可道、不可名的“存在”,也就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加以言说、指称的“东西”。《老子》书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强调道与经验事物的不同,借此说明道的玄妙,确立道的超越性。另一方面,《老子》书又将道说成是“无名”,并将其视为天地万物的开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目的是要强调道作为天地万物根源的意义。但是,《老子》书的这一观点,在湛若水看来,是将道与器分离,将天地视同一物。湛若水认为,根据儒家的看法,尤其是《易传》的看法,道与器是不可分离的,道与天地万物一体,道就存在于、体现于万物之中。《老子》将道器分割,说明《老子》书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因此,湛若水在回答其弟子何滚的请教时说,“可道、可名,道也;不可道、不可名,亦道也。道贯体用、动静、隐显、有无。程子曰:‘体用一源,隐显无间’。二之则非道。老子于是乎不识道矣。”[1](P50)
正由于道与器、道与万物是不可分离的,道就存在于、体现于万物之中,因此,湛若水认为,道并不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是虚无飘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而是平易而近实的。
古之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
非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舍此而必求所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者,又极其形容,祗益茫昧。不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自见卓尔、自见跃如矣[1](P9)。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
非曰:怳惚窈冥,皆想象之言,非真有见,如参前倚衡之实也[1](P12)。
在《非老子》中,湛若水一再引述孔子“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论语·卫灵公》)[4](P191)、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离娄章句上》)[4](P332)等说法,说明道的平易而近实。湛若水在批评《老子》第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一节时,甚至说,“道与天地万物同体,亦家常菜饭,何奥何宝?”[1](P34)道既然是如此的平易而近实,人们若能“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自见卓尔、自见跃如矣”。湛若水认为,《老子》将道描述为“怳惚”、“窈冥”,这些都是想象之言,并不是真有所见;《老子》追求所谓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实就是舍近求远、舍易求难。这样,不仅不能把握到道,反而会让人更加“茫昧”。
第二,在《老子》那里,道器是分离的,其中所体现的体用关系,也是割裂的;在儒家那里,道器是一体的,其中所体现的体用关系,是“体用为一原而无二”的。
致虚极,守静笃。
非曰:圣人之道,虚实动静同体。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将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非曰:道贯根干动静而一之者也,如彼树木,根干枝叶,其气一以贯之。今以根为树,则干枝花叶非树邪?皆当常知常明。圣人之道则是一本,老子则是二本。程子曰:“夫道,一本也,知不二本,则笃恭而天下平之道。”[1](P9-10)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非曰:彼只以母子喻体用,不知母子虽同气而二体,是二物,体用为一原而无二也,岂足以知道乎?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于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非曰:翕辟、动静、小大、强柔,莫非天地自然之道,何必闭门塞口然后为道[1](P28)?
对于一般事物或其属性,例如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声音、前后以及祸福等等,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在《老子》书中是颇为强调的。但是,一旦涉及到道与器、虚与实、静与动等问题时,《老子》书中更重视、更强调的无疑是道、虚、静这一面,确实有将道与器、虚与实、静与动等加以割裂的嫌疑。在湛若水看来,这说明《老子》根本不“足以知道”。湛若水认为,《老子》书之所以将道与器、虚与实、静与动等加以割裂,原因就在于其作者不了解道与器、虚与实、静与动等等之间的体用关系,他以母子来比喻体用,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湛若水认为,依据儒家的看法,道与器、虚与实、静与动等等之间的体用关系,是“体用为一原而无二”的。基于这种认识,湛若水甚至对朱熹所谓“老子有老子之体用”之说表示不满。据《非老子附录》记载:冼桂奇问:“朱子非康节‘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之说,是矣;又谓‘老子有老子之体用,孟子有孟子之体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老子之体用也’云云。窃恐未然。即此二句,亦何体用之有乎?”湛若水答曰:“体用一原,何分体用?文公果有此言,未见的当。若谓老子之体用非吾儒之真用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乃诡谋不正,本体固如是[乎?何以有用?]”[1](P47-48)②
第三,在《老子》那里,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伦秩序是大道沦丧的产物;在儒家那里,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伦秩序就是道的体现,就是道。
大道废,有仁义。知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非曰:仁义忠孝根于人心之本然,天理之当然,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即大道也,岂舍此而别有所谓大道耶[1](P11)?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非曰:圣[人]之教,在心为德,在事为道。仁义[礼]即德也,更无二理。《[老]子》书如此品题,则不识道德[仁]义礼矣。程子曾非[之]。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非曰:礼即理也,即道也。忠信而后能存此道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今曰礼为忠信之薄,已不识道矣。既云道之华,又以为愚之始,自相反也。况《老子》书既薄礼,则后人所称孔子问礼于老聃者为妄矣[1](P20-21)。
《老子》书中,对于儒家所特别重视的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伦秩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或者将仁义忠孝看成大道沦丧的结果,或者将礼制秩序视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湛若水认为,这正好说明《老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道”。在湛若水看来,道不仅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而且存在于社会人伦之中,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伦秩序就是道的体现,就是道。仁义忠孝是道,礼制秩序也是道。
与关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伦秩序的看法相应,在《老子》看来,人类的黄金时代只存在于远古,因而主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儒家看来,道既是永恒的(“古今异宜而道则一”),又是“随时变易”的。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非曰:古今异宜而道则一,圣人亦随时而已,随时变易,道也,是真道纪也[1](P8)。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非曰:众寡器用,莫非自然。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非曰:生今反古,结绳而治,是乱天下也,是不识时也。不识时,是不识道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非曰:太古则然。随时者,道也。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逮(失)“夫”身[1](P42-43)。
由于《老子》作者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主要是对社会政治阴暗面的关注,他所看到的多属于社会政治中负面的东西,以至将人类社会中许多价值观念,如儒家所特别重视的仁义礼智等等,都作了负面的理解,并且加以猛烈的抨击。《老子》作者对其所生活的社会、所生活的时代明显地持悲观态度,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化。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远古。因此,他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他主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方略。当然,儒家也多以为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在古代(尧舜时代),但是那只是衡量现实社会政治的一个标准。事实上,儒家既重视历史,又关注现实;既主张因循,又主张“损益”(《论语·为政》)[4](P69);既强调“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孟子·离娄章句上》)[4](P325),又强调“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5](P17)、“与时消息”(《周易·丰卦》)[5](P454)。依据儒家的观点,湛若水认为,我们既要知道“古今异宜而道则一”,又要知道“随时变易,道也”。像《老子》所谓“小国寡民”、“结绳而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主张,乃是“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这都说明《老子》不识时。不识时,便是不识道。其结果是,不仅害己(“灾必逮夫身”),而且害人(“是乱天下也”)。
其实,《老子》书中所说的“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老子》所说的“道”的本义到底是什么,现代学术界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理解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观点、看法也不相同③。从湛若水论述看,他对于《老子》所说的“道”的本义到底是什么,似乎并没有加以深究,而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从儒家(或儒学)的角度,对《老子》所说的“道”的某些特点或特征加以分析论述、批评非议。其中虽然不乏睿智之言、精彩之论(例如,在批评《老子》“小国寡民”时,说其“不识时”、说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但是,湛若水对《老子》似乎缺乏应有的“同情之理解”。
二
与儒道两家对道的理解不同相关,湛若水认为,在自然的问题上,儒家与道家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湛若水甚至认为,《老子》或者老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然而,在处理自然的问题时,湛若水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宋明时期人们特别重视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几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自然”这一概念;相反,在道家的经典《老子》与《庄子》中,“自然”一词则出现过多次。两者如何比较?当然,没有使用“自然”这个概念,并不等于没有关于“自然”方面的思想。因此,湛若水将孔子所说的“毋意必固我”、孟子的“勿忘勿助”、程颢的“绝无丝毫人力”等,都解释为“自然”。
事实上,对于湛若水来说,“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学以自然为宗”,既是其老师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号石翁,广东新会人,因居江门白沙村,学者称其白沙先生)的遗训,也是湛若水自己服膺数十年、始终坚持不懈的教条[6](P2-3),而且如何诠释“自然”,与江门心学在儒学中的地位问题息息相关。这也许就是湛若水为什么要在其所排列的儒家道统中,将陈白沙列入其中,将自然视为圣学相传之心要。湛若水在所撰《白沙书院记》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曰:“敢问白沙先生之心之道,其有合于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之心之道者,何居?”“先生语水曰:‘千古有孟子勿忘勿助,不犯手段,是谓无在而无不在,以自然为宗者也,天地中正之矩也。’世之执有者以为过,泥空者以为不及,岂足以知先生中正之心之道哉?夫心也者,天地之心也;道也者,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非他,即吾心之中正而纯粹精焉者也。是故曰‘中’、曰‘极’、曰‘一贯’、曰‘仁’、曰‘仁义礼智’、曰‘孔颜乐处’、曰‘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皆天理也,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所谓‘惟精惟一’,所谓‘无偏无党’,即孔子之所谓‘敬’也;孔子之所谓‘敬’,即孟子所谓‘勿忘勿助’也;孟子之‘勿忘勿助’,即周、程之所谓‘一’,所谓‘勿忘勿助之间正当处,而不假丝毫人力’也;程子之‘不假丝毫人力’,即白沙先生之所谓‘自然’也。皆所以体认乎天之理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故学至于自然焉,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之道尽之矣。扩先圣之道以觉乎后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岂不伟欤!后之人欲求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之学者,求之白沙先生可也。非求之先生也,因先生之言,以反求诸吾心之本体自有者而自得之也。……”[7](P29-31)在这里,湛若水不仅排列了一个以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陈为传授顺序的道统,而且将陈白沙所说的“自然”看成是与程颢之所谓“不假丝毫人力”,孟子之所谓 “勿忘勿助”,孔子之所谓“敬”(或者“无意必固我”),尧、舜、禹、汤、文、武之所谓“惟精惟一”、所谓“无偏无党”是一样的,“皆所以体认乎天之理也”;将陈白沙的“自然”看成是圣学相传的心要,以为“后之人欲求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周、程之学者,求之白沙先生可也”。湛若水如此强调“自然”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要说明“自然”不是老庄的“专利”,为陈白沙洗脱援老庄入儒的嫌疑;另一方面是希望借此确立陈白沙开创的江门心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④。
既然自然问题在湛若水的思想之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分析湛若水《非老子》中关于儒道两家在自然问题上的区别这方面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湛若水的“自然”观略加了解。湛若水对自然问题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论述,是《自然堂铭》。其文略云:
仰维宣圣,示学之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川上之叹,不舍昼夜。天时在上,水土在下,倬彼先觉,大公有廓。自喜自怒,自哀自乐,天机之动,无适无莫。知天所为,绝无丝毫人力,是谓自然。其观于天地也,天自为高,地自为卑。乾动坤静,巽风震雷,泽流山峙,止坎明离。四时寒暑,自适其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自无为,是谓自然。其观于万物也,化者自化,生者自生,色者自色,形者自形。自动自植,自飞自潜。鸢自戾天,鱼自跃渊。不犯手段,是谓自然。是何以然?莫知其然。其然莫知,人孰与之?孰其主张?孰其纲维?孰商量之?孰安排之?天地人物,神之所为。曰神所为,何以思惟?吾何以握其机?勿忘勿助,无为而为,有事于斯,若或见之。其神知几,其行不疑。穷天地而罔后,超万物而无前。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阖一辟,一语一默,各止其极,莫见其迹。莫知其然,是谓自然[6](P2-3)。
这就是说,湛若水认为,所谓“自然”,就是孔子所说的“毋意必固我”、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程颢所说的“绝无丝毫人力”;就是因乎阴阳之变,循乎无为之道;就是物各付物而己不与焉;就是天然如此,不需商量安排。用湛若水《自然堂铭》序文的话说,自然就是“圣人所以顺天地万物之化,而执夫天然自有之中也”[6](P2)。
从湛若水的论述看,他显然是强调,“自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不能有人为之私,就是不需商量安排,就是物各付物而己不与。要判断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人为之私、有没有商量安排,关键在于能否做到物各付物而己不与。
依据这样的认识,在《非老子》里面,湛若水认为儒家与道家对自然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不仅如此,湛若水甚至认为,《老子》或者老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然。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非曰:此自然与圣人所谓自然者不同。《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达德;天下之达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乃圣人所谓自然也。世儒以老庄明自然,岂得为自然[1](P27)?
我们知道,自然是《老子》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然无为是《老子》书中的一种重要思想主张。在《老子》书中,“自然”一词共出现过五次(《老子》第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五十一、六十四章),其含义大体上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本来的样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自然”是《老子》的作者用来“说明莫知其然而然的不加人为任其自然的状态,仅为《老子》全书中心思想‘无为’一语的写状而已”⑤。《老子》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意思大概是说,道之所以尊崇,德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能够不命令(即不干涉)万物,而任由万物始终根据本来的样子(亦即自己的本性)自生自长。湛若水认为《老子》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与儒家所说的自然是不同的。从湛若水引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来说明儒家所说的自然看,湛若水显然接受了朱熹关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乃“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仁、智、勇三达德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的解释[4](P33)。既然五达道就是“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那么它就是天道;既然三达德就是“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那么它就是天理。湛若水说,“天即道,道即自然也”[1](P14);又说,“所谓天理者,自然之体”[1](P36)。天道、天理,乃自然之体。只有符合天道、天理的,才是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所说的自然与儒家所说的自然是不同的。
湛若水还认为,《老子》既不明“自然”,也不知“道”;《老子》之所以不明“自然”,是因为不知“道”、不知“道即自然”。湛若水在批评《老子》第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节时说:
老子之道,平日只为其小,如何又称四大?天地人只是一气一体,而云“人法地,地法天”,是天地为二矣,而况于人乎?天即道,道即自然也。而云“天法道,道法自然”,岂足以知天地人之道、之自然乎?其言人法可也,而又于天地道自然皆曰法,是孰法之者?故《老子》书非知道者[1](P14)。
在湛若水看来,天道自然本来是浑然一体的,天即道,道即自然,根本不用彼此相“效法”或者“取法”。一说“效法”或者“取法”,就已经落入人为,就已经不再自然了。然而《老子》却说“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既说明《老子》书不足以“知天地人之道、之自然”,也说明“《老子》书非知道者”。
由于《老子》根本不明“自然”,因此,在其号称自然的时候,却时时不免拂人之性;在其声称自然的地方,又处处带有人为之私。与《老子》不同,儒家虽然没有口口声声说自己明自然,却时时处处表现出自然。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非]曰:道二,善恶而已。善即知善,恶即知恶,此秉彝之性也。拂人之性,非人也。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善]善恶恶而己无与焉,此圣人所谓无为也。今必欲[善]恶皆忘,然后谓之无为,吾恐矫性之过,即反有为。□句句似是而实非[1](P2)。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非曰:天地运化,道之自然不息,故曰生生。不可以言自生,亦不可以言不自生,此不字是谁不他?是老子以私窥天地也。圣人体天地之道,亦本于自然,纯亦不已,亦不曾有意后先内外其身也。圣人“体”天地之道,廓然大公,故能成其公,非成其私也[1](P4-5)。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非曰:圣人体天地之道,刚柔阴阳惨舒,莫非自然。遇争战则争战,遇揖让则揖让,安土敦仁,无往而非天理之自然,而我无与焉,此大中至正之道也。观此言一一有为,非自然矣。世儒谓老庄明自然,遂以自然为戒,惑也甚矣[1](P5)!
湛若水认为,《老子》以为只有做到美丑双遣、“善恶皆忘”,才是其所谓的自然无为,这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不是什么自然无为,而正好是有为;这不仅是有为,而且是“拂人之性”、是“矫性之过”。只有像儒家那样,“善即知善,恶即知恶”,“善善恶恶而己无与焉”,才是真正的自然无为。湛若水还认为,《老子》所谓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等说法,不是“以私窥天地”,就是“有意后先内外其身”,都带有人为之私。与此相反,儒家圣人体天地万物之道,深知天地运化生生不息,深知阴阳惨舒莫非自然。因此,对于儒家而言,“遇争战则争战,遇揖让则揖让,安土敦仁,无往而非天理之自然,而我无与焉”。在湛若水看来,争战揖让,安土敦仁,事皆人为,若能合乎天理,而无己意之私,若能做到物各付物而己不与,则人为即是自然。
在讨论《老子》所说的“自然”问题时,湛若水强调,要判断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人为之私、有没有商量安排,关键在于能否做到物各付物而己不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湛若水批评《老子》虽然主张“自然”、向往“自然”,却不免“拂人之性”、“矫性之过”、“以私窥天地”、“有意后先内外其身”,并不自然。更重要的是,湛若水在讨论“自然”问题时,引入“天理”概念,以为“天理者,自然之体”,主张凡是合符天理的,都是自然的。因此,湛若水认为,争战揖让、安土敦仁等,事皆人为,若能合符天理,而无己意之私,人为亦属自然。这可能是湛若水相关说法之中,最具个人睿智、凸显其理学家色彩之处。
综上所述,湛若水在《非老子》中分析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主要是以“道”与“自然”这两个重要概念为其分析重点的。在湛若水看来,《老子》所说的“道”与儒家所说的“道”是不同的,《老子》所说的“道”并不是儒家所说的“道”,用湛若水自己的话说,就是“道其道,德其德,非吾圣人之所谓道德也”[1](P1);《老子》所说的“自然”与儒家所说的“自然”也是不同的,《老子》所说的“自然”并不是儒家所说的“自然”,套用湛若水的话说,就是“自然其自然,无为其无为,非吾圣人之所谓自然无为也”。湛若水认为,《老子》根本不知“道”,老庄根本不明“自然”。世儒(指王道)以为《老子》知“道”,以为老庄明“自然”,以为儒道之间并无区别,其“惑也甚矣”。总而言之,湛若水的相关观点与看法,是颇具睿智的。当然,在针对《老子》的某些说法上,湛若水可能缺乏“同情之理解”,甚至可能失之偏颇;但是,从其维护儒家(或儒学)的立场语角度言,湛若水的这些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
①湛若水的说法很委婉,说是“今且不暇鸣鼓而攻之于庙庭也”;而其弟子冼桂奇的说法则很明白,说是“鸣鼓而攻,吾辈有馀责矣”参见湛若水撰:《甘泉先生续编大全》,第32卷,卷首、第62页。
②案:引文中所脱文字据《湛甘泉先生文集》通行本补出。参见湛若水撰:《湛甘泉先生文集》,通行本,第25卷,第2—3页。
③例如,傅伟勋先生根据其“创造的解释学”,将《老子》的“道”分析为六大层面,即道体(Tao as Reality)、道原(Tao as Origin)、道理(Tao as Principle)、道用(Tao as Function)、道德(Tao as Virtue)、道术(Tao as Technique),并且说,“从道原到道术的五个层面,又可以合成‘道相’(Tao as Manifestation)”。参见傅伟勋撰:《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385页。
④张佑珍先生认为,湛若水可能还有这样的考虑,这就是“既然陈献章是儒家圣人传统的一环,那身为江门传人的湛若水,理所当然可以依附骥尾,名列儒家正统之列”。参见张佑珍撰:《江门道统与〈非老子〉》,《花莲师院学报》,台湾,2003年第16期,第26页。
⑤车载撰:《论老子》,转引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2页。
[1]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第32卷)[O].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万历二十三年修补本.卷首.
[2]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第27卷)[O].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万历二十三年修补本.
[3]张佑珍.江门道统与 “非老子”[J].花莲师院学报,2003,(16):17-32.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O].徐德明校点.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第4卷)[O].内编,明嘉靖十五年刊本.
[7]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第32卷)[O].内编,明嘉靖十五年刊本.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