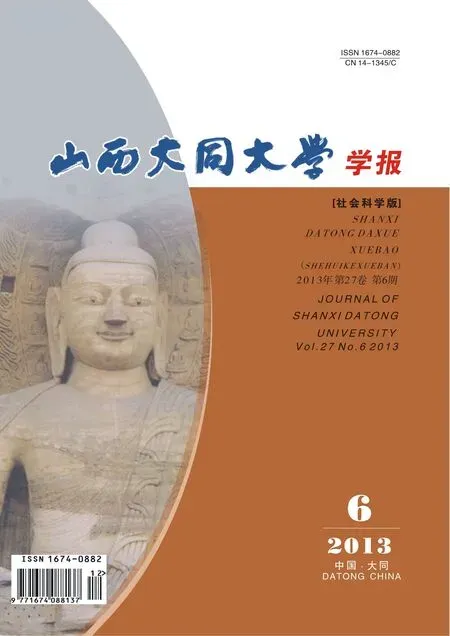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
——《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连慧英
(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 忻州 034000)
作为贾平凹的长篇力作,《秦腔》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竖起了一块碑。在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在我看来,作者选用这种叙述视角,不排除出于扩大小说容量、创新小说叙述方式的考虑。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叙述视角保留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和现实逻辑的真实性,暗含了作者注于其中的哲学思考和情感评价。
一、流年密集式的写法
叙述者及叙述视角是叙事作品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W·C·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中曾作过这样的分析:在阅读《奥德赛》时,“我们会明确地对英雄们表示同情,并对求婚者们表示轻蔑,不用说,要是另一位诗人从求婚者的角度来处理这一系列情节,他也许会轻易地引导我们带着截然不同的期待与担心进入这些历险”。[1](P8)布斯这番分析意在说明叙述者及叙述视角对与小说叙事的重要意义:由于叙述人不同或观察角度不同,都会影响叙述的面貌和色彩。胡亚敏的《叙事学》对“叙述者”这样来定义:“叙述者指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2](P36)。即叙述者就是作者在叙事文中安排的讲述故事的那个人或那个声音,它并非真实的作者,而是产生于真实作者想象的叙述文本中的话语。叙述视角是“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2](P19)是指叙述者或人物在观察和讲述故事时所采取的角度。叙述视角可分不同种类,并对叙述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秦腔》的主体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小说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这种视角:“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3](P1)并且这种视角贯穿了整部小说。“我”作为清风街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游手好闲到处游串,参与过清风街的许多事情,如与君亭等去水库要求放水、戏场维持秩序、跟君亭打架等等;见证过许多乡民们的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如目睹秦安等因赌博被公安局扣留、看中星爹算卦等;也有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如对白雪疯狂而执着的单恋、与白娥交媾后的悔恨等。可以说《秦腔》的叙写是密实的流年式的,作品中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也无意塑造典型形象,而是创造了一个既参与生活又不断跳出生活的“我”,通过日常琐事的拼接和叙述视角的转换生动表现了城镇化之下农村及农村人迷乱而又真实的生活状态。
二、叙述视角的变异
细读作品之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并不是小说唯一的叙述视角,小说中的叙述视角并非单一的、一以贯之的,而是存在着视角的变异:小说时而以“内聚焦型”视角进行叙述,即由半疯半傻的“我”讲述身边的繁琐生活并抒发独特的内心体验;时而却又转换为“非聚焦型”视角进行全知叙述,即以“上帝的眼睛”讲述一切。“我”的叙述时不时会冲破视角限制,讲述那些“我”不在场因而也不可能生动描绘的事,如写到夏风出去撂自己没屁眼的孩子时有这样一段描述:“白雪呼天抢地地哭起来,四婶也哭,堂屋桌子上空吊着的灯泡突然吧地爆裂,屋子里一片漆黑。白雪和四婶在灯泡爆裂的时候都停止了哭,随即哭声更高。夏天智在黑暗里流眼泪。半个小时后,夏风回来了,他空着手,说‘咋不拉灯?’一家人都没有言传,他就到他的床上睡下了。”[3](P396)此时的“我”明显是不可能在场的,这段讲述的视角无疑也就不是内聚焦视角而是全知视角了。这种突破或者以“我”的转述来实现,如“事后我听供销社的张顺说,狗剩在黄昏时候来到他那儿要买一瓶儿农药”;[3](P153)或者借“我”的疯癫身份以荒诞、魔幻手法实现视角转换,如“上善在看报纸……看见了会议室墙上趴着的一个蜘蛛……现在我告诉你,这蜘蛛是我。”[3](P291)这里,“我”以一种荒诞方式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全知讲述;而更多情况下,小说是直接转入全知视角,然后再以“我这说到哪儿了?我这脑子常常走神”、“趁空,该交待我了吧”等转折性语句实现小说整体视角的连贯。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是一副“上帝的眼睛”,全知全能地讲述“我”之外的事情。视角的变异是作家在选用叙述视角时的一种“违规”现象,在一些叙事作品中,理论上互异的聚焦类型往往在实际的运用中会彼此交叉和渗透,即一部作品中的叙述视角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安排了多种不同聚焦类型。视角的变异往往出于作家写作策略的考虑,以此来增减信息或达到其他的表现作用。
三、视角变异蕴含的哲学思考与情感趋向
小说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看似杂乱和“违规”,包含着作者写作策略上的考虑。“我”的别样叙述既是对原生态的现实逻辑的遵循,也是作者情感评价的体现。它以回到生活原点的方式原生态地反映了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及农民的真实生存生活面貌,蕴含了作者之于这种变迁的哲学思考与情感趋向。
(一)“常”中有“变”,杂乱中更见真实与理性以疯癫或痴狂者为叙述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罕见,鲁迅的《狂人日记》、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以痴狂者为叙述人的典型例子。然而,不同于这两部作品的是,《秦腔》中的引生不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启蒙者,也不是大智若愚的圣人。对于前二者而言,叙述者的“癫狂、愚蠢之后有一个巨大的或者根本的真理支撑着他”,[4](P40)而在《秦腔》中,“我”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半疯半傻的农民,“我”的讲述是平凡而琐碎的,在“我”的背后,只有生活。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多是清风街乡民们的日常琐事、泼烦生活与普通人的情感欲望。讲述琐碎、细致又符合“我”的身份,类似讲述还有秦腔演出现场村民起哄之后又被平息、人们哄抢刘新生的苹果、雷庆过生日“我”骗陈星买鞭炮,报了白雪的南瓜当媳妇、与丁霸槽玩“狼吃娃”,甚至是来运与赛虎交媾这些事情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我”的讲述是“拉家常”式的,“我”讲述的是生活中的“常”事。小说正是通过“我”的看似疯癫的讲述,展现了清风街永恒存在而又缓慢流动的“生老离病死,吃喝拉撒睡”的惯常生活。
如果说以“我”的视角来进行讲述的都是生活中的“常”,那么“我”的违规讲述,即小说中的全知视角所讲述的却多是“变”。小说中通过全知视角来讲述的事大致可分为三条脉络:第一条脉络是以夏天义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明在与以夏君亭为代表的农村新文明的抗争中逐渐败落,其中事情包括支持夏天义的秦安丧权、夏君亭搞农贸市场等;第二条脉络是以夏天智和白雪为代表的传统民间文化逐渐被流行文化消解,其中包括秦腔剧团逐渐瓦解、白雪生下怪胎、夏风与白雪婚姻破裂、秦腔沦为红白音乐等一系列事情;第三条脉络则是农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生存生活状态的变化,如在退耕还林示范地里种菜的狗剩因交不起罚款而自杀、进城打工的羊娃因抢劫杀人而被抓、因追缴税费而导致的“年终风波”等。[3](P546)小说在看似杂乱的繁琐叙述中,勾勒出了农村传统文明、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时代冲击下的消逝与变质。作者通过“上帝的眼光”审视了清风街的“常”中之“变”。
有学者在评论中认为,《秦腔》是对“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乡土文化想象的终结”、“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4](P40),这种说法值得采纳,贾平凹确是实现了文学对传统乡土叙事的突破。正如他在《秦腔》后记中所言:“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3](P547),作为一种写作策略,贾平凹不是将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变迁单纯地纳入对乡土文化的公共性想象当中,也不是一味记录琐碎真实而忽略社会变化发展规律,而是通过对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理性与真实的统一。作者规避了单纯以公共意识形态架构小说内容的传统写作方法,一方面通过“我”的视角生动描绘了变迁中的农村和农民们的生活“常”事,记录了他们似乎更久不变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同时又以非聚焦的全知视角将时代变迁、文化更迭的印迹镶嵌其中,揭示了“常”中之“变”,通过视角转换,作者将一个汤汤水水、有骨有肉的变迁中的清风街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我们得以看得农村在新时代巨变面前真实的战栗与迷茫。
(二)还原中的迷惘与宽容 在《秦腔》中,作者试图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与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对所述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然而在这种还原中我们可以窥得到作者蕴含其中的情感态度。如在《秦腔》后记中所言“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茫与辛酸”。[3](546)
1.疯傻叙述下的迷惘
作品中,“我”是被当作思想情感不正常的人来对待的,“我”的表达因而是没有公共效应的,小说以“我”的视角来进行的叙述其实是放逐了意识形态责任的,而这种放逐正是作者无奈的情感取向。“《秦腔》给我们的东西不仅是挽歌、爱、留恋,不仅仅是在一个向前和向后的方位上采取的情感取向,而是一个站在此地,站在广大的沉默的中心,感受到这种沉默的压力,为此而焦虑,为此而不知所措,也为此在小说艺术上采取了现有的这样一个办法”。[4](P40)作者自述“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3](P544)也许,只有这种种疯癫的记录才可以真正表达作者的不知所措吧:规避指引性评价的记录往往是忠实却又无奈的选择。引生的叙述传达了这种迷惘和不知所措。
2.视角转换中的宽容
迷惘和不知所措不是作者在《秦腔》中表达的唯一情感,这点同样可在小说后记中窥探得到,在《秦腔》后记的结尾处贾平凹说:“竖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3](P547)小说中叙述视角的转换承担了对这种宽容态度的表达。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不只停留在由“我”所述的泼烦生活,也不止于由“我”传达的迷惘与无奈,而是在视角的转换中蕴含了理性的宽容。如果说“我”的叙述唱出的是一首疯癫的挽歌,是作者对于一种流逝的犹豫、彷徨,那么“我”之外的讲述则是这种迷惘之后的理性和谅解。两种不同的情感取向和谐融洽地共存于对同一对象的描述,这本身就是莫大的宽容。
随着我国城镇化过程不断向前推进,传统的民间文化也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迅速消亡或变质。于是传统的叙事方式或横截面式的刻画已不适应于对这种微妙变迁的表现,已不足以刻画处于这种变迁中的农村生存生活状态和农民们的精神状态。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水在流淌,混沌不清。可在混沌不清的到处流淌中,情感的青草在成长,人性的光亮在闪烁。”[4](P39)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1]W·C·布斯著,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胡亚敏.叙事学[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张胜友,雷 达等.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J].当代作家评论,2005(05):36-39.
[5]热奈特.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杨 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贾平凹,谢友顺.贾平凹谢友顺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9]陈晓明.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J].文艺争鸣,2005(06):10-13.
[10]王 红.《秦腔》的叙述者与叙述视角[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01):96-98.
[11]张学昕.回到生活原点的写作——贾平凹《秦腔》的叙事形态[J].当代作家评论,2006(03):5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