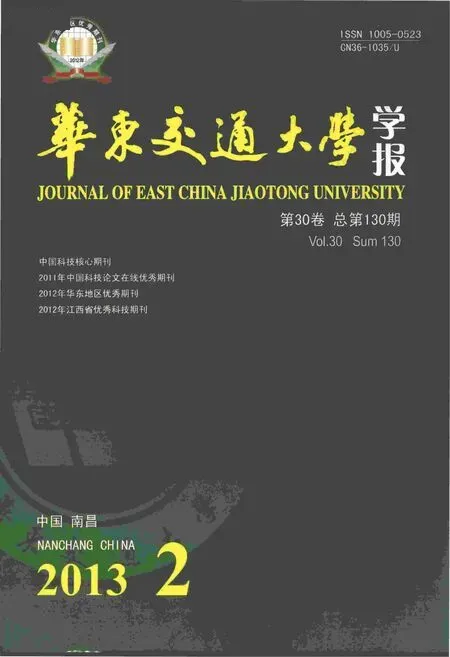翻译伦理视阙下归化和异化的对立统一
訾晓红
(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江苏南京211198)
1 归化和异化的二元对立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常用的两种策略。所谓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去接近目的语读者,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所谓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自从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提出之后,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于该两种翻译策略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施莱尔马赫认为归化和异化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两者毫无共同之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二者择一,尽可能始终采取同一种翻译策略。否则,一旦将两者混为一谈,便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后果,导致作者和读者很有可能永远无法走到一起[2]。在此种对立关系中,施莱尔马赫毅然选择了支持异化翻译,他认为本族语言只有通过与外国语言尽可能丰富多样的接触才能得以蓬勃发展,另外,为了尊重异国事物,可以使用本族语言传承所有的外国艺术和学识,将其与本国艺术学识一起构成完整的历史,因此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异化翻译可以丰富本族语言,有利于文化传承。异化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韦努蒂,他认为目前的英语翻译已经被英美文化所利用,过于归化的流畅翻译可读性高,会让人产生透明的幻觉,误将译本当作原作,从而使译者隐身,是一种潜在的霸权主义,而异化翻译可以使译文打破目的语常规,可以创造出一种富有变化、“含有异质成分的话语”[3]。归化派则认为归化翻译可以“采用透明的、流畅的风格为译文读者把陌生感降到最小”[4],其代表人物是奈达,他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观认为译文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的模式[5]。
在国内,关于归化与异化的讨论也多认为二者是一组矛盾对立体。刘英凯曾指出归化的翻译是意译的极端,是要改变国外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等客观事实,抹杀源语文化的民族特点,迫使其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也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扭曲,因此宁信而不顺的归化译文是翻译的歧路[6]。孙致礼对我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翻译进行了分析后认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先是以归化为主,后来具有从归化向异化转变的趋势,并指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7]。郑海凌认为,“好的翻译是译语的优化,即保持适度的异化”[8],孟志刚在提及归化与异化关系时也指出,“归化是现阶段的折中,而异化是发展的必然”[9]。由此可见,国内对于归化和异化的争论大都倒向异化一边,但是大多数讨论都是两者二元对立现象的反映。
2 翻译研究的伦理学回归
翻译是一种在个人意识支配下涉及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而所有的交际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翻译活动也必然要受到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制约,需要伦理学的指导。20世纪80年代,法国文学翻译家安托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他批判了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行为的正当伦理目标应该是“以异为异”(receiving the Foreign as Foreign),尊重和突出原作与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10]。2001年,翻译界权威杂志《译者》(Translator)出版了“回归到伦理”(The Return to Ethics)的专刊,特邀编辑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在引言中明确提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伦理”。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也日益加剧,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经过认真地考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才能解决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问题。Pym的这一观点受到译界的普遍接受,认为“回归伦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今社会的普遍趋势”。
在国内,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和讨论也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新焦点。吕俊提出建立翻译伦理学来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对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影响,他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对话和交往,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言语交往行为,这就要求人们遵守一些准则和规范,因为是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涉及的问题要更多,更复杂……这就是说它更需要伦理学的指导。这是翻译活动自身对伦理学的需要。”[11]汤君分析了西方与中国文化环境中翻译伦理的观念演化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概况,从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层面分别讨论了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12]。祝朝伟对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范畴及理想追求都被不约而同地赋予了道德色彩,打上了翻译伦理的烙印[13]。因此,正如许钧所说,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层次上的要求,呼唤伦理学的指导[14]。
3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
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于2001年发表了文章《圣哲罗姆誓约之倡议》(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提出了翻译的四大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of the author)、服务的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的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和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
再现的伦理要求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准确地再现原文文本,毫无增删、毫无更改”[15]。这一伦理模式强调译者对作者的忠诚以及译文对原文的真实再现。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该以真实地还原原文本来面目为指导原则,最大程度地反映原文的意图。
服务的伦理指的是服务于委托人的伦理。这一伦理模式将翻译活动看作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翻译最终的目的便是要符合其委托人的要求,实现由委托人和译者对翻译纲要所达成的共同商定目标。此处的“忠诚”要求译者首先要忠实于委托人,其次是目标语读者,最后才忠实于原文作者。在服务伦理中,原文仅仅是一个信息的来源,翻译行为不再以再现原文为目标。
交际的伦理认为翻译是一个交际的过程,体现了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双向交际的过程。译者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中介,不仅要再现原文内容和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对原文作者负责,而且要考虑对原文的诠释方式以及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因此,交际的伦理特别强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行为而非对他族文化的再现和描述,在这一伦理模式中译者的主要职责便是有效成为“交互文化空间”里的“混血儿”[16],千方百计促成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相互理解。
规范的伦理思想来源于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和规范研究。该伦理模式要求译者的翻译行为符合特定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和目的语读者的要求。切斯特曼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两种规范,即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和职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期待规范指的是译文读者对翻译作品形式特征的期待,违反这种期待会使翻译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职业规范指的是合格的职业译者应该恰当地满足原文作者、委托人即译文读者对诚信的要求,并且根据翻译的具体情境要求使翻译交际达到最大程度的优化,此外,译者还要确立并维持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适当的关联相似性。切斯特曼认为翻译规范的目的是要倡导明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与理解(understanding)四种伦理价值。所谓“明晰”是指信息的接受者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内识别信息发送者的意图。“真实”是指译文应该根据翻译情境的需要,尽量真实地反映原文的真实面貌。“信任”指的是交际各方,即原文作者、委托人、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彼此互相信任。“理解”指的是在翻译中译者应该尽量减少实际读者对文本的误解和被排斥在理解之外的潜在读者的数量。
4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和归化与异化
在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中,译者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责任和使命。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也不可能同时兼顾所有的翻译伦理。正如申迎丽所指出的,随着翻译的日益职业化,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服务伦理或再现伦理为借口使翻译活动不受其他伦理的制约;以基于规范的伦理为指导原则的翻译活动在满足了特定文化期待的同时有时也难免会对原文及原文作者施加暴力……因此,在此四大模式下译者需要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截然不同的[17]。
再现伦理体现了原文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译文作为原文的替代品和表征符号应该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基本特征。而译者作为原文作者的代言人,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其职责不仅是忠于原文和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还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模仿原文作者的风格和笔调,最大程度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展现原文的真实面目和风格。这一思想与异化翻译尽量保留源语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传统,在译文中突出源语异国情调的想法不谋而合。
服务伦理则认为委托人,即译文的使用者才是上帝。在理想的情况下,翻译的委托人将包含有翻译目的、目标对象、场合、媒介即译文的预期功能等信息的详细翻译纲要明确提供给译者。译者在遵循翻译纲要的前提下,只要可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其行为便可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虽然还是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已经摆脱原文高于一切的思想束缚,可以根据客户的意愿和自己的喜好对原文进行随意的处置。这一思想为归化翻译提供了伦理学的依据。译文应该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最贴近自然对等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以唤起原文在目的语读者中的共鸣,实现动态的对等。
交际伦理认为译者是促进文化交流沟通的使者,在翻译中处于相对的主导地位。这一伦理模式突出了译者的重要性和翻译参与者的平等性。在翻译中译者需要在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三方平等的前提下帮助完成原文和译文的平等对话,促成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相互理解。在此过程中,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都是有思想、有情绪的主体,并且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此时的译文既不应该是晦涩难懂,甚至佶屈聱牙的异化翻译的产物,也不应当以纯粹随心所欲的归化翻译为目标,而是源语和目的语、作者和读者之间跨文化、跨语言的沟通交流。因此,交际伦理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模式,否定了归化和异化非此即彼的翻译原则。译者所要做到的伦理上的“忠诚”指的是位于“交互文化空间”里的翻译职业,而非单纯的源语或目的语文化。
基于规范的伦理认为译者受到规范的约束。该伦理模式强调的是译文需要符合目标语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期待。在此准则之下,译者要努力让译文符合目标语的各种规范就必须做到:首先,译文要清晰可读;其次,译文与原文需保持适当的关联性,即译文必须真实地源自原文;再次,促进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使双方达成理解;最后,兼顾交际各方的利益以取得多方信任。由此可以看出,规范的翻译伦理往往也会导致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是一种与异域文化和语言密切相关的语际转换活动,为了满足对异域语言文化部熟悉的读者的期望,促进其与原文作者的交流,译者往往会选择将异域文化向目标语文化拉近,以目标语读者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翻译原文,以使读者对译者产生信任。
切斯特曼的四大伦理模式对译者责任和使命的不同定位决定了在不同情境下译者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根据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等几大重要职责。这些职责交织在一起,对译者形成一个“张力网”,规范、制约、平衡着译者的翻译活动。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综合文本性质、翻译目的、社会文化规范、读者对象及职业道德等因素,来决定自己的取舍、翻译策略和方法[18]。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常用的翻译策略,在不同的伦理模式下各有侧重,其使用是一个译者根据具体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等因素自觉选择的过程,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存在于译文之中[19]。
5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伦理模式必然会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切斯特曼对于翻译伦理模式的分类反映了翻译中所存在的不同的伦理价值,他所论及的几大伦理模式也有各自不同的适应范围。因此,由于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交流背景、翻译目的及文本性质的巨大差异,翻译伦理的标准永远不会是固定、单一的。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交流背景和翻译实践中应该灵活使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好地实现翻译中的各种伦理价值。
[1]VENUTI L.The translaters’invisibility[M].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5:20.
[2] SCHULTE R,BUGUENET J.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42.
[3]VENUTI L.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London:Routledge,1998:11.
[4]SHUTTLEWORTH M,COWIE 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St Jerome,1997:43-44.
[5]NIDAE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59.
[6]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58-64.
[7]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8]郑海凌.译语的异化与优化[J].中国翻译,2001(3):3-7.
[9]孟志刚.论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的辩证统一[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82-84.
[10] BERMAN A.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C]//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285-286.
[11]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272.
[12]汤君.翻译伦理的理论审视[J].外国语,2007(4):57-64.
[13]祝朝伟.译者职责的翻译伦理解读[J].外国语文,2010(6):77-82.
[14]许钧.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M].张柏然,许钧,译.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29.
[15] CHESTERMAN A.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C]//Anthony Pym(ed).The Return to Ethics,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1:139.
[16]PYMA.Pour une ethique du traducteur[M].Arto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rtois,1997:38-41.
[17]申迎丽,仝亚辉.翻译伦理问题的回归——由《译者》特刊之《回归到伦理问题》出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3):94-99.
[18]孙致礼.译者的职责[J].中国翻译,2007(4):7-10.
[19]訾晓红.归化和异化:可以调和的矛盾[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12):11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