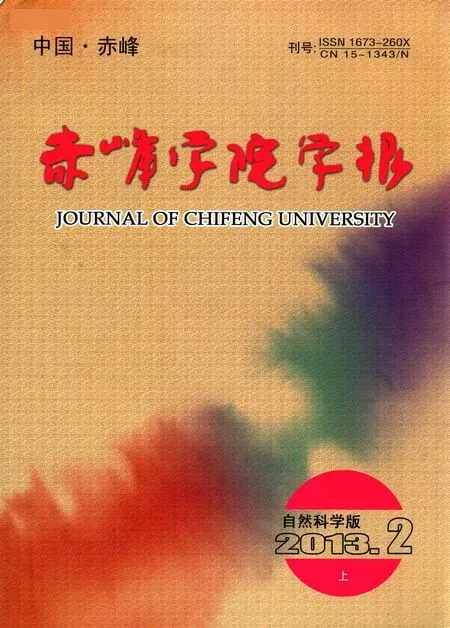社会、学校“二元”空间的体育诉求与实现
盛洪涛,李 洋
(赤峰学院 体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源引自西方的体育,在我国发展近五十余年,其理论体系的更迭与丰满,使得体育在我国现实语境下已初具雏形.无论是宏观的体育文化、体育与其他体系的耦合与分割,还是体育教学理念、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甚至教学方式、教学规范与教学管理方面,均以走向理性的发展路径.然而,当人们窃喜当下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体育在社会与学校中所暴露出的不足与缺陷是难以回避的,也是不得不进行言语与质疑的.
1 体育与个体的互动关系
1.1 体育的存在价值
体育是对人体生理机能的改善与提高,是对精神意志的规训与调节,是使个体进行社会化延展的中介手段,通过体育过程中个体的参与,在群体性游戏与技能的实践中获得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与合理的对抗,是“野蛮”体育精神的理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体的能量与意志意向的宣泄和表述,体育推展的过程中,体育场所为其体育行为提供可操作的空间,是表达自我的空间,是与他人进行配合协同与对抗的空间,在实现生命个体心肺的锻炼,在生理指标获得强化与提升的过程中,渐次的使个体精神层面获得创生性积累.在对抗外界环境、对抗自身、对抗其他个体的运动中获得快乐感、成功感,从而进一步强化对某种特定项目的兴趣.因此,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内获得对某个项目产生强烈的征服欲与获得感,项目以其技艺纯熟的无止境的态势使个体对某项的习得与提升一直处于动态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使个体处于一直不断的追求与探索的过程中.
1.2 个体生命力的彰显——“野蛮”体育精神
言说生命力的今天,个体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是一直无法绕开的主旋律话题.生命力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而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中,更加侧重于显性与积极方面,而隐晦与消极则为人们所回避.事实上,生命的逻辑起点相对诸多个体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为生命力的展现而服务.但是,在个体存在于社会中,经历迥异社会处境的洗礼、道德洗澡与仪式规则的反馈性渗透后,生命的表现则呈现出各种态势.在而对异质性个体差异存在的群体,体育成为缓冲剂,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出现,也成为调整精神与心理的安全阀.体育的存在,使得个体生命的潜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激发.通过不同的体育项目,对身体最原始的“野蛮”进行合理的调动与训导,使其在规则框架的控制下,实现精神上的满足,使个体在进行能量的自我消费的过程中,获得“身体资本的再生”.
2 社会体育范畴下“主”“次”体育的争夺
2.1 现代社会“群体”概念的质变
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的分类,已不再是学者关注的话题,然而,纵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也难以摆脱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层差与等级的出现.其中,自然免不了存在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纵观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士、农、工、商为社会所认可为主流群体,即所谓的“良民”.而其他个体而被归结为边缘群体,而在今天,边缘群体的概念有着质的变化,不再存在无权利的“贱民”,而更加强调的是经济上、情感上、身体上的弱势群体和部分为生存而挣扎的社会阶层.对于体育的参与来说,更加注重的是身体上的弱势群体和精神性弱势群体.
2.2 “主”与“边”的参与差异
城市化的进程,交通的便捷,失去土地的农民工或无业人员的跨地域的垂直与横向流动,使得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的相互影响更为频繁.以城区为中心的周边地带群体的体育意识也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边缘群体的体育也主动依附或被动牵引于主流社会的体育意识形态中.经济上的弱势导致体育行为的参与被强加于经济的控制之下,而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因素、时间因素等方面的限制,而出现选择性差异.实际上,体育本身并无等级差异.然而,在推展的过程中,则表现为主流社会所热衷与边缘社会所热宠,所谓的“贵族运动”与“贫民运动”,也使得从体育项目本身上而言,分为“主流”与“支流”.边缘群体更加倾注于简便、经济、生活相关或实用较强的运动项目,其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更加直接或健身、或娱乐、而与主流群体以交友、以炫耀为目的的运动参与有着质的区别.
2.3 边缘群体的体育实现的诉求
边缘群体的出现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唯有边缘群体逐层过渡为主流群体,才最终实现群体整体结构的均衡.群体的主流与边缘差异递减,才能实现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动态运转.边缘群体在成为群落构成中,是不可缺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权化、时间化日益渗透与控制个体身体的今天,体育对个体的影响已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性影响,而是影响其身心双向的重要手段.在体育实现的过程中,每个个体在特定空间的构成与动态迁移和变化,使得个体体育权利在国家意志和社会规范中得以实现,其价值的体现更多是体现主流社会的整个意识和价值本位所在.无论是国家本位,还是社会本位,或者是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二者合体的集中体现.体育与个体的关系都扮演着双赢的角色,体育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个体给予体育自身提供不断的反馈与修正.在此过程中,边缘群体体育实现则是更为重要.由于边缘群体的体育的实现才能使体育效应实现到最基层面,而摆脱了单一为主流社会所服务的意识,削弱体育国家意志化的“霸权”,更多的以个人的健康为起点和终点.
3 学校空间的体育行为的执行
3.1 学生——体育文化空间的“游离受体”
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从生产、消费、耦合、表征等几个方面表现为一个整体,其核心要素在于个体的存在,使得体育文化形成以空间和人物为支撑点的多维立体.对于学生来说,作为文化的继承人,作为体育文化的接纳者和开拓者.大多数情况,存在着主动吸收与被动接受.在体育教学的影响下,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心理性的训诫与对规则的尝试和默许都是难以回避的,纵使不予以认同,也会在学生生个体中留下记忆印痕.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来自风格各异的体育教学,来自不同项目的影响与体育教师对身体与空间的格式化的训导.在年龄和年级的递增中,所获得的体育相关教学与对体育系统知识的了解呈现出质的跨越,甚至随着个体升学而产生的地域上变更,而使个体在体育文化的认知呈现共性化和本土化的趋势.纵使统一的教学大纲,但由于对体育教学大纲的解读上差异和体育教学方法上的不同,导致体育教学效果的呈现本土化特征.也因为本土化的教学的存在,不同的传承体与受体的差异,则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体育特征,甚至出现与整体结构的冲突的现象.
3.2 体育教学空间给予学生个性的期待
体育教学的逻辑起点是对生命个体身心自由的追求,在个体获得快乐感的同时,使精神意志获得良性的影响,体育教学更加注重的是空间的存在性.在当下学校体育教学更加为人们所认同为“体育教学”.事实上,体育教学也并非专指学校体育教学.体育教学空间被视为场域论之范畴,这是物理角度的划分.体育教学空间远不止于此,体育教学空间所指的是动态的和静态空间的结合,是时间上的延续的教学和场地的更替使用的结合.体育教学的开始是局部场所由于体育教学的存在而瞬间产生爆发性的“活跃”,同时,空间也会因为体育教学的结束,而回归到静谧.良好的教学效果是体育从事者的心理期待,对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国家意志的实现,是社会学界的体育教学开展的现实期待,而体育教学过程中的获得感与成就感则是参与体育教学的个体的最直接的效应期待.
3.3 学生个体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学生个体的能动性已为现代教学人员所认可,教学者在强调主导性的同时,也强调学生个体的特征,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学生个体的需求使得教学理念一度改革.快乐体育、阳光体育、绿色体育的教学理念的标签式的提出,则是应这生个体需求而出发的教学观念.大到体育理念,小到体育教学方法和教学项目的开展,都与学生个体的需求有着不可缺少的关系.铅球、标枪在田径课上的消失,单杠、双杠等体操动作的弱化则是最好的明证.然而,强调学生个体需求的同时,大多数教学专家和学者也关注到学生个体在某些方面上表现的不足.对总体体育发展态势表现出质疑与忧虑.如何使体育教学既满足个体的需求,又适应国家、社会的发展则成为又一轮讨论的新的焦点.
4 结论
体育是体态语言的教授与训导,是示范和讲解下形成的肌肉记忆与精神印痕.体育教学在使学生个体“野蛮精神”得到合理的诉求的同时,使得个体的生命张力得以实现,无论是对社会个体,还是学生个体身心的发展和生命力的维系,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个体对体育教学理念、方法以及项目的设置产生一系列的积极的影响.
〔1〕沈建华.社区体育发展模式[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
〔2〕莫小农,林敬松.论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之结合[J].体育科技,2001(4).
〔3〕高美琼,李洋.蒙古族传统体育民间传承社会学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11):53.
〔4〕李洋,等.蒙古族传统体育民间沿袭转型学校传承之社会学考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