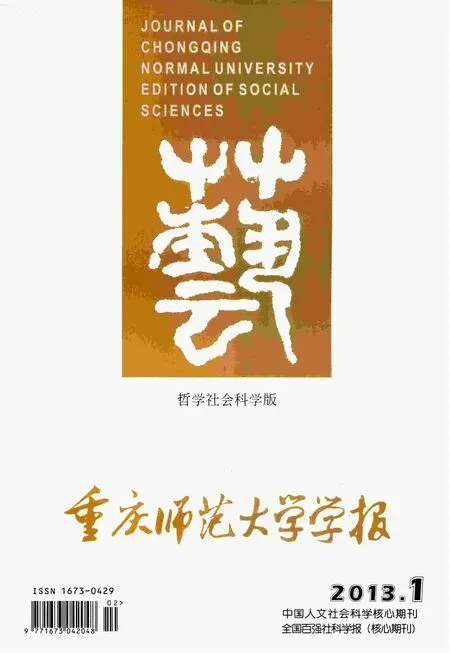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张世友
(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重庆401331)
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西接云南,北依四川,东与湖北、湖南为邻,南与贵州南部及广西相连,跨越贵州、云南、湖北、重庆三省一市,幅员面积87920平方公里,世代杂居着苗、土家、布依、侗、彝、白、哈尼等30余种少数民族。[1]公元前221年,秦王完成六合一扫,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经商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这不仅导致当地原始古国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遭受冲击,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被打破,而且推动了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改造,进而促成了当地的政治一体化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一、仕宦委派与民族政治的一统
秦汉伊始,天下一统的格局促成了封建王朝对全国经略的重新考虑。秦朝虽短且二世而亡,但仍然积极经略乌江流域,遂有常頞略通之举。“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2](卷116《西南夷列传》)西汉以降,朝廷起初对边疆经略的重点只放在西北和北方,但随着国力的强盛和征讨南越的战略需要,到汉武帝时期开始有了针对西南夷地区委派仕宦的经营之举。据蓝勇先生考证,两汉时期当时的四川郡守共60人,其中外籍郡守40人,川籍郡守20人。外籍郡守中有河南籍18人、陕甘籍10人、安徽籍4人、浙江籍1人、山东籍3人、江苏籍2人、河北籍1人、贵州籍1人,其中,河南、陕甘、山东、河北籍占33人之多,明显以北方籍官吏为主,而河南和陕西籍占绝大多数。蜀郡太守和广汉郡太守除3人外,几乎全为外籍官吏;20名巴郡太守中10人为外地籍,10人为本地籍;越雟郡、犍为郡太守中本地籍有7人,外地籍有4人。[3](22-23)又据黎小龙先生考证,两汉时在西南相对稳定的巴、蜀、广汉、犍为、越巂、牂牁、益州、永昌八郡各地任职的太守,其北部四川盆地盆中、盆西蜀及广汉二郡可考籍贯郡守31人,本土籍人士仅3人,其余28人全来自北方中原;盆东巴郡可考籍贯郡守21人(次),其中北方中原籍贯10人(次),西南籍贯11人(次),各占一半。中部今川滇黔交界处的犍为、越巂二郡可考籍贯郡守13人(次),来自北方中原者锐减为4人,其余9人中1人为本地籍,8人为北部巴蜀人士。南部今滇黔地区的益州、永昌、牂牁三郡太守12人(次),除1人为原属巴蜀地区的汉中籍外,其余全为巴蜀籍人士。[4]这种用人状况和官员籍贯的分布规律,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西南开发中北人治南政策的鲜明特征,也体现了两汉时期以川北、成都平原为基础向东和向南开发分区推进的趋势。虽然这些任官不一定长居于乌江流域,但定有不少在当地娶妻生子,安居乐业。
秦汉时期的仕宦委派,构成了乌江流域地方行政机构的政治核心。在他们的影响下,乌江流域各族人民长期保持着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上通下达,用实实在在的自觉行动反复印证着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共同支持着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及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固化着中国西南边疆的版图和维护着祖国的政治一统。如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间,时值公孙述据蜀(25~36年),造成分裂,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广汉梓潼人文齐做益州郡太守,不仅团结益州郡的“夷”、汉移民,“甚得其和”,还发动“夷”、汉移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而且积极招抚流散的移民及当地民族群众,派人到内地去和东汉光武帝刘秀联系,直到公孙述的割据势力被打垮时,益州郡内各民族地区“夷”、汉移民始终团结一致,始终不曾发生任何动乱而归于统一。与文齐同时,在牂柯郡,郡功曹谢暹也团结当地“夷”族及汉族移民中的龙、傅、尹、董等姓“保境为汉”,同样抵制了公孙述的割据势力,还派人从牂牁江水路往番禺(今广州),再转到内地去与东汉光武帝联系,保持住了牂牁郡内安定统一的局面。[5]此外,更有东汉明帝时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被任为永昌太守。郑纯治理永昌也一如既往,“夷俗安之”,最后卒于任上。同时期的益州刺史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吸引了今川西、滇北地区“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的白狼、槃木、唐等百余国130余万户、600余万人,“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其中,白狼王为表“慕化归义”之心而作诗三章(后人称为《白狼歌诗》),“襁负老幼,若归慈母”,穿越崎岖险峻的邛来大山转献于朝,留下了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6]
二、募民实边与民族经济的推动
秦汉时期,为强化西南边疆的统治,封建统治者积极推行“募豪民田南夷”的政策,即大量招募“豪民”到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举办屯务,由他们招募民众进行垦殖屯种,将所产粮食交给县官,经费由国库开支。因当时经营西南夷的大本营主要为四川,故豪民多为三蜀大姓,而屯种之人除巴蜀农民和游民外,还有罪徒。《史记·平准书》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2](卷30《平准书》)由于官员士卒及修路民夫所需粮用浩大,巴蜀难以供给,只好招募内地商人富豪出资到西南屯田,将所收谷物上缴当地官府,再到内地府库领取粮款。而具体从事屯田垦殖者,则是应募而来的大量内地农民。当时屯田的组织形式为部曲,它是边郡特有的军制。《后汉书》卷一一四《百官志一》云:“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军营有五部,每部有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每曲有军侯一人。曲下有屯,每屯有屯长一人。”到东汉,因战乱关系,游离失所的农民投靠豪强地主寻求保护,而豪强地主则将农民作为家丁,遂演变为私家部曲,豪强与部曲之间相处为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封建关系。[7]
此时乌江流域募民的具体数量史无明载,但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及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有关部分人口资料的研究和前后对比中可窥其大概。据《汉书·地理志八》和《后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今乌江流域境内牂牁郡,西汉时下辖17县153 360人,到东汉时虽辖地减为16县,但人口却猛增至267 253人。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所分益州而置设的永昌郡,仅辖8县却拥有人口1 897 344人,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第一大郡。应该说,这种人口数量的变化,既反映了官府对当地民族人口控制的加强而使编户扩大,又说明了外地移民户口的不断增多。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孝武(于永昌)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居之”,就直接表明永昌郡人口的空前增长,定当包含着诸多类似于此种来自封建王朝有组织的外地迁徙的人口类型。加之两汉时的郡夷史料中常见有区分汉人与当地民族的“郡兵”、“郡民”及“夷汉”、“民夷”、“夷民”、“吏民”、“夷夏”之类的记载,也同样说明了外来移民已有相当数量,并在当地的民族构成及社会活动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6]
秦汉政府的“募豪民田南夷”,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守边备塞”,它更多地具有开荒辟土、发展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发展程度低下且地广人稀的乌江流域等西南夷地区,内地移民的大量迁入,必然加快当地人口增长的步伐,助推当地人口素质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增加官府的纳税对象,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这尤其表现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募民实边政策的施行,不但减少了王朝运送给养,稳定戍卒,而且巩固了边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二是通过募民实边将巴蜀一带发展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乌江流域,加快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在乌江流域发掘清理的汉墓中多有铁器,仅可乐汉墓就出土120余件,其中生产工具有锸、铲、斧、斤、凿、锥、锤、钻、剪、夹等68件,兵器有刀、剑、矛、镞等41件。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铁器逐渐推广,主要用于生产工具和兵器制造,在工效上比青铜器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农具和手工工具,有的农具上直接铸有“蜀郡”、“成都”之类铭文。三是募民实边形成了比原先更高层次的生产关系,发展成为封建领主所有制。四是募民实边造成了以军事为后盾,有较大经济实力的社会势力,对以后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7]据《三国志·蜀书·霍峻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等记载: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豪民霍峻及其子霍弋先后领永昌、建宁太守;弋卒,子袭职,领其兵。霍弋孙霍彪继承祖业,东晋时亦官越巂、建宁太守。又据《爨龙颜碑》所载,碑主爨龙颜本为宋文帝时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汉末时“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后迁于南中,任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及宁州刺史等职。爨氏世代相袭,在中原内乱之时成为南中地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一直到唐代中叶南诏兴起,爨氏一门在南中地区割据称雄历时长达三百多年。[6]
三、罪徙流迁与民族文化的碰撞
西南边疆的乌江流域,地理位置偏僻,生活条件恶劣,自然成为秦汉王朝强迫迁徙各种罪人的理想之地。据史料记载,秦汉之际罪犯被流迁至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几成常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有记:始皇三十三年(前215年),“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谴戍。”《汉书》卷39《萧何传》亦云:“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又载:汉开益州郡治滇池,地广人稀,“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三国志》卷43《蜀书·吕凯传》裴注引东晋孙盛《蜀世谱》亦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除了这些记载,甚至更有部分徙迁流官后裔最后演化成为了当地豪族大姓的文献记叙。如曾与高祖刘邦同时起兵,楚汉战争中有怨离去,而后复归的江苏沛县人雍齿,刘邦称帝后为示宽宏,将其封到四川什邡为侯。武帝时雍氏后人被剥夺爵位并同时谪迁入滇黔,及至东汉末年,其后代雍闿已经“恩信著于南土”。[8](卷41《蜀书·张裔传》)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乌江流域考古发现中,也提供了诸多秦汉罪徙流迁的证据。如1978年,贵州威宁县中水区中和乡梨园村汉墓,出土随葬品铜制“张光私印”一件、五铢钱一枚,经学者考证,墓主张光即为西汉元帝时曾参与宫廷斗争失败后被流放之人。[9]1987年,又在云南保山龙王塘一房屋基址中,出土一批板瓦、滴水、瓦当、砖、铁钉等,砖侧有各种花纹及“五铢”、“五王”、“中平四年吉”字样。[10](240)“中平”是历史上东汉灵帝用过的年号,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这说明武帝以后不同类型的移民仍在以各种方式进入云贵地区。[6]
秦汉时期被流放到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的内地奸豪,大多家学渊源深厚,自身学识渊博,本是书香子弟。他们陆续移入乌江流域以后,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逐渐融入当地人群,并通过各种途径散播中原儒家文化,从而使当地的民族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特别是在流放官员带来的外来文化的熏陶下,乌江流域一些地区的风俗习尚发生变化而不断接近内地。如朱提地区,“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12](卷4《南中志》)。犍为郡,“士多仁孝,女性贞专”[12](卷3《蜀志》)。越巂地区,“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11](卷19《恢国篇》)。不仅如此,有的移民后裔甚至主动到中原发达地区拜师求学,以推动家乡文化快速发展。如东汉恒帝时,牂牁郡“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学经书、图谶。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3](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据王燕玉考证[14],尹珍系汉武帝时期“募豪民田南夷”时从今川西迁入,生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卒于桓帝延熙五年(162年)。和帝年间(89~105年),他深感家乡教育落后,遂跋山涉水远赴洛阳,师从经学大师许慎和应奉,刻苦研习儒家经典,学业精进,成为东汉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尹珍学成后,回到家乡牂牁郡,在鄨县各地(今贵州绥阳、正安一带)创办学馆,讲学授徒,传授中原文化。另据1901年云南昭通发现的《孟孝琚碑》的记叙,东汉中期朱提人孟孝琚,12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15](96)。作为朱提郡众多移民大姓之一,孟孝琚自小学习儒学,婚前先聘,死于外地而由族人归葬祖茔。碑文中并称“孔子大圣”等,表明孟氏家族十分熟悉儒家文化并在婚丧方面遵循内地习俗,也由此证明了秦汉时中原封建文化在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的流行,及其与外来移民的密切联系。[6]
四、戍卒驻留与民族争斗的频繁
中原封建王朝在乌江流域的用兵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秦楚之间就展开了对黔中的激烈争夺。据《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所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说明,楚为巩固后防,扩充实力,遂让庄蹻一路西征,以至远达滇地。尽管有人认为“在秦国设立黔中郡以前不久,楚将庄蹻入滇经过夜郎地区,可能因为只是路过,所以至今未见楚文化的痕迹”[16](114),但并不足以否认乌江流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其后,公元前316年,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又率兵进军巴、蜀,首先攻灭了蜀国,并将其改为蜀郡,直接纳入秦国直辖统治的郡县制体系;接着“(张)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12](卷1《巴志》);而后积极进军楚国,秦武王三年(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12](卷3《蜀志》)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 280 年),“司马错发陇西、巴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前277 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2](卷5《秦本纪》)
秦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黔中争夺战,必然驻留大量兵士于其地,成为实实在在的军事移民。1972年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被发现,经过四川省、重庆市和涪陵的文物考古部门于1972年、1983年、1984年、1993年、2002年5次考古发掘,清理战国巴人墓葬22座,出土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文物600余件。其中1972年10月涪陵小田溪3号墓出土的战国铭文铜戈,被认定为军事移民留下的中原文化遗物。[17](380-381)到两汉时,为进一步将今川西南、云贵等乌江流域纳入封建朝廷的版图,王朝政府更是不惜广开驿道和大量用兵。首先是建元间(前140~前135年)唐蒙奉命开南夷道,“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今云南曲靖)二千余里”[18](卷33《江水一》);其后是司马相如略定西夷后,并“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2](卷117《司马相如列传》);最后是汉武帝时再开永昌道,“通博南山,度兰沧水、氵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12](卷1《南中志》),将今滇西永平、保山和施甸一带联通。这些驿道的相继开凿,沟通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使其成为当时中原和巴蜀人民进入滇黔地区的重要路线;而当中的部分修路兵卒事后的就地安置,亦无疑成了当地外地移民的重要来源。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元光五年(前130年),汉遣郎中将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至夜郎及旁小邑,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乃以为犍为郡,并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同时,为通西南夷,汉又发蜀、巴、汉中、广汉四郡吏卒数万人治道路。治道数年,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而道不通,加之“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于是元朔三年(前126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2](卷116《西南夷列传》)又元狩六年(前 122 年),因受张骞对出使大夏后的见闻介绍刺激,汉武帝为寻求通往大夏近道而始通西南滇国,又陆续在西南夷地区设置越巂(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益州(治今云南晋宁东北)、牂牁(治今贵州凯里西北)等郡。加上之前已在当地设置的犍为郡及东汉时所设的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朱提(治今云南昭通)二郡,汉朝时期的势力已基本上覆盖了今乌江流域川西南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地区。而这些地区的郡县辖地必然驻有大量朝廷从内地委派的太守、县令等属官和若干戍守兵士。
秦汉王朝在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的强制征伐和郡县置设,激起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一些戍卒军官利用自己手中的优势和特权,霸占资源,横征强取,奴役和剥削当地人民,多次激化阶级矛盾。据史料记载,从封建王朝经营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之始,当地世居民族与封建王朝的对抗就接连不断。如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年)前后,朝廷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犍为郡和邛笮地区的1都尉10余县,紧接着便征发巴蜀四郡士卒修西南夷道,由于“戍转相饷”骚扰了地方,于是导致了西南夷的规模反抗。又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郡廉头、姑缯,牂牁郡谈指、同并等24邑皆反,杀长吏。汉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击破之。四年(前83年),益州姑缯、叶榆复反,杀益州太守。吕辟胡与战,官兵死者4000余人。五年(前 82 年),汉再遣军正王平、大鸿胪田广明将兵击破之,前后首虏 50000 余级。[2](卷116《西南夷列传》)在这次镇压益州民族的反抗中,牂牁郡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从征有功,被立为句町王。但王莽代汉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贬句町王邯为侯”,“邯怨恨,牂牁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由是,天风元年(14 年)“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19](卷95《西南夷传》)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击之,“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19](卷99《王莽传》)。由于朝廷多次镇压无果,最后不得不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19](卷95《西南夷传》)。再往后,还有安帝元初五年(118年),由于“郡县赋敛烦数”,“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119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叶榆击之……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13](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其实都是秦汉封建王朝因为戍卒驻留而于乌江流域等西南地区引发的夷汉之间的严重摩擦和残酷争斗。
综合而论,秦汉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在秦汉的统治下,包括乌江流域在内的西南边疆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秦汉以来,源自乌江流域之外并以各种不同方式汇集至此的外来移民,不仅给地处西南边陲的蒙昧地区引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而且把内地先进的政治思想意识、生产生活方式及经济发展理念移植到新开拓的区域。从这方面说,各种外来移民不仅通过生产技术改进,加速了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通过民族混居杂处,促进了本地各民族间的融会互动,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了解。[20]当然,这一时期的部分驻戍移民因资源争夺等原因而引发夷汉对抗和冲突,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事实。
[1] 张世友.论历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济推动[J].贵州民族研究,2011,(6).
[2] [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3]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 黎小龙.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6).
[5] 张世友.论历代移民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护佑[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6).
[6] 古永继.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
[7] 曾超.秦汉王朝对乌江流域的经略与治政[J].铜仁学院学报,2010,(1).
[8] [晋]陈寿.三国志[M].中华书局,1959.
[9] 何凤桐.张光徙边丛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4).
[10] 汪宁生.云南考古[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11] [东汉]王充.论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 [晋]常璩.华阳国志[M].商务印书馆,1958.
[1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14] 王燕玉.尹珍身世籍贯和遗迹传说[J].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创刊号.
[15]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6] 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
[17] 涪陵辞典编纂委员会.涪陵辞典[M].重庆出版社,2003.
[18]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巴蜀书社,1985.
[19] [东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
[20] 张世友.明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