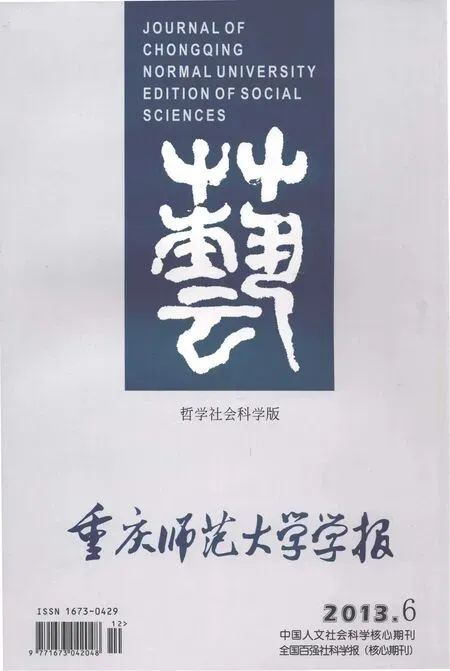论“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以新时期以来的译介为例
王有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变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英美“新批评”的引进和接受。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在引进和接受“新批评”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观念至上”的倾向。这一倾向,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接受和运用。
所谓“观念至上”,是指我们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中,在理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欣赏等诸多关系方面,人为地、不适当地拔高文学理论的地位,以为文学理论可以指导文学创作、可以指导文学批评,更可以指导文学欣赏。这一观念,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并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理论生活。例如,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先行”,文学批评活动中的“引经据典”和对一些新潮理论的生搬硬套等等,都是“观念至上”的不同表现。
新时期以来,国内“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主要表现为:过度重视对“新批评”批评理论的译介,有意无意忽略了其批评实践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新批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引进到中国,于40年代受到高度关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时期以来,“新批评”开始了第二轮在中国的“旅行”,并充当了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入驻中国的“急先锋”。
拒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14种“新批评”代表性著述陆续以中译本的形式与大陆读者见面,它们分别是:韦勒克与奥·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84)、布鲁克斯与潘·沃伦编著的《小说鉴赏》(1986)、布鲁克斯与维姆萨特合著的《西洋文学批评史》(1987)、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1988)、史亮编选的《新批评》(1989)、韦勒克著的《批评的诸种概念》(1988)、艾略特著的《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艾略特著的《基督教与文化》(1989)、瑞恰慈著的《文学批评原理》(1992)、艾略特著的《艾略特文学论文选》(1994)、燕卜荪著的《朦胧的七种类型》(1996)、兰色姆著的《新批评》(2006)、布鲁克斯著的《精致的瓮》(2008)以及艾略特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2012)等。上述14种“新批评”译作中,影响最大、引用率最高的当属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2001年,该书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
可以看出,这14种译本里面,“新批评”的批评理论占据了11种之多,而“新批评”的实践范例,只有《小说鉴赏》(1986)、《朦胧的七种类型》(1996)和《精致的瓮》(2008)3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新批评”赢得重大声誉,也是其“细读式批评”中影响最大的批评实践——《理解诗歌》,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整中译本。
“新批评”在中国已有80余年的历史,但客观地说,它的实际影响一直不大。“新批评”方法,还没有真正融入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更多是“标签式”的概括,对其批评理论缺乏深刻理解,对其批评实践更是一知半解。“新批评”研究专家赵毅衡著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批评的研究在中国向纵深发展,渐渐融入中国文论的基础。在当今学界推进批评理论的努力中,重估新批评在中国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1]青年学者姜飞也认为:“新批评正在切实地影响中国文论,但是,只有在经历了中国学者深刻的研究、领会和改造之后,只有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教育开始贯彻其精神之后,新批评才能真正参与建构中国文论的新秩序。”[2]对此,有学者解释说,“新批评”在中国虽然传播时间早、时间跨度长,但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之间存在着的异质性,决定了其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遇和对中国文论仍未产生过积极而重要的影响。[3]这种分析,充分注意到了“新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质性”关系,似乎可以解释“新批评”在中国的边缘化命运。但笔者以为,“新批评”在中国的边缘化命运,还可以从新时期以来“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里得到解释。新时期的“新批评”译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行为和思想,而是要具体体现为对“新批评”经典文本的选择与编排(侧重于理论文本还是实践文本),也体现为译介者和引进者的学术旨趣(侧重于对其理论观念的撒播,还是对于中国文学问题的思考),更体现了我们对于原有理论的态度(是证明外来理论的正确性,还是对其进行创造性发挥)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显示了译介者、研究者的理论旨趣和学术追求。也许,正是这些主观原因,才可以从根本上解释,“新批评”何以在中国长期被边缘化。
我的观点是,“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才是导致其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遇和对中国文论仍未产生过积极而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
新时期以来对“新批评”的引进,赵毅衡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赵编《“新批评”文集》在介绍“新批评”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方面,国内无出其右者。正是赵毅衡先生编选的《“新批评”文集》(选文29篇)一书,深刻地影响了国内“新批评”研究的基本走向与研究格局。史亮编选的“新批评”论文集《新批评》(选文11篇)一书,也值得注意。
必须指出,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着的“观念至上”倾向,无论是赵编《“新批评”文集》还是史编《新批评》,在文本的选择方面,都明显存在着选译新批评理论文本居多、批评实践文本偏少的倾向。《“新批评”文集》一书共收入“新批评”代表性文章29篇,其中“新批评派的细读式批评”仅有5篇,不到选文总数的五分之一;史编《新批评》一书,收入“新批评”代表性文章11篇,其中批评理论8篇,批评实践仅3篇。而且,两书选译的的批评文本(无论是小说批评文本,还是诗歌批评文本),往往又残缺不全。
英文原版中,布鲁克斯、沃伦编著的《理解诗歌》和《小说鉴赏》两本书,就体例而言,特色极为鲜明:两书的每一章均有前言,各章又选有若干经典文本,每一个文本之后均有分析文字。这些分析性文字,在《理解诗歌》中,是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不带标题的分析性文字,二是“问题”(Questions);在《小说鉴赏》所选小说文本后面,也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不带标题的分析性文字(DISCUSSION),二是若干道思考题。可以看出,在《理解诗歌》和《小说鉴赏》中,布鲁克斯、沃伦都特别向读者、也是“向自己提出一些诱导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有长有短,突出反映了布鲁克斯、沃伦在文本批评中的“问题意识”;在他们在那里,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充分体现了“新批评”实践家的批评观念、批评方法,体现了他们对于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关系的认真思考和严肃态度,甚至还彰显了他们何以将理论原则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方法的具体步骤。布鲁克斯和沃伦曾谈及,为什么在小说文本分析的过程中,设计了那么多数量不等、容量也大小不一的“问题”。他们说,“这些问题不应当只涉及小说的要旨,而且要涉及到它所采用的办法,因为,我们早已了解,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它们往往都是对同一事物,也就是对小说本身要看到的一些方面。不过,除此之外,对于人物和情节,也有必要力求运用想象力来感受。”[4](484)但非常遗憾的是,前文提到的两个选本——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和史亮编的《新批评》,只保留了其直接分析性的文字,却不约而同地删去了布鲁克斯、沃伦批评实践中最有特色的“问题”和“讨论”部分,甚至正文中提出的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删去了。比如,赵毅衡《“新批评”文集》所选译的《克里奥帕特拉的悲悼》(赵毅衡译)和《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万培德译)两篇文章,布鲁克斯、沃伦原文提出的四个问题均未译出;史亮《新批评》所选译的《论〈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论〈杀人者〉》等,对原作者提出的三个问题,也未译出。
先看布鲁克斯、沃伦在分析《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时提出的问题:
1.如果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写这篇小说,将会有何种难处?
2.爱米丽小姐选中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作为自己的情人,为什么说这种举动是意味深长的?
3.就其一般的象征性意义,回顾一下《年轻的布朗大爷》和《杀手》这两篇作品,能不能说现在这篇小说也像那两篇一样,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即对当前社会提出了一种象征性的批评?若是,你又如何对此加以论证?[4](285)这里,第一个问题,是从叙事学角度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设置表明,在布鲁克斯、沃伦看来,小说作品视角的选取,对小说意义的表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影响了意义的设定与主题的传达;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小说细节暗含的爱米丽小姐的性格及小说的主旨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采用了视野开阔的比较研究法提出的(而且,比较法一直贯穿于许多问题的思考和发问之中)。因此,就这三个问题的质量看,其提问角度之专业、研究视野之开阔,说明这三个问题的设计决非可有可无、可译可不译。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引文。下面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5首)中的一节:
哦,夏天蜂蜜般的呼吸怎能抗得住
槌打的日子的灾难性的围攻。
如果我们缺乏想象力,误解了诗人在创造意象的过程中的赋意方式,那我们得到的将是一堆毫无用处的信息。“日子”是时间、时代的转喻,正如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所指出的那样,“时间和时代又被隐喻为对一座城池的围困和攻城槌来攻击之。是什么抗得住这些攻击呢?是青春,象城池般、或城池的统治者般坚定的青春,青春还被隐喻夏天,说得更确切些是被隐喻为夏天芳醇的气息;夏季百花的芬芳之于大地正如甘甜的呼吸之于人体。这是一种以部分或附属部分来比喻全体的方法。倘若人们试图要把槌击的围攻和人的呼吸齐整地纳入一个意象中,那就会显得拥挤滞重。比喻的运动是迅速的,因此是省略的。”这段评论的要点在于:读者不要企图把孤立分散的信息生硬地塞进一个意象之中,倒是应当接受那些快速的、跳跃的和关于思想和(或)情感的暗示。
布鲁克斯、沃伦对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的悲悼》的分析中,主要讨论和比较了诗人使用和发展意象的两种方法:第一种,“诗人给的意象互相连贯,形成一个整齐的序列”,“这种方法的标记就是延续性和意象使用上的自我连贯性。”与第一种“意象使用法”的“连贯性”不同,第二种意象使用方法是创造一种“mixed metaphor”(汉译一般为“混合隐喻”,赵毅衡译为“错逆比喻”),其“主要特点在于不连续性。每个意象都靠其与思想主线的个别关联而立足。”
上述这段引文,是布鲁克斯、沃伦在分析了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的悲悼》后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共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提示读者,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的悲悼》中的意象使用方式,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5首一样,是一种“混合隐喻”或“错逆比喻”,我们不要试图把本来跳跃的、不连贯的、不同的意象硬是塞在一个意象之中。应该说,这第三个问题的设置,既进一步强调和强化了莎士比亚诗歌创作中意象使用上的“不连贯”的特点,又指出了在诗歌创作中意象使用上的不连贯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较为普遍的现象,提醒读者和批评家在分析诗歌意象时,不要一味地强调诗歌意象使用上的“自我连贯性”。
但非常遗憾的是,上述两个示例中的布鲁克斯、沃伦批评实践中最有特色的“问题”部分,国内选本的编译者却不约而同地把它们删去了。
可以说,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的“新批评”,只能说是经过了删节之后的“节本”。这样的选本(或称“节本”)造成的后果是:首先,直接影响到国内学者对“新批评”总体面貌的理解,误以为“新批评”的主要贡献是在其理论表述和批评观念上。其次,使得国内的“新批评”研究,对其理论有着浓厚兴趣,或发掘其哲学基础,或关注其“文学性”,或侧重其理论本身和各种外缘之联系等等而对“新批评”批评实践(包括诗歌批评实践和小说批评实践),缺乏应有的研究。第三,近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也颇受选本影响,编著者大多习惯于给新批评“贴标签”,并因袭了选本对“新批评”的一些误解(认为“新批评”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的文本分析被认为是一种只适合于诗歌文本的批评实践等等)。实际上,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新批评”,正是凭借其在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方面的实践,才奠定了他们在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客观地说,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的“新批评”译介取得了很大成绩。正是借助于“新批评”中译本,国内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才焕然一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才有了新的气象和活力。但译介中的不如人意也确实存在,那种“观念至上”倾向,依然影响着我们对“新批评”的译介、研究和运用。一种追新后的冲动,使得“新批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被真正吸收和消化,便被“后起”的新潮理论所覆盖。在不少人看来,“新批评”似乎已经过时了。幸运的是,仍有一批中国学者持续关注着“新批评”的译介及其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实践,赵毅衡、王富仁、孙绍振、王先霈、姜飞、张惠、胡燕春等,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但愿,他们的辛勤付出,可以换来“新批评”的真正“中国化”(或“本土化”)。
[1]赵毅衡.新中国六十年新批评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2012,(1).
[2]姜飞.英美“新批评”在中国“新时期”[J].学习与探索,2009,(5).
[3]代迅.中西文论异质性比较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4][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小说鉴赏[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5]双引号中的引文出自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2页,其余文字为引者译出,同时还参阅了布鲁克斯、沃伦《理解诗歌》一书中的相关部分。
[6]赵毅衡.克里奥帕特拉的悲悼[A].“新批评”文集[C].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