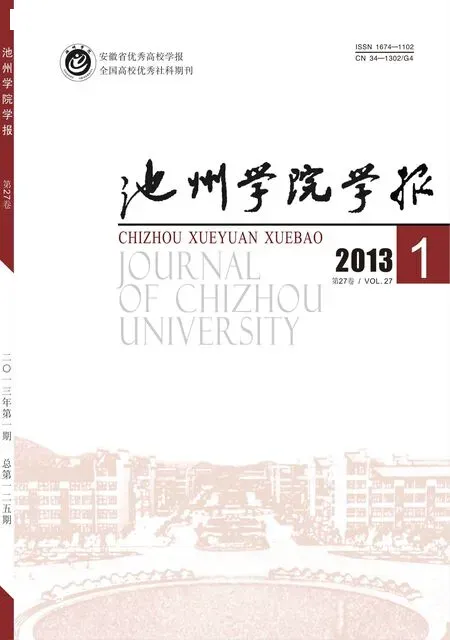困境与出路: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
黄 晖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世界文学是当下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话题,随着讨论与思考的逐渐深入,世界文学研究者更多地将着眼点集中在对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上。“世界文学史新建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倡导研究者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去看待文学史问题。进一步说,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不仅需要考察和整合各种文学事实,而且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辨的、逻辑的思考和研究。这标志着世界文学研究范式进入了其转型期——以新辩证论为思想武器,促进多元文化的互证、互补乃至互动,进而达到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的目的。
1 何为世界文学史:观念的廓清与功能的界定
何为世界文学史?其学科特性何在?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在中国学者近百年的世界文学史编写实践后提出这样的问题,颇显“小儿科”。然而一旦认识到当下中国混杂的文学史编写实践,对这些问题就不但不感到稚嫩、而且甚觉严肃了。
简言之,世界文学史就是指世界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那么,什么是人们能够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世界文学”概念呢?我们现在知道,是欧洲的学者首先提出“世界文学”这个基本概念,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建立超越世界各民族界限的世界统一体的美好蓝图,这一设想被西方的众多思想家如克罗齐和黑格尔等人所继承与发扬,进而发展成为多个领域里的“世界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歌德与马克思的所分别倡导的“世界文学”观念。
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其秘书艾克曼讨论一本中国的传奇小说时,首次运用了“世界文学”这一词汇,“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113。歌德在认真阅读了中国的传奇小说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可以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的观点。但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歌德在意识到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所可能具有的同一性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超越于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之上的标准或者说价值尺度——古希腊文化。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其实是一种文化一元论的立场,因此有学者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概念,而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2]38。
马克思对“世界文学”这一观念的论述,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名言,“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3]255。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观念,而是一个包含文艺、哲学与科学等在内的大文化概念,是植根于工业和贸易全球化物质基础上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提法的现实意义在于消解世界各民族间的隔阂,克服本民族的局限性,把世界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变成各民族人民都能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对马克思而言,“世界文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无产阶级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进而发动群众,把精神的东西变成物质的力量。也就是说,其目的是要求我们树立全球化的自觉意识,用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代替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建构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
正是在充分理解歌德和马克思所倡导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基础上,方汉文教授指出“所谓‘世界文学’就是各国文学的总和与汇集,它既包括各国文学经典名著也包括不同民族文学的历史,这些基本的文献、资料与史实,是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构成,必不可缺”[4]207。进一步说,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其目的并不是要泯灭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精神特质与审美特征,而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特定历史属性的认可、接受与研究,而世界各民族文学也只有置放在世界文学史的整体视域和总体格局之中,才有进一步彰显其民族特色的可能。
2 世界文学史建构所面临的困境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这一设想并非“空中楼阁”,它是针对我国目前的世界文学史建构的缺憾和不足而提出来的。近百年来,我国的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史建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近百年来,冠以“世界文学史”之名的书籍大量涌现,反映出学术界对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关注和热情。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此后此类著作层出不穷:1933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了李菊休、赵景深合编的 《世界文学史纲》,1937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了啸南的《世界文学史大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出版了胡仲持的 《世界文学小史》、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上册);而近年来又涌现出大量以《新编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简史》、《世界文学史纲》、《世界文学史》等等以“世界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然而稍加翻阅,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世界文学史”的编写思路与传统的“外国文学史”相比较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世界文学史”之所以写成了“外国文学史”甚至“欧洲文学史”,就是因为把“世界文学史”理解成不包括中国文学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史。根据我们的理解,一部真正意义上世界文学史绝不能把中国文学史排除在外,中国文学应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只有在这种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杂语共生模式。
(2)文学工具论所导致的文学史建构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在茅盾编写的《西洋文学通论》中,仅写实主义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尤其是在现在看来文学成就其实并不是很高的自然主义文学,用了大量的文字加以介绍。而对于同样是写实主义作家的莎士比亚,因其属于古典派,就简略地一笔带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为需要思想舆论来确保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艺创作,都被规训到主流意识形态所预设的话语体系之中,所以一些文学价值不高但却能为主流的宏大话语服务的文学作品反而被经典化,最终导致世界文学史叙事话语的单一与审美功能的基本丧失。在1949年后的世界文学史撰写中,把无产阶级文学等带有明显左翼倾向的世界文学作为介绍和研究的重点,并上升为主流话语,将其经典化。而另外一些在世界文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学类型,则被排斥在世界文学史之外。例如,“玄学派”诗歌、哥特小说等,就因为其黑色意味和死亡母题等所谓“不积极”的内容,而被彻底排斥在我们所建构的世界文学史之外。
(3)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两分法对整体世界文学的人为割裂。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世界文学的划分都大体遵循一种约定俗成的地理观念,即分为西方(欧美)文学和东方(亚非)文学两大基本类型。从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看,西方与东方的地理和文化划分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西方与东方概念的形成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结果。萨义德曾认真研究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建构,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5]6,而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日益模糊的东西方文化与地理边界和汹涌而至的文化全球化大潮,对我们的世界文学史建构提出新的挑战。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我们越来越难以区别哪些是纯粹的西方文学和西方作家,哪些又是纯粹的东方文学和东方作家了。具有跨文化性质的流散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兴起,已经慢慢消解了东西文学与文化二分的观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具有跨语言与跨文化性质的文学,会越来越因为其创作的文化多元性,而成为最能反映当下世界文学特质的文学类型。
(4)忽视了世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目前所使用的世界文学史教材虽然已几经修订,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依然可见,主要是从反映论的立场出发,结合时代背景或者社会状况来分析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割裂了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只强调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世界文学史,必然将时代背景简单等同于文学内容,用时代精神和作家的世界观来阐释作品的主题思想,从而导致文学的审美价值被历史价值取代,偏离了文学的本质。
(5)教材的编排体例的封闭性。目前的世界文学史教材就结构而言是相对封闭的,多年来主要内容几乎固定不变,没有任何弹性,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和国别地域来划分,大都先介绍文学发展的概况,然后是重点的作家与作品。这种固定不变的僵化模式,直接导致教学方式的模式化与简一化,教师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对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按照文学的规律进行整合,也无法启发学生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进行积极的思考。
3 新辩证论视野中的世界文学史观及其理论意义
无论是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还是法国人的比较文学观念,抑或中国当下所提出的跨民族与跨文化的文学研究,都隐含着一个在理论上必须解决的难题:在跨民族与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克服文化立场上的西方、东方(中国)中心主义的排他性选择?文化一元论的危害在于看不到异彩纷呈的多元存在,看不到世界各民族文化古往今来的交流与会通,看不到文化先进民族与文化滞后民族都有一些优于别人的长处,从而在看待许多的文学和文化问题时,偏离客观事实,并很有可能把一己民族的存在与价值观,当作唯一合理的诉求,从而成为诱发不利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的因素。因此,在以跨文化对话为理论目标、以和而不同与多元共生为文化导向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就显得很有必要。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大卫·达姆罗什就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理想,即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6]34。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歌德与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文学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可贵的乌托邦”[7]140。世界文学的新建构不应只是各民族文学的简单聚合,而是在互识、互证和互补的基础上带有比较文学意味的有机整合。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应以全球多元文化意识为理论根据,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学相互平等的地位。它应当把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看作人类所共享的精神财富,不偏不倚地加以比较和阐释,从而深入探讨人类文学发生、发展与整合的规律,在理论上推进以各民族文学的艺术个性和审美特征的充分发展为旨归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这才是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文学研究理应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发挥主导作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研究范式的参照系。
然而遗憾的是,在世界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我们长期受制于西方中心论和中西二元论这两个根深蒂固的研究模式。针对当下的世界文学史建构而言,这两种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阐释世界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新辩证论是对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特性和共同规律进行整合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语境中,新辩证论完全可能成为推进研究拓展的动力,进而成为研究范式转型的选择之一。这种转型对于世界文学史学科的建构是完全正常的,“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8]55。在世界文化日趋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理应形成一种新的辩证理论,在本文化与异类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承认他者的同等地位,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相互平等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各具特质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理应是互为主体,以多元而非一元的态势来丰富“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根据我们的理解,世界文学其实就是在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碰撞、交流、对话、借鉴和会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是辩证统一的良性互动关系。
王国维认为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9]30。文学研究会在其《丛书缘起》中声称,文学艺术的功能并不是为个别“民族”服务,而是为“人类”大众服务:文学“能够以慈祥和蔼的光明,把人们的一切阶级、一切国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10]73。“世界文学重构”这一理念蕴含着人们渴望摆脱孤立状态,走向一个辩证统一的话语平台的美好憧憬,同时它也为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彰显自己独特的审美倾向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但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需要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多,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全球视野,考察各民族文化在纳入世界整体结构之后如何影响文学发展的问题,审视每个时代的文学在他者影响和克服他者影响的双向互动中的发展历程。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说过:“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11]159。由于地域、种族和语言等都具有多样性,我们应当考虑到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不能简单主观地用某一种标准来衡量世界各民族文学,而应尽量客观与公正地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学。(2)从国际学术界的文学史编纂实践中,借鉴建构相对完整的世界文学史的基本方法,有效解决世界文学的起源、发展动力、文学史分期基本范畴等问题。(3)认清专业研究者的使命,鉴别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历程与基本规律,形成系统而准确的各国文学史,把中外(东西)文学史相互融合,把不同语言的文学纳入统一的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从而建构起一种宏大的全球文学观。
总之,建构有当下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史,无疑是一项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学科建设工程,任重而道远,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艰难险阻自然也不会少。然而,这项工程和建立“以我为主”的“中国世界文学学”有密切关系,前者(编写自成体系的世界文学史)是后者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能遵循 “传承——超越——创新”的规律,假以时日,一定会出现有中国特色、形成自己体系的世界文学史。
[1]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高小康.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J].社会科学辑刊,2002(2):37-42.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方汉文.世界文学的阐释与比较文学理论的建构[J].东方丛刊,2007(3):193-212.
[5]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6]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J].山东社会科学,2012(3):34-42.
[7]乐黛云.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2011(4):140-142.
[8]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J].New Left Review,2000(1):54-68.
[9]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10]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11]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