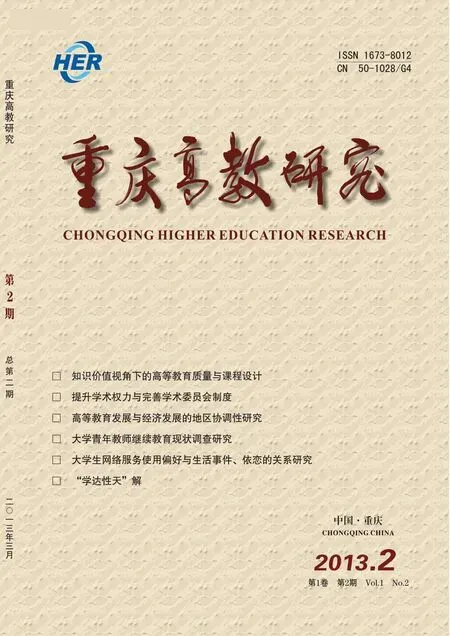“学达性天”解
——教育目的之存在论诠释
张晚林,姜 燕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一、引言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休闲娱乐之去处不在少,但可以怡情养性之所则常难觅。然而,有一个地方——古代书院——却不同,常是笔者心之所寄,一俟其可能,必去瞻望景仰。近年来,笔者先后拜谒了武夷书院、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这三个书院分别位于武夷山、庐山及岳麓山山麓,门前亦有涧水流过,全得造化之宁静与悠然;其设计也,内则亭阁画廊,外则飞檐翘角,尽显人情之自然与博雅。人置身于其间,恍然有隔世之感。钱锺书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1]此间玩味此语,倍生余韵与幽思。这与书院里的醒目匾额——“学达性天”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时常因“教育的目的为何”而纷争,而“学达性天”四字应该是教育目的之全尽而简明的表述,至少人文教育应以此四字为依归。本文即从存在论的角度切就“学达性天”何以能够作为教育的目的进行深入的学理诠释与义理论证。
二、“学达性天”之学理源流及其存在论意涵
“学达性天”四字最早是康熙二十五年(1687年)御题之匾额,分别颁给宋儒周濂溪、张横渠、邵康节、二程、朱子之祠堂及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①很明显,这四个字意在表彰宋儒(实则亦应包括明儒)之学术精神以及由这种学术精神所主导的书院教育理念。所以,“学达性天”四字虽然只在清代康熙年间才出现,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教育理念,在宋明儒那里已经完成。只不过,那时不叫“学达性天”,而是以“天人性命之学”或“天人之学”名之。如“先生之文,尤长于诗,晚益玩心于天人性命之学,其自乐者深矣。”(《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四《华阴侯先生墓志铭》)又,“其为文操行率类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学,竟以寿终。”(元·王逢《梧溪集》卷一《题宋太学郑上舍墨兰》)又,“先生致政归,设教宏运书院,日讲天人性命之学。当时称为明学贞予先生。”(清·沈佳《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二)再如“非先王之言不道,以天人之学自修。”(宋·李昭玘《乐静集》卷十七《谢徐州范教授》)又,“此书还往,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国家之患也。”(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一《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又,“君子学以慎独……其常运而常静处,便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天人之学也。”(《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由此可见,宋明时期,“天人性命之学”或“天人之学”确为普遍认同的教育理念,且得到了时人较高的评价与颂扬。但应该说“天人性命之学”或“天人之学”之教育理念只是到宋明时方才显明与完成,并不是意味着这种教育理念是一种全新的产物,其来实乃绍述于先秦原始儒家。实际上,在《论语》那里,孔子就有“下学而上达”的理想。另外,诸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同时,其弟子子贡亦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之叹。在孟子那里,则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之观念。这些说法虽与“天人性命之学”或“天人之学”殊异,但在义理上却一脉相承,开启了这种教育理念之统绪与源流。故后世学者常以孔孟这种理念自警与策励。太史公就以孔子之精神自勉,且以为《史记》就是要绍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理念。显然,太史公准确地把握到了孔孟儒学的学术精神与教育理念乃“天人之学”。正因为如此,学者一般都能肯认宋明儒之学不过承此统绪与源流而推明光大之,并非臆造新学以标高也。以是叶梦得曰:“天人之学,孔子始略而不尽言,使学者以意求之而已。”(《春秋考》卷六)而乾隆皇帝亦曰:“朱子谓三代学校之法废,天下学者非俗儒记诵词章,即是异端虚无寂灭,其论确矣……程朱出而昌明千载不传之遗经,而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似可得闻矣。然学者不务诚身以明善,学古以入官,徒以口耳为性天之学,其与虚无寂灭者,要亦名异而实同耳。”(《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可以说,“学达性天”是宋明儒之“天人之学”乃至孔孟原始“内圣之学”简明而精确之表达与概括,尽得儒家教育思想之精髓。但可惜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很少受到教育研究者或儒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与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②使得这四个字之精义未能得到应有的阐发与推明,进而使中国传统之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淹没而不彰,其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与价值亦鲜有开发与光大。
那么,“学达性天”到底有何涵义呢?要理解这四个字,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教”的涵义。我们一般认为,教育不过观念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使懵懂者知之。但中国文化起始即不如此看待教育。许慎《说文解字》训“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训“育”为“养子使作善也”。这可以说尽得中国传统“教育”之心。从许慎的训诂中有两点须注意:第一,教育在于促成人的一种行为,而且,第二,这种行为还是善的行为。但在中国文化看来,善的行为只可能从一个“仁者”或“真人”那里方可生发,或者说,只要一个人是“仁者”或“真人”,则自可产生良善的行为。若不然,仅只是外在观念的灌输或规则的传授,往往是无效的,甚至徒生虚伪。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就是说,若一个人不是“仁者”,外在的“礼乐”是无效的,不但无效,且让人文过饰非。故孔子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庄子亦曰:“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马蹄》)这里的“纯朴不残”“白玉不毁”“道德不废”“性情不离”都是让人回到“真人”那里去。由是观之,中国传统之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成“人”的教育。就其最高目标而言,这里的“人”应是尽性全德之人,即“圣人”。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就是这种教育理念之体现。这意味着,“诵经”与“读礼”只是教育之门径或方法,若不能至于尽性全德,则终是小成。故荀子又曰:“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荀子·劝学》)若教育只是知今日宣扬此一概念,明日又批判彼一原则,则是“一出焉,一入焉”,此无异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是决不可成“人”的。此种教育,不过是记问之学,这历来为中国文化传统所轻视。是以《礼记·学记》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教育在成尽性全德之人,此种教育理念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谨守与执持。元·王义山曰:“先儒教人,八岁小学,十五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成人之谓也。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夫子且然。”(《稼村类藁》卷十一《犹子希文冠说》)可以说,这是自夫子以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共识。
教育在成就尽性全德之圣人,但问题是:尽性全德之圣人有普遍的可能性吗?亦即是说,人人有普遍成为圣人之可能吗?或者说,成圣有形上的根基吗?若没有,则作为一种普遍的教育观念是不合法的。这涉及到对人的认识问题。我们知道,在孟子那里,已经得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主流,为历代读书人所肯认,并成为人人努力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孟子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能得到正统儒学的认可呢?这是因为人天然地固有四端之心或良善之性(亦即后来宋明儒所讲的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又曰:“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只要是人,就必然具有四端之心(良知),这是形上的必然。这意味着人是一个内在自足的系统,成圣人人可能,无待于外在之穷通、机遇与知识。可见,孟子“性善”论的提出,乃是一种存在论,而非一种伦理学。对于此种学说之意义,徐复观先生尝曰:
这代表了人类自我向上的最高峰。所以孟子性善之说,是人对于自身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有了此一伟大发现后,每一个人的自身,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普遍,即是一永恒。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运命,解决人类的运命。每一个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觉中,得到无待于外的、圆满自足的安顿,更用不上夸父追日似的在物质生活中,在精神陶醉中去求安顿。[2]
人既是一个内在自足的系统,则教育不必外求,只须“尽”这个四端之“心”,“全”这个良善之“性”即可。这就是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的理论之由来。其实,稍早于孟子的子思,在《中庸》的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亦是表达此种教育理念。即教育不过是“修道”,而“修道”亦不过是“率性”,而所谓“率性”不过是“全”人之天命之性也。这样,教育不过是“尽”人之所固有者,“全”人之所得于天者,绝非向人灌输认为构造的原则规范与义理系统。这里“自觉”的“工夫”重,“他力”的“传授”轻。是以孔子有“予欲无言”之说(《论语·阳货》),子贡才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之叹。老子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庄子曰:“夫知者之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这里所说的“不言之教”实则是重“自觉”的“工夫”之意。人是一个自足的内在系统,良知或天命之性作为成“人”之根基,人人具足,只要“工夫”到,必能“尽”之、“全”之。故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若教育是“尽”在我之“心”与“全”在我之“性”,则“求”之必得,无有例外;若是获得“外”在的知识,则“求”之未必能得,因为这涉及到外在的诸多因素。后来,《白虎通义·辟雍》对于这种教育思想作了一句总结:“学之为言觉也。”所谓“觉”就是“自觉”“培养”“扩充”人内在固有的道德,非外索于知识观念也。此一教育理念,后世学者都能坚守而不失。王阳明曰:“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徳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这样,教育究不是让人勉为其难地接受外在的知识,而是发扬、光复人固有之“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清·陆陇其曰:“圣贤教人学教人虑,并不是勉强人。人之本来原有不学而能之良能,原有不虑而能之良知。只是囿于气禀,蔽于物欲,不学而能者不复能矣,不虑而知者不复知矣。故学也者,所以复其不学之体;虑也者,所以复其不虑之体。并不是以人所本无者强人。”(《松阳讲义》卷十二)这固有之“良能”“良知”一旦自觉、扩充而至于其极,则成为生命之“大主”。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即谓此“大主”也。人之于“大主”呈现,即是“尽”心,即是“全”性。而人一旦至此,必感觉到天命与天道之召唤与威临,绝不只是囿于个人的成圣成贤。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上》)又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这些都是因天命与天道之召唤而来的使命感。这是“尽”心“全”德者所必至的认知与境界,是笃实内修后的必然高远外发。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依孟子之意,“知天”“事天”是“尽心”“存养”者的必然担负,亦是其宿命。我们似乎可以如此说,即天命担负是“尽”心“全”性者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这与个别人的认知与理想毫不相干。“尽”心“全”性是人的伟大之处的前提。假使一个貌似伟大的人不能作笃实的内修工夫而“尽”心“全”性,则他如果不是一场闹剧的滑稽演员,就是一个炫耀盲目力量的粗人。
可以说,至孟子提出“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而“事天”,就确立了“天人合一”的义理规模。由此,天道与性命可以贯通,亦必然贯通。“天人之学”之建构已完成矣,而“学达性天”四字则简明而充实地表达了此学的精蕴与内涵。须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学”字,内在“存养”的意味重,外在“传授”的意味轻,可谓“德性之知”而非“见闻之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才说:“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朱子语类》卷第十)如果说“读书”是“学”的话,那么,须“经历过”便是“养”,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家合下完具的显现。实际上,孔子所说的“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中间之“而”字训为“养”最为谛当。平常以“而”乃一虚字,意义不大,实则不如此简单。“下学”以至于“上达”,不是学问程度之升进,乃是异质的豁然开朗以见“天(道)”。既如此,则必有联接相异二质之媒介,此“而”之一字,乃此媒介也。故“而”不只是一虚字,实有一大段学问工夫在,此一大段学问工夫即“养”也。此非训诂问题,乃学问历程之体悟与开发问题。“存养”是内修工夫,而“四端之心”“良善之性”又人人具足,故“天人之学”人人可“学”,亦人人必“学”,这亦是一种存在论,而不是主观殊异教育思想的选择,实则并无选择。“学达性天”有其不可移易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因为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本质。
三、“学达性天”与西方教育思想的会归
我们说“学达性天”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教育思想,而是基于人之存在论而来的真理绽放。既如此,这种教育理念就不应该仅仅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所具有,在别的文化系统也应该有,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的确如此,事实上,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所说的学习乃是“精神接生术”,柏拉图所说的知识乃是灵魂的“回忆说”,都应该在教化的意义上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学达性天”。而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论自在的人的使命》中所表达的思想,可以说与“学达性天”之理念如出一辙。在费希特看来,我们对人的经验规定至少绝大部分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人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外物又是多种多样的,故我们很难把握到人绝对真实的形式。但人活在世间有一个绝对的使命,就是向其最真实的存在迈进与回归。他说:“一切有限的理性生物的最终使命,就是绝对自相一致,始终自相同一,完全自相一致。这种绝对同一就是纯粹自我的形式,是纯粹自我的唯一真实的形式。”[3]9这意味着,人既是理性的生物,就应该回到他所“是”的存在,这不是基于任何道德伦理的要求,而是基于其存在论本质。费希特进一步说:
人之所以应该是他所是的东西,完全是因为他存在,也就是说,他所是的一切,应该同他的纯粹自我,同他的纯粹性相关联;他之所以应该是他所是的一切,纯粹是由于他是一个自我;而且因为他是一个自我,所以一般说来,他根本不应当是他所不能是的东西。[3]8
费希特还认为,所谓“善”无非是理性生物的自我一致。并非造福的东西是善的,而是只有“善”即理性生物的自我一致方可是造福的。显然,同孟子一样,费希特这里的“善”亦不是一种伦理学,而是一种存在论。而教育无非是针对人的这种存在疏远,使其回复到存在的本真中来。费希特说:“如果人被看作是有理性的感性生物,文化就是达到人的终极目的、达到完全自相一致的最终和最高手段。如果人被看作是单纯的感性生物,文化本身则是最终目的。感性应当加以培养,这是用感性可以做到的最高的、最终的事情。”[3]10所谓“感性应当加以培养”就是不使感性逸出理性之外,从而使人成其所“当是”,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文化教育。故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驶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费希特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不停止其为人,如果人不变成上帝,那么教育的目的似乎总难达到,但教育的使命就是“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3]11从费希特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虽然不能变成上帝,但毕竟可以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在费希特那里,教育的目标就是让人与绝对自我相一致,而一旦如是,则人必无限地接近了上帝。“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4]以中国传统名言说之,自我一致属尽“性”的方面,观察天国属事“天”的方面。由此,亦可说教育的目的是“学达性天”。尽管费希特的理论与中国教育传统在名言上有殊异,但终归是往“学达性天”的义理规模走,此则定然而不移。此亦可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
现在再来看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否可归结到“学达性天”那里去。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家,但在教育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其高远的心志与超越的精神,而提出了“教育无目的”论。所谓“教育无目的”是指教育不应该有外在的实用性的目的。杜威说:“有一个假定,相信社会条件决定教育目的……这是谬说。教育是自治的,应该自由决定它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目标。离开教育的作用,从外部资源去借用目的,就是放弃教育的事业。”[5]25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不应该强调“学以致用”,“适合于大众的教育必须是学以致用的教育,而这种学以致用是在与人文教育思想相互对立的意义上说的……意在功利结果的灌输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再能够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优雅的趣味,也不能深化我们的理智与洞见。”[6]如果教育只注重“学以致用”必将疏离人的存在,是对人之“性天”之限制与减杀。故教育应该回到人自身。杜威说:“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5]22杜威的这一意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教育目标比一般的教育改革者或哲学家之目标都要高:
因而,美国教育的问题不是向年轻人讲授职业规则:没有人知道他们将来的职业是什么。问题在于:如何帮助他们了解这一点: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如何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中作一个好公民?如何成为人?[7]
尽管杜威表示,“教育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8]但如果教育不能把握住“成”人这个最高点,则经验如何被改造或改组呢?特别是,杜威指出,“教育科学的资源包括进入于教育者的心、脑和手的任何部分确定的知识,这种知识进来以后,就使教育的职责完成得比过去更加开明,更合人道,更具有真实的教育意义”。[5]26我们知道,如果除却人之“性天”的良善良能,纯粹的科学知识是无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开明,更加人道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生活,使其更加开明、人道,势必先须肯定人之“性天”的良善良能,并且通过教育手段使其在生命中具足而成为“大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成杜威所说的“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9]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知,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学达性天”在名言上似乎相去甚远,但其义理规模依然是在往“学达性天”这个方向走,这是依“义”不依“语”的解析。笔者以为,如果杜威看到这四个字,亦必“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
另外,康德把人分为现象界的人与物自身界的人,黑格尔把世界与人类社会看作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异化与运动,则他们在教育上绝对与“学达性天”异曲同工,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了。可见,“学达性天”四字虽然由中国文化传统所表诠出,但却在教育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中西有见地的思想家那里,只有名言表述上的不同,并无义理本质上的殊异。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为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10]
四、结语
“学达性天”是圣人在践仁尽性中所显现的义理模型,所谓“不言之教”“不得而闻”都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是一种实践态度而不是一种理论态度,是人的存在回归,这是“行动”而不是“学习”。牟宗三对“性”与“天道”不得而闻的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义理模型与实践态度。他说:
因孔子毕竟不是希腊式之哲人,性与天道是客观的自存潜存,一个圣哲的生命常是不在这里费其智测的,这也不是智测所能尽者。因此孔子把这方面——存有面——暂时撇开,而另开辟了一面——仁、智、圣。这是从智测而归于德行,即归于践仁行道,道德的健行……他的心思是向践仁而表现其德行,不是向“存有”而表现其智测。他没有以智测入于“存有”之幽,乃是以德行而开出价值之明,开出了真实生命之光……原来存有的奥秘是在践仁尽心中彰显,不在寡头的外在的智测中若隐若显地微露其端倪。此就是孔孟立教之弘规,亦就是子贡所以有“不可得而闻”之叹之故了。[11]
此可谓是因“行”称“义”。庄子曰:“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庄子·齐物论》)“学达性天”乃“圣人怀之”而来,本文只是“辩之以相示”,以使其义理显豁便于学者了悟其心。虽然,“学达性天”自悬于天壤间,有本文,何曾“添得些子”?无本文,何曾“减得些子”?③最要者,须有践仁尽性之工夫。若工夫至,虽不说一字,亦可迹本兼得;若工夫不至,虽千言万语,亦恐是枉费笔墨。
注释:
① 《皇清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
② 笔者搜寻的结果,大陆只有陈怡教授的一篇短小的论文《“学达性天”解读》,发表于《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三期,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因资料所限,未曾搜录。
③ “添得些子”“减得些子”出自陆象山。“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1] 罗厚.钱锺书书札书钞[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314.
[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58.
[3]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默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73:72.
[5] 吕达,等.杜威教育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6] Dewey John.Democracy and Education[M].The Macmillan Company,1916:298-303.
[7] Huchins Robert.Some Observations on American Education[M].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95.
[8] 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59.
[9] 杜威.道德教育原理[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365.
[10] 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M].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41.
[11]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