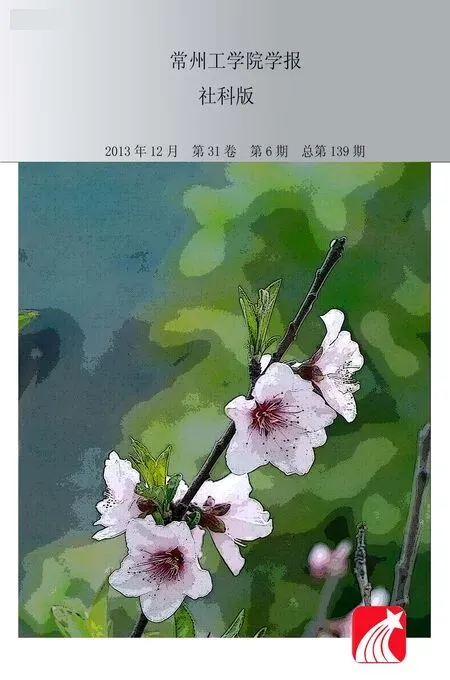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零度写作”
施云波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2)
多丽丝·莱辛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齐名的英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有《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简述下地狱》《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简·萨默斯日记》等。1950年,处女作《野草在歌唱》的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然而,1962年莱辛的另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即在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被誉为具有开创性风格,并成为莱辛折桂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充分理由的《金色笔记》,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提倡古典主义宏大叙事的评论家看来,《金色笔记》语言上平平淡淡,几乎没有优美典雅的句子;结构上混乱不堪,支离破碎,与其说是小说创作,不如认为是剪报或文献记录。多丽丝·莱辛的同时代人,著名的作家、诗人、语言学家和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就曾公然否认小说的艺术价值,认为它不是一部艺术作品。
无独有偶,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写作的零度》的文章,与存在主义权威萨特《什么是文学》的介入式写作针锋相对,动摇了萨特的“为谁写作”的命题。罗兰·巴特以现代结构语言学的理论为基础,在语言学革命深刻影响的背景中,发现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提出了写作是单纯的“不及物”活动,文学不再是观念意识的传声筒,作家在沉默的“白色写作”中实现零度写作和写作的真正自由,这对传统的“风格即人”的西方经典文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反拨。
表面上莱辛与零度写作的罗兰·巴特并无太大关联,国内也未见此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两人在创作精神上有着契合之处。基于此,文章拟从零度写作的角度解读莱辛的《金色笔记》,进而发掘其丰富的社会价值。
一、零度语言
罗兰·巴特认为言语与文体从两个维度制约了作者的创作。古典写作中的语言符号承载的是工具的作用,意义和语言符号之间虚构了一种透明的确定关系,语言符号作为作者思想的载体,存在的必要性来自于对意义、情感、思想的表达或转译,即语言成为创作主体的奴隶。罗兰·巴特受结构主义影响,发现所指与能指无必然联系,相反,能指作为独立的因子,可以完全游离于所指之外。语言符号并不通过与外界事物联系获得意义,而是作为一种结构,一种系统组成部分的结果。零度语言通过发现字词的独立品质,标志着“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
零度语言在《金色笔记》中首先体现在近乎白描的对话上,白描是中国画中摒弃色彩,完全用线条来表现物体的画法,具有简洁朴素、概括明确的特点。在文学上,白描是用最少最精练的文字,不加渲染、铺陈地勾勒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自由女性I》的开头安娜与摩莉的对话开始,简短的对话贯穿了本书的始终,最常见的句子字数约为15字左右,而长句不到4%。作家发掘动词与名词的想象力,较少用到形容词、副词和状语,句型多为无变化层次的简单句,如“主+ 谓+ 宾”的框架,多使用无感情色彩的中性词。对话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那样,以最原始、最纯朴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加丝毫文学上的修饰渲染。在《黄色笔记》的《第三者的影子》中,爱拉被情人保罗毫无理由地抛弃后,万分痛苦,好友朱丽娅只是问她“要不要来支烟?”,爱拉也只是回答说“我要去睡了”。此处作家写得平淡克制,完全摒弃了古典写作的长篇大论,用最简洁朴素的对话,增加作品的维度,使文本富有立体感,省略的使用,无声胜有声,调动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作家如同摄影机般忠实地记录这一切,叙述者不介入叙事,以客观、冷静、平实的笔调,以一种洞悉世事沧桑的含蓄和深沉来展示笔下自由女性爱拉无法言说的苦痛。正是这种近乎白描、低调清爽、笔法瘦硬、风格干脆的对话体现了罗兰·巴特的毫不动心的纯洁的写作风格。
零度语言在《金色笔记》中还体现在片段式的语言上。在《黑色笔记》的开头,主人公安娜写道:黑色/黑,它太黑了/它是黑的/这里存在着一种黑①。安娜在笔记中乱涂乱画,点缀着各种符号,笔记中很多故事戛然而止,甚至有的句子只有一半,尤其是《蓝色笔记》,以剪报的形式记录了50 年代广岛原子弹、美苏冷战、麦卡锡主义、苏共二十大等历史事件。各种新闻剪贴凌乱无序、松散重复,意义又大相径庭。这些片段式的语言我们无法将其归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我们仅仅可以将之称为文本而已。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语言片段绝不是因为莱辛语言基本功薄弱,而是为作品的最终目标服务的,即反映主人公安娜的意识流、片段式思绪,以及迷乱、失重的灵魂。莱辛打碎了语言符号本来的形象,撕裂其逻辑上的联系,再将这些语言碎片重新组合,于是便有了半截的、不完全的、陌生化的文本。这种陌生化效果使读者阅读时备受煎熬,但也正是这种痛苦,使读者对文本产生了创意性的理解,精神境界为之拓宽,获得一种春蚕蜕皮般的新生的快乐。
二、零度结构
罗兰·巴特认为与线性不可逆的古典语言相反,现代语言则是一些独立语言片段的临时聚会,它们无序而混乱,可能随时分化,也可能貌合神离,充满矛盾和悖论。为了反映后上帝时代纷乱的社会现实和人类价值观的多元化,文学不再需要,也不能提供单一的价值标准,来营造一个有序、公正、理性、现实的虚假世界的感受。
零度结构在《金色笔记》中首先体现在其独特的网状结构上。古典主义小说的结构往往按照铺陈—发展—高潮—结局这样一种线性叙述模式,尽量使得作品意义连贯,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却无法掩盖其封闭性和虚伪性。莱辛在《金色笔记》中借女主人公安娜之口,评价安娜自己写的《战争边缘》这部传统小说,由于迎合了读者低级的猎奇审美心理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安娜自己却从此失去了写作的信心,陷入写作障碍。因此,在这部作品中莱辛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模式,将6 万字左右704页的小说按空间和时间进行分割,传统小说《自由女性》被分割成I,II,III,IV,V 5个部分,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4本笔记依次插入《自由女性》中。《金色笔记》最后出现,它被放在《自由女性V》之前。《自由女性》作为《金色笔记》整部书的主干部分,支撑整个框架的构成,而其他五个部分的笔记则是以《自由女性》为基础,向四处延伸。《黑色笔记》是关于安娜的作家生活,《红色笔记》记录的是安娜的政治生活,《黄色笔记》描写安娜的爱情生活,《蓝色笔记》是关于安娜的精神生活。四本笔记象征着安娜四个分裂的自我,最后,合成一本金色笔记,意味着安娜的自我由分裂最终走向整合。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经,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作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既有纵向脉络又有横向联系、交错复杂的网,建构了一种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这样一部结构如此独特、内容如此庞杂的作品,无疑给读者带来混乱的感觉,这也是《金色笔记》饱受争议,甚至被认为算不上一部真正的经典小说的原因。然而,这也正是莱辛匠心独运之处,正如作家莱辛自己所说:“这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本书的结构自己做评,是一种无言的表述,通过它的结构方式来说话。”②事实上,作家正是要用这种文本之“乱”来象征外部世界的乱和由此导致的人精神内部之混乱。
《金色笔记》讲述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中期。那时二战的阴影尚未散去,战争摧毁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打破了内心世界的平衡,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使置身于精神荒原的人们备感焦虑和恐慌。如女主人公安娜是有着独立思想和稳定经济来源的中产阶级女作家,表面上,她的生活可以称得上自由和幸福。可是,作为简纳特的母亲,她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作为自由女性,她在爱情的名义下无名无分地做了多年的情人,最终还是被人抛弃以致精神几乎崩溃;作为作家,她作品《战争边缘》的真正价值不为世人所承认,安娜发现自己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作为共产党员,她对自己信仰的一切感到绝望。多重身份反而使安娜的生活一片混乱。通过错综复杂的乱序结构,《金色笔记》摆脱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阅读时读者无不为作品人物所经历的混乱、破裂、无序的生活而震撼。而莱辛认为“乱”更体现了生活的本质。在《黄色笔记》的《第三者的影子》中,她描绘了一个意欲自杀的年轻人,他表面上生活井井有条,内心却涌动着混乱、疯狂、失望的暗流。小说中,莱辛还采用了拼贴术,《蓝色笔记》中出现了大量剪报,涉及《快报》《每日电讯报》《政治家》等报刊上常见的关于战争、暴乱、谋杀等新闻内容,杂乱无章的形式象征当时世界的混乱秩序。《金色笔记》中小说结构跳过内容直接揭示主题,从而完全颠覆了古典主义写作那种形式从属于内容的观念。莱辛正是运用这种让语言形式代替内容和意义的手法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意图,这正好与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语言和形式摆脱附属地位、不再隐匿于意义之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对象的零度写作理论相契合。
零度结构在《金色笔记》中还体现在多重复合视角的开放式叙事上。叙事视角是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它分为三种,即零聚焦——叙述者大于人物,全知全觉;内聚焦——叙述者等于人物,指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外聚焦——叙述者所说的比人物所知的少。小说《金色笔记》主要采用了零聚焦型即全知全觉的叙述模式和内聚焦型即第一人称叙述模式这两种视角。《自由女性》是莱辛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女主人公安娜的故事,而黑、红、蓝、金色笔记采用的是内聚焦型第一人称视角,是叙述者“我”——安娜·伍尔夫对自己的生活从不同角度的记录、讲述和呈现。此时安娜成为小说叙事的中心和焦点,小说的视角由此发生了改变。除此之外,在《黄色笔记》中,安娜还充当了自叙传小说《第三者的影子》中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通过安娜之口讲述了爱拉的故事,并且爱拉也作为叙述者写了本小说。尽管安娜·伍尔夫是小说中事实上的叙述者,但这个叙述者在《自由女性》和“笔记”中由于人格分裂产生了多重性的视角,叙述视点经常跳跃,如《黄色笔记》中的安娜在自传小说中化身为爱拉,主人公爱拉的话语和叙述者安娜的话语常常混杂在一起,安娜自己也承认这一观点:“我见到爱拉在一个空空的大房间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她一边沉思一边等待。我,安娜,见到了爱拉,而她当然就是安娜自己。”③莱辛正是用多重复合视角的叙事方式,消解了作者的主体性,将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分离,将小说作者这一主体游离在情节之外,冷静克制如同摄影机放映般娓娓道来,对人物对错不置可否,从而进入了一种不介入、中性的白色状态。故事的结尾安娜与摩莉话别,也是开放性的,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读自由,读者可以与作者一起参与作品意义的构筑。由此可见,《金色笔记》中的多重叙述者在令人困惑同时,使文字充满无限可能性,没有趋向,中性、自足、饱和、客观——这就是罗兰·巴特一再强调的语言行为:零度的写作。
三、零度——莱辛的话语方式而非话语目的
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产生于古典写作虚伪地标榜 “真实”和“自然”的神话的特定背景下,强调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和无趋向性,以此反击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秩序、公正和理性。然而这种零度写作并不能被理解成无意义的、虚无的写作;作家游离于作品之外,更不意味着作家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评论家认为,莱辛的《金色笔记》语言平淡,结构混乱,主题模糊,只是一场语言虚无的游戏,毫无社会目的,关闭了文学艺术通向思想、价值、终极意义的通道,没有承担起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它充其量算是文献记录或新闻报道,无法跻身莎士比亚等作家的经典文学之列。其实,这是对莱辛零度写作的误读,因为零度写作是莱辛的话语方式而非话语目的。
莱辛写《金色笔记》无疑是有其明确的目的的。莱辛认为,《金色笔记》是一本精心构思、组材严密的书,它用形式表明了小说的意旨。在1972年版的序言中,莱辛曾明确地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即写出像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红与黑》那样的全面描写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小说。事实上,作为向现实主义大师致敬之作,《金色笔记》在内容和形式上走得更远,莱辛完全无愧于“将自己的怀疑、激情以及幻想投入在对分裂的文明的审视上”的评价。
莱辛使用平淡到近乎白描的语言,并非没有能力写出华丽的词句,而是基于美学的少即是多的原则,去掉修饰语,突出重点,突出名词和动词的想象力,使文本增加维度,富有立体感。莱辛从不借人物之口直抒胸臆,冷静克制地叙述并不是她缺乏感情,而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比如《黄色笔记》中的爱拉被抛弃后,莱辛只是平静地写她日复一日地站在窗前等待,读者却不由自主地为“自由女性”掬一把同情之泪。她从不硬塞给读者什么观念,并不是她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将价值判断蛰伏在语言形式中,投射在字里行间,正如演员面无表情的表演却反映内心最大的震撼。作者的中立使作品的审美蕴涵获得最大张力。她片段式的句子绝不是她没有完成句子的能力,而是因为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主人公本身的思维就是片段式的,意识流的。莱辛精心设计的小说的网状结构于混乱中显秩序,形式不再是内容的奴隶,而是与内容并驾齐驱。莱辛独特的多重复合视角带来的开放式叙事,使创作主体游离于作品之外,不是作者失去叙事控制力,而是为了淡化创作主体的功利目的,反对作者如全知全能上帝般直接干预作品,使作者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客观、可信。由此可见,莱辛用零度写作的话语方式的确更好地表达了话语目的。
四、结语
《金色笔记》是一部反映20 世纪中期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人类精神风貌的伟大作品。莱辛通过淡而有味的语言,匠心独运的结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零度叙述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在“混乱”中创建“秩序”、从“分裂”中走向“整合”的努力,尽管她将价值观隐匿得很深,但读者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她对当代社会的深刻思索和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莱辛的零度写作对于中国的文坛也有很大的启迪性。自盛唐以来,中国文学一直是寒门学子投之当道的行卷,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为了迎合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文章往往词藻华丽,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并习惯直接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伦理观念,真正在写作中体现语言表自由的作品并不多见。莱辛《金色笔记》中的零度写作,以及她真诚而犀利的批判精神,值得当代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努力效法。
注释:
①③(英)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陈才宇、刘新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2页,第487页。
②Lessing D.Critical Studies.Dembo: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4,p20.
[参考文献]
[1]Lessing D.The Golden Notebook[M].N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9.
[2](英)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M].陈才宇,刘新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施云波.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多丽丝·莱辛的《草原日出》[J].安康学院学报,2011(5):80-82.
[5]王宁.多丽丝·莱辛的获奖与启示[J].外国文学研究,2008(2):148- 156.
[6]瞿世镜,任一鸣,李德荣.当代英国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