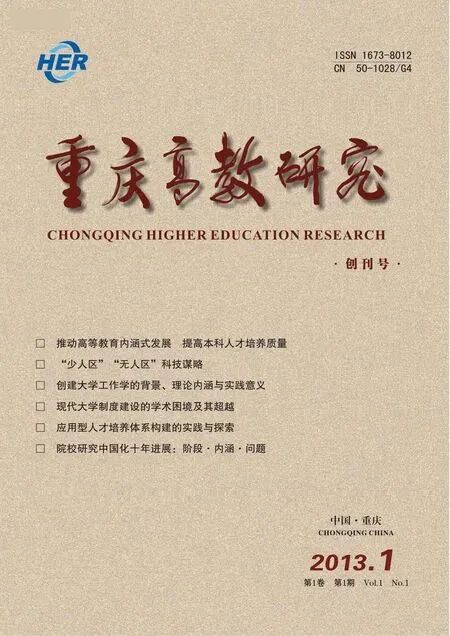20世纪西方教育流派中精英与大众价值取向之解读
董志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海淀区 100191)
20世纪西方教育流派中精英与大众价值取向之解读
董志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海淀区 100191)
20世纪对高等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西方教育流派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其中,实用主义和要素主义流派主张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观,自由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这三大流派则坚持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观。虽然各流派所持的精英与大众价值取向各有不同,但本质上都蕴含着明确的教育民主化和现代化思想,对推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教育流派;精英;大众
20世纪是西方教育流派林立、教育思想家辈出的世纪,也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些教育流派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都对高等教育的精英或大众化发展方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高等教育的精英与大众发展观视角,对这五大教育流派进行解读。
一、自由主义的精英价值取向——以罗素为代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新发展趋势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欧洲兴起了改革旧教育的“新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思想核心是与卢梭、裴斯泰洛齐等自然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自由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中,罗素较多地关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他的精英价值取向。
罗素反对教育被贵族和财阀子弟垄断的事实,倡导教育民主化。他指出: “我们已经讨论过品性和知识方面的教育,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里,这种教育应当向所有人敞开,并且在事实上应当为所有人享受”[1]188。他所认为的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一种能使每个儿童都获得最优机会的制度。理想的教育制度必定是民主的,虽然这种理想不会很快实现”。[1]4但是,罗素所主张的教育民主并非平均主义的民主,他认为教育不应是某些特权阶层的权利,应对所有阶层开放,但却只应当对具有一定能力和天赋的少数儿童开放。他指出:“明确民主与教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坚持绝对的一致极为有害……是否人人都应受最高等的教育,我很怀疑,即使如此,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粗暴地实行民主原则,其结果很可能是谁也得不到最高等的教育。”[1]4可见,罗素所提倡的民主的教育应该是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最好发展的教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得到最高等的教育。他认为,如果把教育民主理解为绝对的机会均等,“必定使科学进步遭受致命打击,并且使百年后的一般教育水平变得极为低下。不应当以牺牲进步来求得现阶段的机械平等。我们必须审慎地接近教育上的民主,以便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少地破坏那些与社会不平等偶然相关的宝贵产物”。[1]4
罗素的教育民主观从根本上说是精英教育取向的,他指出,虽然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但“大学教育应被视之为有特殊才能者的特权”[1]192,而不应当是某些特权阶层的专有品。因此,罗素认为,高等教育的选拔标准应当非常严格,而且选拔的标准“应当是教育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1]188。大学应当通过“能力测验”来决定学生是否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对进入大学之人要经常进行督促和检查,同时,“那些有才能而无资金的人应当享受公费教育”[1]192。
在当时封建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罗素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他的矛头直指封建残余势力,对当时教育的贵族化和宗教垄断化状况给以有力的一击。
二、实用主义的大众价值取向——以杜威为代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运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它是美国南北战争后适应工业革命、城乡变化、开发边疆和大量移民的需要而出现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20世纪40年代以前,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在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杜威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教育民主化思想。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以个体生长的统一性为基础,提出了“教育统一性”的原则。
杜威在他的经典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猛烈抨击了传统社会中的精英价值取向,并提出了他的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如果回溯几个世纪前,我们就发现一种学术上的实际垄断。的确,‘有学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名词。学问曾是一个阶级的事。这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绝大多数人缺乏任何手段去接近知识的源泉。……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学术上的高级僧侣防守着真理的宝库,而只在极严格的限制下才对人民群众给点施舍。”[2]35在此基础上,杜威还专门论述了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柏拉图希求依赖教育铸造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金字塔,以哲人教育为王冠而剥夺广大奴隶受教育的权利。杜威就此批评道:“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活动的无限的多元性。因而,他的观点就局限于几种天赋能力和社会安排。”[3]98在杜威看来,理想的民主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利用各人不同的天赋和才能,来共同促使社会前进,绝不该借口人的天赋不齐而造成阶级鸿沟。杜威的结论是:“声称机会均等为其理想的民主制度需要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把学习和社会应用,观念和实践,工作和对于所做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并且始终如一地结合起来。”[2]373
此外,杜威还从“生长的统一性”方面提出了他的“教育统一性”原则。杜威指出,传统教育的弊端就是教育缺乏统一性,表现在学校制度的各个部分、各个层次、各门学科之间缺乏统一性。杜威认为,儿童的身心成长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有机统一体,而传统的学校教育将教育的各个层次分割开来,这样不仅肢解了教育的统一性,也人为地割裂了儿童自身经验的连续性,割裂了个体生长的统一性。他提出,个体统一、连续地生长是统一教育的目的,即“教育即生长”,此外,“要把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与日常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借以统一教育,组织教育,并把它的种种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2]66。
传统教育认为,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高级阶段,只有具备一定资格的“精英”(身份、地位或者能力、水平)才能接受高等教育。杜威打破了这种观念,他认为“大学和学院的含义是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研究场所,是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所在地,在那里搜集、保管、组织了过去时代的最优秀的资料。然而,探索的精神只有通过和依靠探索的态度才能得到,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如此。……教育制度的最高部分若不与最低部分有完善的相互作用,要看到这些目的达到是很困难的。”[2]60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只是一个个体继续成长、继续发展的地方,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对于初等、中等教育而言,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凌驾于后者之上的一个阶段,它只是个体成长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应该接受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杜威提出,“要把一切教育上的事情结合起来,打破把幼年儿童的教育和正在成熟的青少年的教育分割开的障碍,使低年级的教育和高年级的教育统一起来,使它被看起来不存在低级和高级的区分,而仅仅是教育”[2]67。综上所述,杜威认为高等教育只是个体生长到某一阶段就可以接受的教育,因此,它不应再是某些“精英”所拥有的特权,事实上每个个体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义务和权利,而且,从完善个体的发展角度看,每个人也应该接受高等教育。
杜威所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期间,在他9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正是美国由农业国发展成为工农业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转变时期。这一期间正是精英高等教育传统开始动摇,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思想逐渐萌芽、发展的时期。杜威提出的这种“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统一性”原则,为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要素主义的大众价值取向——以科南特为代表
要素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苏联卫星上天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教育的思考,要素主义由此兴盛起来。代表人物科南特曾任哈佛大学校长达20年之久,他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和主张。
为了促进美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科南特非常强调教育机会的均等问题。这是由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多数移民来自于欧洲,如何有效地增强移民社会的凝聚力并吸引更多的移民来此定居,是当时美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论著中提到,“对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平等首先就成了机会的平等——在竞赛性的斗争中的一个平等起点。这一平等的概念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其他国家的居民,引来了他们的移民,这些移民在美国大陆的定居大大充实了美国的文化,增强了美国的种族。”[4]33为了促进美国文化的融合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科南特提出,“对许多新来的美国人来说,平等的含义不仅是政治上的平等,也是机会的平等……平等也意味着一切诚实的劳动在地位上的平等”[4]34。对于每一个移民美国的人来说,机会的平等首先应表现在教育机会上的均等,“在青年中,上学院或大学的已经从4%跃到了35%,今日这个数字已增长为70%以上。……这些变化,一个美国教育研究人员在1900年时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他可能已看到机会平等和地位平等这对孪生的理想的强大力量;很明显,美国人民已逐渐相信,多受一些教育是实现这些理想的手段。”[4]34他提出,“一切儿童机会均等,一切职业团体同样受尊重,无论对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两个原则。”[5]他所强调的教育机会均等首先是平等主义的教育机会均等,即接受教育并不是个人的特权,而应是人人都享有的一种权利和义务,要求教育向所有人开放;其次意味着不同职业和专业的人,无论在哪种学校就读,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科南特提倡的教育机会均等直接促进了美国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的发展,他对美国本土教育传统的肯定和坚持,使美国的教育模式在世界上逐步树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并为其他国家所仿效。
四、永恒主义的精英价值取向——以赫钦斯、阿德勒为代表
永恒主义教育流派产生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一流派是在反思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弊端中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观点是:人性的永恒,教育目的的永恒,教育内容的永恒。永恒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赫钦斯和阿德勒,他们在大学中推行名著教育计划,力图在大学中恢复西方传统教育的精神,同时,他们反对当时高等教育中日渐兴盛的大众化倾向,提倡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
永恒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是赞成教育民主化的。他指出,“我们的民主观使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同样数量和类型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全体国民对学位的热情。”[6]但同时,他并不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它仅仅面向那些有能力从中受益的人们。为繁荣学术、改进职业和培养心智提供机会,也许是各州的最高职责。如果它允许纳税人的子女随心所欲地接受高等教育,那它只会贬低这些目标并阻碍它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学位不再有任何意义,而且大学的确不应该继续存在。”[6]从教育目的方面来讲,永恒主义者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完满的人,教育的重大使命是使得生命个体达到心智的成熟和完善。永恒主义的教育目标就是通过阅读古典名著这些经典的知识来培养每一个人成为有高尚兴趣的(精神)贵族。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为什么要满足于降低要求呢?为什么不能使每个人成为在某种知识方面的魁首呢?比起满足于培养庸才并且把培养庸才跟民主精神错误地等同起来,上述目标肯定更有价值一些。”[7]
可见,永恒主义在高等教育发展观上所持的是精英主义的教育机会均等观,即民主并不是要求高等教育向所有人开放,而只能允许那些对智力劳动有兴趣和有能力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五、存在主义的精英价值取向——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
存在主义教育流派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存在主义关注人,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心理体验等本真存在的方式。在存在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中,雅斯贝尔斯对高等教育的论述较多。
雅斯贝尔斯提倡教育民主化,他主张打破身份和阶级的束缚,认为所有阶级的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他说,“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应该寻求读书的机会”[8]147,“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8]146。可见,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每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而不应为少数特权阶层所拥有,教育应当是归属于所有人的事业。
然而,另一方面,雅斯贝尔斯所持的却是精英价值取向的教育民主思想。就高等教育的教育对象而言,雅斯贝尔斯认为其接受者应该是天资超群、禀赋优异的少数人,应当是精英教育。他说:“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8]144。他认为这为数不多的“精神贵族”才是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对象。就高等教育的目的而言,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从意志力极强而且具备足够条件的人之中挑选出一些人来接受大学教育”[8]157。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方式和甄别标准,“大学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8]145,“选择的标准在于:具有追求真理的意愿和准备为之而接受任何牺牲的精神以及对精神世界孜孜不倦的追求”[8]157。
可见,一方面雅斯贝尔斯提倡教育民主化和教育机会均等,但另一方面,他认为高等教育之门只应为那些天资优异、能力超群的学生敞开,并且从教育对象、教育目的、入学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精英高等教育蓝图。
六、结语
在20世纪的这五大教育流派当中,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科南特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流派所持的都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观,而自由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这三大流派则坚持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观。但从后面的三大流派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们所持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倡导教育民主化,反对教育的特权化和宗教垄断,认为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同时他们并不是强调平均主义的教育民主,而是提出高等教育只能为才能优异的人所接受。由此可见,在这五大教育流派中,虽然他们秉持不同的精英和大众教育倾向,但事实上各流派都蕴含着明确的教育民主化和现代化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普及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世界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罗素.教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2]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8.
[4]科南特.科南特教育论著选[M].陈友松,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5]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69.
[6]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69.
[8]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责任编辑吴朝平)
AnInterpretationontheValueOrientationaboutEliteandMassEducationofSchoolsofWesternEducationinthe20thCentury
DONG Zhixia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Haidian,Beijing100191,China)
There were five schools of western education in the 20thCentury.They were liberalism, pragmatism, essentialism, perpetualism and existentialism which had a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mong of them, the schools of pragmatism and essentialism proposed the view of point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ones of liberalism, perpetualism and existentialism presented elite higher education.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t view of point, they all imply the thought of educ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hich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schools of education; elite; mass
G640
B
1673-8012(2013)01-0109-04
2013-01-16
董志霞(1976-),女,内蒙古包头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创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