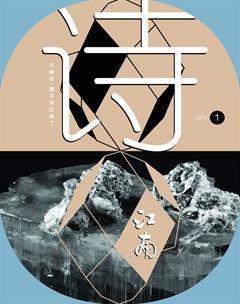有的词句是需要裁减的
汪剑钊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臧克家的才华是无可否认的。相传,1930年夏,年轻的诗人报考青岛大学。当时,在入学考试中,国文出了两个题目,一为《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为《杂感》,两题任选一道。臧克家两题都做了。关于后者,他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就是这三句“杂感”引起了初到青岛大学主持文学院工作的闻一多的欣赏。对此,他在回忆录《诗与生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我到注册科报到的时候,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姓庄的职员,看到我的名字,笑着瞪了我一眼,报喜似的对我说:‘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入学后,在闻一多的提携和推荐下,臧克家的才华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经常在《新月》、《现代》等杂志上代表作品。在校期间便出版了诗集《烙印》。
臧克家于1932年创作的《失眠》便带有明显的新月派诗歌柔美的风格特征:
一只一只生命的小船
全部停泊在睡眠的港湾
风从夜的海面上老死
鼾声的微波在恬静地呼吸
只有我一直还冲跌在黑夜的浪头上
暴风在帆布上鼓荡
心,抛不下锚
思想的绳索越放越长
诗的开篇以“生命的小船”自然地引出“睡眠的港湾”,带有体温的文字从一个比喻过渡到另一个比喻,显得贴切而启人想象,尤其出句的“一只一只”更是营造了一段滞重、徐缓的节奏,渲染出夜的深邃与压迫。三、四句再由“风”的“老死”拈出“鼾声的微波”形象地渲染了周围“恬静”的氛围,藉此反衬我焦躁难抑的“失眠”。整首诗的意象带有层层递进的特征,由“船”停泊在“港湾”,进而“冲跌”在“浪头上”,将辗转反侧的心绪,借用“锚”的无法“抛”下描摹了出来,把一个日常的生活现象所释放的负能量转化成了诗意的正能量。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首二句以“寒”韵相押,随后两句的韵脚为“齐”韵,韵式为“aabb”,接下来则以“江阳”韵“ccdc”相缀连,较好地体现了闻一多所倡导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特征。透过此诗,我们可以约略发现,早在三十年代初,臧克家的诗歌艺术已抵达了一个不低的高度。这一时期写下的《难民》、《老马》、《洋车夫》、《当炉女》和《罪恶的黑手》等一连串佳作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年轻诗人血脉中所流动的“农民的血”。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闻一多、王统照的赞助下得以出版,随后,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茅盾不无慷慨地认为,在当时的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朱自清则断言,正是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这类诗歌出现以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自此基本奠定了他中国“乡土诗歌”第一人的地位。
不过,迄今为止,诗人臧克家的作品中传播最广的作品却不是上述提及的那些诗歌,而是《有的人》。这首诗因体现出较强的艺术概括力并迎合了主流宣传的潮流而传诵一时。如今,它又被选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二(下)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六年级(上)的《语文》课本,更为其流传提供了格外的便利。《语文》编选者的用意其实也不难揣度,其一当是为纪念鲁迅以及和他一样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其二则是为中小学生提供一个诗歌的范本,同时也肯定臧克家作为一名杰出诗人的写作之成就。根据史料记载,《有的人》创作于1949年11月1日,它是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写成。诗人对鲁迅先生一直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他在自述中曾如是表达:“读他的书,景仰其为人,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黑暗时代,鲁迅的作品像一道明光,引导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探索,郁抑的心情好似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口子。”这种由衷的感佩之心为作者铺垫了一个较好的创作起点,激发他创作出了警句式的前面四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短短十八个字,完成了两则充满悖论性的陈述。诗人对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其中饱含了对轻于鸿毛的生和重于泰山的死的深刻思考,它们以浓缩的语言为生命的价值做出了恰切的判断。至此,应该说,这首诗在题旨和韵味上实际已经完成,就像一座艺术之屋的建造到达了“封顶”的阶段。
毋庸讳言,作为一首纪念性的作品,《有的人》一诗明显带有五十时代初已初露端倪的“主题先行”之印痕。或许正是因此,臧克家似乎忘却了内心关于“简练含蓄”的艺术追求,也不再强调“以经济的字句去表现容量较大的思想内容”,而是开始为主题而造情,为结论而搜寻词句,仿佛怕读者不能理解自己的创作用意似地,加上了一大段近似散文的说明,于是,把读者的思考空间给塞满了,不留余地。当我们读到随后那些诸如“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且不说“作牛马”的意识或许还存在某种旧意识的残余,哪怕从意象和语词的精简和凝练来看,它们都是零碎的文字,更宜出现在散文的文体中。尽管它们因押韵而造成了一定的声音效果,但无法掩饰词语缀连上的缺乏节奏,因而成为诗歌中很大的败笔。对它们的诵读,除了能够像政治口号一般振动读者的耳膜外,很难在后者的艺术感受域中引发美的触动。
臧克家写作中出现的这种情形令我想起了美国诗人庞德的一则写作轶事。庞德在1916年写道:“三年前在巴黎,我在协约车站走出了地铁车厢。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然后又看到一个,然后是一个美丽的儿童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那一天我整天努力寻找能表达我感受的文字,我找不出我认为能与之相称的、或者像那种突发情感那么可爱的文字。那个晚上……我还在继续努力寻找的时候,忽然我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不是说我找到了一些文字,而是出现了一个方程式。……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许多颜色小斑点。……这种‘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我发现这对我为了摆脱那次在地铁的情感所造成的困境很有用。我写了一首30行的诗,然后销毁了,……6个月后,我写了一首比那首短一半的诗;一年后我写了下列日本和歌式的诗句。”这“和歌式”的作品就是庞德仅有两行的传世名作《在地铁车站》:“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这首诗因为作者刻意的“提纯”而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其迸发的力量和催人想象的潜能甚至超过了许多长篇的史诗。庞德在另一个地方回应读者的疑问时说道,他之所以把头两次写的30行诗、15行诗销毁,是因为诗歌含纳了不少属于“次等强烈”的元素。
无独有偶,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一则传闻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艺术应该有自己的“减法”。1891年,罗丹从法国文学协会那里接受了制作巴尔扎克雕像的任务。为了创造一件艺术精品,罗丹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寻找模特、构思草图,捏塑模型,等等,有时甚至在完成了一座塑像后将它粉碎再重起炉灶,最后,他终于将心目中真正的巴尔扎克形象塑造了出来。作品完成后,他满意地请到自己的三名学生来欣赏。结果,其中一名学生布德尔在较长时间地盯视了塑像那双逼真有力的双手之后,直率地告诉自己的老师,它们显得非常生动、非常有力。对此,罗丹的反应却是,毫不犹豫地拿起锤子将它们砸掉了,尽管此前罗丹为塑造它们曾经付出不少心血,并且获得了如此出色的艺术效果。因为,这双手已经具有独立的生命,不属于雕像的整体了,如果留下它们,只会喧宾夺主,进而破坏整座雕像的魅力。于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巴尔扎克像就洋溢着某种残缺的“美”:穿着一件多明我会的长袍,高扬着雄狮般头发蓬乱的头颅,吊着两只空荡荡的长袖……
这两个分属诗歌和雕塑的例子告诉我们,创作有时需要舍弃那必须舍弃的部分,需要去除那些影响整体表现效果的“次强烈”的元素,去除那些影响良苗生长的“莠草”。明白这一点,我们大约也就知道《有的人》这首诗的瑕疵所在了。为此,我想模仿庞德的做法,为这首诗“瘦身”: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如果要对这首诗作进一步的删削,或者说“割爱”,那么,有的词句“有”了比“没有”更糟,同时,有的词句“没有”比“有”更好。这样,我们不妨留下那最深入人心的四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