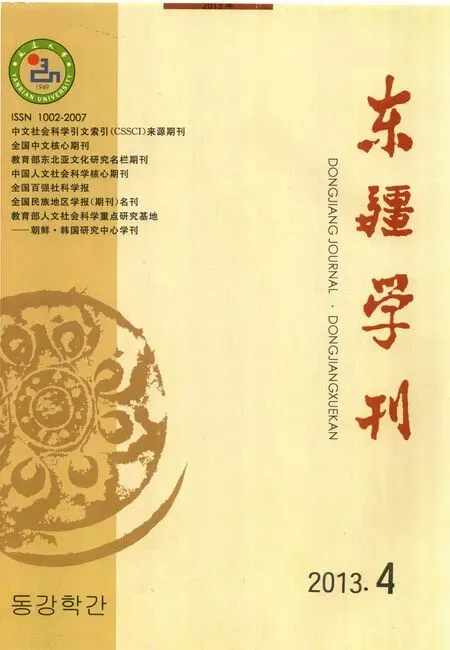日本文化空间下日本动画的“狂欢化”色彩——兼论日本动画的无法模仿性
高 晨
日本的文化特性与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日本“岛国”的自然特征,孕育出日本对自然无比崇拜的民族本性。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培养了日本人对内狂欢和对外含蓄的矛盾性格;在不断地学习外来文明中,日本文化保持着自我个性的同时,也培养了吸收外来文化的习惯。矛盾性和杂糅性便成为日本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毫无疑问,日本动画作为日本文化的载体,也继承了矛盾和杂糅的特性。在各国竞相展示民族文化个性的时代,日本以动画为载体打造“文化大国”的形象,主要依靠日本文化空间中杂糅的外来文化元素,拉近日本与世界的距离,以日本文化空间中的陌生化矛盾元素吸引观众的视线。
对于日本动画中日本文化因素的分析,中国学术界已付出了很多心血,但始终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日本会产生独特的日本动画?为什么日本动画会将世界文学变换面貌?为什么被日本动画变换形象的中国文学会遭到中国观众的嫌弃?为什么中国动画模仿日本动画会以失败告终?这些问题一直苦苦困扰着中国动画创作界,更是中国动画研究的未解之题。
统观日本各类动画,往往上演着人与自然、人与神妖、人与人的“狂欢庆典”,庆典中世界各国的各界生灵都在日本文化空间中重新装扮。故事在与世界文学的杂糅中发展,人物在矛盾中塑造。究其原因,日本文化空间具备消解国与国的边界、人与神妖的界限、人与人的隔膜的能力。日本动画的“狂欢化”色彩正反映出日本文化空间的个性特征;日本文化空间也因此成为了巴赫金“狂欢化”范畴中的动画符号。
一、日本文化中的动画性
提到日本文化,不得不提《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教授在没有踏上日本国土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将日本文化总结得很清晰,可以想见日本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的单薄。书中她开篇便总结日本人的心理特征: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踞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1](2)
在以上表述中,读者感到的是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而对于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早在《古事记》中便有描写。日本神话主神天照大御神的弟弟速须佐之男命在天照大神的大殿上拉屎,“天照大神并没有加以谴责,反而替他辩解说:‘那些象屎的东西,其实是我兄弟酒醉后呕吐出来的。至于毁坏田埂,填平沟渠,是因为他爱惜土地才这样做的吧!’”[2](20)面对弟弟将织女惊吓而死的惨状,这位姐姐却也只是躲进天之岩户不出来而已。最终将这位凶残的弟弟赶出天界的不是温柔的姐姐,而是愤怒的八百万众神。
与温柔的天照大御神相矛盾的是她的母亲伊邪那美。据《古事记》记载:日本民族的祖先七代神祗哥哥伊邪那岐和妹妹伊邪那美结合,生出了日本各岛屿。然而,这对兄妹没有美好和睦到永远。当伊邪那美生火神时不幸去世,她的丈夫悲痛欲绝,到黄泉去求她回来。伊邪那美不准丈夫看她现在的模样,但伊邪那岐忍不住偷看到妻子的污秽。伊邪那美从此与丈夫恩断义绝,发誓每天勒死丈夫土地上的一千人来报复他对自己的不忠。而这种不忠不是因为丈夫有了别的女人,而是因为没有听她的话,做了令她难堪的事。
在与日本文化接触过程中,会感受到两组矛盾的日本性格:在日本母亲的温柔背后还潜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恶”;庄严的神职人员还具备着常人无法相比的色性;武士是忠诚的象征,同时也是反叛的代表。而在审美情感方面:日本文化中深沉的物哀与外露的可爱;对自然的崇拜和对机械文明的狂热;武士道中的强者意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集团意识。无不体现着日本对传统文化既继承又反叛的历史个性,这种文化个性在日本动画中也表露无遗。
《西游记》作为被日本动画改编最多的中国文学,它的身上已被标注太多的日本文化特征。在众多改编版中,神佛形象大多被塑造成具有庄严的假面和轻浮内在的形象。《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改编过程中,高大的三国男性英雄普遍被外表温柔可爱而深爱暴力的美少女所代替。然而,女版三国英雄往往因为简单的个人情感就与主公倒戈相向,与原著中信奉大义的男性英雄们相比,战争、权力显然只是她们的玩物而已。以完美表达日本独特的审美情感——“物哀”著称的《源氏物语》,在动画中除却悲伤的基调外,人物形象也表现得活泼可爱。日本动画在表达对自然尊崇的同时,还呈现出对机械的狂热喜爱。例如,宫崎骏的动画一直在寻找将自然与文明和谐共存的“博爱”。可以说,正是动画的夸张、梦幻为日本文化的矛盾性提供了舞台,与其说是日本动画传播了日本文化,不如说是日本文化在现代与动画的碰撞中,迸发出日本动画狂欢的“花火”①日语中,花火是烟火的意思。。
日本独特的风土人情促使其产生了矛盾的、内外有别的处世方式,“日本文化从其源头就具有封闭的空间观念,内外分界、你我有别、对内依赖和对外排斥,乃至划分势力范围是其基本的政治逻辑。这种特点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体现为两种行为原则,即对内与对外的不同。”[3](112)对待外国,日本采用世界普遍道德观,而对待本国人民,则采用日本的道德标准。因此,在外国文化进入日本时,一定被日本文化所改造。这时的文化变异不以对外来文化的尊重为前提,而是以符不符合日本人的喜好为标准。因此,外来文化从来没有触及到日本文化的内核。可以说,日本文化以高傲的不规则选择权,有选择地对外国文化进行排斥,对与自己有异的文化现象进行极端的变异,从而引发原产国的争议,这也是日本文化矛盾性难以为他国接受的原因之一。在矛盾性指导下塑造的日本动画中的他国文学形象,自然也引发原产国的争议。
除了人物形象的矛盾性表现,日本动画还经常创造奇怪的景象:《圣斗士》中,古希腊神话、北欧神系、埃及神话、中国神话和印度神话中的“神”纷纷登上舞台。他们分为正邪两派,在现代日本展开武斗,争取地球的统治权。《圣杯之战》更是云集世界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展开了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战争。根据《小仓百首》改编的动画《歌之恋》,用后现代的手法描写着和歌作者们感伤而波折的情感历程。即便是在日本战国时代的纷纭历史,日本动画创作者也经常在人物对话中加入英语、汉语以突出英雄人物的性格。这些吸引观众的世界文化集锦和语言杂烩,在日本创作的每一部动画片中都有所表现。这并不是偶然所为,而是日本文化的杂糅特性与极具包容性的动画艺术的共识。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中,对日本文化的杂糅特点作了形象的表述:
可以称得上对日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方面是迫近大海的山和水边的松林、隐现在松林背后的渔村的白墙、那个水墨山水画常常描绘的古老而美丽的日本,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世界;另一方面,船从玄海滩一进入关门海峡,船的右侧便呈现北九州的工厂区、林立的烟囱冒出的烟柱和高炉的火光以及活跃勤奋的国民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现代的”日本。……港口的栈桥也好、起重机也好,大街的西式建筑物也好、风俗习惯也好,一切都是日本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由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日本的文化不正是典型的杂种文化吗! 所谓杂种,即指在根本上而并非枝节问题。[4](3~4)
“和魂洋才”这一提法恰当地表明了日本杂糅精神与富国强民发展目标的紧密联系。作为日本文化产业支柱的日本动画,更将这种精神体现出来。
日本的文化空间,以矛盾性为经,以杂糅性为纬,两方面相辅相成。日本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原本的文化个性已与学习来的其他民族特色相融合,具有个性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普遍性。日本由于其历史短,文化薄,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借鉴他国文化以期达到加速文化发展的目的。可以说,正因为日本文化的杂糅性习惯,才有今天影响世界丰富多彩的日本动画。原本迫切的“拿来主义”思想,无意中创造出独具陌生化风格的动画性格,是日本文化由“输入”到“输出”的成功转型。
二、中国无法复制的日本动画
日本动画一方面杂糅他国文化,创作新颖而活泼、丰富而个性的作品,受到世界观众的喜爱;另一方面通过动画,将日本文化远播世界。当代,日本文化产业成功树立起文化“输出”大国的形象。因此,中国在振兴动画产业的道路上,以日本动画为榜样,希望沿着日本动画的创作经验,可以激发本国动画创作革新的热情。
中国大陆在成为世界动画加工基地后,政府对国产动画制作越发重视,先后扶持了一系列原创动画,但是这些原创作品从内容和画风上都明显带有日本动画的痕迹。例如在社交网络中引发了诸多争论,例如中国动画《大耳朵图图》的语言、人物形象中发现了日本动画《蜡笔小新》的影子;宣传中国围棋文化的《围棋少年》也被认为有抄袭《棋魂》的嫌疑;而《我为歌狂》中极端的人物形象和青少年爱情的描写也有模仿《蓝球飞人》之嫌。与其它国内动画加工公司不同的是,上海美影厂依然生产着“具有本国特色的教育性儿童动画片。每年要完成 300—400 分 钟的动画片”[7](311)。另一方面,美影厂每年还为海外公司生产“ 500—700分钟(动画片)的订单”[7](311)。1995年,上海美影厂制作出品、由张光宇先生的同名漫画改编的《西游漫记》,第一集中塑造了模仿手冢治虫的动画片《悟空大冒险》的人物形象。后因观众反应,从第二集开始四人造型回归了传统。由此种种表明,中国在模仿日本动画创作的过程中,深感无力和无奈。探究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中日文化基本特征的差异。
矛盾存在于事物之中,事物的矛盾又各具特征。然而,由于其产生的自然环境不同,矛盾的存在方式也有差异。同为文化,中华文化也存在矛盾的特性,但是又区别于日本文化的矛盾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综合地独立地发生的民族文化”[8](48),因此,中国拥有很多世界上第一的文明创造,这表明中华民族是最早开始具备理性概括的民族之一。然而,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人也对自然有着深深的敬畏。十三经之首的《周易》便是中国人运用理性对自然的高度概括,应用理性为自然解码,解码后的自然规律再应用于农业生产。在中国先秦时代,便出现无神论思想,“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的儒家和道家皆表现为缺乏超自然人格神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说”[9](16)。中华文化在既尊崇自然又挑战自然的矛盾中前行。这种矛盾潜藏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中国古代文人,他们一方面有入仕(挑战)之心,但当入仕得不到实现时,则会选择出仕(顺应自然)。比如,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探索的苏轼和整体作出出世选择的魏晋文人,他们的出世之选大都出于无奈。在中国文化矛盾的两方面中,一方是文化主流,另一方则是为无法成为文化主流时提供的一种退隐自然的生存态度。
与中国文化的矛盾性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矛盾双方势均力敌。矛盾的相互并列,没有强弱之分,也没有主流与次要之别。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是人性的表现,是自然的天性,是对人性的一种顺应而后的选择。日本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矛盾的自然天性,也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阻隔在外。当外民族的科技触碰到岛国时,日本文化便饥渴地吸收着先进文化的养料。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华文化,是影响日本文化性格最深的文化资源。
独立发展衍生的中华文化、广阔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文化交流是庞大的中华文化的建构基石,早在先秦时期便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儒家思想。儒家以伦理学说规约思想,以“道”总括规律,以普遍教育的形式传授治世之道,在汉族文化占主流的文化背景下,儒学将中国政教统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但因其崇“道”而不推崇神灵信仰,因此缺少身份意识,呈现开放的文化姿态。然而,这种开放的姿态是建立在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思想体系下。早在两汉便传入中国的佛教,也是在与儒学融合后,支持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才得以保留和延续。中华文化君王般的包容性与日本文化的杂糅性有着很大的差异。
自然赋予了日本人传统的审美情感,外来文化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经验,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逐渐形成具有独特杂糅特征的文化。因此,日本拥有自己独特环境下产生的自然性格,但无法形成文化,是外来文化填补了日本文化的缺失。可以说,日本文化是自然本能支配着的文化空间形态。
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存在着矛盾性,在文化交流中,各民族文化都具备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开放性。然而,独特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独特文化精神的不同,促使其文化的矛盾性和开放性显现出不同之处。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差异势必影响着两国的动画创作。只有日本文化空间下出产的日本动画,才可能继承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和杂糅性特征。
只有成功进行文化输出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当今的“文化大国”。日本将世界文化全盘吸收,发挥其传统文化优势,将它们吸收重组输出。然而,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在面对日本动画的文化输出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压力,因此,中国动画界以学习和模仿日本为榜样。在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和消化日本动画成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会产生日本动画的问题时,便急于求成,势必遭遇挫折。因为,独特“狂欢化”个性的日本动画,呈现给世界观众的陌生化感受,是对日本文化空间的镜象反映。
三、狂欢化:文化空间的镜象讲述
动画片是综合性艺术,“因为动画片的拍摄对象是通过造型艺术手段制作出来的形象,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动画片都具有重新赋予或重新塑造的特性”。[10](14)正因为这种特性,与其它艺术相比,动画更可能打破各艺术间的界限,形成综合多元的艺术形式。巴赫金在分析陀氏体裁和情节特点时认为:
狂欢化帮助人们摧毁不同题材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化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之所在。[11](177)
极强开放性的“狂欢化”理论,显然非常适合概括动画艺术的特征。
动画作为一种流行世界的艺术形式,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民族化动画特征。动画是对文化的反映,继承了本土文化特征。日本动画对外不仅展露出外国人普遍认识的严肃而呆板的日本人形象,还大胆展现了矛盾的日本性格。日本文化选择了动画表现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认识蕴含在生活之中,是日本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日本动画描述着日本人的生活,以日本的妖怪、神仙、人与人的关系等为创作内容,既描写古代日本的历史景观,也反映当代日本的精神世界,日本人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日本动画创作的内容。
由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改编的《一骑当千》、《恋姬无双》等系列日本动画片,将三国男性英雄变异成为既温柔又泼辣、凶狠的女性形象,体现出日本女性文化的矛盾;在《西游记》中添加复仇情节,表现了日本武士道中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并存的矛盾性;将世界神话融入一部动画片中,诉说日本神系与世界神系的融合;让日本古代历史人物身披现代机械铠甲,说着夹杂着英语的日语,最直接地表现出了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杂糅特性。
对于在日本文化空间下生活着的日本观众,日本动画的“狂欢化”式创作是最符合他们审美情趣的娱乐。在日本随处可见手拿漫画的人,动漫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娱乐方式。因此,在普遍的民族审美基础上,日本动画自然不断提高,进而成为世界动画大国。而中国从其传统文化便可看出,这种夸张的毫无顾虑的幻想式动画创作,很难得到文化认同。因此,日本动画只有在日本文化空间下才会产生,而中国动画界在模仿中只会迷失方向,并且中国文化并没有为大动画产业大发展创造一个可行性空间。日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周边产物,为动画提供了发展空间。中国之所以感到对日本动画模仿的可能性,不在于个性上的相似,而在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动画的误导而非真正的指导。[11](108)
中国是个文化大国,几千年来中国最引以为傲的便是深广的中华文化。在象征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学作品被进行一次又一次改编的时候,我们违背中国文化而模仿日本制造,只能使中国动画越走越远。日本动画的腾飞有着日本文化的支撑,日本文化非常适合创作变幻无常的日本动画,只有日本矛盾而杂糅的文化个性构筑成的空间,才能够生产出如此“狂欢化”的日本动画。
当今世界的多元化生活,急需多元化的“狂欢化”色彩加以装扮。文艺这种已传承几千年的文化载体,也在逐一进入多元化的文化空间。无论是对传统的变异改编还是对未来的幻想,文化都是不可替代地标识民族个性的最好符号。最具狂欢化色彩的动画,作为影视艺术的一个分支,已引起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关注。作为人文与科技结合的平台,动画无疑要以科技和文化为基础。对于大力发展科技普及的中国动画界来说,文化创作却成为最为薄弱的一环。当年日本遣隋、遣唐使们以几十年之功,只为学习中国文化。他们把大量的中国书籍带回日本,其文学、历史、科技、宗教等等无所不包。因此,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是由‘书籍之路’造就的独特文明景观”[12](98)。通过阅读世界书籍学习和感受到的综合审美,才促使日本形成今天独特的文化空间,衍生出风靡世界的日本动画。反观今天,还在简单模仿日本、美国的中国动画,更应该加紧对中国文化个性的发掘,这才是日本动画给予中国动画的最好启示。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日]安万侣:《古事记》,邹有恒、吕元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潘畅和:《日本文化的发生学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
[4][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杨铁婴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5][美]约翰·A·兰特:《亚太动 画》,张慧临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6]顾晓鸣:《中国文化特征形成的文化学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7]韦元:《论中国宗教的包容性》,《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0卷。
[8]贾否、陆盛章:《动画概论知识.概念》(第二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9]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王勇:《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日本学刊》,2007年第6期。
[11]李琦珂,曹幸穗:《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