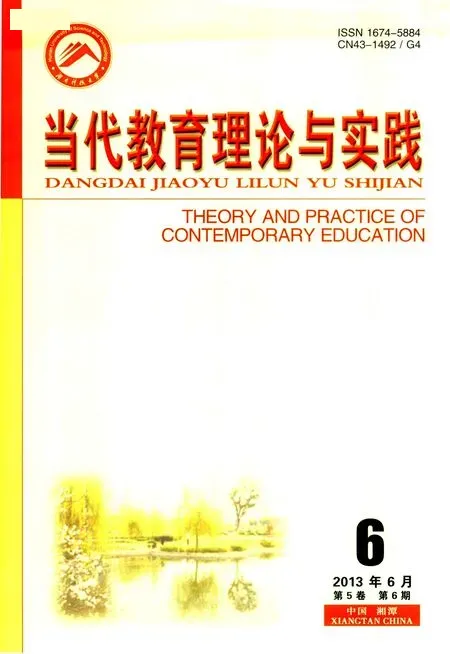论川端康成《雪国》中新感觉主义建构下的女性美
秦 亚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雪国》是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之一。其创作时间从1935年起到1937年止,曾以相对独立的短篇形式,断续地在多种杂志上连载。其完成标志着川端康成在创作上已经成熟。它是一部登峰之作。《雪国》是一部日本现代抒情文学的经典,是一首日本唯美主义的绝唱,是一副带有独特而神秘东方美的画卷。细读其中,便会发现在这片白茫茫的雪国中营造了一个属于女性之美的感觉世界。瑞典皇家科学院表彰他有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现聚焦《雪国》中的主要人物——驹子和叶子,来探讨其新感觉主义建构下的女性美。
一 主观的表现
新感觉派文学是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片冈铁兵认为,新感觉主义理论相信主观的力量,相信主观的绝对性,立足于“扩大主观”,把个我看作是存在的核心,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个我”的变现、补充或者阻碍[1]。川端康成在《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一文中强调:没有新表现就没有新文艺。新感觉主义是“感觉的发现”。他强调说:“感觉至上,亦即直觉论,就是高度的精神性,……天地万物都存在于自己的主观之中,外界只不过是主观世界的扩大而己。”
《雪国》中的女性美的描摹常常是来源于川端康成的主观直觉。什么是新感觉,川端康成举过眼睛和蔷薇的关系这一例子。一般的文艺是我的眼睛看到了蔷薇,眼睛和蔷薇是两种东西;而新感觉则变成为我的眼睛就是红色的蔷薇,将二者当作一件东西来看待[1]。这种主观的表现来自于作者直观的感觉。《雪国》中岛村在火车上初见叶子,出现暮景幻影就是一种主观的表现。叶子的脸,玻璃,窗外流动的山林之景和灯火,三者本是三种东西,毫不相联系的;在川端康成敏锐的洞察力下,这三者连成一条线,缺一不可地共同浓缩在被雾气布满的玻璃镜子上,成为一副流动着的,似有似无的画卷。人是透明的,镜子是模糊的,景色是朦胧的。单独看,都是真实存在的,联系起来便成了幻景,深刻地刻画出了叶子的神秘之美、充沛着精灵之气。
在对驹子外貌之美的描写上,川端康成也是非常注重主观表现的。岛村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他远离城市,在寒冷的冬天来到这个偏远的、冷清的雪国,就是对自然的追求。岛村眼中的驹子之美总是与自然景物相互映衬。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川端康成就是用这种物我合一的主观感觉来体现驹子的纯净之美。她的出尘脱俗总使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初夏群山的郁葱、一尘不染是驹子的自然脱俗。山野的色彩使她娇嫩得好像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镜子里白花花闪烁着的原来是雪。在镜中的雪里现出了女子通红的脸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2]这又是一个镜子、雪、脸颊的画面重叠,川端康成特意强调雪是白花花的,而驹子的脸颊是通红的。一片白色中的一抹红,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色彩对比,这种直觉带着赤裸裸的震撼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种感官的视觉享受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的诱惑美。
《雪国》中驹子和叶子的美总是相平行而存在的。平行是因为有驹子的存在就会有叶子的出现。在行男、岛村这两个男人的生命中都是既出现驹子又出现叶子。对于行男来说,驹子是他“家人”式的未婚妻,叶子是她的情人。对于岛村来说,驹子是倾慕他的人,叶子是他倾慕的人。驹子和叶子就这样平行地踏在两个男人的世界里。她们的美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
川端康成的主观体验具体表现在岛村这个男人对这两个女性的主观直觉。他总是自觉地将这两个女性的美在心中进行对比。两个女性的形象便在岛村的直观感觉中呈现出来:一个是凭着指头的感触而记住的女人,一个是眼睛里有灯火闪映的女人。川端康成对这两个女性各有一段镜中幻象的描写来突出各自的美:叶子的幻境是暮色中火车上玻璃窗与山林之景的混合,这是属于夜色的神秘之美;驹子的幻境是镜中白茫茫的雪与通红的脸颊混合,这是属于白昼的明朗之美。从这两处岛村对她们直觉的对比中可以读出驹子和叶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美:驹子是热情开放的,叶子是含蓄清纯的。
二 艺术的象征
新感觉派非常重视感觉的作用,认为“生命活在物质中,活在状态中,而联系实际的最直接的‘电源’就是感觉”。川端康成常用象征和暗示来描写主观感受的世界。外在形态是主观感觉的触发物,使之象征化、个性化,能刺激人们产生一种新的感受[1]。
“穿过县境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幕下一片白茫茫。”[2]雪国是一片白色的世界,从繁华的东京城里出来,穿过长长黑黑的隧道,迎面而来的就是一片白茫茫及催人清醒的清冷。有点儿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意味。黑与白两种对立的色彩在这里象征着一个城市和一个穷乡僻壤,黑色象征着城市给人的压抑感,白色象征着雪国遗世而独立般的豁然开朗。
雪国的雪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首先,雪是干净的象征,驹子这位看似不干净的女性也特别爱干净。她总是将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衣物放置井然有序,在与岛村说话时也时时刻刻注意着头发丝和烟灰。其次,雪是纯洁的象征。它既是驹子和叶子两位女性的美的纯洁,又是驹子对岛村、叶子对行男爱情的纯洁。这种纯洁是一种无杂质的执着。黑格尔说:“爱情在女子身上显的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火焰被第一阵风吹熄掉。”驹子和叶子的爱情执着地开放在这片雪国之都。火车站上叶子对行男不厌其烦、细微细致的照顾,宛如一个慈母,这种爱情已经上升到不离不弃的亲情的相濡以沫。叶子在提到去东京找工作时表示不愿意做护士,因为她一生一世只照顾一个人。行男死后,她日日上坟,衣带渐宽终不悔。叶子对行男的爱也是这样的执着,尽管不能在一起,尽管生离死别,也并不能影响爱的延续。驹子对岛村同样有着执着的爱,她渴望做一个正正经经的女人,渴望过一个正常女性的生活。她害怕岛村将她看待成一个艺妓,每每察觉,总要不依不饶的暗自哭泣。在这里,爱情的纯洁和执着彰显的是心灵之美。
在刻画驹子的女性美时,反复出现红色。鲜艳的红色,既是美的代表,又有热情的意义,象征着驹子对岛村热烈的,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爱恋。驹子在与岛村一起时,脸红的次数有多次,非常频繁。这种羞涩中暗示着三种信息:一是驹子的愧疚,为自己身为艺妓的一种困窘;二是这是一种小女生或者说是属于正经女人的羞涩,是驹子对岛村迷恋、深爱到无法自拔的表现;三是懂得羞涩暗示驹子心灵上的纯净,撕去她烟花女子的标签。为岛村眼中的洁净,甚至连她脚趾弯里也是干净的这一纯洁形象做铺垫,达到身心皆洁净的效果。
“右边是覆盖着白雪的田野,左边沿着邻居的墙根种满了柿子树。房前像个花坛。正中央有个小荷花池,池中的冰块已经被捞到池边,红鲤在池里游来游去。房子也像柿子树干一样,枯朽不堪了。积雪斑斑的屋顶,木板已经陈腐,屋檐也歪七扭八了。”[2]驹子住的房间原本是放蚕的。那是一个像旧纸箱的房间,黑压压的,冷冷清清,好像浮在半空,给人一种不安全之感。驹子就像一个蚕蛹一样,她洁净的、透明的身躯就栖居在这里。这里驹子的房外房内环境就象征着大的成长环境,暗示着这是一个生活在底层、卑微的喘息、凭着精神信念呼吸于天地之间而生存的弱女子。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三大问题之一的“饥饿使妇女堕落”,纯洁少女芳汀的故事使多少人潸然泪下。驹子为报恩而负担行男昂贵的医药费,为支付这笔钱而走上艺妓之路。如果可以,如果生活给她选择的机会,她一定会选择干干净净的,做个正正经经的女人,结婚生子。驹子就像蚕一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雪中缫丝、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晒,从纺纱到织布,一切都在雪中进行。有雪始有绉纱,雪乃是绉纱之母也。古人在书上也曾这样记载过。”[2]绉纱这个意象在表现女性美方面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岛村非常喜欢绉纱,甚至喜用它做贴身的单衣。雪国有雪,是绉纱的最好场地。纺织是很难的,姑娘们从小就要开始学,优质的绉纱可以来评定一个女人的等级,成为选媳妇的标准。绉纱特别凉爽而驹子的身体也是凉爽的。岛村对绉纱的喜爱象征着对驹子的依恋。岛村喜欢把自己的绉纱拿去曝晒,除去夏日的污秽象征着岛村在雪国两位女性身上得到的身心的净化和洗涤。岛村将绉纱的使用寿命与对驹子的感情之期相对比。绉纱只要保管得当,可以50年不褪色,而人的依别之情,往往没有这么长的寿命。暗示着离别的迫在眉睫,暗示着此情的不相守。
三 文体的革新
川端康成将文体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反复强调文体是支撑一个作家的价值,反映出作家的风格和特色[1]。他在《新文章读本》中提到,“考虑有生命的文章,是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宿命。”在《雪国》一文中,文体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
西方的意识流作品往往无视时间的顺序,也不考虑线索的设置和连接,一切都是自由的联想,没有任何界限。川端康成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不注重传统完整的故事情节,采用一段段的故事穿插其中,采用意识流的手法,但是保留了时间顺序。《雪国》是以岛村第二次来雪国为开端,与驹子相见后借助朦胧的意识活动,采用了大量的倒叙。穿插了岛村第一次来到雪国的回忆。这是现实与过去的交会。三次到访的季节性跳跃也大,第一次是在雪山满绿的登山季节,第二次是在下过一场初雪的冬天,第三次是在又一年的秋天。而每次到来,岛村对驹子都有不同的感觉,叶子则是在岛村第二次来雪国的时候认识的。时间的跳跃伴随着眼前的景象、过去的回忆、幻想的心理叙述剪辑组合,现实与虚幻交替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
结尾一段,叶子被困于大火之中,这副场景川端康成将其描绘得诗情画意,是一组慢镜头:“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僵直了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然而,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地毫无反抗,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斜着掉下来两三根架子上的木头,打在叶子的脸上,燃烧起来。叶子紧闭着那双迷人的美丽眼睛,突出下巴颏儿,伸长了脖颈。火光在她那张惨白的脸上摇曳着。”[2]这里采用了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是对传统文体的一场革新。这副美丽的图画是一种自由式联想,这种随心所欲的意识流完成了对叶子女性之美的最后塑造。在死面前,她是那么淡然从容不曾反抗,或许是因为行男的离去使她备受痛苦的煎熬,或许是生存太沉重,拥有那般心灵美的她已经不能再背负。叶子,这个被塑造得几近完美的女性,像美的幻影般的存在如同海市蜃楼,终是不容于现实的。川端康成把一个本悲惨的场景描写得如此美,是受佛教生死无常观念影响。他认为生命存在于一刹那,死亡只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死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起点。在他看来,“生来死去都是幻。”生是一种徒劳,死也是一种虚幻。所以,叶子的死被描写得优美而柔和,那是一种凤凰涅槃般的重生。火光在她那张惨白的脸上摇曳着,看到这一幕,“岛村忽然想起了几年前自己到这个温泉浴场同驹子相会、在火车上山野的灯火映在叶子脸上时的情景,心房又扑扑地跳动起来。”而且,“仿佛在这一瞬间,火光也照亮了他同驹子共同度过的岁月”[2]。火灾在极短的时间里把读者从现实中带出来,使读者穿梭于过去和未来之间。这正是意识流的典型表现手法。
“新感觉派”文学是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滥觞。大正十三年(1924),亦即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年,石浜金作、川端康成、片冈铁兵、横光利一、中河与一、今东光等作家为核心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它标志着“新感觉派”文学的开始。新感觉主义离不开主观的表现、艺术的象征、文体的革新这三个方面。它“捕捉新奇的感受和印象,表现在将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渗进客体中,使感觉升华。即使视觉、听觉、触觉乃至嗅觉对象化、客体化。”[1]《雪国》是川端康成新感觉主义走向成熟后的作品。其在直觉、象征、意识流手法的新感觉主义建构下的女性美代表着传统的东方女性美。她们纯洁、执着、质朴、善良,虽生在淤泥中,却始终保持着昂扬、虔诚的人生态度。
[1]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2]川端康成.雪国·古都[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陈 雪.川端康成感觉世界的构筑——《雪国》女性形象建构艺术手法探微[J].合肥学院学报,2011(7).
[4]何乃英.川端康成——新感觉派的理论家[J].国外文学,1995(1).
[5]张晓宁.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的“感觉艺术”[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1).
[6]范传新.洁白的幻想——川端康成《雪国》思想探微[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