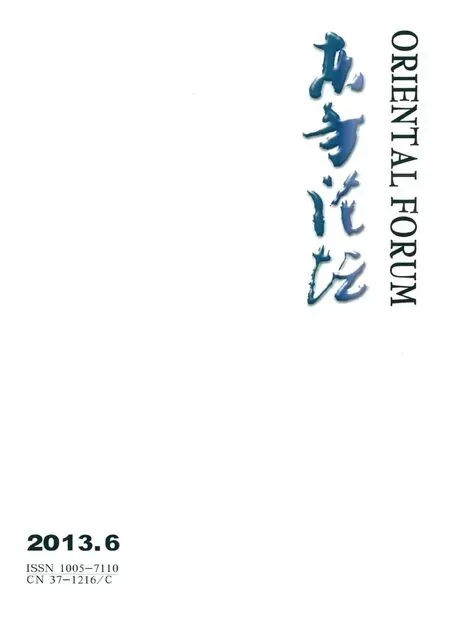“倒孔运动”:战时的抗争政治
吴锦旗
(金陵科技学院 思政部,江苏 南京 210038)
“倒孔运动”:战时的抗争政治
吴锦旗
(金陵科技学院 思政部,江苏 南京 210038)
抗战后期发生在昆明的“倒孔运动”是战时大学生抗争政治的一种表现,它是一次无领导、无组织、无预谋而有目标的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的学潮,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而引发的。“倒孔运动”是大学生在拥护政府统治合法性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其目的在于反对官僚的贪污腐败。大学教授在学潮中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有“同情的旁观者”、“热情的鼓动者”和“急切的防范者”之分。“倒孔运动”的发生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政权一次预警,既说明国民党政权对大学校园党化努力的失败,同时也表明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资源在逐步流失。
民国时期;“倒孔运动”;战时;抗争政治
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学潮问题,学生成为大学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蒋梦麟曾做过这样的总结:“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失败。”[1](P87)而且学生势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学内部的斗争,它还会走出校门到社会上举起抗争的旗帜,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即闹学潮)来进行利益的表达和政治的参与,学潮就成为民国政治社会中一个常规政治参与形式。但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潮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逐渐收敛,大学校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毕竟在全民抗战期间再闹学潮就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发动学潮就会给人以破坏团结抗战的印象,因此在抗战前期学潮基本不再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学潮就销声匿迹了,事实上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学潮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学潮问题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学生运动就不再是完全自发的现象,而常常掺杂了政党的参与和争夺。对于学潮的起因,以往的许多研究者都把它归结为共产党的煽动和影响,认为学潮是共产党在国统区所开辟的“第二条战线”,如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就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爱国运动。”[2](P3)甚至国民党方面也认为学潮的发生,共产党是幕后的黑手。其实,这样的看法未免片面,因为在大学的师生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虽然能对部分学生造成一些影响,但却无法操纵整个学生群体,认为共产党能操控学潮未免言过其实。而国民党在大学中开展“党化”教育和管理,成效并不明显,反而引起大学的“异化”,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不满,造成了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立。 国民党自执政后对于“党化”大学一直不遗余力,其用意既是为了显示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视,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对大学的控制,以保持高校的稳定。抗战爆发以后,虽然国难深重,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希图恢复和重建大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3](P25-48)但国民政府却始终无法真正掌控大学。实际上,学生运动也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如果说1945年以后学潮更多地表现为“运动学生”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的学潮则更多的属于“学生运动”, 学潮的爆发更多是学生的一种政治自发和自觉相混合的集体行动,抗战后期的“倒孔运动”就是一个例证。
一、加值理论视角下的“倒孔运动”
“倒孔运动”是抗战后期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自发形成的两次学生运动,“孔祥熙与联大先后发生两次纠葛,联大学生名之曰倒孔运动。这是近年来学生运动的先声。”[4](P23)第一次运动发生于1942年1月6日,由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游行。当时在昆明的其他大学如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的学生以及一些中小学学生也赶来参加,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学生高呼“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号在闹市游行,并沿街用粉笔书写标语。[5](P288)第二次运动发生于1944年3月,孔祥熙为调停蒋宋两家纠纷去昆明,顺便去云大慰问被征调受译员的学生,结果会场遭到学生公开的侮辱和谩骂。[4] (P24)在严格的意义上,第一次的“倒孔运动”中,学生上街的示威游行可以视为学潮,而第二次由学生发起的对孔祥熙的人身攻击和辱骂,只能属于被动式的“日常抵抗”①“日常抵抗”这个概念是由斯科特所提出来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生活处境悲惨,在反抗过程中使用了“磨洋工”、“怠工”等反抗形式。参见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并非学潮。
学潮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抗争性质的集体行动,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这些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逻辑关系。斯梅尔塞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全部具备了这六个条件,集体行动就必然会发生。[6](P21)这就是所谓加值理论,可以用它来解释“倒孔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第一,学潮产生的结构性诱因。抗战的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秩序,山河破碎,家园沦陷,为了保存中国教育的血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次由东向西的高等院校大转移,其悲壮和惨烈实属罕见,成千上万的教授讲师、员工工友和莘莘学子,千里辗转,共赴国难,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乐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先是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战局危急,三校又从长沙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虽然远离战争前线,但并不安全。“从1938年9月开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便生存于时时有可能有日本侵略者的空袭危险中。……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之中,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大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情,部分师生在空袭中受伤甚至遇难。”[7](P56-57)蒋梦麟感觉“轰炸行为显然是故意的,因为联大的校址在城外,而且附近根本没有军事目标。”[8](P212)为躲避空袭,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的功课之一就是“跑警报”。除了战争的威胁外,真正危及联大师生生存的是贫困和饥饿。由于战时经济困难,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就使得学生的生活、学习处境不断恶化,正如有人描绘的那样,“战时一般的伙食都很坏,像我们这样不能生产的学生更不能例外了。……于是每日两餐就只有拿出嘴来和糙米‘战斗’了。”[9](P105)
第二,社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怨恨和剥夺感的产生。抗战初起时,全国的大学生大多随自己的高校内迁,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政府抗战事业,其中就有联大学生搞的“从军运动”。但皖南事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封闭了除开重庆以外的所有各地的新华报馆和生活书店,公开大批逮捕所谓‘奸党分子’以及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士。看一本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就可能受到盘查,学校里稍稍前进的活动都被认为‘危险’而遭受监视。于是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会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10](P2-3)正是战时政府对社会的整肃和对大学的严密控制形成了学生的怨恨和不满,这些被剥夺的心理因素在学生中开始积聚。
第三,一般化信念的产生。仅有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尚不足以引发学潮,在学潮发生之前,人们的结构性怨恨必须转化为某种一般化信念,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的一个共同的认识。[6](P65)而且这样的一般化信念不一定是真理性的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强化和扩大人们的怨恨和剥夺感。“这时国家由专制独裁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危机,一天天的严重。……看见了不合理的现象,年轻人是忍不住不喊的。”[10](P2-3)同学们意识到政府有问题,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善意的批评促使政府改进和完善。联大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的传统,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对于社会现实十分关注,反应也是最为强烈的,尤其是当一个坏政府出现的时候。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引发了联大学生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他们开始批评政府,并试图寻找其中的政治原因。也就是从那时起,联大学生开始深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通过学校各种活动和一些进步刊物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径进行猛烈的抨击,得到了师生的响应和共鸣,吸引了很大一批人投身于反对腐败、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去,完成了对学生的整合和动员,使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对立情绪日益严重,一旦有了导火索,积聚在人们心中的不满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第四,触发性事件的出现。当大学生形成了一般化信念后,学潮就为期不远了。而引起学潮的直接原因则是要有一个道德震撼事件作为触发机制,“它是指在社会运动刚开始时,未曾料想的事件发生或未曾料想的信息被公布,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愤怒,从而使其倾向于参加集体行动,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进行动员。”[11](P97)学潮的导火线就是所谓的“飞机洋狗”事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了香港。滞留在香港的许多文化界人士下落不明,联大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被困在香港,从香港传来的消息使联大师生焦虑万分。而此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却用飞机运送自己的私人物品,他家的狗和抽水马桶都用飞机运回了重庆。1941年12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社评中就对此做了影射性的指责:“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当敛锋谦让,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顾忌。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义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12]此事一经披露,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本来,这事如果是别的要人干的,或不至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发生在集贪污,腐败,反动,愚昧于一身的孔祥熙身上,怎能不令人对数年以来腐败引起的愤懑,来一次总发泄!”[4](P23)孔祥熙贪污、腐败的行为早已令他臭名昭著。孔祥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与蒋介石是连襟关系,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1933年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1935年任代理行政院院长。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确立起战时行政体制,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甚至国民内部重要成员唐纵对孔祥熙也很是不满,“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13](P253)
第五,有效的社会动员。这里的社会动员就是信息的快速传递。当时承担信息传播任务的主要是报纸。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了避免滞留于香港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成为日军俘虏,决定派飞机将这些人抢运回内地,《大公报》社长胡霖也在被抢救之列。结果1941年12月10日,从香港起飞的最后飞机到达重庆机场时,《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但并未见到胡霖等人,反而是见到了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登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报道《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这篇报道写的很简单,并没有实质性内容,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逃避当局的新闻检查。而后由王芸生写成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箱笼、老妈和洋狗,矛头直指孔祥熙,该评论违背当局审查不准刊发禁令,全文在《大公报》上发表。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之评论,将题目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洋狗”事件遂被突出。不过这却是一篇不真实的报道,关于孔祥熙家用飞机运狗之事,版本比较多,其大意相同,但在细节描绘上有差异,有人考证此事很可能是子虚乌有,但却以讹传讹,沿用至今。①详见杨天石:《“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王晴佳: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在课堂上借古讽今:“南宋亡国时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14](P101)吴晗的言论无异于是变相动员,对学潮的发动起了助推作用。
第六,政府对大学控制力的下降。国民党执政期间,一直试图对大学进行控制,而抗战前政府对高校党化教育的效果还是比较糟糕的,[15](P126-127)政府希望掌控大学的努力经常会受到来自学校和学生的抵制。“1938年陈立夫出长教育部,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继续战前管理教育的一套做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尽管在党内与陈立夫不属一派,但却执行大致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教授,在大学开展党务和团务的工作,以求掌握学生。姚从吾等人受命于朱家骅,在联大组织建立三青团直属分团,鲜明反映了这种意图。”[3](P25-48)战时的高校中出现了“教师入党,学生入团”的风潮,但问题是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国民党政权控制大学的举动并不成功,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西南联大期间,“国民党对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的加强了。……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16](P301)
“倒孔运动”的学潮正是由上述六个因素层层递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一般信念的形成,因为这是集体行动参与者所持有的共同实现意识,不过斯梅尔塞加值理论模型认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因为一般化信念的形成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6](P66)“倒孔运动”也是一个非理性的以学生的情感宣泄为特征的集体行动。
二、“倒孔运动”中的动员、组织和话语分析
从“倒孔运动”发生过程来考察,这是一次无组织、无预谋、无幕后推手但却有具体目标的偶发性集体行动。“先是,有国民党党籍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细描述了飞机运洋狗之事,全校为之喧嚷。接着有一‘响应’壁报出现,继‘响应’之后,各系会,学会,级会,同学们都有响应的启事,不到两小时,新舍里头尽是打倒孔祥熙的口号标语,和有关时局报导,如此鼓噪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上午,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同学在全体必修的中国通史班上提出游行的主张,而且立刻整队向新校舍出发。新舍同学随即全体自动在图书馆前集中,经过十几分钟的讨论,决定上街游行。事先没有游行的准备,在几分钟内,同学们拿出自己的白被单做旗帜,各人掏出钱来购买毛笔写标语。事情发展之快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常委闻讯后,也跟着游行的队伍上街。联大的学生走上街头时,有中法大学和几个中学及小学的同学云参加,游行以后,全体大会决定通电声讨孔祥熙,要求政府改良政治。”[4](P23-24)相对而言,学生运动比较容易发动,它往往不需要有领袖人物的导引,也不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在学生中的渗透和动员,只要有一两个人振臂一呼,就可以得到群体的响应,这主要和学生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学生运动往往会在校内某一特定地点开始,领头学生在此地一闹,吸引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就围着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游行,呼喊口号做出种种响动以吸引学生。大量的学生于是出来支持、围观、起哄,游行队伍因此而扩大。”[6](P40)可见,大学校园中拥挤的生活环境使学生彼此之间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动员,吸引大学生参与学潮。不过缺乏组织性的学潮很难持久,常常表现为一哄而起和一哄而散。“倒孔运动”也是如此,“可是没有健全的组织,至第四天以后,三青团的同学受到长官的训斥,一反其原来态度,从中阻碍事情的进行;另一方面,康泽从重庆飞来,伸出一只阴暗的巨手。造成恐惧。而现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校长声色俱厉的从正面劝说同学停止活动。于是这一运动就无声的结束了。”[4](P23-24)
而第二次“倒孔运动”无论从人数、声势、规模、影响等方面来说都不及第一次,而且同样是学生的自发行动。“一九四四年三月,联大一九四四级的学生已全部征调受译员训练。孔祥熙适于其时为调停蒋宋的纠纷,继蒋夫人匆匆来昆。译训班当局向同学们宣称孔院长定于某日亲自来班慰劳,并令同学们忙着整理了一天内务。届时,忽接命令饬学生会同联大全体同学往云大听训。所谓亲自慰劳云云已改为‘听训’了!同学们在军事教官的强迫下,整装赶到云大。不料,到云大后,译训班的同学被摈弃在讲堂之外,站着等了半小时,还不见孔祥熙的影踪。及孔博士驾到同学们再也抑不住愤恨之情。‘打倒贪官孔祥熙!’有人这样吼了。‘你看他胖得象猪一样!’有些人当面指着他说。在讲堂内外一片喊叫和嘘声之中,孔祥熙还厚着脸皮爬到台上大讲其祖宗孔子之道,说他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泽,他们孔家从来不想做官,可以以他为证,他之所以在政府中任职,实在是不得已。他还说青年人看事,常常只受到别人的宣传便乱说一顿。希望大家以后看明白了事实真相再下判断。要理智一点。不要受别人利用。……同学们啼笑皆非,更有力地嘘起来。当时蒋梦麟氏幽默地说:‘因为同学们都想瞻仰孔院长的风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长,所以秩序乱一点。’”[4](P25)这更象是一场闹剧,学生仅仅是通过话语来发泄不满和愤恨,并无过激之举。
“倒孔运动”的经验就是:“都是激于热情,而毫无组织,结果,孔固未倒同学反吃了大亏。但同学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学生运动是不能没有组织的。”[4](P25)
不过国民政府方面似乎并不相信此次学潮是无组织的行动,因为学潮不仅在昆明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波及到其他地区,形成了连锁反应。当时已迁到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也起来响应,1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学文学院百余同学在礼堂举行讨孔大会,即席推举八人组成讨孔委员会,主持本校讨孔运动。嗣后很快形成全校性的讨孔怒潮,并以该校讨孔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学校和报馆,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17](P114-115)浙江大学的学生也行动起来呼应“倒孔运动”。国民党高层对此极为震惊,蒋介石认为此次学潮与国社党罗隆基在背后操纵鼓动有关,“近来学潮愈闹愈广,委座对此甚为震怒,曾命康泽赴昆明调查,结果与国社党无关。”[13](P252-253)而当时共产党在联大内力量也很薄弱,“皖南事变”后,依照共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迫撤离了学校。[7](P98-99)所以,“倒孔运动”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
“倒孔运动”学潮中的话语建构十分重要,它决定着学潮的性质、目标以及其合法性。在第一次“倒孔运动”的游行中,国民党当局一共收集了24条标语:1、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2、拥护政府修明政治;3、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4、孔贼不死,贪污不止;5、打倒祸国害民的孔贼;6、打倒国贼孔祥熙;7、请新闻检查所勿扣倒孔之消息;8、各界参加,打倒贪官污吏孔祥熙;9、屈杀留港官员者是谁;10、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11、请报界发表舆论;12、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孔祥熙;13、孔存款十七万万元在美国;14、打倒操纵物价的孔祥熙;15、打倒操纵外汇的孔祥熙;16、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17、要修明政治必先铲除孔祥熙;18、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19、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20、孔祥熙为一国财政部长,不好好管理财政,专做囤积居奇生意,简直是汉奸,我们非杀死他不可;21、香港危险时,政府派飞机去救党国要人,带转来的是孔祥熙夫人及七只洋狗、四十二只箱子;22、枪毙孔祥熙;23、欲求抗战胜利,先从倒孔做起;24、前方抗战流血,后方民众吃苦,发财的是孔祥熙。[18]
标语可谓是学潮的符号性标志,是学潮的话语表达形式,其中传递了以下一些信息:第一,学潮的矛头直指孔祥熙,24条标语中有20条是攻击孔祥熙的,所用词语多带有暴力倾向和非理性色彩,且有人身侮辱的意味,如对孔祥熙进行污名化处理,“打倒”(使用频率最高)、“孔贼”、“杀死”、“枪毙”等等,表达的大学生对孔祥熙的不满、愤怒和痛恨。第二,表达了对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孔祥熙是贪官污吏,应该打倒,但打倒孔祥熙并不意味着反对政府、颠覆国家政权,在这两者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孔祥熙是腐败官僚的代表,但并不表示所有的官僚都有问题,与孔祥熙相对照,学生的标语中有拥护龙云的表示,而龙云是作为孔祥熙的对立面出现的,属于好官的代表,而且学生并没有因为孔祥熙的腐败进而抽象扩展为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否定,是传统社会“反贪官不反朝廷”思想意识的现代翻版。第三,开放舆论,要求新闻自由。要求有关政府部门放松对倒孔报道的新闻检查,允许报刊对孔祥熙的恶行予以评论。第四,要求民主自由。这是联大学生在受到长达两年的高压政策之后的自然反弹,是联大民主思想的又一次复兴。民主自由可以说是联大的价值谱系,从此以后,联大学生运动的主旋律发生了转变,从抗日救亡转化为争取民主自由。联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在校园里重新活跃起来,校园里的壁报又重新出现,壁报中谈论最多的是民主问题,重点讨论的是关于战后的民主建国和民族文化的重建等问题,政治色彩更浓了。
从“倒孔运动”话语建构来看,学生在学潮中喊出的口号或标语没有经过仔细的斟酌和提炼,目标指向具体而明确,以情绪化的表达和愤怒的宣泄为主,缺少抽象的概括和升华,没有触及到政治制度的本质,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学潮中并无有效的领导和组织,属于乌合之众的集体行动。
三、“倒孔运动”中教授的角色
在民国大学中,大学教授对学潮的态度历来是复杂而分化的,这主要因为教授群体本身就是高度分化的,因为彼此的政治立场、观察问题的视角以及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对学潮的态度各不相同。王晴佳曾将教授对学潮的态度分为“同情的旁观者”、“热情的鼓动者”、“急切的防范者”三种。[3](P25-48)
一般而论,战前的学生运动背后都有教授的身影,且有时可能还涉及党派力量的影响,“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其他的政治势力。”[8](P125)抗战前大学教授多是学潮的“同情的旁观者”,学潮之所以能被人同情是因为,“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8](P123)学生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成为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政府处理学潮比较困难。教授群体中有一部分人尤其大学校长对学潮并不支持,以蔡元培对五四运动态度为例,“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同学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8](P116)大学校长所以同情学潮而不支持学潮的复杂态度是从治校角度出发的,认为学潮容易导致学生自由散漫,不受学校规章约束,破坏现有的教学秩序。 “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梁实秋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学潮“爱国的表示逐渐变质,演化为无知的盲动,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冷静的人均不谓然。”[19](P142)后学校当局劝阻无效,开除为首的若干学生,得到了闻一多等教授的支持。不过也有一些教授支持甚至参与学潮,如朱自清[20](P82-89)。可见教授在战前的学潮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有“同情的旁观者”,也不乏“热情的鼓动者”甚至是“积极的参与者”,但以同情者居多,鼓动甚至参与学潮的教授并非多数。
而对于“倒孔运动”而言,学潮之前吴晗在中国通史课上的煽风点火,无疑承担了“热情的鼓动者”的角色。而当学生上街游行时,西南联大两位常委蒋梦麟和梅贻琦参与了学生的游行,但这并不表示两位校长对学潮的支持,可能更多是出于维持秩序的考虑,“蒋梦麟校长声色俱厉的从正面劝说同学停止活动”,成为学潮中“急切的防范者”,当第二次联大的译电班学员当着孔祥熙的面起哄和谩骂时,班务实际负责人吴泽霖教授泪眼双流地说:“‘你们叫我如何得了!’盖吴氏正当飞黄腾达时也。”[4](P23)可见吴泽霖也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却无可奈何。
而作为旁观者的傅斯年对“倒孔运动”的看法很是值得玩味,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一般的政治情形,我久病之人,知道不多,但去年在渝时,大家都感觉到,经济情形实在不太妙,当局于此似未了其病之所在,乱花钱,越无钱,越多花,弄得人心以为钱必贱而物必贵,普天之下,一个心理,今尚不知收拾。至于管财政者之泄泄沓沓,毫无觉悟,更不待说。即以一事而论,前年冬,到去年夏,不到一年之中,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业务减了甚多,而人员增加了三倍!至于管交通的,无论属于交部与属于军部者,都是奇糟,可为长太息者也。最近闹了一回‘狗官司’。香港战起,好几个飞机去接要人,而要人则院长(许崇智)、部长(陈济棠)以下都未接到,接了一大家,箱笼累累,还有好些条狗。于是重庆社会中,愤愤然,其传说之速无比,但曝烈不出来,《大公报》做了一文,说此事,扣了,后来交通部之official version(官方说法)是一切要接的人都赶不上(何以某家赶得上?)箱子是中央银行公物,狗是机师带的!这消息传到昆明,学生几千大游行,口号是打倒孔某。‘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这次不能说是三千里远养病的病夫鼓动的罢!”[21](P541)傅斯年在信中对学生的游行未加指责和批评,反倒是有些幸灾乐祸,因他对孔祥熙的贪污行径一直愤愤不平,自1938年起,傅斯年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上书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免去孔的行政院长,另选贤能,但蒋不为所动。但傅斯年并不罢休,而是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舞台,对孔祥熙多加质询,并继续给蒋介石写信,提议撤换孔祥熙。他还不断地收集孔祥熙贪污腐败的证据,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予以公开的揭露,此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在1940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列举了孔祥熙的斑斑劣迹:“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先生久在国外,未能深知。2、他之行为,堕人心,损介公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使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他一向主张投降,比汪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21](P479)傅斯年是教授群体中“倒孔”的急先锋,可谓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当时内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在1941年12月份由进步学生成立了“倒孔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抗议的电报,并在校内张贴了漫画、壁报,对孔氏和四大家族进行揭露。[22](P127)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1942年的日记中对此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十六日学生游行所发传单,攻孔谓飞机去香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全系谣言也。”[23](P568)竺可桢所了解的事实是,“又谓香港飞机载狗事,查八日香港曾有二航班机飞渝,九日中央一机载银行中人员,十日一机载宋霭龄并大小狗各二只,但以机停九龙,故往来者少,机中甚空云云。”[23](P569)可见浙大学潮的起因也是“飞机洋狗”事件,飞机上载有洋狗是因为乘坐飞机的人很少,空间甚大,与党国要人被迫滞留香港并无关联,其中有谣言的成分。竺可桢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其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对于浙大的学潮,竺可桢通过对学生进行劝诫和训导,避免事态的扩大和恶化。竺可桢因为校长职责所在,不得不充当了“急切的防范者”的角色。
“1942年1月18日 星期日[遵义]阴终日
……此次驱孔运动左派学生活动者,遵义陈天宝、董维宁、陈立、陈海鸣、王天心;湄潭张秋芳、李学应、钱念屺、滕维藻及教员黄川谷、潘家苏。接到联大苏生(锡旗)之信者为刘玉钊,制油墨发传单者伍学勤。又黄川谷前并常得共产党大批接济云云。
1942年1月19日 星期一[遵义]阴终日
……送渠出后,余训斥学生星期五游行行动。大意谓大学生之尊严由于学生能自治,德国为一例。学生不能安分守纪,必召军警干涉;且述所发传单中关于吴稚晖全家自杀,王宠惠、胡宗南、郭复初在港被拘之无稽。训勉学生务须保守秩序,奉公守法,以求是为精神。十二点散。……”[23](P568)
“倒孔运动”的学潮中并未出现大量教授卷入其中的情形,教授多是扮演着带有同情成分的旁观者的角色,而学潮所涉及的各大学校长虽然为了维护学校的秩序和稳定,想方设法制止和平息学潮,但并未因此而对学生采用严厉的惩罚手段,而是通过个人的威望和影响力来化解学潮,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也表明,学潮问题最好由学校出面解决,这样效果可能更好。
四、余论
亨廷顿认为“在大部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学生中占优势的积极分子集团是反政府的。而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就在大学里。”[24](P265)大学里的反对派既包括了学生,也包含了一部分教授。青年学生是社会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力量,他们真诚坦率,富有正义感,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平和腐败,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是一股健康向上的力量。在黑暗专制的社会中,他们总是扮演着社会反叛者的角色,因为“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性质如何,学生总是反政府的”。[24](P306)在抗战时期,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学生运动开始汇聚成持续的反政府的浪潮,“倒孔运动”只是以后大规模学潮的前奏和预演,在此之后的学潮则愈演愈烈,大有燎原之势。
学潮是抗争性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按照蒂利等人的看法,抗争性政治有这样一些特点:“……针对当局提出了自身的要求,在提出要求时都采用了公开行动的方式;……利用了传统的集体行动[我们称为抗争剧目(repertoires)]形式,还创造出一些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它们还都分别与各自所在政治体内有影响的成员结成同盟,利用现政权内出现的机遇并制造一些新的机遇,……”[25](P9)游行示威成为学潮的主要形式,对于抗争政治而言,“抗议示威已然成为世界各地的提出要求者们所采用的主要的、传统型的抗争形式了。”[25](P19-20)
“倒孔运动”是一场比较平和的学潮,它既不以获取政权为目标,也不以暴力作为手段,更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是在承认政府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治抗争,斗争矛头指向的目标也是贪官个体,而不是整个政治制度。它实际上是对当时的国民党统治的一次预警,如果执政党能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有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消除腐败,推行民主宪政以回应学生的正当要求,平息社会大众心中的怨气,或许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此次学潮还暴露出国民党政府在处理学潮时方法上的缺陷和能力的不足,“事后,康泽把昆明的特务阵容重新布置一番,还传出了一张黑名单,据说因联大常委的力阻,才没有捕人。”[4](P24)试图用特务政治和暴力手段来对付学生运动,非但不能起到正面疏导作用,反而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激发学生的怒火和斗志,加剧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紧张,使学生原有的对政府的信任和忠诚资源流失,将学生视为是政府的对立面,逼迫学生与政府为敌,这也成为日后国民党政府处理学潮的一大败笔。
国民党政府对高校的控制沿用的是以党治校的套路,抗战期间在高校中成立党团组织,以此来钳制学生的思想,压制学生的民主运动,但这个制度性的设计和实际的操作效果并不好,因为它背离了大学的自由精神本质,难以得到教授和学生的支持,“倒孔运动”的出现就足以说明以党治校的不得人心和破产。应该说,国民党政府对于学生运动确实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化解,既然内部的控制和约束失去作用,那么剩下来的就只能是从外部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对学生运动进行无情的镇压了,政府与学生的冲突日益激化,武力手段遂成为日后国民政府处理学潮问题的必然选择。
[1] 单纯编. 冯友兰自述[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2]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辑. “一二·一”运动[Z].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3] 王晴佳. 学潮与教授: 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J]. 历史研究, 2005,(4).
[4] 公唐. 倒孔运动[A].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联大八年[C].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5] 翟作君, 蒋志彦. 中国学生运动史[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6]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7] 赵新林, 张国龙. 西南联大: 战火的洗礼[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
[8] 蒋梦麟. 西潮[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9] 永年. 师院生活[A].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联大八年[C].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0] 我们的道路(代序)[A].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联大八年[C].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1] 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拥护修明政治案[N]. 大公报, (重庆)1941-12-22.
[13]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Z].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1.
[14] 苏双碧, 王宏志. 吴晗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15] 王奇生.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06(4).
[16]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7] 梁山, 李冰等. 中山大学校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18] 转引自杨天石. “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N]南方周末, 2010-03-18(24).
[19] 梁实秋. 清华八年: 梁实秋自传[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20] 参见朱自清自传[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21] 傅斯年. 傅斯年致胡适[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2] 李华超等. 浙江大学在眉潭[A].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C].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
[23] 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Ⅰ)1936-1942[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24]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5] [美]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抗争政治[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侯德彤
“Anti-Kong Movement”:Cotentious Politics in War Times
WU Jin-qi
( Jingling Technology Institution, Nanjing 210038, China )
The "Anti-Kong Movement" was an express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Kunming in the late stage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t was a spontaneous student movement without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or premeditation, but with targets. It was trigger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 "Anti-Kong Movement" was a collective ac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with the aim of fghting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Professors' performance in the movement was complicated: some being "sympathetic observers", some being "enthusiastic agitators" and others being "eager preventers". This movement was actually a warning to the Kuomintang regime, indicating its failure to control the university campus and the gradual loss of its political resources.
Anti-Kong Movement; war times; contentious politics
K265.9
A
1005-7110(2013)06-0034-08
2013-09-06
吴锦旗(1968-),男,江苏盐城人,法学博士,金陵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