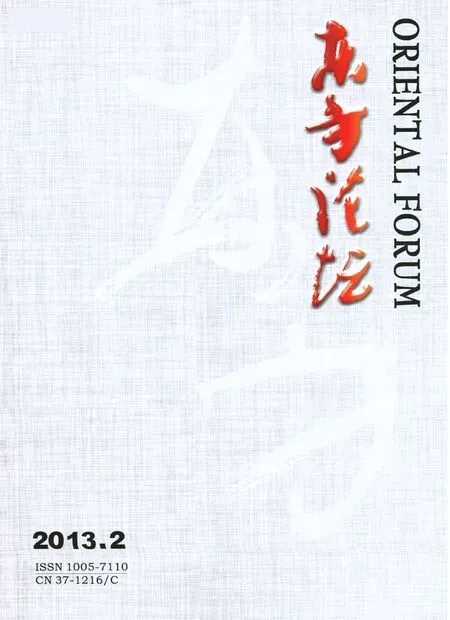歌德《论德意志建筑艺术》的美学精神
王 静 张 典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牛津大学 哲学系,英国 牛津)
一
早在1770年初,歌德就曾在斯特拉斯堡参观了由斯坦巴哈(Erwin von Steinbach,1244-1318)等人设计建造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而在1771年认识赫尔德之后,受到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他才开始写作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建筑风格的《论德意志建筑艺术》,1772年完成,后被收录在由赫尔德编辑、1773年匿名出版的文集《德意志的风格与艺术》中。这部文集包括四篇文章,除歌德这篇文章外,赫尔德还收录了自己论莎士比亚和论莪相民歌的两篇文章,以及莫斯特(Justus Möster,1720-94)的《试论哥特式建筑》。赫尔德编辑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德意志”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精神内涵,其更远的目标是在精神层面强化德意志的自我身份认同,为德国未来在政治上的统一奠定基础。由是,《德意志的风格与艺术》侧重于从颂扬与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角度分析问题,因而带有极强的倾向性。
《论德意志建筑艺术》(1772)这篇文章在歌德的艺术观念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它也是欧洲艺术史上的一篇重要论文。关于这篇文章的主题,歌德在《诗与真》中《关于德意志建筑的论文》这一节中有所总结:“我关于大教堂的建筑艺术的设想和描绘,曾拉杂写下来。就中我主张最力的,就是:第一,我们应当称这种建筑为德意志式,而不是哥特式,不是外来的,而是国粹的;第二,我们不应当把它来与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术相比较,因为它的形成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原理为依据。如果这个大教堂是建筑在和风丽日的天空下,以圆柱来支持屋顶,那么它自身自会为有空隙的墙壁所围了。可是,我们北国的人,既必须到处绕以厚壁来御寒,所以,天才的建筑家设法把厚大的外壁弄到有种种花样,从外表看来象是有孔眼那样子,打破全体的单调,使观众对那巨大的平面产生优美之感,那是值得我们敬服的。这个道理也可应用到塔的方面。那个塔不是象圆顶阁那样,在内部作成穹窿之形,而是要在外部向着天际高插,并且要使设在它的底层的至圣所的存在,传达给远远的周围的地方知道。至于这个可贵的大建筑的内部,我只敢以诗的观点和敬虔的心情来谈论了。”[1](P532-533)
歌德在文章中表现出的爱国情感受到了赫尔德的影响,赫尔德在《德意志的风格与艺术》论莪相民歌的文章中分析“德意志”这个名称的意义:“德意志”(deutsch)实际上接近“日耳曼人”(Germanic)或“北欧人”(Nordic),包括凯尔特人(Celtic);而“德意志民族”(deutsche Völker)则意味着哥特人(Goths)、伦巴族人(Lombards)、汪达尔人(Vandals)、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等。赫尔德从德意志民族独特的精神角度强化其与南方民族的不同,突出了风土(climate)概念在形成民族精神中的重要意义,民族精神植根于一个民族活生生的风土之中,民歌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活的精神;在农民那里、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那里才有民歌的精神,这是民族精神赖以生长的土壤。赫尔德之所以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德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赫尔德倡导民歌,也是藉此反对德国贵族社会,希望新兴的中产阶级能为未来的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作好准备。[2](P221-222)
歌德的《论德意志建筑艺术》并是不从建筑史的角度分析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风格,而是延续赫尔德的思路,主要为强调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是德意志精神的集中表现,以及这种精神是独特的、有别于希腊罗马的建筑风格。从建筑史的角度,由斯坦巴哈斯等人设计建造的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现存部分属于中世纪盛期到晚期的哥特式风格,其建筑元素与罗马建筑风格并没有一种本质的中断,哥特式建筑是在延续罗马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罗马以北的民族与东方伊斯兰建筑等风格形成的。歌德在这里的立论主要是基于当时对哥特式建筑的一般认识,以及自己的独特观感。对哥特式建筑的批判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瓦萨里,瓦萨里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将哥特式看作是北方原始、野蛮风格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盛行于17 至18世纪欧洲的新古典主义运动中。
歌德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精神取向和写作立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重申德意志精神的独特性,德意志精神是植根于德意志从中世纪以来的哥特式精神;其二、歌德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开始批判德国当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而这正是歌德此前一直在尝试接受的精神。德国的新古典主义由温克尔曼开创,继由莱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美学派别;歌德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时代(1765-1770)一直希望自己理解并接受新古典主义,但对新古典主义的态度却由于缺乏情感上的认同而一直处于矛盾心理;赫尔德促使了歌德对温克尔曼与莱辛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的反动。不过仔细分析歌德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比想象要复杂得多:歌德在反对新古典主义、强调德意志哥特式精神的独特意义时,其实已经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精神的人性内涵,尽管他在理智上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歌德著名的诗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772-1774)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诗歌中表达的是人挑战神的权能的泰坦式的反叛行为,讴歌人性的高贵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同样,《论德意志建筑艺术》也是一种建立在对启蒙时代的人性理解之上的精神表达。
因此,歌德虽然在《论德意志建筑艺术》中歌颂德国哥特式的建筑精神,但此时的德意志精神已不是德意志中世纪的哥特式精神;哥特式建筑也不再是敬拜神的场所,而是在歌德笔下化作人性之树向上生长的形象。文章显然存在三个交互的视点:德国浮士德精神中的魔力、普罗米修斯的人性内涵,以及整体性的生命哲学。歌德在写作这篇论文时还非常年轻,尚未形成稳定的精神走向,而是处于一种比较朦胧的情感波动时期,渴望开拓一条自己的道路;他的精神世界存在着裂缝。直到1776年到魏玛之后,歌德才开始走向狂飙突进时期的反面,努力去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着的过于强烈的魔力精神。
二
鲍桑葵在《美学史》中称歌德的《论德意志建筑艺术》为18世纪最深刻的美学论文之一。鲍桑葵认为《论德意志建筑艺术》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创新:其一、对后期文艺复兴的伪古典主义的态度。其二、对哥特式建筑的同情以及对哥特式名称的贬义所提出的批评。其三、一种关于显示出特征的艺术理论的征兆。[3](P392)鲍桑葵的分析与歌德自己在《诗与真》中的表白没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德国新古典主义与德意志哥特式风格的对立,而最有价值的分析则在于第三个问题,即鲍桑葵认为歌德在文章中显示出一种特征论(Charakteristische)美学理论的迹象。这三个问题展现的是德国当时时代精神三个紧密相连的方面:德国新古典主义、德意志哥特式风格以及德意志性格特征;这三个方面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完全分开。
温克尔曼在他1755年发表的《在绘画与雕塑中对希腊模仿的思考》长文中有这样的宣言:“让我们变得伟大的唯一一条道路,或者说,如果可能的话,无可比拟的就是模仿古人。”[4](P5)这个倡导中的希腊中心主义观念造成了接下来的希腊对德国的专制,这个宣言为德国新古典主义奠定了基础。不过,德国新古典主义模仿的对象除了希腊、罗马古代艺术,还包括受到希腊、罗马古代艺术影响的意大利以及法国的文艺复兴、巴洛克等艺术。从德国新古典主义的角度,哥特式艺术是原始、落后的艺术。而在赫尔德看来,哥特式是本土的,新古典主义是外来的,外来的因子如果要扎根于本土,则必须首先在尊重本土精神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功。歌德在赫尔德的影响下,重申德国哥特式艺术的内在价值;他在《论德意志建筑艺术》中比较了南方古典建筑与哥特式建筑的形式方面的不同,这种形式感的差异源于民族特性的不同;出于爱国精神,歌德呼吁大家改变对哥特式建筑的狭隘看法,而肯定哥特式建筑具有伟大的风格。
歌德在《论德意志建筑艺术》中,以这样的形式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对哥特式建筑的态度:“1、对文艺复兴的态度。(对哥特式艺术)‘低级趣味’意大利人说着走开了,‘孩子气’法国人说。这样,你们就在给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涂上一层真和美的外观。圆柱的光辉的效果给予你们很深的印象,你们也想造几个圆柱,于是,你们把圆柱造在墙壁里面,你们想要建立柱廊,你们就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院的周围建筑了一些没有出口的大理石通道,结果,大自然母亲既然嫌厌和鄙视无用的和不必要的东西,也就迫使你们的人民置于公共的阴沟中,以及你们要在这座世界奇迹面前避开你们的眼睛,捏住你们的鼻子。圆柱绝不是我们的房屋的一个要素;它同我们的一切建筑物的本质是抵触的。我们的房屋不是覆盖在四个角的四根圆柱之上的;它们是覆盖在四面四堵墙上的。墙壁代替了圆柱,排斥了圆柱。你要是再添四根圆柱,圆柱就显得累赘和多余。”[3](P397)
歌德在这里多多少少比较武断地批判了南方建筑的廊柱、长廊、拱顶等这些古典元素,认为其不适于北方的气候,而哥特式建筑更适合北方人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从新古典主义的偏见中走出,看到了哥特式建筑的伟大:“2、哥特式是一个贬义词。当我最初动身去参观那座大教堂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充满了良好趣味的笼统观念。根据道听途说,我对部件的和谐和形式的纯粹表示尊敬,竭力反对混乱任性的哥特式装饰。我把朱红色印体‘哥特式’当做字典一个条目,把我所想到的一切不适当的同义词都归在这个字眼下面,‘不明确的,紊乱的,不自然的,一堆零碎,千疮百孔,负担过重。’我就象一个把全世界都叫做‘蛮族’的人一样不聪明,把一切不适合我的心意的东西都叫做哥特式的,包括我们的资产阶级贵族用来装饰他们的房屋的精致的玩偶和形象作品,直到德国古代建筑的坟墓遗迹。……当我站在那座建筑物面前,看到那令人惊叹的景象时,我的感受又是多么出乎意料之外。我的灵魂中充满了一种伟大而完备的印象。这个印象由于是无数和谐的细节所组成的,因而是我所能品味和欣赏的,但是,却完全不是我所能理解和解释的。我又多么经常回去享受那种宛若置身天堂的愉快,去从我们老大哥的作品中领会他们那种巨人式的精神啊!……因此,当德国艺术学者听了满怀嫉妒的邻人的话,把自己的长处加以抹杀,用不可理解的‘哥特式’一词来贬损这一作品时候,我真不该对他们生气。他们应该感谢上帝使他们能够大声宣布:‘这是德国的建筑,我们的建筑,同意大利人没有关系,同法国人更没有关系。’”[3](P398-399)
在《诗与真》中,歌德对自己当时的写作心态有这样的表露:“我在非难哥特式的建筑术的人们中长大,养成了对于太过繁缛杂乱的藻饰的憎恶。这样的藻饰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使一种宗教的阴郁的特征讨厌到了极点;我因为从前只看见过这一派的没有生气的建筑物,尺寸大小的配合既不适宜,也不看见首尾一贯之处,所以我的厌恶更增强。但是,在这儿我相信获睹一种新的启示了,因为那种值得非难之处我绝感不到,而它的可赞美之处反逼人而来。我既发现这个建筑物是在古德国的基址上建立,并且在真正德意志的时代有那样的成就,连那朴素的基石上的建筑师的名字也是祖国的读者和来自祖国的语源。我为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所激励,我大胆地要将向来误呼的名称‘哥特式建筑’更改,而还给它我国的‘德意志式建筑术’的名字。此外,我却少不了先在口头上,继在一篇献给斯坦巴哈的论文中把我的爱国的思想披沥出来。”[5](P394-395)
我们不难发现歌德在对哥特式建筑的了解方面存在着一些常识性误区,例如,哥特式建筑首先在12世纪的法国出现,斯坦巴赫也不是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唯一设计者,甚至不是最主要的设计者,把斯坦巴赫视作斯特拉斯堡教堂的主要设计者只是歌德的臆断。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歌德对哥特式建筑的思考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歌德当时正受到赫尔德的一些误导:德国那时的贵族阶层欣赏的主要是法国文化,因此流行的建筑也是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歌德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反对这种流行时尚,希望以哥特式建筑所显示出的整体生命力来重整德国精神。所以,歌德对于哥特式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最鲜明的感受就是这些建筑是从土壤中直接生长出来的,具有盛旺的生命力,而这正是狂飙突进时代精神所追求的东西。
歌德虽然在赫尔德的影响下,认为德国的新古典主义过于强调形式而缺少对德国本土精神的反思,不过他也并没有完全丢弃温克尔曼与莱辛的新古典主义,而是拓展了他们关于人性的理解,突出其德意志天才与魔力的精神,因此鲍桑葵以“特征的艺术理论的征兆”来定义歌德的这种精神。特征论指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对歌德来说,最能明显体现德国民族性格的便是浮士德精神。莱辛从启蒙精神的角度刻画了理性清明的浮士德形象,而歌德将莱辛的启蒙理性对于人性的理解转化为对于整体生命的哲学理解,浮士德于是成为一位在酒神精神推动下不断提升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歌德与莱辛的区别就是一个注重理性反思,一个注重整体的生命哲学;歌德将浮士德精神内在化,所以,浮士德精神已不再是理性反思性的,而是行动式的,在行动中彰显出整体的人性。
三
鲍桑葵之所以提出歌德的“特征的艺术理论的征兆”,根据的是歌德在论文中的这样一段表述:“这种显出的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人之手也好,它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你可以在各个民族和各个个人身上,看到无数不同程度的这种情况。灵魂愈是能感受到那种唯一的美的和永恒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和弦可以表现出来;这种关系的秘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天神似的天才的生活才能迸发为愉快的曲调;这种美愈是渗透到心灵的存在中去,似乎和心灵具有同一起源,以致心灵再也不能容忍任何别的东西;愈是这样,艺术家也就愈幸福,……去认识在中世纪狭窄而阴郁的祭司场地上、从强悍粗犷的德国灵魂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关系中的真和美的最深刻的感受吧。……近代人好嘲笑富于男子气概的阿尔伯特·丢勒,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你笔下的最拙笨的形式。”[3](P400-401)
鲍桑葵所谓歌德“特征的艺术理论的征兆”,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歌德的特征论就是强调有内容的形式;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其特征,艺术家必须刻画出这种性格,才能达到艺术的典型性。特征是一种有内容的形式,人们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洞观到艺术的精神;歌德倡导的整体生命也是这种有内容的形式,艺术犹如植物从土壤中生长起来,具有完整的生命——当人们看到德国的哥特式建筑时就会产生这样的感受。歌德的特征论无疑是由于赫尔德的原始生命力的观念所强化而产生出来的。歌德从整体性的和谐一体来理解哥特式建筑,建筑的主体构架与装饰性的藻饰是和谐的整体,繁复的装饰是哥特式建筑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歌德受路德、莱布尼兹一直到赫尔德的影响甚深,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是他们精神的哲学表达;单子论是德国的一种生命哲学,强调整体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自身内在的灵魂。歌德眼中的哥特式建筑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作为整体生命力的表现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
“有机生命力”观念是一种象征观念,是艺术特征论最重要的观念,歌德用“生命之树”来象征哥特式建筑的艺术精神。歌德在文章中写道:“很少有人的心灵里怀有建造巴比伦塔的理想,从完整、庄严、毋庸置疑的美直到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完整有如上帝之树。”“对于直耸云霄的高墙,装饰它并赋予它以生命,让它长成巍峨、茂密的上帝之树,有着一千枝树杈,百万条树枝和多得像海里的沙子一样的叶子,显示着主的荣光。”“为你欢呼,年轻人,你生来就有发现均衡的热切的眼睛,能准确地抓住任何事物的特征。当生活中的一桩桩欢乐把你唤醒,你感受到劳动、忧郁和希望之后的令人欣喜若狂的乐趣,就像酒商看到秋天的果实盛满他的酒桶后精力充沛的呼喊,也如割草人把空闲的镰刀插在房梁后轻快的舞蹈;当强有力的欲望冲动和苦恼以巨大的活力激励你的画笔;当你充分地体验了奋斗、痛苦和欢乐的滋味,你的心中就充满了人间的美,并且获得了在女神的手臂中休息的权利,你在她的怀抱中,体验了给予赫丘利的新生——于是你又接受了天国的美,成为神和人之间的调停人,因此,比起把神的福地带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你更加伟大。”[6](P285-290)
歌德以“庄严高耸、广袤的上帝之树”来形容哥特式建筑,他进入斯特拉斯堡教堂就如进入了原始森林,在一种自然的生态中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歌德以植物来形容哥特式教堂可以在他与爱克曼的对话中看到,爱克曼记载下1823年10月21日歌德与他的谈话:“在早期德国的建筑艺术的作品里,你可以看到一种特殊情况的全盛期。谁要是直接看到这样的全盛期,就只会赞叹不已;可是,谁要是向内看植物的秘密的内在生活、力量的运动,以及怎样逐渐地开花,谁就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他在看什么。‘我愿设法让你在今年冬天了解一些有关早期德国建筑艺术的情况,以便你明年夏天到莱茵地区作一次放行,相信你看了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和科隆大教堂之后,会从中得益不浅。’”[7](P19)
在《论德意志建筑艺术》的结尾一段中,歌德将斯坦巴赫歌颂为创造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这个神奇世界的天才,这种天才具有神赐予的能力,而又经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了理想的境地。歌德的神是异教的、但也带有基督教天国的色彩;人既是赫丘利、普罗米修斯,更是一种对他们精神的提升形象,他们经过不断的实践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他们毕竟是有局限的,必须在神的呼召下才能看到天国的美。但歌德歌颂的美只是人间天国的美,他并没有期许另外一个天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歌德《浮士德》精神演化的一个模型,因此,《论德意志建筑艺术》可以被认为是歌德一生发展的一个起点与缩影。
[1] 歌德.诗与真 (下) [M].刘思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Wulf Koepke.What Is “German” Literature Supposed to Be? In: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Johann Gottfried Herder.Edited by Hans Adler and Wulf Koepke.Rochester:Camden House,2009..
[3] 鲍桑葵.美学史 [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Trans.Elfriede Heyer and Roger C.Norton.La Salle,Ⅲ.:Open Court,1987.
[5] 歌德.诗与真 (上) [M].刘思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 迟柯编.西方美术理论文选 (上)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 [M].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