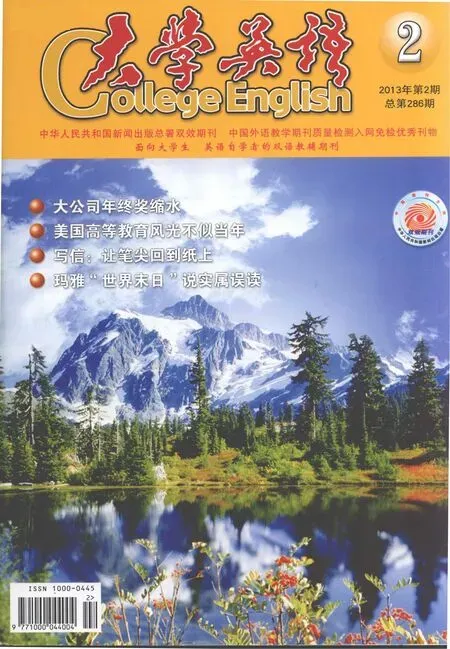散文译作的风格再现——A Modest Proposal两种译文分析
郎丽璇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引言
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称为四大文学门类,“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的重要特征,其表现形式十分灵活,写法自由,作者可以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文风特点和气质精神,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要把握其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创作风格等,要透过作者笔下的文字心领神会作者的意图,才能在译文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其作品的韵味与风格。散文A Modest Proposal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18世纪英国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他的散文语言平实却铿锵有力,饶有韵味,幽默风趣中蕴含着一种强大的讽刺力量。
1.A Modest Proposal原作风格
18世纪20年代后期爱尔兰经历了三年天灾,民不聊生。统治阶级的谋臣策士们提了许多建议,都不仅于救灾无补,反而是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继续压榨人民。义愤之火促使斯威夫特写出他“爱尔兰政论”中最著名也最受读者欢迎的A Modest Proposal(1729)。在这篇文章中,斯威夫特模仿英国统治者的策士们的口吻,也像他们一样口口声声唱着爱国救民的高调,提出自己解决爱尔兰问题的“理论”和“建议”,最后提出的方案竟是把爱尔兰穷人的小孩子,除了“留种”外,一律卖给英国地主贵妇做餐桌上的食物!翻译此文时如何再现原文辛辣的笔锋以及嬉笑怒骂的口吻,是译者主要的任务。全文用反语冷嘲的手法,得以将一种血淋林的计划说得理由十足,轻轻松松。因此,表面上看来作者如此残忍、狠毒,实际上正是这副极端的“文字漫画”,深切的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愤怒,英国殖民者及其帮凶的吃人的面目昭然若揭。王佐良(1983)在评论本文时说:“论到嘲讽运用之妙,本文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一。”
2.两种译文对比的对比分析
本文要对比的是刘炳善和林必果两位老师的译文。如上所述,本文最大的风格特点即为讽刺。如何再现原文的辛辣笔风,便成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总体而言,刘译和林译都很成功地把握了散文翻译的大方向,从选词和句式安排方面都做到了合意、流畅,译出了原文语言幽默,讽刺辛辣的特色。本文将从词汇、语句和篇章方面对两种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从中考量译文在再现原文讽刺风格上的得与失。
2.1 词汇层面
原文第1段的第一句话,有importune一词,《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中解释为“to make repeated request to,often in an annoying or troubling way”。刘译将它译为“哀求”,虽看上去与整句中所描述的悲伤场面相吻合,但放在这里却是不大适当。因为,importune动作地发出者是children,他们大多不会,或者说还不大懂得去动情地乞讨,他们只不过是在父母的“教导”下去重复而后又习惯于重复这一动作罢了。这种在仍旧不谙世事的年龄就习惯于乞讨的场面,难道不比“哀求”更令人心酸吗?我想也正因如此,原文作者选用importune而非beg。而林译“缠着”,形象、生动、准确地译出了其意。
第4段第二句话中“solar”一词是相当引人注意的,这是原文用词精确的体现。 林译直接将“a solar year”译为“一年”。原文“solar year”所指的这个太阳本精确到秒,指365天5时48分46秒,我分析原文作者选此词原因有二:其一,母亲真正凭自己能力哺育婴儿的期限仅为一年,一秒不多,突出了状况之惨淡;其二,用精确性体现其严谨性,增强了讽刺效果。因此这个“solar”在句中并非无足轻重,刘译将其译为“整整一年”可谓颇费心思,恰倒好处。
第9段第一句话中American一词刘炳善译为美国人,但认真考虑一下,原文作于1729年,而美国成立于1776年,所以刘译很明显地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林译考虑了这一点,译为“美洲人”是正确的。
第26段第三句“honest”一词,应该怎么译,是刘译“正当”,还是林译“公正”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第二句中也有“honest”一词,是指“母亲无法以正当手段谋生”。原文作者一前一后两次使“honest”一词还是有其用意的。前文写到那些身为人母的女人,找不到正当手段谋生,只好讨口饭吃。看,乞讨都被列在“正当谋生手段”之外了,那后文所述“看谁能出售最胖的孩子”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正当竞争”,因此,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这个对比又一次讽刺了英国统治阶级,他们根本没有把穷人当人看。所以,林译“公平竞争”显然是不合适的,易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妇女们站在一条起跑线上,遵守共同的竞争法则去公平竞争,这样就与原文之意相背离了。
2.2 语句层面
第17段第二句话的最后一个小分句 “and these to be disposed of by their parents,if alive,or otherwise by their nearest relations”,刘炳善译为“可以趁这些人一息尚存,由他们父母加以处理,或由他们近亲代劳。”显然,刘译将“if alive”描述的对象看作“these”,将“or otherwise”译为“或者”。 实际上,“or otherwise”是表示相反情况的连词,而“if alive”是描述“their parents”的,原文意思应是:如果父母活着就由父母来处理,如父母已死就由最近的亲戚代劳。这一点林必果的翻译是正确的,但明显犯了一个画蛇添足的错误,“这些少男少女,如还未饿毙,可由其父母亲手宰杀;如其父母早已饿死,则可由其近亲代杀。”林译中“如还未饿毙”多余,将“dispose”译为“宰杀”和关于父母死因的推测——饿死都是多余的,这些都只可能而非必然,所以这样处理就使译文有些过犹不及了。
第23段的第一句是全文理解和翻译的一个难点,“Thirdly,whereas the maintenance of an hundred thousand children,from two years old and upwards,cannot be computed at less than ten shillings a piece per annum,the nation’s stock will be thereby increased fifty thousand pounds per annum,besides the profit of a new dish introduced to the tables of all gentlemen of fortune in the kingdom who have any refinement in taste.”林必果译为“如果要这10万儿童抚育到两岁以上,每人每年的花销至少不低于10先令。而若实施鄙人的方案,则不啻增加国库岁入五万镑。此外,还有一个益处:这将为国内精于美食的富绅们餐桌上平添一种盛馔。”他在原文理解上出了一点偏差,将“十万儿童”想当然的推断为待宰杀的儿童,因此导致错误地理解了整句话地含义。我们知道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甚至应该包括所有语种在内,连词在一句话内,在句与句间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它能够清晰直白的表达出语义上的逻辑关系。我们看到这句话中whereas和thereby前后对应,表明了前后句子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孩子的抚养开销是国库增加的原因。原文作者的意思是,宰掉小孩的好处在于提供了精美菜肴,而抚养留下的又能增加收入。容易引起原文理解错误的主要是“a hundred thousand children”。原文作者在前面做了一个计算,20万育龄期妇女,3万有能力抚养孩子,5万小产者(或孩子夭折),2万婴儿留种,那么确实有10万个适于在周岁时宰杀,也正因此,如果后文的“a hundred thousand children”顺而译成“这十万个孩子”那肯定会造成意义理解上的偏差,实际上作者在此是分析余下的十万个,他们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刘炳善译为“十万个两岁以上小儿的养育费,每人每年非十先令不办,因此,国库每年就可增加五万磅的收入;这还不算摆到全国有口福的富家绅士餐桌上的那一道新鲜菜肴。”他对原文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样分析也确实存在一个漏洞,余下的十万个“孩子”有一部分因母亲小产或夭折而不能存活,自然也没有那一部分抚养费支出。这个漏洞我想在此看作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无意中的疏忽,另一种是作者有意的失误,以显示这一策士表面英明、实则糊涂的特点。
2.3 篇章层面
我们知道,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这是翻译的全部目的,而译文的通顺,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第十段第一句后半部分,“my reason is that these children are seldom the fruits of marriage,a circumstance not much regarded by our savages”,刘炳善译为“我这样主张,乃因为这些小儿多半不是正式婚姻所生(我国的乡野愚民对于这一点是不大在乎的)。”林必果将其译为“我的理由是:这些婴儿很少是婚生的,因为国人野蛮愚顽,并不以婚否为意。”对比一下两种译文,我们能感觉得出刘译更加流畅,对于原文意义的表达更加通顺。原句中“a circumstance”指“children are the fruits of marriage”这种情况,刘译用括号形式表解释说明,并且用“这一点”三字译“a circumstance”避免重复其所指内容,简洁明了。而林译以因果关系安排此句,而且将“a circumstance”含混地译为“婚否”,使得整个句子逻辑性不强,表达不甚清晰。
第二例在第13段中——“For we are told by a grave author,an eminent French physician,”这两个身份指的是同一个人,该如何去译呢?首先我们要弄清这两个身份的关系。原文作者此处所指的这个人是法国著名的讽刺作家拉伯雷,用“grave”修饰虽然是反话,而“physician”身份放在这里便是要加强他们所说的话的科学性。因此“author”身份是基本,而“physician”身份是需要突出的。在这一点上,两种译法都做的不错。但让我们读一下林译“因为据一位身为医生的法国严肃作家言:……”,感觉非常拗口,而刘炳善译为“一位严肃的法国作家,又是法国的名医说过,”,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文形式,而且读起来也很通顺。
第三例位于第21段,“and who stay at home on purpose to deliver the kingdom to the Pretender,hoping to take their advantage by the absence of so many good Protestants,who have chosen rather to leave their country than stay at home and pay titles against their conscience to an Episcopal curate.”刘炳善译为“他们趁许多善良新教徒出走之机,自己留在国内,图谋把国家送给那个冒牌国王;那些新教徒则不愿呆在本国,违背良心向副牧师交纳什一税,只好出国他走。”林必果译为“他们呆在国内的目的,就是要趁这么多善良的新教徒不愿留在国内、违心地向主教副代表交纳什一税,而宁肯出国、远走他乡之机,把这个国家拱手送给僭位者罢了。”英语中常出现很长的定句从句,却往往成为英译汉中不好处理的地方,我们通常把这种长的定语从句拆成一个独立的句子,但前提是形式上独立,意义上却不能脱离,否则读者在阅读时就难以把握文章语义上的承接。本文中有至少20个长句,斯威夫特用长句制造出矫揉造作的感觉,符合文中所创造的“献策者”的风格。刘译把定语从句拆出来,但没有译到位,因此在语义上与前句连接不紧密,甚至有些唐突。林译虽然在“趁……之机”中间有很多内容,但更契合原文冗长的句式和缓慢的节奏,较刘译更加可取。
结语
A Modest Proposal可谓是斯威夫特政治讽刺文章的顶峰之作,他以一种极其荒谬的建议形式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呐喊。本文所对比的刘炳善和林必果两位老师的译文,各有千秋,却都译出了原文的意味和神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意义的解读和再呈现对再现原文的风格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能够在保持原文整体风格的基础上,又在译文中融入自己的行文风格也很重要。刘译谋篇布局严禁从容,林译选词造句准确精致,两个译文都很好的再现了原文的风格意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
崔永禄(2001).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林必果 (1998).英国散文名篇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炳善 (1997).伦敦的叫卖声 [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王佐良 (1983).英国文学名篇选读 [M].北京:商务印书馆。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