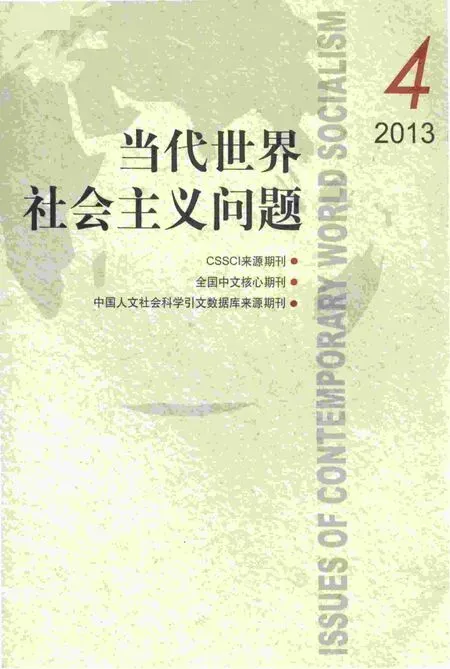秋风徐来忆世鹏
张光明
我和世鹏相识是在1985年,从那时起到他去年7月份谢世,中间经过了27年。现在回忆起来,与他有关的种种情景,都还是那么清晰。
1985年,我还在人大国政系读硕士研究生,随导师杜康传教授去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国际共运史学术研讨会。会议安排我们几所高校的研究生同住一个里外套间。大家都是年轻人,难得相识相聚,又是第一次开这么大规模的会,个个兴奋得有点超常,于是会前会后,扎堆起哄,欢声笑语,甚至大呼小叫,煞是热闹。世鹏年长几岁,又有北大教师身份,会议主办方自然不会安排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他一有空就往我们这里跑,和大家混得都很熟。当时的世鹏,三十多岁的年纪,充满年轻人的活力,一口北京土语,插科打诨,妙语连珠,全然看不出教师辈的矜持和严肃——许多年后我才听说,他少年时曾追随侯宝林、马季这些诙谐大师学过相声,是个耀眼的小童星。难怪!
可能由于这些印象,我觉得这个老师热情开朗,和他在一起不光不觉得拘束,反而感觉挺“好玩”。但当时我对他的学术活动和路数并不了解。
毕业后,我到外地工作,转入世界近现代史领域教书去了。此后多年间忙忙碌碌,未与原先这些朋友互通音讯。然而,在刊物上仍不时读到世鹏的文章,得知他在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党研究领域里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颇多建树。1992年,我出差去北京,在中央编译局又一次遇到了他,原来他已经调到这里专职搞研究了。此次重逢,我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不过七年,世鹏已经鬓发斑白,满面倦容,仿佛从一个青年人突然变成了老者!交谈起来,才知道他苦于哮喘,身体状况不佳,饱受病痛折磨,已非一年两年了。
90年代初,在我教书的那所大学里,政治气氛不佳,不学无术的小人得势,青年教师们三天两头在会上忍受他们的训斥,一无可为。我和别人一样,心情备感压抑,琢磨着换个讨生活的地方。世鹏了解我的处境和想法后,很是同情,大力支持我回京工作,为此他和另外几位同事出主意,想办法,很动了一番心思,令我十分感动。但大家都是读书人,无权无势,要平白调一个人进京,谈何容易!多方努力未果,最后我只得重贾余勇,考取了博士生,借此回到了北京。
1996年博士生毕业后,我到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工作,与世鹏成了同事。严格地说,我对他的了解是从这时开始的,这种了解在工作和交往中逐渐加深,最后发展为友谊,而这份友谊一直保持到了他去世。
人到中年的世鹏,性格上似有变化,变得举止沉稳、神情凝重、不苟言笑,颇有昔日儒者之风。由于这个缘故,一些年轻人对他有些敬畏之感,觉得不好接近。其实,这只是外表而已,在自己熟悉的人中间,他还是十分健谈的,特别是当谈起学术时,更是如此。他是个视学术如生命的读书人,崇尚学问、淡漠权势,对学养深厚、术有专攻、有思想、有见解的学者敬重有加。当时编译局的老先生们都还在职,那一代人对学问的严肃谨慎态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相比的。例如,他们中间的殷叙彝、李宗禹诸位先生,都是外文好、学问深的老一代著名学者。世鹏对他们十分尊崇,即使在离开编译局多年之后,每当在学生们面前谈起殷叙彝这个名字,总是恭敬地尊为自己的老师。他这种老派学人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即使在我这一代人中间,这种尊师之风也已经日渐淡漠了,到了更加年轻的一代口中,自己的导师干脆就变成了“老板”。
世鹏在学术上异常勤奋,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他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当代欧洲政治思潮、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方面,写了众多文章和好几本著作,还翻译了大量的文献,这本身已经是很突出的成就了。如果你再想到,它们都是由一个常年被疾病纠缠着的人做出来的,你就会更加敬佩了。这当然首先来自他的天资,但与他惜时如金、绝不虚掷光阴的态度也大有关系。在编译局时,他是西欧处处长,我是他的下级。他的领导作风是无为而治,不搞什么集体项目,给大家加码,只要求各人抓紧时间搞好自己的研究,拿出自己的成果。这个政策深得我心,因为在我看来,治学本是十分个性化的事,如果硬要把学养修为都大异其趣的一群人强凑到一起,弄成个“团队”,那样搞出的东西,多半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世鹏的这个做法,乃真正懂得学问三昧者所为。
世鹏为人谦逊低调,从不以自己的学术成就自矜。但他也有知识分子的傲气,一般情况下不随便称赞别人,更不会当面讲恭维话。遇到那些到处放言高论、夸夸其谈,其实腹中空无一物的冒牌学者时,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我亲眼看到,在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术会议上,他痛斥流行的学术作假和夸饰之风,说到激愤处,甚至拍起桌子来,这种几乎“不达时务”的耿直,让他很得罪了一些人。
大概是因为看出我也算是个正派的读书人吧,他从一开始就对我表现出亲切感。我当时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但博士毕业不久,在社会主义研究领域里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他年比我长,资比我深,已经发表了大量著述和译述,被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研究领域里中年一代的佼佼者,这让我起初对他多少有些仰视的感觉,但他从没有给过我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印象。这样,我们之间很快就没有界限了,和他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了。我还间接地听说,他在许多场合,对我发表过的一些学术文字很表示过欣赏,这让我十分感激。而这些,他是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白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他“瞧得起”你,他会发自内心地帮助你,赞赏你,和你平等相处;至于回报,他是从来不要求的,因为这在他的头脑里是连想都没想过的。
世鹏本人一心专注他的研究,除了一周两次的上班日,平时很少来单位。即使是在上班日,也总是看到他在自己办公室里读书、翻译、写文章,再不然就是去图书馆借书,难得过来聊聊天。所以,尽管我和他的办公室是隔壁,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基本上限于公事,言简意赅;几句话一讲,他就回头去搞他自己事情去了。后来我移居到了他家附近,偶尔也会因事到他家里坐坐,谈的仍然多半是学术和工作,至于生活之类的话题,在我记忆里好像从来没有涉及过。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说是地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再后来,他调回北京大学去了,但仍然常常和我通电话,还曾多次邀我和殷叙彝先生一起吃饭、看京戏。世鹏是个爱戏、懂戏的人,殷先生更是个老戏迷,他们都是看过梅兰芳,见过大场面的,极会挑错。只要台上的演员们 (这些演员可是不得了,大都是当红的“角”)稍有偷懒或舛误,一句唱腔,一个动作,台下的这两位立刻就能看得出来。这着实让我吃惊,也让我长进不小。我从小看过几出戏,也读过些戏本之类的东西,在自己的同龄人中间还可以冒充一下行家,跟他们在一起,自己觉得就成了地道的小学生。记得有一次,由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到北大演出,世鹏买了最好的贵宾席的票,邀赵宝煦先生、殷叙彝先生和我一起去观看。台上载歌载舞,如泣如诉,台下观众陶醉其中,忘乎所以。而世鹏们这几位呢,虽然也有不少称赞的话,但还是觉得传统韵味不足,演员功力尚有欠缺。我当时心想:先生们,依我看这够好的了,还这么挑剔?
2004年,我正在德国做访问学者,世鹏紧急给我打电话,要我在最短的时间里决定,是否愿意调来北大。我当时手足无措,回答说愿意,但在内心里,感觉自己和北大素无渊源,心里没底,加之对编译局的丰富藏书也不舍得放弃……那就试一试吧,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十分迅疾,一步步就走到了办调动手续。后来我知道,在整个过程中,他和黄宗良老师起了很大的推荐作用。就这样,我在2005年进入北大国关学院,又一次和世鹏成了同事。
世鹏这时候的身体又已大不如前了。后来那些致命的症状,全都显示了出来。在编译局时,他还可以偶尔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甚至发表一席讲话,但现在,他除了来校上课,就很少参加别的活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哮喘越来越严重,上课和开会讲话时又是气喘,又是咳嗽,经常被痰堵住,好一阵缓不过气来。我们大家看着他痛苦的样子,真是替他难受,可谁也没有办法。我所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少一点他的工作,凡是我能够替代的,由我接过来。但是,各级学生的教学,特别是带博士生,加上随便从哪一级主管部门派下来的杂事,加在一起,还是相当忙碌的。世鹏去世后,我有时想,如果他中年以后不是回到教学岗位,而是仍旧在书斋里一心搞他的学术,毕竟简单纯粹些,那样的话,是否对他的身体更加有利?或许今天他还在世?唉,现在谈这些,只是无用的猜想而已,如今只空余遗憾了。
然而,世鹏自己仍旧很乐观,也很达观。他照样上课,照样完成他的科研课题,发表一篇篇的论文,不时还拿生与死的话题来开一下自己的玩笑……我多次劝他:老兄,已经不错了,这辈子也算得上功成名就了,该放松一点了。不管怎么说,身体第一,工作第二!他倒是满口答应,可最后却不服气地又垫上一句:话是那么说,可要是不写东西,你说叫我干些什么?于是我明白了,科研和上课,已经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前面说过,世鹏在学术上的主攻方向,是西欧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他先学俄语,后学德语,对这个领域的外文材料相当熟稔,他发表的许多著述在学术界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这一领域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治学特点是认真、踏实,从扎实可靠的材料出发,不讲空话;在思想上,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和他有不少地方相似,但也有不同。我自认为是那种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学说我十分推崇,但我想首要的是吸收其中富有历史感的分析方法,而在这个前提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少观点和主张,对后来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史的进程,我认为是需要重新考察和评价的。世鹏对我的这个主张是完全赞成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也常常有所不同,例如,对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看法,就是如此。世鹏对我们俩之间的不同处也很清楚,但他绝不是那类固步自封的宗派主义者, “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恶习在他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他只要觉得你的观点有道理,就诚心诚意地同意并吸取;如果你的观点是有理有据的,但还不足以说服他,他也能够平心静气,坦然对待。即使对那些与他的观点完全相左的人,只要在他眼里是真诚的和有学问的,他照样推崇。他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激烈批评者,但在遵循思想和学术自由这一原则时,我没有见过比他做得更好的学者了。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说:“世鹏,我觉得我比你右一点,而你比我左一点。”这是我对他太了解、太熟悉之后的口无遮拦之语,他不但不以为意,反而把这个玩笑话拿到研究生班上大讲特讲!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饱受病痛折磨。起初没到退休年限,他必须来校上课,而这三节课对他来说近乎一次博命之役。好几次下课后在院里相遇,只见他手扶着墙或别的什么能够支撑的地方,面无血色,眼睛无神,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地喘气。问他一句“你感觉怎样”,他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喘,往往要过十几分钟后,才能稍微缓和一点,慢慢恢复正常,打车回家。有一次,托马斯·迈尔等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者来京,在东三环一家饭馆请我们吃饭,陈洪捷教授、我和他一起前往。当时正值酷暑,浓云密布,又闷又热。一路上车流汹涌,壅塞不堪,起初我们还能聊几句,后来他就感到越来越透不过气了。但他像平时一样,勉力支撑着。到了饭馆之后,餐厅在二楼,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移。我感到,这段短短的几步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万里长征。好容易走到了楼梯一半的转弯处,他再也走不动了,大口喘气,说不出话,只是扶着栏杆,一头冷汗。周围的人都吓坏了,德国学者们也走下来问长问短,他根本无法回答;饭馆的服务员们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当时众人的感觉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就在于这辆救护车了。但一等不来,再等不来,联系多次,才得到答复,说是路上堵车,没办法。真是一筹莫展啊!就这样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才听到他艰难地从胸腔里发出两个字:回家……
这次让人惊悸的事件之后,在我记忆里,他就再没有参加过外面的应酬活动了。但他仍然在带研究生。如今在网上把大学教授叫作“叫兽”,对研究生导师更是骂成一片。不错,这样的“叫兽”确实不少,他们到处揽课题,转手把“活儿”塞给学生,自己心安理得地当老板。学生们在老板面前不敢怒更不敢言,还得赔着笑脸。这号教授的确该骂!但世鹏绝对不在此列。与其说学生们为他服务,不如说他为学生们服务。他审读自己博士生们的论文,一丝不苟,从观点到文字,从布局到引证,一句一句地批改,如此反复多次。在许多情况下,他对那些论文所做的修改,比他自己写论文还要费力。他对学生看上去有点严厉,其实全都是为了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在未来有所造就。他有时也会觉得烦恼,私下也会跟我发一通牢骚,对那些糟糕的论文抱怨一番,但这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对自己工作的热忱。他把为自己学生所做的工作,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名教师的本分。按说,这样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教师的职责本来就应该如此,但现在又有多少人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呢?像世鹏这样诚实无私、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的教师,我们的教育体制又是否给过他们应有的尊敬呢?
世鹏最后一次住院,我从他夫人那里得知,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内心里一天比一天紧张,可还是抱着一丝侥幸:也许,靠着医院的救治和他自己的顽强,这一次他还能像前几次一样挺过去,重新回到大家中间?我去医院探望过几次,眼看着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颜面越来越枯槁,遍体插满管子,但我依然不愿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世鹏的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不会再有奇迹了。是的,事实就是那么无情。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够走出医院。痛哉世鹏!哀哉世鹏!如果不是可怕的绝症,以他的年龄、勤奋和智慧,他还能够为我们的学术做出多少贡献啊。
岁月易逝,世事无常,世鹏去世转眼间就过了一年多的光阴。悼念这位多年老友,我觉得任何高调赞颂的话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一点也不看重这些。我只想自问:像这样一位正直坚毅、朴实诚挚、表里如一、内心纯净得如同清水一样的朋友,今后我到哪里去找?
(写于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