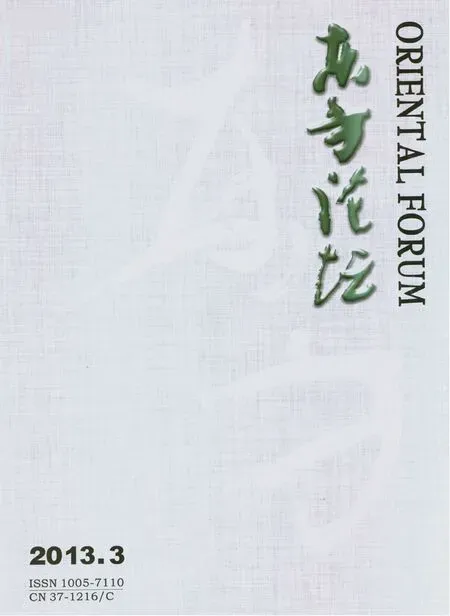论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策略与文本形态
李萌羽 温奉桥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论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策略与文本形态
李萌羽 温奉桥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张恨水小说的成功源于其文化策略的成功。文化“配方”策略决定了张恨水小说的叙事模式和故事架构,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张恨水小说的文本形态,特别是其小说的“双极结构”,更是其文化“配方”策略的外部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的分裂。
张恨水;小说; 文化策略; 文本形态
作为现代市民小说的集大成者,张恨水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张恨水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作家,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如《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都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张恨水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策略,对于一个通俗小说家而言,张恨水的文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小说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这种文化策略又对其小说的文本形态、审美取向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恨水的小说的典范性意义,不仅表现在其巨大的影响力和作为新文学的参照性存在,更表现在他对市民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文化自觉方面。
一
在对市民读者阅读心理的了解和把控方面,张恨水堪称是大师。张恨水对普通市民阶层的人生悲欢以及他们的生活欲求和潜在期望,相当了解。对一般市民读者而言,也不太需要和喜欢“教训”的意味,他们读小说,主要是消闲、娱乐,喜欢刺激和趣味,“故事”的趣味性比思想性要重要的多。因此,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讲的都是世俗故事,不避俗,不怕俗,不故作姿态。张恨水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从本质上与市民阶层没有大的差别,这是张恨水“走红”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
张恨水做过几十年的“报人”,这使他对社会有着较常人更为深刻的了解。张恨水深知市民读者的心理,也深知自己小说的“卖点”所在。张恨水的小说是与市民阶层的文化心态相契合的。张恨水生活的那个时代,政治上的黑暗和高压,言论上的极端不自由,更进一步刺激了市民读者“窥视欲”的膨胀,普通的民众在“阅读”之中,达到了某种宣泄和幻想性满足。特别对官场和“上流社会”的“窥视”和憎恨心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张恨水小说特别是他前期的《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在一定意义上,为满足这种“窥视欲”,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张恨水在谈到《春明外史》时曾说,“《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一条路子。”[1](P34)所谓《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实际上就是“谴责小说”的路子。“谴责性”主题在《春明外史》之后的《魍魉世界》、《纸醉金迷》、《五子登科》、《八十一梦》中都有集中表现。这些小说之所以引起普通市民的广泛关注和兴趣,除了自身具有某种刺激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了普通市民某种被压抑的潜在的正义欲望,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法实现的正义期盼,在这里得到了某种替代性补偿,这符合中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道德原则和文化心理。《春明外史》可以认为是张恨水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在艺术性上无法与《金粉世家》、更无法与《啼笑因缘》相比,但是,这部小说在当时的“轰动效应”,似乎并不在这两部小说之下。《春明外史》之所以引起市民阶层的广泛阅读兴趣,恰在于小说所体现了普遍性市民社会文化心理。张恨水说:“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写《春明外史》的打算。”[2](P119)所以,在小说文本建构方面,以新闻记者杨杏园的眼光,夸张性地呈列了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态、怪态。这类夸张性描写,张恨水似乎还感到不足以抓住市民读者的阅读欲望,需要进一步“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在《春明外史》中,还有许多明显的“影射”故事,张恨水甚至将许多真人真事略略改头换面,直接写进小说,以至于许多熟悉北洋政府和当时文坛的人,认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时,许多读者并不把它当作虚构性的“小说”来读,而是把它看作是“新闻外的新闻”,甚至有些读者“将书中人物,一一索隐起来。”[3](P4)虽然张恨水后来意识到这种“野史”式的写法“欠诗人敦厚之旨”[1](P39),但确实“刺激”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世界晚报》连载不久,就引起了北京读者的热烈反响,甚至有些读者为了先睹为快,每天下午到报馆门口排队等报,《春明外史》成了《世界晚报》的第一张“王牌”。《春明外史》的成功,与张恨水对市民文化心理的深刻了解有关。张恨水说:“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4],对一般市民读者而言,对达官贵人、上流社会的生活的窥视欲和潜在的嘲弄心态,在《春明外史》中得到了幻想性满足。这是《春明外史》成功的一个“秘诀”。在《金粉世家》中,这类夸张性、暴露性的描写明显减少,但豪门巨族的生活本身就具有吸引力,权且不说国务总理的家庭生活,也不说金铨在官场上如何与对手争斗、周旋之类,但就国务总理家里的摆设,在当时就成为饶有兴趣的大众“话题”,更不用说那些豪门里的艳闻、秘事。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满足了读者的猜测和想象,如第二十九回金燕西过生日,金太太送了一套西服,二姨太送了一支自来水笔,梅丽送了一柄凡呵零(小提琴)、两打外国电影明星大照片,等等,从这些“小物件”可以透释出某种进步和“文明的气息”。再如《金粉世家》中多次描写了舞会上女性的晚礼服,上身仅仅是一层薄纱,胸脯和脊背露出一大截雪白光洁的肌肤,下身穿着稀薄的长筒丝袜也透出肉红。这类描写在《啼笑因缘》里也多次出现,樊家树的表嫂陶太太到北京饭店参加舞会,穿的也是西式的盛装,长筒的白丝袜,紧裹着大腿,非常新潮,更不用说何丽娜的洋化作派,所有这些,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这符合当时市民阶层某种时髦和追逐“高雅”的文化心理。
张恨水小说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是建立在市民审美文化心态基础之上的。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张恨水小说所体现的通俗化与高雅化是相互融合的,是相辅相承的。他的作品的高雅不是纯艺术的脱离民间情趣的高雅,他的作品中的通俗也不是完全平民化的毫无文采的通俗。张恨水小说的突出特征是高雅化的通俗,总是有一种蕴味包含在他的小说中,这样,就使他的作品既能在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又能被市民所接受。”[5]张恨水的小说,其审美情趣雅俗兼有,就其故事类型而言,言情、武侠等极为适合一般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故事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但是,张恨水与一般通俗小说家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的通俗中所表现出来的“雅趣”,如《金粉世家》,这本是一个带有“传奇”性的通俗故事,但是这其中也常蕴含有某种“雅趣”,表现出某种富有一定深度的人生感喟。第三十五回,金燕西与冷清秋到西山游玩,看到漫山黄叶飘零,冷清秋的某种人生感慨:“天气冷了,这树就枯黄了不少的树叶。忽然之间,有一阵稀微的西风,把树上的枯黄叶子,吹落了一两片,在半空中只管打回旋,一直吹落到他们吃茶的桌上来。……人生的光景,也是这样容易过。”[6](P461)这种“雅趣”,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口味。再如,在《金粉世家》中,张恨水并没有把豪门金家写成多么腐败和落后,相反,处处显示某种“文明”气象,金铨曾留学巴黎,他的两个女儿敏之和润之,都曾留学欧美,读英文小说,青年男女开口闭口“密斯”,但有时由于“照顾”和迎合一般市民读者的某种“俗趣味”,故意卖弄,如第四十三回,写冷清秋与金燕西夜宿西山后,在西味楼约见金燕西,告诉他自己怀孕之事,由于羞于开口,冷清秋先打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哑谜让金燕西猜,然后又取出自己一张名片,在名片背上,写了一行字道:“流水落花春去也,浔阳江上不通潮。”这类写法虽然格调不高,但是颇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趣味。
二
对市民文化的深刻理解,使张恨水能够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文化策略”,每每都抓住读者的“兴奋点”。张恨水的这种“文化策略”,在他的小说中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配方”。
张爱玲曾说,喜欢看张恨水的书,因为不高不低,又说,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张爱玲所谓的“不高不低”、“代表一般人的理想”,其实就是张恨水的一种文化“配方”策略。由于深谙市民读者的文化心理、审美口味,张恨水小说的文化“配方”,客观上满足了市民阶层多种文化需求和阅读兴趣,成为他小说老幼咸宜、妇孺皆知的秘诀。范伯群称张恨水为“善于脍炙‘通俗化的三鲜汤’的能手”[7](P325),张恨水在谈到《金粉世家》的成功“秘诀”时,说“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切有味。”[1](P42)实际上无论是范伯群还是张恨水自己,所说的是一个问题——文化“配方”策略。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港台的一些文学作品的“配方”,说这些作品“有一些文化但绝不坚实,有一些伤感但绝不沮丧,有一些愤怒但绝不激烈,有一些知识但既不十分生僻也不十分流行,有一些爱心但是并不疯魔,既不是基督式的爱也不是我佛的那种爱,这样的作品特别容易被现在一个时兴的词叫什么‘小资、白领、中产’特别容易被接受”[8]。市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一方面直接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文化市场潜在地影响或制约小说的审美取向,从而最终影响小说的文本建构。这在张恨水的市民小说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从大的方面讲,张恨水小说都自觉遵循着一个大的“配方”:那就是“X+言情”策略,这个“X”在《春明外史》、《斯人记》、《金粉世家》以及《啼笑因缘》、《夜深沉》、《艺术之宫》等小说中是“社会万象”;在三、四十年代的《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热血之花》等小说中,则为“抗战”。这种“X+言情”的“配方”策略,决定了张恨水小说的故事模态。就张恨水前期小说而言,其“文化配方”模式主要有这样几种:《春明外史》:黑幕+言情;《金粉世家》:豪门+言情;《艺术之宫》、《美人恩》、《斯人记》、《夜深沉》:社会底层人(女模特、舞女、戏子等)+言情;等等。其中,《啼笑因缘》的“配方”最为成功。这部小说综合了以上各种“配方”模式,既有准豪门如何丽娜、陶伯和,军阀刘德柱,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樊家树,贫寒人家沈凤喜一家,豪侠之士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等。权且不说小说对北京民情风俗画的逼真描画,和婉转曲折的爱情故事,仅就小说的“平民+言情+武侠”的文化策略而言,也无不抓住了当时市民读者的想象兴奋点。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配方”从根本上决定了张恨水小说的“言情”叙事策略。张恨水小说的言情故事,即使是“抗战”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三角”或多角恋爱的“叙事模式”。对此,台湾学者赵孝萱曾有详细条述:“一男两女模式”如《春明外史》杨杏园、李冬青、史科莲;《金粉世家》:金燕西、冷清秋、白秀珠;“一女多男模式”如《啼笑因缘》樊家树、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一女两男模式”如《天何配》白桂英、王玉和、林子实;《杨柳青青》桂枝、赵自强、甘积制;“一女多男模式”如《夜深沉》杨月容、丁二和、宋信生、刘经理;《美人恩》常小南、洪士毅、王孙、陈东海;等等。“三角”或多角恋爱成为张恨说小说的最重要的言情策略,这种叙事策略也许来自于张恨水对《红楼梦》的某种领悟。新锐批评家们喜欢用“叙事圈套”之类,这种“三角”或多角的叙事模式,大概也可以算作张恨水的某种“叙事圈套”。张恨水小说中的这种大量的“三角”、“准三角”或“多角”故事模态,单纯从这种言情故事的外在形态而言,确实带有某种鸳蝴派的影子,带有某种才子佳人气息。但这其中包含了张恨水的某种“苦心”以及小说叙事哲学,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增加故事的“趣味”一面。以《啼笑因缘》为例。据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讲,《啼笑因缘》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张恨水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写”,“改写”的原则除了要有“噱头”以外,还必须“不能太隐晦,又不能太明显,同时,既不能太抽象,又不能太具体。主要还得雅俗共赏,骚人墨客不讨厌它,而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可以听得懂,叫得上来…”[9](P215)《啼笑因缘》在上海《国闻报》连载时,“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请我写两位侠客”[1](P44)。于是小说里面有了关寿峰、关秀姑两位武侠式的人物,和一系列的侠义行为的描写。本着这一“原则”,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把各种审美质素进行了最为“合理”的“配方”:封建军阀刘德柱的飞扬跋扈,“平民化大少爷”樊家树的贞情,寒门鼓姬沈凤喜的爱慕虚荣,豪爽女侠关秀姑父女的仗义除暴,更不用说樊家树、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之间的多角爱情纠葛,诸多故事,熔于一炉,张恨水就像魔术师一样,把这诸多的审美质素,进行“调和”,成为市民文化的“大餐”。《啼笑因缘》这部小说不仅在一般市民读者中“脍炙人口,尽人皆知”,而且,当时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男女学生也为之“疯狂一时[10](P230-231)。《啼笑因缘》出版70多年来,至今已经有26个版本[11],先后14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荧屏,几乎每5年一次[12](P65);被改编成各种地方戏曲、剧种等,更是难以计数。《啼笑因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配方”策略的成功运用。
三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配方”,还直接影响了其小说的文本型态。在故事的“经营”和“设计”方面,张恨水无疑是个天才的作家,单就经营故事而言,张恨水在现代作家中是屈指可数的。
现代小说理论认为,小说的关键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如何讲故事。对通俗小说而言,同样如此。如何让这个故事有趣,抓住读者,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事。这就需要一种真正的“经营”故事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是建立在对市民读者的文化需求、审美口味深刻了解基础上的。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市民小说,可以称之为“世情小说”,描写和反映的是现代以来处于“过渡时代”市民社会的人生百态、生活万象,对市民阶层而言,没有“言情”就没有“趣味”,少了某种“情趣”,但是,仅有“言情”,又容易让人起“腻”,让人厌倦。对此,张恨水有很深的领悟。因此,自张恨水创作初始,就抛弃了纯“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之路,走的是一条社会言情小说也即是“世情小说”的路子。
张恨水的市民小说,远承古代的“世情”、“人情”小说传统,又受民初“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的影响,应该属于现代“世情小说”的范畴。在这种“社会+言情”的故事构架策略的同时,张恨水更注重市民读者的审美“口味”。“社会+言情”的写作策略,表现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上,就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13](P103)的小说构架,张恨水的这种故事构架,似乎受到民初小说家林纾的“经以国事,纬以爱情”的影响。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认为,在张恨水的小说中“爱情不过是穿针引线的东西,他所要表现的,是社会上真真实实存在过,发生过的事情,应该属社会小说,记述的是民初野史。”[10](P248)张明明的说法大概是受到侯榕生的影响[14](P358-373)。其实张明明所说的“社会小说”,无非是突出张恨水小说的对市民社会的暴露性、批判性描写的一面,也即“社会性”,但是,爱情之于张恨水的小说,即使是前期的作品,也并非是“穿针引线的东西”。
就张恨水的创作实际而言,其最精彩、最雅致、最细腻之处,在其“言情性”,而不是那些社会性内容的描写。具体到《春明外史》而言,似乎言情的成分占小说的比重并不太多,但它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魂”,成为这部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张恨水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言情”都构成了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张恨水在诗中说自己的小说“替人儿女说相思”,也就是指其小说中的“言情”。“言情”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具有本体性意义,也就是说,“言情”是张恨水小说成功的一个决定性质素。左笑鸿说张恨水的小说“拿恋爱故事绕人”[15](P62),所谓“拿恋爱故事绕人”,其实正是张恨水小说的制胜法宝,也是抓住读者的最重要的“武器”。对此,似乎不应该特别回避。
其实,张恨水的这种文化“配方”策略不仅成功运用在小的故事构架上,也成功运用在了人物性格的“合成”上。有的学者分析樊家树吸引读者特别是的女性读者的原因在于“樊家树是一个具有中庸之道的好男人,这个角色也满足了不同类型的女孩子的想像”[16],你说他传统吗?他有传统才子的那种气质,吟诗作赋,惜香怜玉,但是他又不是冬烘先生,不是老封建,他又很新,他又新又旧;他又能够接受现在的自由平等,他又讲忠孝两全,又讲自由平等,所以两边他都占着,他又风雅又果断,所以樊家树你挑不出他太多的缺点来。从文化“配方”策略和读者文化心态的角度讲,孔庆东把《啼笑因缘》称为是“大众文学的范本,是最精致的一范本”是有道理的。应该说,《啼笑因缘》不仅是张恨水当之无愧的代表作[10](P231),也是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经典之作。
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文化“配方”策略容易导致文本撕裂,也就是文本的非统一性。一般认为,张恨水小说存在普遍的“双极结构”,其实,所谓“双极结构”,也就是文本分裂的产物,这一点在前期的《春明外史》,特别是后来的“抗战—国难”小说中表现明显。在《偶像》自序中,张恨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抗战文学的思想: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然而抗战文艺,要怎样写出来?似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我有一点偏见,以为任何文艺品,直率的表现着教训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认为是一种宣传品,根本就不向下看。……
文艺品与布告有别,与教科书也有别,我们除非在抗战时期,根本不要文艺,若是要的话,我们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训读者之手腕。[17](P253-254)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自1931年《满城风雨》起,先后推出了《太平花》、《满江红》、《热血之花》、《巷战之夜》、《潜山血》、《大江东去》等——在整体上是“抗战+言情”的路子。张恨水最早的抗战小说《弯弓集》可以说“言情”与“抗战”平分秋色,寓“抗战”于“言情”,如《最后的敬礼》,故事的曲折性、趣味性很强,笔法浓艳,有点徐讦《风萧萧》和陈铨《野玫瑰》的意味。在这些小说中,张恨水力求在“抗战”和“言情”中寻求平衡,既体现“时代意识”,又力求能够发挥自己擅讲故事的长处,尽量在“抗战”的背景上将故事讲得曲折生动感人,在这方面《满城风雨》和《大江东去》结合的相对较好,较好地体现了张恨水出色的结构故事的才能和细腻的笔法,较好地体现了张恨水的艺术个性。如《满城风雨》对具体的战争场面描写不多,采用了《春明外史》中“双极律”的结构手法,既以主人公大学生曾伯坚的活动为线索展开正面的描写,表现了对军阀混战的揭露、谴责,同时又以曾伯坚与淑芬、淑珍姐妹的爱情故事展开情感线索,相互交织,具有较强的情节性。
但“抗战+言情”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冒险。“抗战”和“言情”有时相互游离,相互拆解,容易成为“两张皮”。就写作技术层面而言,“抗战”小说一方面要避免“书生写故事”,另一方面还要有可读性,这实际上是也是两难。在《虎贲万岁》中,张恨水说:“小说就是小说,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他“找点软性的罗曼斯穿插在里面”[4]。从这种考虑出发,在这部基本是“战史”的小说中,张恨水施展了他惯用的“三角恋爱”模式,“穿插”了程坚忍与鲁婉华、刘静婉的爱情罗曼斯故事,还有王彪与黄九妹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张恨水对于在这种抗战小说中能否“穿插”过多的罗曼斯缺乏信心,不敢“跑野马”,所以,实际上“软性”故事所占篇幅太少,几乎可有可无,根本无法起到“引起读者的兴趣”的作用。丢掉了“言情”的张恨水,实际上已经不是张恨水了,他的“抗战”小说,许多就是“干炒海参”[18],意味全无。客观而论,张恨水抗战小说的文本分裂,源于其此时创作心态的“分裂”:“意识”与情趣的分裂,艺术个性与主流价值的分裂。他的许多“意识”先进的作品大都艰涩难读,而他最擅长的作品、最符合他的艺术个性因而最富有情趣的作品又往往被指责为“意识”落后。在一定意义上,张恨水前期小说的成功,源于其市民文化策略,后期作品的失败也同样源于这种文化策略。
张恨水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他绝不仅仅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啼笑因缘》等经典小说,“张恨水现象”其实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1]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2] 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A].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3] 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A].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4] 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A].张恨水.虎贲万岁[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5] [埃及]侯赛因·伊卜拉欣.张恨水小说的俗与雅[J].东北师大学报,2000,(5).
[6] 张恨水.金粉世家[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7] 范伯群.漫谈《啼笑因缘》[A].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8] 王蒙.文学的期待[J].王蒙研究,2006,(5).
[9] 张明明.有关《啼笑因缘》的二三事[A].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10] 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A].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11] 袁进.与“三”结缘的张恨水[EB/OL].http: //www.cctv.com/ program/bjjt/20040928/101925.shtml,2004-09-28.
[12] 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M].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6.
[13] 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A].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14] 侯榕生.简谈张恨水先生的初期作品[A].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侯榕生在此文中,有类似的观点.)
[15] 赵孝萱.张恨水小说新论[M].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2002.
[16] 孔庆东.《啼笑因缘》的爱情三模式[EB/OL].http: //www.cctv.com/program/bjjt/2004 0928/101941.shtml,2004-09-28.
[17] 张恨水.偶像·自序[A].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18] 张恨水.干炒海参[N].益世报,1928-02-09.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the Cultural Strategy and Narrative Mode in Zhang Henshui's Novels
LI Meng-yu WEN Feng-qiao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
The success of Zhang Henshui's novels lie in his cultural strategies,which determine his narrative modes and story structures and decide his textual forms in a fundamental manner.Particularly,the "double polar structure" of his novels is the outside representation of his cultural formula,and intrinsically is a kind of disintegration of his novels.
Zhang Henshui; cultural strategy; narrative mode; textual form
I207
A
1005-7110(2013)03-0089-05
2013-03-29
李萌羽(1968-),女,山东日照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温奉桥(1969- ),男,山东沂源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