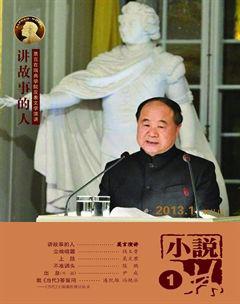我们生活,我们焦灼
最近刚刚又翻了一遍《红楼梦》。早期阅读对人影响的顽固性,往往超出你的想象。当纷繁的各种小说(尽管它们都很优秀)让我觉得嘈杂、疲倦之后,我就回到《红楼梦》,翻阅,然后澄净、松弛。真是积习难改。习惯自然就会孕育偏见。比如我读后四十回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前八十回,因为随手翻看,纸张不但陈旧变黑,而且几乎散落。
事实是,反复翻阅《红楼梦》成了我基本的生存状态之一。很多时候,我竟然会觉得,《红楼梦》似乎具有某种我私人的色彩。家族或社会批判小说,这种界定只能换得我从心底的嘲笑,就像有人声称你的亲人有某种嗜好,却完全张冠李戴一样。它甚至也超越了汉语文学里最缠绵动人的那一场旷古恋情。它远远不止是描绘爱情。
就像古典诗文四处涌动着生命飘逝的感叹,时间也是《红楼梦》编织的基础维度。不仅因为它牵涉众多死亡、家族命脉的兴替转换。《红楼梦》的时间进展是模糊的,而且汊港纷繁。但文字累积,蓦然间就已物换星移,人们或已成长,或已经凋落。当然,《红楼梦》首先是个人的。有关个体的欲望与体验,有关个体的成长或衰老,有关生命的消磨与确证。我的疑惑是,某些清晰确定的东西,比方究竟谁跟谁在相爱,都会众说纷纭。难道一个让古代女孩烦杂纠结的情感命题,至今暗昧难明?尾随着林姑娘出场,总是翻卷起的那层层语言的浪花,她的刻薄而狡黠,任性而敏慧,都是生命的张扬和挥洒。但传统习俗给予爱情的表达空间非常缺乏,因此对它的每次挑拨和叩问,都变成了确证个体实存的渴望。
科技进展疯狂,时间和空间被挤压得紧密异常。近二三十年,信息、交通极度提速,日常生活内容和人际联接,都已面目全非。价值评判体系,甚至包括认知事物的概念,都将彻底革新。每当审视“爱情”这个词汇,热烈、持久、忠贞,甚至饱受磨砺,都是人们笃定的心理期待。但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男性为主导、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是传统爱情的基础。而当拥挤的城市孕育过分丰富的变化和冲突;当女性绝对弱势的处境发生转变,爱情附着的外壳自然纷纷剥落,洒落一地。
爱情逐渐变得只像是一个虚幻的童话,我们迷恋的仅仅是它的非现实色彩,或已逝的缥缈。有谁还像林姑娘那样,在猜忌环伺中闪转腾挪,自己却在没猜破爱情哑谜之前就香消玉殒?有谁还幻想能邂逅杜小姐,然后与之生生死死、忠贞不渝?或者有谁像托翁那样,即使安娜长期压抑,当她爱情自然萌动流露,也要鞭辟入骨,将她推向冰冷的铁轨?
也许没等我们来得及察觉,巨变就已经发生——偷情正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被排挤出去,不知是应该悲哀抑或庆幸?
上一段感情已经变得日渐平庸,并显露出它真实却可怕的面目。在它有堕入庸俗的危险时,李果下意识地准备好了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当它自然却又突兀地靠近时,他触碰把玩它,其中的自得和满足不言而喻。但他很快意识到了我们“70后”的痼疾:当我们费劲去掂量一段感情时,我们其实已经身在其中。
《不准调头》的尴尬就在于,在陈果内心深处,对那份新感情的定义和期待,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它要求当事双方苛刻的感情投入。但在“偷情”被取消的年代,它沉重得难以承受,而以婚外恋的方式呈现,更让它很荒诞。陈鹏的初衷可能是向前辈作家致敬,创作一个足以跟他们的伟大小说相媲美的“偷情”故事。结果完全出乎意料:这个具有时代鲜明特点的婚外恋故事,恰恰反映出“偷情”正在消亡的现实。
陈鹏叙事感觉真的很好。凭本能,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故事应该终结的地方:从爱情撤离,然后回到坚实的地面——生活。生活总是无比强硬,也无比肥沃,那是滋养我们的地方,也足够疗救我们。
就像已经说的,爱情本身已经有了诸多改变,但作为对个体实存进行确证的一种方式,可能不会改变。难道这也仅仅是我的个人偏见,或者仅仅是一个成长环境相对稳定的“70后”的问题?
作者简介:宗永平,笔名自树,江西新余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十月》杂志社编辑部。早年出版有中篇小说集《怀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