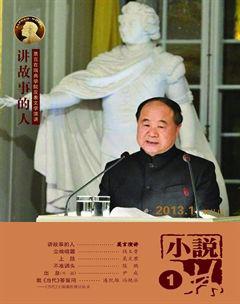上肢
直到现在,她依旧被固定在橱窗里的一个玻璃架子上,——看上去就像她自己悬在那儿,要不是那几根故意留下的肌肉纤维,指骨的色泽也细微的有一些差别,说她出自匠人之手,是一个细致的工艺品,也没什么不可信的。
不知多少人注意过,在这个画廊、古董家具店、咖啡馆云集的街区,还有这样一家人体博物馆。青灰色,两层,开着玻璃天顶,光线明亮。
进来的人依次看完全身人体、内脏系统、循环系统,穿过绘有器官图案色彩绚烂的走廊,进入第二层展厅,就会看到她站在光束中,指尖并拢,柔和地往下垂着,肩胛骨斜翘,很像背着一对翅膀的天使的侧身。也有人说她像踮起脚尖的女芭蕾舞演员。她的指关节衔接得很好,一点没有矿化变异。但其实,闭馆以后,把她卸下来,就知道明显没有以前光洁了,暗绿的毛细血管一样的东西从骨质内部丝丝缕缕扩散开来。
负责处理她的人,每过几个月,用专用的软布擦拭她一次,涂上防腐的药剂。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医学博士了,把她从一堆杂乱的肢体中找出来,带回医学院,花费不少功夫,把她制作成现在这样。这个人也是年轻的,来这家小小的人体博物馆刚一年,手势温和细致,看她的眼光也有些特别,好像她挺值得爱抚。
和别的展品一样,她也有一个独立的说明,刻在钢制的牌子上。
“上肢”。
如今,她就以“上肢”的形式存在着。
她出生时,家中已没有像样的家具,由祖母作主,仍沿袭有钱时候的习惯,请了人给她拍周岁照,还悄悄请人给她排了八字。
“金木水火土,样样齐全。”此人在纸上写算半天,连连说,“此命好,此命好啊,在家帮父母、出门帮丈夫呢。”
祖母喜滋滋拿出金镯给她戴上,——周岁照上她被面容疲倦的母亲抱在胸前,右手腕上的确有只镯子,但是等她长大后并未见过。丢了的也不仅是这只戴过,却没有戴过印象的东西。反正每年都会不翼而飞一些东西。
父亲对同居一屋擅长搬嘴弄舌的兄弟姐妹毫无办法,只会站在他们这一边帮着训斥母亲。看多了母亲暗暗饮泣,发着高烧也没人端一口水,她从小不喜欢这幢住过很多代人的老宅子。她也不喜欢春熙弄,憎恨这里的狭窄阴暗,憎恨地上墙上到处孳生的霉花和偷懒把脏水泼到路上的邻居。
其实过去住春熙弄的都是殷实人家,房子虽旧,但很结实,门板上留着门环叩过的凹痕,院子里残存的石块,依稀还有几分假山的轮廓。可是,在她看来,晒不进太阳的春熙弄是黑的、冷的,进出的人虽客气地打招呼,心里却藏着一个更黑、更冷的屋子。不是这样,十五岁的时候她也不会走了。
母亲刚查出来得了肝硬化,她就决定走了。依旧每天早上去学校,放了学去医院照顾母亲,小心不露破绽,直到四个半月后母亲去世。
母亲断七那天,她偷拿了办丧事剩下的钱,怕父亲找,舍近求远,从邻市上了火车。车开了,正是晚饭后天将要暗下去的时间,她看着车窗外滑过的站牌,松了口气。——她成功地从春熙弄走掉了。第二年,父亲不知从哪儿听说她在长白山开参茶店的表哥那儿,赶到东北,却扑了个空。对春熙弄来说,她整整消失了二十一年。
她回来这年,已经三十六了。
父亲早几年就走不动路,靠一根拐杖,从房间踱到门口,再从门口踱到房间。这是他早年下乡,两派争斗火并,伤了腿肌腱的后遗症。这几年加上高血压、痛风,情况更糟。她从一个同学那儿听到这个消息,没有犹豫就回来了。她不是二十一年前的她了,随便他说什么,都能应对。可是,她在弄口下了出租车,远远看见伸出院墙的泡桐树,叶子在风里簌簌地晃着,心突然跳快了。
几个人正在说话,声音越过院墙飘出来,她辨出父亲的声音,“我讲给你们听,随他们怎么弄去,变来变去,我们这些人反正也发不了财,也饿不死,不过等死吧……”
她从开着的院门走进去,声音断了,站着、坐着的人都回过头看。她一眼看到父亲,红润的脸小孩儿一样笑着,头发只剩稀疏一圈儿,全白了。手里捧一只碗,几块豆腐覆在饭上,也不知算午饭,还是晚饭。
他依然含着笑,默默看着她,那眼神,就像给她的心上压了一块石头。他在责备她吗?他凭什么责备她?她想起母亲死去的脸,却激不起过去的恨。
走进客堂间,饭桌还是过去那张。那时她一怕,指甲就在桌角乱画,画出许许多多条鱼。她画得最多的就是鱼。她摸着桌角,再看纱罩下的半碗豆腐,挂在墙上的篮子、镜子,堆得山一样高的旧书报,角落里积着灰的酒瓶,心里一酸,拿出带给他的羊毛衫、烟,一件件摆到饭桌上。他高兴了,跟旁边的人介绍,“我女儿。我女儿。”
他们说着话,这些人也不走开,就在旁边忙着。他们都从江西过来,租着这儿的房子住着,靠做防盗窗,日子过得不错。
大伯父、二伯父、三姑、小叔早搬走了,这些江西人住的就是他们的房间。父亲告诉她大伯父自己开了印刷厂,二伯父的女儿去美国了,嫁了个美国人,去年二伯父他们还去美国住了半年,帮她带小孩,三姑前几年生了肠癌,今年复发了,怕是不太好。一阵大咳,放下碗,点了根烟,抽着,很有兴味地问她,“王林生你还记得吧?”
她说记得,不是在广州开公司吗?那时弄里他们最有钱,过年回来风光的不得了。
“公司不开了,”父亲说,“你真想不到,赌钱,广州待不下去,回来了。那天我去领老年证,在车站上碰到他,穿件破夹克衫,撑了把伞,在啃一只冷馒头。”
“还有宗国华,木器厂厂长,你也知道的,老婆在曲艺团,儿子吸毒,也不结婚,夫妻两个这几年一直在替他还债,三个人挤在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宗国华和弄里的慧芬的事,她也听过,说慧芬的儿子不是她丈夫的,是宗国华的,脸生得跟宗国华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就用自己的脸揭开了父母的隐私。她不关心这些人,却还是有些黯然。这些人都是弄里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的结局让她感觉到一种东西的存在,——也许世间真的有因果报应。
她坐在矮凳上,偶尔看一眼藤椅上的父亲。他的脸,在太阳光中更红润了,也是苍老的。风吹着,江西人养的一只黄狗跑过来,挨着他,摇着尾巴。她就像回到了过去,挨着他的膝头,听他讲故事。她后来是把母亲的痛苦全算到了他头上,这样到底对不对呢?沉默了一阵,父亲问起了她。她过得实在也不怎么样,去过不少地方,广州、珠海、哈尔滨,结过婚,又离了。现在在上海。一个人。
“孩子呢?有没有?”父亲问。
她摇头说没有。
“噢。”父亲拖长了声音说,像是叹气。
回到上海,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回味着父亲声音里的遗憾。他希望她有个孩子呢。她其实生了一个孩子的,是个男孩子,眼睛大大的,一头软软的头发,跟她很像。只不过离婚时,归了前夫。
听说前夫又生了一个儿子,她给他打电话,想把孩子要回来。她在上海,孩子可以跟着她在上海读书,不管她说得如何恳切,保证不给孩子改姓,前夫还是不肯松口。
不久她听说前夫为生儿子花了不少钱,跑了许多趟医院,在从美国请来的医生协助下用试管做出来的。是他现在这个老婆的问题,她又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他们才有爱情的结晶。
最让她诧异的却是这个结晶的脑子有问题,三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大了怕读不了书。这样,他更不会把孩子给她了。
可这些,是没法跟父亲说的。
元旦,她买了烟、鱼油,又回去看父亲。推开门,房间里冷冰冰的,没一点儿热气。父亲坐在门口,还拖着夏天的塑料拖鞋,手上结着紫红的硬痂。他泡方便面,手被开水烫了。她埋怨他不去医院包一包。他说包什么,不包不也好了。快死的人,有什么关系。他还是这种语气,铜墙似的,什么好意也泼不进去,让她讨厌。她真想不管他了,出去买菜,烧了够吃三天的饭菜,自去车站坐火车。深夜下了车,望着那一幢幢楼房上的灯火,如同睁着无数只苍白的眼睛,下了一个和先前相反的决心。
她不仅回来过了年,还在新建的小区租了一套小小的单身公寓。现在她只需要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也厌倦每天把五六个小时花在路上。某一天,她在马路上无意中邂逅了一个同学,聊了几句。同学问她在哪儿上班,她说正找呢,“别找了,来我这儿吧。”同学说,她开了家旅行社,国内、海外都做。没费周折,她就去上班了。
她的生活又开始井然有序,每次回春熙弄,看到那棵泡桐,她都有一种淡淡的陶醉之感。中午的弄堂里是这样安静,泡桐把它花蕾一样的影子投在房顶上、墙上、地上。为什么过去她这么憎恨这条弄堂呢?而这憎恨纵然那么深地刻在心里过,现在却翻到了另一面。既然书上说痛苦和美丽原来就是人的一体两面,那么憎恨的另一面就是爱恋。
老房子没有浴室,她在泡桐树下准备好开水,倒进鱼贩卖鱼的大塑料盆,给父亲擦身换衣。围上围裙,把穿脏的衣服鞋袜找出来,放到门口水斗里刷洗。坐在树下补缀父亲破了的裤衩,他只穿旧的。
抱孩子的邻居笑吟吟看着她忙碌,问她,“怎么都是一个人来啊?”
“我就是一个人啊。”
“你这么好个人,该有个人,喜欢得拉着手不放呢。”
她笑了,脸也有些发红,“哪有什么拉着手不放的人啊。”
“早点结婚吧,给你爸添个孙子,他可喜欢我们家娃儿。你生一个,还不知他欢喜成啥样。”
她心里微微一动,回头看父亲,他惬意地看着书,好像没听见他们这边的话。
旅行社的一个阿姨听说她还单身,热心地拉她出去相了几次亲,告诉她婚离了就要尽快交男朋友,尽快忘记头一次婚姻里不好的那些东西,把自己想象成年轻的,还对结婚充满希望的未婚女人。一个人老是关在家里过无味的生活是会败坏感觉的,而感觉那东西说不清楚也讲不透彻,败坏了就会让人越过越暮气沉沉了,自己不喜欢,别人也讨厌。
她心里多少也想摆脱一个人的生活,于是同意了跟伍京堂交往。
伍京堂是律师,从农村老家出来,硬是白天烧锅炉,晚上背课本,苦读出一张律师资格证,不到三十就谢顶了,不过因为生了一张娃娃脸,又有两个酒窝,还算可爱。他的这个脸也常常流露出什么都有办法的神气。认识不久,就带她去了杭州,还在西湖坐了船。看着湖光山色,她有了点跟这个人相依相伴的感觉。上了岸,经过美术馆,她进去看。他陪她看了一半儿,中途接了个电话,不见了。她看完出来,他无聊地坐在走廊上抽烟呢。
“那有什么好看的。”他不以为然掸掸烟灰,随手把烟头丢在地上,伸长脚一蹍。她就像眼看着一样什么东西被打碎了,最终也没说什么。在他眼里,她快四十了,条件也不算好,他肯找她,很不错了。对她来说,什么都有办法的男人还是很有吸引力。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她发现伍京堂其实有点小孩脾气。
他经常要去外地,几天回不来就打电话给她。
“你快点来看看我吧。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多可怜。”
“来吧。来吧。”
“我等你。”
她拗不过,果真打电话查车次,买了车票,坐车赶过去。找到他住的房间,他还没回来,她没心绪按照他指的路线去吃饭,就先洗好澡,啃啃面包饼干,无聊地看一会儿电视。好几次伍京堂压上来她才醒。
早上她要走了,伍京堂还在熟睡,睡得四仰八叉的。她怎么买票,怎么回去,他一概不问,也没有一个电话。一想到跟伍京堂结婚,她心里就像发了疟疾,一阵冷一阵热,却又始终没有明确回绝他。一个人的日子毕竟不大好过。何况,父亲临终前,他还跟她回去见了父亲。
因为她,父亲最后一段时日过得还算舒坦平安,一天,还少有地谈起她跑掉后,他去找过她,含含糊糊问她,“为什么跑掉?为什么?”
她回答不出。那是少年的仇恨。她要用破坏自己的命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预感父亲离开的日子已经不远,打开包,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那时他才六岁,站在游乐场的摩天转轮前,依着她的手臂,腼腆地笑着。她替父亲戴上老花镜,把照片拿给他看,“你有孙子。他在珠海,跟着他爸爸。十一岁了。”
父亲脸上流露出赞许的笑,“像你。”
她卖关子说,“等会儿再让你看个人。”下午四点,眺望了窗外好几次后,到走廊上把伍京堂带了进来。看见他,父亲努力坐起来,抱歉病房里不能抽烟,不然一定要跟他抽一根,叫她不要嫌他抽烟多,做律师可不容易。看他这么讨好他,她有些不是滋味,更想不到告别时,他拉住伍京堂的手说,“倪倪别的都好,就是脾气大点,你不要跟她生气。”
“知道知道。放心。放心。”伍京堂说,回头凑近她说,“我没觉得你脾气大呀。”觑了她一眼。她明白那一眼的意思,他是认为自己演得好,要她夸奖。
安葬完父亲,她就像脱了一层皮。头七晚上,独坐在饭桌前,隔着窗子看着院子里的树。月亮升上来了,在树梢上落下银亮的白霜。她听到父亲的咳嗽声,那么清晰,就在他往常坐的藤椅那儿。她没有怕。没有起来开灯。依然一动不动坐在朦胧的黑暗里。
这只是她想象出来的。父亲再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咳嗽了。即使咳嗽,也是在另外一个她看不到的世界。她不怕那个世界。如果真有那个世界,那么,母亲一定也在那儿。那么,将来,她也要去那儿。但是她活着的这段日子里,再也听不到这咳嗽了。从前她为什么这么憎恨这咳嗽声?为什么忘记不掉的,恰恰是从前憎恨的?她的眼泪掉了下来。
某些日子,博物馆会突然涌进许多人,多是些孩子,被大人带来增长知识。他们喜欢色彩艳丽的东西,比如血管,比如像珊瑚一样的支气管。在某个局部标本前,大喊大叫:
——哇噻,太恐怖了!
——瞧这家伙的肺!
楼上楼下全是小麻雀一样的叫嚷声,在玻璃橱窗上挤来挤去。
也有一些时候,尤其雨天,展厅里静静的,上肢也是静静的,在她的那一小块舞台上。如果她能回忆,一定能透过微波晃动的隔膜,看到仙踪林冷饮店门外那块不大的空地。
仙踪林在沃尔玛超市西侧,卖影碟、丝袜、保暖鞋的把那块地方当作做生意的好地方。
那天又来了一个拉大提琴的,把大提琴的柱脚支在砖缝里,就拉了起来。
她拎着刚买的一袋纸巾、饼干、肥皂、火锅丸子,走过去了,又转回身,站在一棵树下。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呢?音乐是能洗刷心灵的。
那个人拉完最后一支曲子,把盒子里的钱零零落落地收起来,她挨近过去,问他刚才拉的是什么。
他好奇地看看她,说,“悲伤的大提琴。”
“哦。”她点了点头,好像这一问,让他付出了很多似的,从包里摸出钱包。
“你感动了。”他感叹地说,看着她的眼睛。
她不懂他的意思,“音乐不就是为了感动人吗?”
“不。”他笑着摇摇头,“你一定不大去外面,所以不了解。会感动的人现在就像外星人一样了。”
“外星人?”
“听说过外星人吗?肯定听说过,对吧?那,你见没见过?他们长着三只眼睛,皮肤像橡皮。”他说着笑了。他的脸稍有些长,配合这脸,眼睛也是细长的,一头软软的头发,看上去有点柔弱。她挺喜欢他的长相。
第二天这个时候,她想到仙踪林,心里一阵阵地浮过悸动,勉强又坐了会儿,索性关了电脑,戴上围巾手套帽子,朝着仙踪林去了。她没在那儿看到他,徘徊了一阵,却听见一阵悠扬的琴声。
她找到他,远远地看着他,等他收起琴,走过去,“还是有人感动的啊!”微微一笑,“至少比外星人多。”
他也笑了,显然还认得她,“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在做实验。”
“实验?什么实验?看看有几个外星人?”
他笑了,“可以这么说吧。”
当然他也想借此机会筹点钱,他想去巴黎参加一个音乐节,可钱不够,钱不够就去不了,他现在上班的艺校也没办法。他说得很含蓄,因为他并不想提钱,跟她提钱有什么用呢?但是她脸上的诚挚吸引了他,何况她挺好,挺美的。和脸相比,手长得更好,修长,纤细,匀称,这是一双适合弹琴的手啊。她可以去做手模,以后有机会,他要跟她好好说说。“我叫果宁,你叫什么?”
“蒋倪。”
“再见啊!”
“再见!”
走了几步,她回头,看见果宁柔和的背影,头抬着,走得急急忙忙,像个准备去天上摘星星的小孩。
她的眼前闪过自己那些存折。她有一些钱。她肯堕落一点,在跟男人睡觉这件事上随便一点,钱会多得多。这可是她替人卖烤串、卖钱包、卖衣服一点一点积攒的。她没有父母丈夫,寥寥几个朋友,和她差不多,都不怎么会赚钱。她只有这一点钱,它们就是她的依靠。她诧异自己这个时候想到这些钱。她还不至于爱上他。不至于就这么陷进去了。何况他还比她小那么多!他不会跟她结婚的。她什么也不会得到!
她一路乱想着回到家里,暂时忘了果宁,也忘了那些钱,连同她那意念里要把钱奉献出去的呆气。
她走进卫生间,开始洗手。只要去过外面,哪怕到楼下拿张报纸,回来也得洗过。她知道这就是别人说的洁癖,却没有办法。她有专门洗手用的檀香皂。檀香皂洗过的手,会长时间保留着檀香的香味。
用水长时间冲洗自己的手,对她来说无与伦比的舒畅。——没有一个细菌留在皮肤上了,一切污秽除去了,心干净了。
这还是前一次婚姻留下的后遗症,前夫有了别的女人,抛弃了她,又结婚了,就是这样。她也为改不掉这个习惯苦恼,可不洗到干净,就会有一个污点梗在心里一个地方。
她洗了手,就去做饭。一个人的饭是很简便的,她下了碗水饺,开了电视,一面吃,一面瞟一眼电视。她看的是一部连续剧的中间部分,一对热恋的男女因为家里反对分手了,恍惚间,这两个人变成了她和果宁,变成他在发嗔,还痛哭起来,果宁无可奈何看着她。她一个吃惊,他们立刻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吃完,天已经黑了。她又想起她的钱,眼睛无意识地停在一团亮光上。慢慢的,亮光动了,开走了。原来那是一辆汽车的尾灯。
这次她直接去艺校找的果宁。他穿着毛衣跑到门口,看见是她,有些惊讶。不过,他脸上的笑,让她感觉到他很高兴她来。“我陪你转一圈儿。”他说,马上做出主人的样子,在前面带起路来。她跟着他,看了喷水池、雕塑,又顺着缓缓的坡上了山。山很小,山腰上有座墓,是一个德国音乐家的。他跟她介绍那个音乐家,她听得很认真,还是没听进去。不知他是不是失望了,没再说话。树木的气息从路两侧的林子里渗透出来,她吸着这清凉的空气,也没再说话。下了山,就是宿舍了。“去不去?”他问。她也犹豫了,也许他只是这么说一下,她倒当真了,说,“就不去了吧?”他踌躇一下,笑着说,“去一下吧,都到这里了。”
出了楼梯,迎面走来几个女孩,吱吱喳喳抢着跟他说话,他也笑着,拿她们中的一个打趣。她含着笑,看着她们,她们却没一个看她。这倒不是她们对她有什么敌意,这个时候,她们的眼睛里全是他一个人,而她,也实在不像他女朋友吧,引不起她们注意。意识到这点,她原来的局促一下没有了。是啊,她根本不像他的女朋友。在他的房间里,她大方地坐到写字桌前,看着桌上叠得整整齐齐的书,盛着半杯温茶的黑陶杯,电脑里响着音乐,她不知道这是哪个大音乐家的,一声不吭听着,心里有一种东西飘忽着,阳光照在玻璃窗上,屋内金光闪闪,这么宁静美好。
他给她倒了水,放到桌上,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包,递给他。他一愣,嘴上问“什么?”已经从那纸包的形状上看明白了,不相信似的看着她。
“这里是七万。你先拿去。”
“这,我可能很长时间还不起。”
“那就到还得起的时候还吧。”
“我怎么谢你呢?”他抓着耳朵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给你写个收条?”说着,马上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写了起来。房间里只有写字的沙沙声,像小时候她养过的蚕,在皮鞋盒子里沙沙地吃着桑叶。她听着这声音,每天在等这些蚕吐出丝,结成茧子。
他写好,从笔记本上撕下给她,她接过来,先一眼看见他落在最后的名字,——果宁,年月日,抿着嘴笑了,把纸叠起来。他一直看着她,看着她把纸放到包中,抬起头来,撞到他的眼睛,他们同时笑了,就像合谋完成了一件秘密的事。
果宁的签证办得还算容易,但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当中请她吃了次饭,逛了一下夜市。她羞于拉他的手,她的手却被他硬抓住了,握在手里,和别的逛夜市的人一样,顺着一个个摊子走着,看看瓷器、彩绘折扇、洋娃娃,什么都津津有味。人多,转身间,手臂肩膀免不了挨到一起。在“香气世界”里,她把每个玻璃瓶子都掀开盖子闻了一闻。“这个好,金色沙滩,你喜欢哪个?”她问他。“海洋。”他把瓶子递给她,脸几乎挨到她的脸,她假装不知道,脸却热烘烘的发烫,几乎要失去自制力,整个人偎依过去。从那儿出来,话骤然少了。
“怎么啦?”他不停地问她,关心地看着她的脸,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到了必须分开走的路段,他还是不安地看着她的脸。她眺望着远处,嘴里说,“怎么还不来?”他在几次察颜观色之后,拉住她的手,顺着手、手臂,爬到肩膀上,停了一停,在她心脏难以承受的跳动中,拥抱了她,嘴唇紧紧贴在她额头上。
起初,她只是僵在那儿,不相信这接近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随后她轻轻挣脱他,“车来了。”她说。车是来了,她上了车,找到地方站好,他在外面笑着朝她挥挥手。夜色中,他笑得有些奇异,她被他眼睛里的两点光刺到了,她知道他是完全明白她了,覆盖在她身上的矜持,包括她去艺校送钱,他会以为,她因为爱他而心甘情愿奉献一切。她有点难受,她不希望他这么理解。不是这样的。她能跟他解释清吗?车开了,看不见他了,她尽力使自己不以为然,不对这分别存什么难过,更不要有从此再见不到的预感。她不至于花去自己许多年的积蓄买一次春,这太昂贵了,也太不值得。她不想要别的,如果一定要,就要帮他摘到星星的快乐吧。
他的行程很快定下了。她知道他会来,每天都在等他。早上一起来,就觉得也许这一天他会来。到了离起飞还有三天的黄昏,他的电话来了,说他来看看她,“到你家附近吧,找个地方吃点,天冷,别跑远了。”
她依言在公寓边找了间小饭馆,点了很多菜,说给他饯行。他很高兴,对远在地球另一边的音乐节充满憧憬。他的确会遇到想象不到的机会吧,她插不上话,含着笑听他说。
吃饭时间一过,小饭馆转眼显出人迹凋零的冷清,不适宜再说什么。出了饭馆,从那狭窄的门里走出来,并肩站在街沿上,他踌躇说,“才八点,你有事吗?”她知道他的意思,说,“要不去我那儿,喝杯茶。”他的眼睛里又闪现出两点光,她别开脸,没去看他。默默地和他一起到了公寓,开了门。
这是她第一次带男人回家。她叫他随便坐,倒了茶,端过去,他却不接,眼睛直视着她。他依然是柔弱的,却有一种力量,让她拒绝不了。她把他领进来,就已经表明了她的默认。她什么都不用再说了,依顺着他,仓促中把水杯放到桌上,水晃动着洒到她手背上,一阵灼痛,她喘息着,由他解开衣领,衣服一件件剥下来,冰冷的空气中,像个成熟的果子,从壳里绽出整个温暖的果肉。
她很久不敢睁开眼睛,听他去卫生间了,摸索着,从揉皱的小床上下来。
她有些羞愧,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出来了,她不敢看他,低下头,急忙抱着衣服进了卫生间。磨蹭了一会儿,出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窗前——她总是吃饭、看电视那张椅子上。看见她,他迷茫了一下,好像对刚才的事一样不知道理由,不明白为什么,却又是高兴的。
写字桌的一只小匣子里放着几张车票,他拿起一张,“丹阳。”又拿起一张,“常熟。你喜欢旅行呀?”
仿佛一块石头砸来,“听音乐吧。”她拿开车票,过去打开音响,头也不转地说,“悲伤的大提琴。”
“你哪儿买的?”
“网上。”她说。
他过来拉她,她顺从地坐过去,看着他拿起她的手指,轻声说,“真美。”贴到唇上。她的指尖就像遭受电击一样震颤了一下,随后,痛感像电流一样通过指尖传向心脏。原来幸福是这样的。她想,她现在已经获得了幸福。可是,她又为什么这么难过呢。离别的阴影灰雾一样笼罩下来。
果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放开她的手,看了时间,起来穿大衣,“我得走了。我妈规定我十二点前一定得回家。她会疯了似的打我电话,没准还会报警。”围上围巾,揽住她的肩,又说,“等我电话。到了给你电话。”
她没说话。
“怎么,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那为什么?”他热烈地从背后抱紧她,嘴埋进她脖子里。
她的眼前闪过那个守在家里等儿子回来的女人,却迅速把她抛到了一边。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她扭过头,把脸贴到他脸上,而后,一遍一遍热烈地亲吻这张脸,心里一个固执的东西打开了。
那是果宁去巴黎的第二个星期了。伍京堂来电话叫她去金华,他在金华好几天了,“你来吧。一会儿就来。”她说不去,挂掉电话,没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她坐着发了会儿呆,还是收拾东西,去车站了。
她这次去,一定要跟他提结婚的事。如果他不同意,她再也不想跟他这么继续下去了。可是,如果他同意呢?她想到他的脸,想到他在美术馆门口伸长了脚蹍烟头。
田野在车窗外渐次滑过,她靠着车窗打起瞌睡。似睡非睡的朦胧中,车停了。
大巴司机跳下车。
有人问司机,怎么了?怎么了?
司机钻到车底下,没吭声。
车上的人一个个跳下车去,钻入树林小便,抽烟,打电话,聊天。她也下了车。太阳很好,照在身上暖烘烘的,没有早上那么冷了。她走到护栏,靠在那儿望着远处的山。她必须下一个决心:跟伍京堂结婚,还是不结婚。
她根本不会想到,这一辆车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一辆车风驰电掣一般朝他们开过来。那是一辆五个吨位的货车,载了十一吨重的黄沙。疲倦的司机半天加一夜没合眼了,从安徽某地开出,困倦中继续驾驶着货车驶向目的地。
大巴司机从车底钻出来,点了根烟,准备抽完就上车出发。他看到了那辆货车,目睹它越来越近,却毫无变更车道的意思,心忽地一沉,本能地感觉到灾祸即将到来。货车司机与此同时也感觉到灾祸即将到来,措手不及往左打死方向,冲向护栏,訇然侧翻倒地。
扬起的漫天黄沙中,货车司机战战兢兢爬出驾驶室。
哭声四起,从震惊中醒悟过来的大巴司机绕到另一头,她正努力地伸长手臂,要拿起落在地上的手机,那柔软的手臂,在午间太阳的照射下,却如垂死的优美的天鹅。两条破碎的腿还没有完全落到地上,血缓慢的,由小股汇成粗重的一道,爬过路面,又向路旁的树根、草丛爬去。
仍处在惊吓中的人们围上来,她的手指与地仍相隔着三四厘米,一个男人跑过去,拣起手机递给她,对她说,“你要打给谁,我给你打。”
她把手机拿到手里,短暂的一霎,围观的人看着她拿起手机拨通了,轻声说,“我出车祸了。”都以为她的情况并不像看到的这样严重,她好像还笑了一笑,感谢地看着递给他手机的人,轻轻地吐了一句,“我不会死的。”
救护人员把她抬上担架时,她停止了呼吸。
一个交警从她握得紧紧的手里拿下了手机。
这次车祸,导致一死五伤,报纸、电视都作了报道,报纸在公告版刊登了认尸通知。始终没有人来认领她,她被视作无名尸暂时收存起来。
时间往前,现在已经到了2051年。这一天,攘攘的人群里走过来一大一小两个人,是一个祖父和他的小孙女儿。
“来。”男人侧过头,对一个跑着的小姑娘招招手。他有一头软软的白发,一双细长的眼睛。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手。”他轻轻地说,把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推向她,紧接着两只很小的手掌也贴了上来,贴在橱窗玻璃上,嗓音清脆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手。”
两个人一同出神地看着。男人跟小姑娘的目光当然是不一样的。这条上肢,让他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人,那个人有一双很美的手。他困惑地望着上肢珍珠般串在一起的指关节,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到了这些。几乎完全遗忘了的记忆,这一刻竟全部涌了上来,温暖地包围着他。他想起她的脸,想起去巴黎参加音乐节前他们在一起的晚上。在巴黎,他接到过她的电话,当时正和伙伴坐在出租车上准备到达音乐节现场,他听不清她在说什么,等他下了车,再打给她,手机关机了。再之后,就停了机。从巴黎回来,他去找过她,却没找到。房东也不知道她的下落。他记得她说过有一个男朋友的。也许,是结婚去了。她既然不来要回她的钱,渐渐地,他也就心安理得,忘了这些事。他有了女朋友,忙着恋爱,然后结婚、拜师,再次出国,他竟像小时候希望的那样成了音乐家。
小姑娘睁大眼好奇地看着,突然皱着眉头说:“不好,不好。上面还有肉呢。不好,我不喜欢。”挣脱开他的手,跑了。
男人回头又迷惑地望了上肢一眼,去追他的孙女儿了。
上肢一动不动,仍保持着她一直以来的姿态,指尖并拢,柔和地往下垂着。但其实不是,她感觉得到,——真令人惊奇,她仍有感觉,在恒久不变的风速中不易觉察地震颤了一下。随后,痛感像电流一样通过指尖传向虚空。
作者简介:吴文君,浙江海宁人,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近年陆续在《北京文学》、《大家》、《收获》、《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