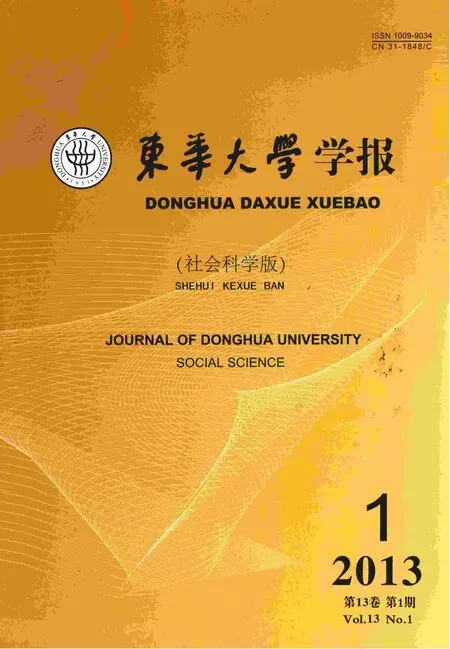阐释、改编与传播——莎士比亚跨越时空
黄培希
(东华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201620;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被誉为“时代的灵魂”[1]。几百年来,他跨越时空,属于“所有的世纪”[1],属于整个世界。莎士比亚作品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不仅在于其“像宇宙一样伟大和无垠”,“包含着整个现在、过去和将来”[2],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无穷的魅力,还在于几个世纪里人们对作品不断地阐释、改编和传播。本文以莎士比亚作品的阐释、改编和传播为线索,试图回答“莎士比亚跨越时空”①“莎士比亚跨越时空”是“上海国际莎士比亚论坛”的大会主题。该论坛由东华大学外语学院主办,杨林贵教授主持,于2011年10月15日在东华大学举行。大会云集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地40多个学校和机构的一百多名学者,围绕该主题进行了研讨。的原因,探讨当今莎士比亚研究的主要课题以及发现异域文化在一国传播的规律。
一、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基础——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阐释研究
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阐释研究是莎士比亚研究基础的一环。所谓的文本阐释研究是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各种要素,如对作品的语言、主题、人物、情节,思想性和艺术性等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加以阐释。莎士比亚作品是永恒的、不朽的。“不朽作品之所以不朽,就因为它在不同的时代,都能被重新解读,被赋予新的意义,因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当然,不是所有作品都能不断得到新的阐释。伟大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拥有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的可能性”[3]正因如此,直至今天,国内外学者们,仍然坚守着文本研究这块土壤,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莎士比亚经典作品加以解读和评判,这都充分体现了文本阐释的广阔空间和重要意义。
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阐释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们选择不同的视角阐释莎士比亚文本。如,在对“哈姆雷特是否替父报仇”这一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进行阐释时,李庆涛选择从圣经入手,从莎士比亚与圣经的关系展开,指出“哈姆莱特化解自己困境的努力是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对上帝权柄的僭越,在上帝缺场或者神意干预缺场下人类试图把握自己命运的种种努力终将归于徒劳。”[4]王飞鸿则“以萨特的处境戏剧理论为基础,结合他关于人的本体论的存在主义哲学,从亲情、友情和爱情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哈姆雷特身上所体现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上的生存困境。”[5]在分析李尔王的悲剧时,俞建村将“社会表演”的概念引入了讨论,指出李尔王的悲剧“是一场社会表演悲剧,是一场由社会表演意识缺乏而造成的悲剧”[7]。在解读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董尼》长诗时,李伟民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在褪去了神性的维纳斯的人间之恋中,莎士比亚张扬了人性,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在爱与美中表现出来,将爱与自然联系起来,并赋予‘真’的人性以崇高的地位。”[7]邱佳岭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莎翁作品《驯悍记》,指出了莎翁作品所透露的女性主义观念[8]。同样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姜山秀发现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具有“边缘性”的性质[9]。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阐释研究还体现在莎士比亚文本研究中的新发现。如聂珍钊从文本的对白和独白研究中发现捕鼠器真正捕捉的猎物是哈姆雷特的母亲格特鲁德①Nie Zhenzhao.Who is Real Prey in Mousetrap:Claudius or Gertrude?,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宁平等从英国历史剧文本中发现莎士比亚的种种战争观[10]。
以上研究,或从基督教、社会表演、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对莎翁作品进行了阐释,或通过文本阅读,对文本内容进行新的解读,或阐释作品中新的思想内涵,或重新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等。这些研究体现了文本阐释研究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和无穷的动力。当然,对莎士比亚文本阐释的视角远远不止这些,随着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和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学者们不断地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置于新的背景之下并从新的视角对其加以阐释。
二、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莎士比亚作品的改编研究
改编是一种传承,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莎士比亚剧作具有双重改编的性质。一方面,莎士比亚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成功的改编,同时,莎翁的剧作又不断地被后人改编着。从电影、电视、广播、歌剧、舞剧等多彩多姿的艺术形式到全新的现代诠释,都表明莎翁戏剧作品的无穷魅力。“在人类艺术史上,越是伟大的作品,越不会单纯地停留在一种艺术形式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不断地成为其他艺术形式创作的题材与灵感源泉。”[11]改编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关于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研究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戏剧改编本身的讨论,二是对改编后作品的探讨。
2012年,原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主席吉尔·莱文森在《英伦旅者——现代全球舞台上的莎士比亚编年史剧》一文中,从莎氏编年史剧改编的现状、原因、方式和影响等方面介绍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改编情况。她指出:现代戏剧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改编主要表现在对其戏剧独特要素的“借鉴”(borrow)和对其戏剧文本的“挪用”(appropriate)。[12]吉尔·莱文森所论及的“借鉴”和“挪用”是对改编一词进一步的诠释,是莎氏历史剧改编活动的重要内容。关于改编的阐释,陈红薇认为改编是一种“拼贴”(collage)。她对改写莎剧的大师,英国著名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对莎剧文本与现实事件进行狂欢式的互文和拼贴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这种互文和拼贴是两者彼此“嬉戏”,能够“构建出一个特有的意义生成的创作语境”[13]。她所谈及的在互文条件下的“拼贴”不失为对改编方式的又一探讨。日本学者森佑希子以《李尔王》衍生剧中女性人物为例,认为改编是原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的“改变”(transform)和“重构”(reconstruct)。她认为爱德华· 迪麦特雷克导演的《断戈浴血记》和黑泽明导演的《乱》将原作中三个女儿改编成儿子是源于日本历史文化背景对男性而不是女性需求。较于原作,改编作品体现了男性的主导地位,而女性角色被边缘化。②Yukiko Mori.Female Characters in King Lear Spin-offs — Animals and Animal Images in Two Films,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森佑希子的研究不仅认为改编是脱胎换骨的“改变”,而且需要剧作家进一步重构,并且指出改编往往受到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上学者对改编不同的诠释丰富了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研究的内涵。改编研究不仅限于对改编自身的认知研究,对改编的目的、方法、原则和影响等因素的考察也是莎剧改编研究的重要范畴。
关于莎剧改编坚守的原则,熊杰平指出莎剧改编应遵循清代李渔“机趣”原理。他认为应该运用“机趣”原理来考察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机趣”的得失;盲目地忠于原著以及迁就于理智是失去“机趣”的主要原因,机趣的得失也是戏曲改编莎剧创作中的得失之一。[14]日本学者吉原由里香认为日本本土的消费文化对原作的改编具有消极影响。她以一部冠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日本动画片在影迷中的反应为例,指出了消费文化以及经济因素等对作品改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①Yukari Yoshihara.Shakespeare in Consumerist Culture of Japan,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同样,孟智慧等撰文指出消费文化语境下,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度”与“量”不应顺应消费文化市场的潮流,而应在艺术性和商业之间寻求平衡点[15]。可见,消费文化对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影响。台湾学者王淑华认为莎剧改编在本土化的同时还应保持原作的特点。她以台湾改编的豫剧《威尼斯商人》为例,指出改编后的作品将现代台湾的戏剧和莎士比亚作品进行了跨时空的联结,让英国观众和华语世界对人性问题有新的评判。但改编的作品由于牺牲了杰西卡和罗伦的故事情节,忽视波西亚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夏洛克反省戏份的删减等都大大降低了戏剧的紧张气氛,使得夏洛克这一人物悲剧成分也大打折扣,更像舞台上的白衣小丑。该部剧作成了取悦观众、宣扬因果报应的喜剧作品,而原作中诸多关于种族、信仰、法律、道德等发人深省、纷繁芜杂的矛盾却荡然无存。②Wang Shuhua.Shakespeare Unbound:Locality and Identity in Bond,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
上述有关改编问题的研究涉及了对改编需遵循原则的研究和本土化过程中本土文化对改编的影响以及改编自身的认知研究等。这几个方面反映了改编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和方向。对改编的理解及对其遵循的原则进行研究将为改编提供理论指导,而对改编后作品的研究,将促进改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内容便是对改编后作品的研究,即对改编作品的批评研究。如田俊武等对肯尼斯·布拉纳导演并搬上银幕的电影《王子复仇记》进行了研究。他从影片中的蒙太奇效果、音乐音响效果、布景以及演员的服装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电影语言和镜头在重新演绎莎剧经典文本时的特殊功能和艺术效果,以及布拉纳表现原剧精髓和意境的成功之道。他强调电影改编对莎士比亚在当下的意义,认为“时代给电影艺术家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也为莎士比亚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进行两种艺术比较的研究领域。”[16]对改编后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有十分广阔的空间。“随着莎士比亚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业关系紧密,莎士比亚影评也逐渐成为莎士比亚评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尽管经典的莎士比亚和电影的莎士比亚之间,的确存在着表现技术方面的差异,这其实并不能支持把莎士比亚影评排除在学术圈外的观点。”[17]无独有偶,吴辉认为通过对2006年冯小刚执导的《夜宴》和胡雪桦执导的《喜马拉雅王子》中的哈姆雷特的形象进行比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戏剧改编的现状,而且能够更好地了解戏剧改编的艺术,从而了解莎剧原型作品是如何从舞台搬上银幕,从西欧搬到东亚,而且从伊丽莎白时代推上了21世纪充满竞争的国际电影市场的③Wu Hui.Three Hamlets,Two Gentlemen and One Time to Love:Shakespeare on the Chinese Screen,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
因此,无论是对改编后的作品进行品评,还是对来自于同一原作的不同改编作品进行比较,还是将改编作品和原作进行比较,都大大丰富了改编研究的领域。
三、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集中体现——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研究
莎士比亚研究是开放的、动态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传播研究体现了莎士比亚研究的与时俱进,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集中体现。对莎士比亚在异域文化中的接受研究、对如何在异域文化中培养适合传播的莎士比亚语境以及对改编作品的本土化思考成为莎士比亚传播研究的热门话题。
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芝加哥大学国际莎学专家戴维·贝文顿考察了戏剧人物的改编对莎士比亚作品命运的影响。他认为哈姆雷特对待奥菲利亚的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冷漠让剧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倍感失望,以至于此剧的商业演出大大减少。[18]作者从原文文本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改编过程中的变化这一视角出发,考察了改编作品的传播命运,这为解释作品的成功传播与否提供了一种借鉴。同时为研究如何成功传播莎士比亚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尝试。关于莎士比亚作品如何能够在异域文化中得到更好的传播,张冲强调莎士比亚异域文化语境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中国学生而言,莎士比亚作品不仅是“西方文明的瑰宝”,还需要随着其作品的人物一道进入人们更广阔的视野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审视;需要从其不计其数、五彩缤纷的改编剧作、挪用剧作和模仿剧作中寻求解决当代人们关心的种种问题,才有意义,才真正具有当代的意义。只有使莎士比亚和各方面建立联系,并使他的作品和各方面都有关联,莎士比亚才得以生生不息。①Zhang Chong.Making Shakespeare Related and Relevant,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由此可见,只有适合莎士比亚作品生长的土壤具备了,莎士比亚作品才能更好地在中国学生中得以传播和接受,而不是仅仅选取有限的几个范本加以学习。莎士比亚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研究,日本学者南隆太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互动研究提供了研究的范例。他指出在日本“莎士比亚的作品好比米柜,是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有了它,我们将不再饥饿。尽管莎士比亚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它不断地被本土化,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日本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②Minami Ryuta.Shakespeare is a Rice Chest:Intra-cultural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 in Japan,Broch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Forum,2011.从南隆太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日本的传播首先是它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来源而加以接受。他们没有将莎士比亚作品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将其作品很好地融合到日本本土文化之中。一方面莎士比亚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日本本土文化的繁荣。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本土化研究是莎士比亚作品传播研究的课题。如何将其本土化,如何促进本地文化的发展仍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除了上述学者传播研究的领域之外,随着影视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这些新媒介必将为莎士比亚传播研究赋予新的意义,并成为莎士比亚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新的亮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主要在于其作品本身不断地被阐释、改编和传播。这是莎士比亚作品研究的一般过程,也是一个符合异域文化传播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及各环节的具体研究,成为国际莎士比亚研究的重要课题。文本阐释研究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莎士比亚作品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该项研究随着时空的变化和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将会进一步发展。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改编是莎士比亚作品得以跨越时空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对改编的理解及其遵循的原则将为改编提供理论指导;而对改编后作品的研究无疑将提高改编的质量和水平。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是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集中体现。对如何培养适合传播异域文化的莎士比亚语境、改编作品的本土化思考以及传播手段的研究都必将促使莎士比亚得到更好的传播。
致谢
文中部分引文源自 “上海国际莎士比亚论坛”会议手册,原文为英文,由作者编译,在脚注中注明作者和出处,在此对原作者深表谢意。
[1]本琼·生.转引自华泉坤等著莎士比亚新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序言).
[2]别林斯基.转引自张泗洋等著莎士比亚引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2(序言).
[3]谈瀛洲.莎评简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引言).
[4]李庆涛.哈姆莱特困境的化解——兼与约伯的困境比较[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2,(6):36-41.
[5]王飞鸿.存在,处境与自由——从生存困境的角度解析哈姆雷特的情感冲突[J].戏剧文学,2009,(3):42-47.
[6]俞建村.国家政权与社会表演——从社会表演学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5):34-38.
[7]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278-292.
[8]邱佳岭.《驯悍记》与莎士比亚的女性主义意识[J].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4):28-29.
[9]姜山秀.徘徊在边缘——四大悲剧女性形象解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1:217-221.
[10]宁平,屈荣英,李炳军.莎士比亚战争意识初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01-506.
[11]吴辉.莎士比亚剧作的双重改编[J].艺圃,1997,(3/4):28.
[12]Levenson,Jill L..EnglishTravelers:Shakespeare'sChroniclePlaysontheGlobalStagesinModernTimes[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12,(1):1-9.
[13]陈红薇.汤姆·斯托帕德与莎士比亚的对话——《多戈的〈哈姆雷特〉》和《卡胡的〈麦克白〉》对莎剧的“重写”和“再构”[J].外语教学,2012,(1):81-84.
[14]熊杰平.戴枷起舞——论机趣在中国戏曲改编莎剧中的得与失[J].写作,2012,(5):41-43.
[15]孟智慧,车文文.消费文化语境下莎士比亚戏剧的电影改编“度”与“量”的权衡[J].长城,2012,(12):181-182.
[16]田俊武,孙晶晶.论莎剧《哈姆雷特》电影改编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J].戏剧文学,2006,(12):79-84.
[17]张冲.莎士比亚专题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45-446.
[18]Bevington,David.OpheliaThroughtheAges[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12,(1):10-18.
-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透析麦迪逊多元民主理论的分权制衡机制
- 目的论视域下博物馆文物名称英译研究
- 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