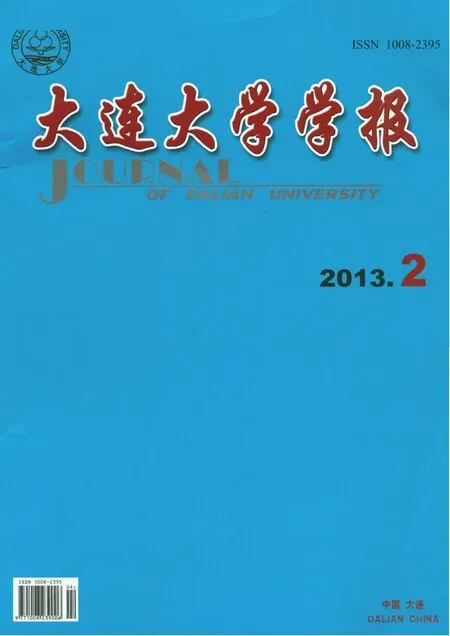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公共外交
张建威
(大连市外事办公室,辽宁 大连 116012)
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公共外交
张建威
(大连市外事办公室,辽宁 大连 116012)
随着世界经济龙头亚洲的崛起,澳大利亚战略权重日渐转向亚洲,以便在亚洲世纪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由于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原因,澳曾长期与亚洲格格不入。在现实利益驱动下的坎坷融亚之路上,澳倚重公共外交重塑国家形象,全面推动地区公共外交实践,其面临的挑战对寻求与亚洲共同发展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亚洲世纪;澳大利亚;公共外交
由于坎坷纠结的历史和大相径庭的价值观,许多亚洲国家从未把澳大利亚这位“不合群”的太平洋居民看成是“自己人”。自诩为英国在亚洲“前哨(outpost)”的澳大利亚,1788年漂洋过海在南太自立门户后,本来应当随遇而安地“本土化”,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邻居居为善为伴,但它常常把自己当做亚洲的看客,不愿甚至不屑与亚洲国家为伍。“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当年大行其道正是这一居高临下心态的真实折射。
两个多世纪以来,澳因与亚洲交结、交融而变得焦虑、焦急,终于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尘,在亚洲问题上形成了国家共识:“不管本世纪会带给我们什么,亚洲的崛起是注定的。”2012年10月,澳政府孕育了11个月之久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书呱呱坠地。这份关于澳未来亚洲政策的报告和宣示,是“一幅跑赢亚洲的路线图”,凸显了“拥抱亚洲”的运筹已不再是桌面推演,而是拉升到了国家战略。其全面阐述与亚洲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关系”的第九章,更是把澳建成“知亚、能亚的国家(Asialiterate and Asia-capable nation)”的外交构想表白得淋漓尽致。
投身亚洲,可说是澳做出的重要战略选项。如何传播正面形象,广结亚洲“国缘”,最终有效地为本国核心利益服务,不啻是一道有关软实力的必答题。作为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软实力需要政府和民众的精心历练。公共外交,这个软实力的坚实抓手,在澳世纪决策中自然而然地充当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更是走向亚洲的必由之路。
一、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成因
总理吉拉德在白皮书前言中坦承:“亚洲地区经济问鼎世界的进程加快,势不可挡。要在亚洲世纪里得以繁荣发展,需要国家制定明确计划,抓住经济机遇,迎接战略挑战。”显而易见,经济权重在澳“融入亚洲”的原由中举足轻重,但也不能就此断言这种“趋炎附势”是利字当先。多因素交织,多层面合力,才是澳亚洲意识从被动思忖到主动谋划转变的根本动因。
(一)地缘政治原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地缘政治解释为“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1]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战略选择、行为模式和利益诉求。发端于欧洲的地缘政治的概念,在冷战后的澳大利亚,逐步移植成了“定向锋线模式(directional-front model)”[2],即北部合作安全锋线,南部环境安全锋线,东部援助锋线,西部贸易锋线。这四条锋线织就了一条环绕“世界上最大岛屿”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安全带”,从而为澳未来奠定了稳固的地缘政治基础。
澳亚关系的战略意义首先是由地缘塑造的。随着冷战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成为亚太主导力量;中、日、印、韩及印尼等国日渐成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力量;《东盟宪章(The ASEAN Charter)》签署后紧锣密鼓加快一体化进程的东盟已呈次区域力量之相;APEC、ASEAN+3、EAS、TPP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峰会纷至沓来,稀释、强调、整合、斡旋着该地区地缘政治力量的重组。尽管多边地缘政治势力角逐的厮杀声响成一片,但亚太地缘政治的巨大红利无疑令人垂涎。在地缘上天生超脱,在外交上努力均势的澳大利亚,在别国大秀肌肉之际,务实地辨明价值层次,做出利益判断,取得主流共识,促成了澳世纪之初的政治决断。
(二)亚洲经济原因
澳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长期以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一直是其经济命脉,特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二战前,澳70%出口输往英国等欧洲国家。至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一比例仍高居40%。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英联邦特惠制(Commonwealth Preference System)”的叫停和欧洲经济日益一体化,英加入欧盟,澳农矿产品的出口环境渐趋恶化。传统经济模式面临的重大挑战,日益沦为亚洲经济圈外的看客,迫使曾经“喝远水解近渴”的澳大利亚,在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中收拢目光,就近取材,拓展新的出口市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
此间,以东亚为亮点的亚洲经济强劲发展,魅力不可抗拒,让苦心经营的澳大利亚人看到了潜在希望,找到了经贸出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亚洲)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给世界带来了信心。”总理吉拉德强调:“我国曾受惠于亚洲对我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受益于他们未来的需要。”2011年,澳10大贸易伙伴中,有7个在亚洲,依次为中、日、韩、新、印、泰、马。英作为澳第六大贸易伙伴,仅占其出口总额的3.8%。中、日、韩、新四国则占据了41.8%。据澳《2011-2012年度贸易构成》数据显示,2011-2012财年,中国依然是澳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1278亿澳元。《澳大利亚人》报载文称:“澳过去十年的繁荣,归功于扮演了中国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3]
(三)安全战略原因
冷战结束后,出于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澳美依然保持着同盟关系。在美“重返亚洲”的战略链条中,澳无疑是重要一环。2009年5月,时任总理陆克文在发布《2030年:在亚太世纪中加强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时指出,“澳美同盟依旧是我国家安全的基石(bedrock)。”在2010年11月美澳“2+2”防长外长会上,双方进一步认同美澳同盟是“亚太战略之锚”。有鉴于此,澳力挺美介入亚太事务并保持地区军事存在,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唯美马首是瞻,甘当美离岸制衡(ofshore balancing)的棋子。
力主在“多国家体系”里运筹“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基辛格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美相对军事实力会日渐式微,尽管这尚需几十年的时间。新的国际体系会朝着均势方向发展,对美而言,在军事领域如此,在业已失势的经济方面更是如此,而且挑战起来还愈发安全。”[4]
基于“能实际或潜在地影响本地区大国间关系左右着我安全环境”这个战略判断,澳“要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中塑造国防力量”,其国家安全的关注范围,显然已经笼罩了整个亚太地区。澳安全战略一方面立足于本土防御,另一方面又强调对邻国安全做出贡献,并宣称参与亚太地区的多国军事行动,以应对在近邻以外发生的与澳利益相关的危机。在经济上傍正在崛起的亚洲,在军事上靠转向亚洲的美国,全面、高度的利益契合,使得澳战略性分配不能出现任何顶层误判或举棋不定,回归亚洲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2013年1月,与《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相辅相成的《强大与安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Strong and Secure: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面世。吉拉德政府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未来澳安全战略的3个核心关切:第一,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正持续东移,我国家安全要着眼于本地区的机遇和挑战;第二,国家行为,而非非国家主体,将在未来驱动并塑造我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第三,在驾驭多极世界复杂嬗变的形势时,外交工作将举足轻重。”不难看出,这三个关切的视野里,站着同一个令人瞩目的庞大身形——亚洲。
(四)外交策略原因
1931年12月,英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The Statue of Westminster Adoption Act)”,给予包括澳在内的自治领以内政和外交自主权,从此澳成为英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独特的国家历史发展路径,导致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就不是澳政府所要考量的先决问题,直到1941年底,身陷太平洋战争的澳大利亚人,才在时任总理柯廷的新年贺词中,读出了久违的惊喜:“没有了与英国传统亲缘关系藕断丝连的痛苦,我毫不犹豫、明白无误地宣布,澳大利亚转向美国。”这篇讲话成为澳对外政策的分水岭。如果说二战前澳还在缓慢地了解、接近亚洲,那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使其迅速、被动地卷入了亚洲。二战期间,澳将自身命运与亚洲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即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也为其改善格格不入的以英国血统自傲的国家形象、逐步协调与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44至1969年,澳在海外建立了62个外交机构,其中亚洲就达20个[5]。然而,上世纪50、60年代澳的对亚外交政策又走进了新的误区,追随美国在亚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极大地损害了刚刚起步的与亚洲的关系。
1972年12月,惠特拉姆政府执政后,改变了对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着力加强了与亚经济联系;与中、越、朝等国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越、新、马陆续撤军;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国家签订了多项经贸协定,对亚关系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1995年10月,时任总理基廷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安全与繁荣系于亚洲。我们促进自由贸易、推动多元文化、加强教育培训的种种举措,都是这一策略的组成部分。”多年来,作为亚洲第4、世界第12大经济体,澳始终致力于“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中等大国外交(active and creative middle power diplomacy)”,并且对澳亚“在彼此心里(in each other's minds)”
的理念推崇备至。吉拉德政府认为,“与亚洲国家成功地建立起广泛深入的关系,需要政府之外的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改善民间交往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能量。”“全面融入亚洲应当列入我们重要的议事日程。”经过多年来曲折反复的涉亚外交实践,澳对亚洲感同身受的集体认知终于具象成21世纪的外交抱负、政治共识和一系列务实拓展的公共外交实践。
二、澳大利亚公共外交在亚洲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弱化令人难再以主义划分敌我。主要敌对国关系解冻,使得大规模武装冲突失去靶标。与此同时,文化经济交流顺势而为,信息传播势如破竹。国家影响力的大小,国际地位的消长越来越难用传统标准来加以衡量。这样,以能与军事、经济实力相配套组合的软实力为载体的公共外交便风生水起。“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
澳公共外交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的对外文化传播项目。如今,澳公共外交立足亚太,辐射全球,形式和内容多样而广泛。由于公共外交有助于修复国家形象,亚洲,这个澳形象毁誉参半的重灾区,就成了其公共外交的重中之重。2011-2012财年,超过50%的公共外交预算分配给了澳在亚洲的外交机构。澳借助公共外交的手段来经营亚洲,是顺应地区战略格局演变的内在需要;是树立积极、正面、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的必然要求;是回应亚太和全球软外交势能的主动追随。
(一)公共外交架构完善
2007年8月,澳国会发表了题为《澳大利亚公共外交:塑造我们的形象》(Australia's Public Diplomacy:Building Our Image)的外交报告。它标志着澳公共外交一改政府单独谋划、主导实施的惯常做法,进入到了一个致力于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
一是在政府层面,外交贸易部主管公共外交事务。分管的澳形象局(Images of Australia Branch)落实日常工作推进,并负责召集由21个相关部门参与的公共外交跨部门协调委员会,以共享资源、优化行动。此外,其分管的澳国际开发署和澳贸委也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透露,截止2012年6月,澳外交贸易部的593个海外工作岗位中,42%被安遣到了亚洲;澳1700个海外工作岗位中的45%在亚洲。这些人员、部门和机构里应外合,共同描绘出一幅澳国家正面标准像。据美国麦肯世界集团旗下的未来品牌咨询公司公布的2012-2013年度“国家品牌指数(Country Brand Index)”显示,澳在全球排名第六。
二是在地方层面,各州、市政府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积极创新打造公共外交品牌项目。始于2007年3月由悉尼首次倡导举办的“地球一小时”公益活动,到2013年3月已有近200个国家的数千座城市参与其中。在黯然失色的悉尼湾夜景里,人们读出了一个阳光、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精心策划推出的“世上最美差事”的护岛保礁公益活动,吸引了全球近200个国家的34000人踊跃报名。该项活动的“全球公关价值(global publicity value)”逾两亿美元;与亚洲国家省市对口结好,是澳地方政府的传统对外交流品牌。截止2012年,这种友好关系在中国已发展到80多对,在日本更是多达百余对。
三是在非政府组织层面,全国40余万家非赢利草根机构在澳总体外交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些二轨外交(Track 2 Diplomacy)中,澳中理事会、澳印理事会、澳马学会、澳泰学会、澳印学会、澳韩基金会、澳日基金会等致力于双边或多边交流的理事会、基金会和研究机构以及遍布亚洲高等教育机构里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Australian Studies Centre),在重塑澳国家形象上对亚洲地区施加了润物无声的影响。
(二)传媒覆盖渐趋立体
多年来,澳积极干预、影响和管理媒体,多措并举,强力执行前瞻性的媒体管控战略,旨在为亚太地区“提供可信、可靠、独立的声音;以超脱公正的方式提升澳形象;涵养对澳战略利益广泛理解的受众资源;增进对澳经贸能力和教育、旅游产业的认知度”,最终达到离岸推销澳公共外交目的。
1.确保澳国家形象“声形并茂”。2007年重组的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ABC International)旗下的澳洲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国际电视台是国际传媒的主力军。1939年12月,为对抗轴心国特别是日本的宣传攻势,澳短波电台开始播音,1944年二战晚期,改称“澳洲广播电台”,主要面向亚太地区,用英语、汉语、越南语、印尼语、高棉语、缅甸语等6种语言向46个国家全天候播出,目前每周受众约154万。澳国际电视台成立于2001年。该台除已覆盖亚太地区的3120万个家庭外,还提供免费卫星电视节目并已实现网络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
2.切实加强公共外交的“在线存在”。因特网在澳公共外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据澳外交贸易部《2011-2012年度报告》显示,该部及其驻外机构的网站总数逾90个,平均月访问量达56.5万人次。在社交新媒体方面,澳外交贸易部还开通了推特帐户、优酷频道、脸谱网页和手机微信,以配合亚洲近10亿网络用户和亚太地区近30亿手机用户消费习惯的转变,不断拓展公共外交的最新渠道。澳驻华使馆新近推出的澳在华文化门户网“想象澳大利亚(Imagine Australia)”,就是由澳国际文化理事会协助策划的一次影响较大的公共外交实践,而由澳国家旅游局2012年隆重推出的《独一无二的澳洲(There's Nothing Like Australia)》广告片,更是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被下载了两千万次。
3.精心制定媒体战略计划,大力资助国际传媒来访项目。据澳外交贸易部年度报告透露,2011、2012年度,澳为来自印度、日本、韩国、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老挝、巴新、印尼等国的35名记者组织了11次访澳项目。越南、帕劳、印尼等国的记者还参加了在澳实习活动。此外,国际媒体接待项目(International Media Hosting Program)还筛选、邀请了外国记者和电视团队访澳。每年都有数百篇正面文章见诸国际知名报端;同时,还搭起国内媒体发稿项目(Domestic Media Program)的平台,就土著文化、自然地理、澳洲内地、海岸生活、餐饮娱乐、都市旅行等选题撰文,向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有世界影响力的报刊杂志发稿,为精准塑造品牌澳洲(Brand Australia)营造舆论环境。
(三)国际教育匠心独运
1.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对国际学生数量的限制取消,留澳亚洲学生数量增长迅猛。在过去10年间,约250万国际学生留学澳洲,其中,190万来自亚洲。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国际学生数量将从2000年的180万增加至720万。作为世界上国际学生比例仅次于卢森堡的澳大利亚[6],其由39所大学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堪称世界级。2012年,在世界排名最好的100所大学里,澳占第三位,名列美英之后。澳教育出口已跃升至仅次于煤、铁矿和黄金出口的高位,成为第四大出口产业。据澳政府统计,2011年,55万留澳国际学生中,77%来自中、印、韩等亚洲国家,为澳经济贡献150亿澳元。拥有巨大上升空间的国际教育,在澳公共外交中扮演着“民间亲善大使”的重要角色,正日益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2.为巩固澳官方奖学金项目的发展成果,使公共外交收益最大化,进而塑造一批有深厚澳教育背景的未来世界领导人,2009年,澳整合设立了“澳大利亚奖(Australia Awards)”项目。2011、2012年度,该项目总额高达3.25亿澳元,业已超过始于1950年并在35年间资助两万名亚洲学生的“科隆坡计划”。2012年,约6800名国际学生、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获得该奖项,其中大多数来自亚洲。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教育概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澳(7%)已成为继美(17%)、英(13%)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未来5年,澳还将为亚洲国家提供1.2万个澳大利亚奖,“以促进本地区人民间的交流”。
3.澳是实施显性语言政策的典型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始,澳实行优先语言政策,逐步向亚洲语言倾斜,亚洲语言的经济价值和公共外交作用不断显现。为培养澳学生的“亚洲能力(Asia relevant capabilities)”,以便更好地与亚洲打交道,为融入亚洲做好战略储备,《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制定了明确务实的国家目标:(1)所有学生都要学习亚洲知识,以增强他们与亚洲为伍的能力;(2)每所学校至少与一所亚洲中学结好,以便更好地开展优先语言(priority language)教学;(3)所有学生都要在中学阶段选修至少一门优先亚洲语言,即汉语、印地语、印尼语和日语,因为“这些国家可以为澳在亚洲世纪中带来最多的机会”。
(四)文化外交有声有色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跨文化交际离不开有效沟通,而沟通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掌控信息的日常沟通、特别谋划的战略沟通和着眼长远的根系沟通[7]。
文化作为深刻影响、夯实人脉、默化植入、高调浸染的一张公共外交王牌,是澳在融入亚洲的过程中实现务实转圜的重要沟通手段。
1.大力扶植土著文化。据澳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1年6月,澳土著人口达575,552人。土著人在澳洲大陆已经生活了4000至6000年。2008年2月,时任总理陆克文在讲话中声称,澳土著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可见土著文化对年轻的澳大利亚来说弥足珍贵。在澳走向亚洲的进程中,作为澳文化内核的土著文化起到了突出的引领作用,始终是一张独特的公共外交名片和符号。土著人使用的笛节里度管(didgeridoo)和回力镖(boomerang)被开发成独具魅力的涉外礼品和旅游纪念品;土著人的“点画(dot painting)”时常成为澳每年在海外举办的当代美术作品展的亮点。2011 2013年,澳在亚太地区还举办了“信息棒(message stick):都市澳洲里的土著认同”视觉艺术巡回展。每年5月末“和解周”期间,澳政府都会为外国驻澳使节团举办土著文化展览活动,力求把土著文化这个招牌当做多元文化外交的一个维度来加以强力拓展。
2.不断增强本土文化海外传播力度。2009、2010年度,澳国际文化理事会资助了17个文化项目,其中11个在中国。2010、2011年度,它又支持了21个文化外交项目,其中10个在中国,5个在韩国。“澳大利亚周”、“澳亚文化节”、“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澳韩友好年(2011)、澳中文化年(2012)、澳洲越南年(2013)、澳洲印尼年(2014)等公共外交活动异彩纷呈,辅之以特别访问项目(Special Visitors Program)和国际文化访问项目(International Cultural Visits Program),使得澳文化外交在推陈出新中佳绩连连,尤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最。上海世博会期间,澳国家馆共运营2,622个小时,迎接公众访客818万,赢得了7500多篇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服务态度”获得100分,“政治印象提升”也被评为第一,尽显澳公共外交的不凡之举。
(五)足球外交扎实推进
澳历来重视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对公共外交的拉动作用。几年前推出的澳体育推广计划(Australian Sports Outreach Program),就是一次对体育外交的顶层战略和基层战术的全面设计。2005年9月,澳足协正式成为亚足联的第46个成员,开始闯荡亚洲足坛。这不仅改变了亚洲体育传统格局,而且也首次通过足球在澳亚间搭起了意义深远的体育桥梁。澳著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树立地区形象、强化地区融入”的千载良机,于同年11月出台了《足球外交》的政策报告,强调指出:
(1)足球为澳亚国家间对话提供了一个公允的平台。球迷热衷追逐自己喜爱的球队的同时,往往在不经意间跨越了国界和文化边际,实现了广泛的过去未曾有过的草根融合,从而潜移默化地转变了原有的认知与偏见。
(2)足球为澳找到了一个摆脱“亚洲国家”之争的办法。尽管地理、文化、种族都是求得亚洲认同的重要因素,但只有足球促成澳被端端正正地摆进亚洲。在强调“亚洲价值”在政治利益和行为取向上的份量时,足球价值(football values)显然为澳走向亚洲开辟了捷径。
(3)足球是文化活动的极佳舞台。尽管体育是澳社会中的日常主角,但在亚洲文化外交中却经常缺席。围绕高级别体育赛事来策划外交、文化、教育、商务活动并使之机制化,可以借助人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4)足球是公共外交的难得载体。举目世界外交,乒乓球可破冰,运动会能添彩。体育场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化解龌蹉的外交论坛。利用赛场吸引政治家参与远比循规蹈矩的双边外交来的更加便捷和有效。
《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称,随着亚洲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足球运动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2006年,亚洲踢球人数约8000万,到2020年,将超过3.8亿。看球的人将会更多,由此带来的机遇俯拾皆是。基于这样一个国民研判,将于2015年1月下旬在澳举行的第16屇亚洲杯足球赛正在演变成澳开展公共外交的舞台。预计将有4.5万现场观众,潜在的电视观众将达25亿。澳政府、商界和全社会无疑将充分利用承办亚洲杯的机会加强对亚洲的“更广泛融入”。有关智库甚至建议组建“亚洲足球理事会(Football Asia Council)”,来协调以亚洲杯为核心的系列公共外交活动。
三、澳大利亚公共外交在亚洲面临的挑战
成立于1990年的亚联组织(Asialink)主张,鉴于亚洲对澳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意义,公共外交是澳在本地区最合乎逻辑的战略投资(most strategic and logical investment),必须优先推进。然而,由于澳与其强大的盟友间身份辨识度较低,对亚洲而言,英美仍然是认知澳洲的基准点(reference points),这就使得澳自身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和文化的传播变得较为曲折和复杂。加之亚洲公共外交领域历来强手如林,中、日、韩、印、马等国在本地区对公共外交投入的不断追加,对公共外交手段的日益翻新,致使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空间里欲得到亚洲公众的回眸呼应变得难乎其难。
(一)战略规划执行乏力,公共外交任重道远
虽然专家学者对澳公共外交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与官方外交发展战略布局的不对称性问题,但澳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理论贡献仍时有缺位,在战略规划上难免“釜底抽薪”;其次,联邦政府、国会和地方政府尚未形成三位一体的整体运作模式,经常单打独斗,顾此失彼;再次,尽管在2012、2013财年澳将有15亿澳元的预算盈余,逆转连续四年的财政赤字,但澳外交战略的内在缺陷和投入不足使得公共外交捉襟见肘。另外,对公共外交活动和项目缺少科学的评估体系,只管播种,不问收获,导致澳公共外交因缺乏“总体战略影响(overall strategic impact)”而形成了“1+1<2”的局面,沦为陪衬和点缀。
(二)价值观大相径庭,公共外交举步维艰
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认为,文化与宗教的认同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澳则是被西方文明传统和对亚日渐融入所撕裂的国家(torn country),完全地皈依亚洲文化与澳现行外交政策和文化价值观无法兼容。目前,澳2284万公民中,74%为英国和爱尔兰后裔。澳现仍在联合国里作为“西欧与其他国家集团(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s Group)”中的一员进行投票,保持着与殖民地君主国的象征关系。难怪2000年11月在接受澳广记者访谈时,新加坡李光耀一语中的地指出:“融入亚洲并非意味着你们成为亚洲人或文化亚洲化,抑或把亚洲人引入澳洲。你们要理解亚洲人,要让彼此能够舒服地相处。和谐(rapport)是需要用个人热度(personal warmth)来温暖的。”即使是在澳国内,唱衰亚洲政策的也大有人在,担心亚洲不会真心实意地揽澳入怀。求得亚洲国家的普遍认同,构建心灵共同体,澳公共外交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种族主义沉渣泛起,公共外交如履薄冰
约100万生活在海外的澳公民中,23万人居住在亚洲。同时,有约200万出生于亚洲的人定居澳洲;每年约有200-300万澳公民到访亚洲。尽管如此,澳种族主义情绪并未因多元文化的强力推行而销声匿迹,而是不时沉渣泛起。近年来,瞄准国际学生的暴力袭击、国际教育欺诈、紧缩移民政策等都暴露出了澳在公共外交上的战略短板,让人瞥见了“白澳政策”不散的阴魂。据澳媒体报道,85%的澳洲人承认澳存在种族歧视。2002年印尼巴厘岛爆炸案、2009年印尼恐怖袭击事件、2011年印度学生墨尔本遇害案,无一不与肤色有关。把一个干净、包容的国家形象展示给亚洲,是澳公共外交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澳有识之士指出,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于起飞伊始就保驾护航,而不是在危机关头“紧急迫降(emergency landing)”。
(四)政策摇摆不定,公共外交前途未卜
二战后,澳自由党(Liberal Party)与国家党(National Party)结成长期稳固联盟,与工党(Labour Party)轮流执政。近亚的工党与亲美的自由党政治抱负迥异。澳外交政策因政府的更迭而变化也就尽在意料之中,顺理成章地成为亚洲国家的隐忧。冷战结束后,澳迄今虽然只经历了基廷(工党)、霍华德(自由党)、陆克文(工党)和吉拉德(工党)四届政府,但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已成大概率事件,特别是在霍华德执政的11年间更是如此。历史地看,澳美关系与澳亚关系经常相向而行。作为美盟国,澳尚未开出治愈其面亚靠美顽疾的药方。澳更深入、更持久地融入亚洲,政策维稳是前提,政策定位是条件。在经济与安全双轮驱动下,摆正心态,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政策互信,努力在亚美间保持战略平衡,在亚洲一体化中寻求现实合作,是澳不二选择。这决定了澳的国家长远发展路径,也决定了为之鼓与呼的公共外交的未来走向。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96.
[2]Dennis Rumley.The Geopolitics of Australia's Regional Relations[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3]David Uren.Prosperity Boils Down to Five Letters–China[N].The Australian,2012-5-31.
[4]Henry A Kissinger.Diplomacy[M].First Touchstone Edition,1995:23.
[5]张秋生.战后初期伊瓦特的亚洲协调政策与澳亚外交贸易关系的发展[J].世界历史,2007(5):53-60.
[6]Indicator C4 Who studies abroad and where?[R]//Education ataGlance2012.OECD Indicators,2012.
[7]Joseph 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Public Afairs,2004:107-118.
Australia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sian Century
ZHANG Jian-wei
(Dalian Foreign Afairs Ofce,Dalian 116012,China)
With the rise of Asia as a leader of the world economy,Australian strategic weight has been shifted gradually to Asia in order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fght against challenges there.Due to reasons of history,culture and values,Australia had long been alienating itself from Asia;while,on its road to re-embrace Asia driven by realistic interests,it has given priority to reshaping its national image,going all out to push forward the regional public diplomacy.The challenges Australia are confronting are of signifcance for China to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with Asia.
Asian century;Australia;Public diplomacy
D83
:A
:1008-2395(2013)02-0081-07
2013-02-15
张建威(1963-),男,大连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英文副译审,主要从事外事翻译、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