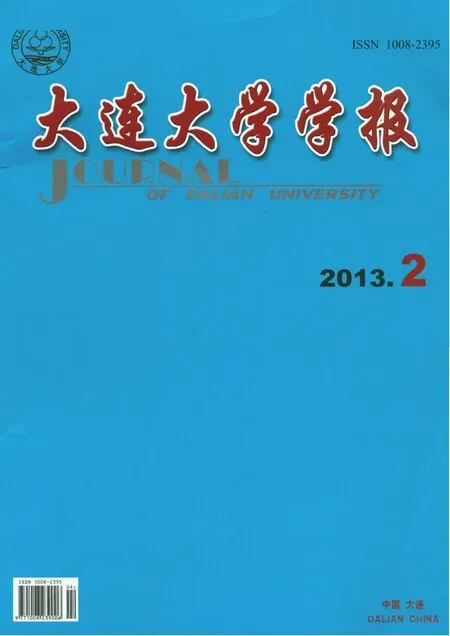大凌河流域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一)
王禹浪,程 功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大凌河流域隋唐时期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一)
王禹浪,程 功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位于大凌河畔的古营州(朝阳),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与东北,东北亚与中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无论是中原的农业文明、还是中亚地区的锡尔河流域文明,以及草原文明都曾经以朝阳为中心而得到了充分的融合与发展。尤其在隋唐时期,营州由于地理优势的明显与多民族的开发,使其一度成为辽西地区乃至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由于三燕政权和北魏政权的早期开发和积累,加之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营州必然成为隋唐帝国经略东北的边疆重镇。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天的朝阳地区就陆续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墓葬,截止到2010年为止这一地区隋唐墓葬发现的数量多达205座。我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琳琅满目数以千计的各类随葬品中,透视出曾经辉煌和灿烂的文明印记。隋唐时期的营州对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融合,以及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梳理和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便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隋唐时期营州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价值所在。
大凌河流域;隋唐营州;研究综述
一、大凌河流域隋唐营州的地理空间与历史背景
在辽宁省西部,燕山北麓与大兴安岭山地南麓交界处的群山环抱中的大凌河谷,有一座古老的城市——朝阳。历史上曾有“柳城”、“龙城”、“营州”等不同的称谓。自三燕、北魏以来朝阳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贸易往来的重要都市,同时也是贯通长城南北、连接幽燕文明与东北文明枢纽和交通要道。今天的朝阳市,依然是东北西南部连接京、津、唐地区,以及河北、内蒙古和朝鲜半岛的重要城市。
早在先秦时期,商周及其燕国就是通过陆路上的辽西古道,由朝阳经义县、北镇而入辽东,继而打通了进入朝鲜半岛的通衢。在中国历史上,由中原通往东北和漠北草原的平岗、无终、卢龙、黄龙、营州等古道,都是以古朝阳为中心进行着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与传递。穿越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大凌河谷与青龙河谷,实际上就成为了由华北通往东北地区天然通道上的咽喉之地。无论是“山戎越燕而伐齐”,还是曹操“道出卢龙、东指柳城而北伐乌桓”,皆经此地而跃进千里之外。历史上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勿吉人,还专门开辟了从黑龙江下游,经松花江、嫩江、洮儿河,沿着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接合部的丘陵地带南下,并直达古代龙城——即营州的路线。
朝阳周边的地理环境极其复杂,地处内蒙古高原向环渤海地区及松辽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地形大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犹如一个向东开口的簸箕形状。地域内山峦起伏、河道纵横。其中努鲁儿虎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斜卧于建平县东部及凌源县的西北部。大青山脉亦为东北——西南走向,经北票市西北,穿过喀左县和凌源县的中部,在凌源境内与努鲁儿虎山脉合拢;黑山山脉自建昌县黑山一带,由东北——西南走向延伸到建昌县南部;松岭山脉亦以东北——西南方向,经过朝阳县中部、喀左县南部后,入建昌县境与黑山山脉相接。群山万壑连绵不断呈环抱之势,并形成了以喀左县、朝阳县为主体的山间盆地。
朝阳东部的低山丘陵区,由于河流的冲积作用形成几个小型冲积平原。这些小型平原和山间盆地地势较为平坦,是该地主要的农业耕作区。在各山脉之间有5条河流贯穿其中,即大凌河、小凌河、六股河、青龙河、老哈河。这些河流除老哈河的流向向北流淌外,其余4条河流的流向均为由西向东折而东南或径直南流。值得注意的是,大凌河是朝阳市最大的一条河流,它由北、西、南3个源头。西、北2个源头于辛杖子汇流,并在山嘴乡汇入南源。三源汇流后呈西南—东北流向,经朝阳市城区于金沟车站附近东流进入北票市境。大凌河流入北票市境后继续流向东北,在九官台门地方进入锦州市义县境内,再经锦县流入渤海[1]。
以大凌河谷为中心的附近山地,一直都是古老的华夏族群与东夷族群、东胡族群交融、碰撞、接触的核心地域。如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等诸多充满活力的族群文化几乎都在这里驻足、生根、繁衍而生生不息。近几年来,在大凌河上游地区发现的东杖子大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群的发现,又为揭示大凌河流域的古国文明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实际上,以大凌河谷朝阳为中心包括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礼制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无论是商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还是辽、金、元、明、清,古老的朝阳历史文明的脚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从先秦时期的辽西郡到柳城、营州和龙城,朝阳都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设置郡县的地区。近年来,在朝阳市区内考古发现的波斯人形象的陶塑,以及东罗马的古币、西亚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物造像等,都越来越证明朝阳不仅是古代沟通中国南北地区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是联结和沟通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域。
如果从地域文化的特征角度观察,这里既是草原文明、农业文明,也是森林狩猎、海洋文明、渔捞文明的交会点。应该说,以大凌河谷为中心的文化与文明,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悠久的古代文明的典型区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朝阳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尚停留在较为浮浅的基础上。目前学术界通常把朝阳的历史与文化归结为西辽河流域的文化,其实从严格的流域文化的角度上观察,朝阳的古代文化并不属于辽河文化,而是属于大凌河流域的文化。著名的查海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的中心地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都属于大凌河流域。如果从流域概念上看,大凌河流域与西辽河流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流域范围。然而,古代文化的分布往往打破了单纯以现代地理的流域概念的限制,其文化的分布则是以相邻的地域或地区向周围扩散。当然,地域文化的流向则是以沿着河流的流动方向为发展路线。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与高山、森林、峡谷、川地、丘陵、平原、近海之地相伴。因此,西辽河流域文化与大凌河流域的文化,实际上应属于辽西地区的文化。辽西的地域概念作为上述两大流域文化的综合解释,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当然,大凌河流域的朝阳市是辽西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典型的东北地域都市文明的代表。这个文化中心经历了数千年的多种文化的交融和多民族文化的碰撞,才最终形成了以三燕文化为中心的城市文明。从地域上看,其西接蒙古高原,东滨辽海大地,北镇白山黑水,南连幽燕河山,具有文化和民族聚合的地理特征[2]。
代人、汉人、契丹、鲜卑、高句丽、靺鞨、粟特、波斯、斯基泰等不同的民族与种族,都曾经在这里聚合、相处、贸易、交换与交流。北齐末年,代人高保(宝)宁为营州刺史,颇受周边部族的尊重。时年正遇北周大举攻伐北齐,高氏便联合营州周边契丹、靺鞨等民族来抵抗北周的入侵。《北齐书》卷四一《高保宁传》载“周帝遣使招慰,(高保宁)不受敕书……还据黄龙,竟不臣周。”[3]而《隋书》卷三九《阴寿传》载“及齐灭,周武帝拜(高保宁)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4]可知,高保宁在周齐战争之际以营州为依托来抵抗北周,而北齐灭亡后在大势所趋之下,向北周归降,并继续任营州刺史一职。所谓其“甚得华夷之心”说明了高保宁的汉化程度和深得汉人的信任。公元580年北周静帝鲜卑人宇文阐继位,外戚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营州刺史高保宁又连接契丹、靺鞨举兵反北周。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改国号为隋。时年高保宁招引突厥兵围攻北平,隋文帝杨坚遣大将阴寿率兵万骑平息叛乱。高保宁弃城而逃,营州被隋朝收复。隋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营州总管府,治所为龙城县(开皇十八年易名为柳城县),即今朝阳市。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废除营州总管府,取秦汉“辽西郡”名之。大业八年(612年)又废除辽西郡之名,改名为柳城郡。隋朝末年,幽州总管罗艺割据柳城郡自立,并改柳城郡复为营州。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武德元年设置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武德七年,改为营州都督府,管营、辽二州。武周时期,由于营州都督赵文翙的“骄沓”作风,对契丹等民族“数侵侮其下”并且面对契丹饥荒也“不加赈给”,“视(契丹)酋长如奴仆”,使民族矛盾激化,并招致松漠都督府都督李尽忠的不满。于是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李尽忠与孙万荣共同起兵反唐,诛杀赵文翙,占据营州。李尽忠自封“无上可汗”,任用孙万荣为将,并纵兵四略,进攻唐河北道。这时,武则天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灭叛乱。李尽忠等闻大军将至,释放俘虏,并言:“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唐军听闻便“争欲先入”[5]在黄麞谷李尽忠又让老弱迎降,种种表现目的只在于让敌军放松警惕。于是曹仁师三军放弃步卒,率骑兵先行,在硖石谷遭遇契丹兵的伏击,主帅被擒。《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八月丁酉条”记载了唐军战败时的惨状“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5]6507,可谓是全军覆没。此后,契丹再次设伏兵击败前来的唐军燕匪石的部队。同年,契丹又击败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并围攻安东城。十月,李尽忠卒,孙万荣代替其位统辖诸部。此时,突厥默啜可汗率兵袭击,并掠走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儿。孙万荣再次收合余众,并遣兵攻陷冀州,屠吏民数千人,震动河北。第二年,孙万荣率部破唐军,并于柳城西北四百里处依险筑新城,以安置老弱妇女与所获器仗资财。正当孙万荣率精兵攻打幽州之际,孙万荣部的后方却遭到了突厥人的袭击。突厥默啜可汗听闻契丹即将大势已去,遂发兵围攻新城,持续三日将其攻克。一时之间,众心离散,依附于契丹的奚人也背叛契丹。武周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族兵众击其后。契丹大军溃败,孙万荣也被手下杀死。历时一年多的“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终于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契丹叛乱之际,营州靺鞨人大祚荣与其父乞乞仲象则趁机逃往“故国”东牟山;脱离了唐王朝的控制建立“靺鞨国”,即后来唐朝册封的渤海国。
唐朝虽然剿灭了营州的叛乱,但是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制却一度失去了有效的管辖。唐中宗即位后,将营州都督府内迁幽州之东的渔阳城。开元二年,薛讷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由于军事失利,直到开元五年才还治柳城。《旧唐书》卷一〇八五下《宋庆礼传》载:“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衞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6]又《全唐文》卷二七收录了唐玄宗在这一时期颁布的《柳城复置营州诏》,诏书曰“朕闻舞干戚者,所以怀荒远,固城池者,所以款戎夷。国家往有营州,兹为虏障,此北狄不敢窥觇东藩,由其辑睦者久矣。自赵文翙失於镇静,部落因此携离,颇见负涂之睽,旋闻改邑之叹。高墉填堑,故里为墟,言念於此,每思开复。奚饶乐郡王李大酺,赐婚来朝,已纳呼韩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弥嘉秺侯之节。咸申恳请,朕所难违,宜恢远图,用光旧业,其营州都督府,宜依旧於柳州置。管内州县镇戍等,并准旧额。太子詹事姜师度、贝州刺史宋庆礼、左饶卫大将军兼营田都督邵宏、郑州刺史刘嘉言、屯田员外郎游子骞等,并贞以干事,恪勤在公,爰精众官之遇,任以一方之役。师度可充营田支度及修筑使,游子骞为副。宏可兼充燕郡经略镇副使,仍兼知修筑使事。应、须人夫粮等,一物已上,依别敕处分,有司仍速支配。师度等并驰驿发遣。”[7]由此观之,营州对于整个唐朝东北边疆的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更加有力控制营州地区,唐开元五年(717年),于营州设置平卢军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使,经略河北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并兼押两蕃、渤海、黑水经略处置使。由此可见,唐平卢军节度使成为管辖东北最高的军政长官,节度使由唐营州都督所兼任。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范阳起兵反唐,这一持续八年的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为“营州柳城杂胡”,长期担任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等职务,因此在营州地域颇有影响力。《旧唐书》卷一四五《刘全谅传》称:“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以平卢军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军节度使……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遗心腹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6]3938。此时,营州地域已陷入安史叛军之手,由此可以看出安禄山在营州的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亦不能忽略唐廷多年经略营州的作用。“(刘)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6]3938,唐朝中央马上授刘克奴为柳城太守。同时,安禄山又派遣徐归道夺回营州,任平卢军节度使。此时,平卢军裨将侯希逸又与安东都护王志玄袭杀刘归道,重新夺回营州最高权力。
由以上诸多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安禄山与唐中央政府在营州的势力呈犬牙交错的状态,双方竭尽全力想把营州掌控在手。此后王志玄病故,侯希逸任平卢军节度使。此时,奚族势力崛起,在内忧外患之下,侯希逸率军2万人南下到青州一带驻防,从此平卢军再没有能力北返营州。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取消了营州都督府的建置,遣卢龙节度使统辖营州,这也标志着唐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对东北的无力经营,同时也为10世纪契丹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总之,隋唐之际朝阳做为最重要的节镇东北及北方的古代民族的重镇,其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具有多重因素。
二、大凌河流域隋唐营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
公元581年,北周重臣杨坚取代宇文氏的北周,建立隋王朝,在平定高保宁营州叛乱之后,在北齐营州基础上置营州总管府。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废营州总管府,置辽西郡。隋大业八年(612年),辽西郡改名为柳城郡。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营州地区逐步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因此唐王朝在此相继设置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等,它们作为营州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以管辖控制东北边疆。隋唐时期营州的地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三燕”与北朝时期在此留下的民族迁徙和经营的积淀,经过隋唐统一后的整合。另一方面,随着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盛,加之营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朝阳成为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的聚居地。因此隋唐时期的营州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特征。目前,学术界对隋唐营州的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综合梳理朝阳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对于隋唐时期营州对东北与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从营州的历史地理、地域的行政建置与职能、民族融合、风俗宗教文化、墓葬形制及墓志、国外研究状况等六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关于隋唐营州历史地理研究
金毓黻在《东北通史》[8]一书,考订了隋唐营州(柳城)的地理位置,纠正了学术界原来认定“柳城”为河北昌黎的错误。辽代的营州,虽袭故名,实为新置,与北魏至隋唐时期的营州并非一地。辽代的兴中府才是隋唐时期的营州,即今天的朝阳。金毓黻先生的这一考证,奠定了确认隋唐营州的学术基础。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9]中认为,隋唐时期的营州通往东北藩国的道路共有三条:其一,东北至契丹牙帐通往东北诸国道。其二,西北越西陉至奚王牙帐通往北蕃道;其三,东至辽东通往东方诸国道;而隋唐的营州则是这三条通道的起点。王绵厚在《隋唐辽宁建置地理述考》[10]主要考证隋唐在营州设置的羁縻州县的地理位置。史念海在《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11]认为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是农耕地区。燕山以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就是游牧地区。王绵厚、李健才的《东北古代交通》[12]主要考订隋唐时期营州通往安东都护府的三条重要道路,即南道由营州东南陆行,经大凌河下游的“燕郡”(今义县附近)、“汝罗城”(大凌河西岸老君堡)去往“安东都护府”(辽阳);中道,从营州出发经“怀远镇”(北镇一带),向东至“安东都护府”;北道,从营州出发至通定(今新民县高台山)过辽河至(玄菟)新城(今抚顺北高尔山山城)东南沿浑河到“安东都护府”。邵京彩的《三燕至隋唐时期朝阳城市地理初探》[13]对三燕至隋唐时期朝阳的地理环境、城市形态进行了论述。
(二)关于隋唐营州地区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隋唐时期在营州地区相继设立过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以及平卢节度使等机构,作为该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以管辖控制东北边疆。这些机构对于隋唐的东北部边疆的稳定和有效管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慧庆在《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14]中,主要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论述了营州平卢节度使在东北边疆所起到的作用。王俊在《唐平卢节度使始置年代辨证》[15]中认为,唐开元七年(719年)始置平卢节度使,并非如《资治通鉴》、《新唐书·逆臣传》中所言,始置于天宝元年(742年)。郭继武在《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治所的变迁——兼论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16]认为:营州作为唐代前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负有统制东北诸蕃的战略重任。营州都督府位置的变动、权力机构的变更,尤其是其两次侨治以及向节度使体制的转变,都受到奚、契丹叛服的深刻影响。许辉的《隋朝幽州军事防御的演变》[17]指出隋朝营州的主要职责是镇抚东北诸族及防犯辽东,并相应地负担了幽州东北的防御任务。由此,导致幽州的防御目标和防御地位发生了转变。幽州主要将目标集中于突厥,积极配合北边的军事行动,同时为营州的防御提供支持。王义康在《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18]中认为,后突厥的复兴是促使平卢节度使建立乃至军力加强的直接或间接因素。虽然唐以优势兵力遏制了突厥对东北诸族的进攻,巩固了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军事上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岳聪的《略论唐代营州都督府》[19]一文,主要探讨“营州之乱”后,唐朝对营州都督府的重建,并以宋庆礼为个案进行研究。他认为:在宋庆礼经营之后,营州都督府逐渐变为唐政府的重要军事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吉林大学的宋卿博士在这一领域发表过数篇论文,并颇有建树。其《唐代营州研究》[20]主要从地方建置、民族与人口、官署机构与职官、职能实施等多角度入手,探讨营州在唐王朝东北区域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21]对唐代东北地区设置的各种形式的羁縻府州,既有设置正州即营州内的羁縻州,亦有设少数民族原居地的羁縻府州,诸羁縻府州的职官与正州职官有所不同;《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22]对唐代营州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征收赋税与土贡、经营屯田、管理互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23]分析了唐代营州府行政职能;主要是选拔考课官吏、管理朝贡活动、少数民族诸羁縻府州等问题;《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24]认为平卢节度使的任命渠道主要有三种:朝廷任命,安禄山任命,先将士推立后,由朝廷再任命。平卢节度使以汉人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边疆民族将领。其任前多为武将,亦有文官,还有宗室亲王遥领。平卢节度使多在营州地方官或军府官员中提拔任命;《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25]指出唐代平卢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七年,与营州都督共同负责营州军政事务。在官职任职中,平卢节度使多兼任其他官职,相继以营州都督、柳城郡太守、营州刺史充任。并且兼充支度使、营田使、运使等职,或摄御史中丞(大夫),亦兼押蕃使以负责监督、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26]认为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在维护唐王朝与东北边疆诸少数部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实现唐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防范、平定东北边疆叛乱,发展东北边疆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27]、李治亭的《东北通史》[28]、程妮娜的《东北史》[29]、《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30]分别以通史的角度对隋唐时期营州的地方建置进行了论述。
(三)隋唐时期营州地区的民族分布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叛乱以及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杜日新在《隋代“营州靺鞨”琐议》[31]中指出,隋朝末年靺鞨人开始移民到营州,在其演化过程中,有两个主要去向:进关,成为中原朝廷州郡属下的臣民,后来成为汉族的一部分;返回靺鞨故地,成为中央唐王朝在东北渤海国的王室和编户。张春海在《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32]中指出,唐代营州地区的高句丽人,由于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遭到破坏,再经过近300年的动乱、变迁,组织力更加微弱。因此,平卢军中的高句丽武人被排斥到了高级将领的队伍之外,对以安禄山为首的胡人军事集团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趁安禄山从平卢军抽调大批精兵猛将发动叛乱,对军内却未做周密人事安排之际,高句丽武人集团趁势崛起。范恩实在《论隋唐营州的靺鞨人》[33]中指出,隋唐时期先后有数批靺鞨人流入营州地区,包括隋初内迁的突地稽部粟末靺鞨人,唐初入附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以及唐伐高句丽过程中内附的粟末、白山等部靺鞨人。万岁通天年间营州靺鞨人东走建立渤海国之前,营州地区当有10万以上的靺鞨人。此外,隋唐时期营州的“高保宁之乱”与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也备受学界关注。王小甫在《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34]中认为,隋初平定营州高保宁的叛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突厥与高句丽对辽西地区的染指,安定了北部边疆。许辉在《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35]指出,隋初平定营州高保宁之乱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突厥的进攻。韩昇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36]一书中认为,营州高保宁之乱主要依托高句丽的支持,背后牵涉到隋朝与高句丽之间对辽西地区的争夺,前者希望占据该地进而断突厥右臂,后者则希望利用此地来屏藩本国。李文才在《论“营州事变”的成因及其影响》[37]中认为,武则天时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武周统治集团内部的武李之争,是造成“营州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并对东北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松涛在《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38]中论述到;唐在“营州之乱”后;为了确保东北地区的安定,调整了防御体系,形成营州、幽州犄角之势,同时也为安禄山的反叛提供了客观条件。肖爱民、孟庆鑫在《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39]认为契丹“营州之乱”,不仅让武周政权在军事上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边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迫使武则天在立嗣问题上,态度发生了转变,由支持武氏转为支持李氏。都兴智在《略论契丹李尽忠之乱》[40]中,论述了李尽忠发动的营州之乱使唐王朝在很长时间内失去了对辽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迫使原设在今朝阳市的营州都督府;暂时侨置于河北的渔阳,同时设在营州附近的一些管理少数民族的羁縻州县也都分别迁往异地。使唐王朝去往东北的陆路通道长时间不能得以畅通。蒋戎在《靺鞨参与营州事变的原因及其东奔》[41]中认为,营州靺鞨参与营州事变的原因:不是反唐而是反对武周政权,而东奔的最初目的也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而是为了与武周对抗。
[1]朝阳市史志办公室编.朝阳市志第1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142-149.
[2]王禹浪.三燕故都古朝阳的历史、文化与民族融合[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3).
[3]李百药等.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47-548.
[4](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48.
[5](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清)董浩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09.
[8]金毓黻.东北通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1:188.
[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86:1756-1769.
[10]王绵厚.隋唐辽宁建置地理述考[J].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1).
[11]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C].//史念海.唐史论丛·第三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33-34.
[12]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0-152.
[13]邵京彩.三燕至隋唐时期朝阳城市地理初探[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4]孙慧庆.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J].北方文物,1991(4).
[15]王俊.唐平卢节度使始置年代辩正[J].六安师专学报,1999(1).
[16]郭继武.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治所的变迁——兼论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7]许辉.隋朝幽州军事防御的演变[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9(3).
[18]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6).
[19]岳聪.略论唐代营州都督府[J].枣庄学院学报.2011(3).
[20]宋卿.唐代营州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1]宋卿.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J].北方文物,2009(1).
[22]宋卿.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J].社会科学辑刊,2009(3).
[23]宋卿.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J].东北史地,2009(5).
[24]宋卿.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2).
[25]宋卿.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J].西南大学学报,2011(1).
[26]宋卿.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J].东北师大学报,2011(2).
[27]佟冬.中国东北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28]李治亭.东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9]程妮娜.东北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30]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1]杜日新.隋代“营州殊揭靺鞨”琐议.社会科学战线[J],1994(3).
[32]张春海.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J]江苏社会科学,2007(2).
[33]范恩实.论隋唐营州的靺鞨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1).
[34]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C].//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34-53.
[35]许辉.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J].晋阳学刊,2005(3).
[36]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77-180.
[37]李文才.论“营州事变”的成因及其影响[J].河北学刊,2002(4).
[38]李松涛.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C].//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94-115.
[39]肖爱民,孟庆鑫.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2005(4).
[40]都兴智.略论契丹李尽忠之乱[J].东北史地,2008(2).
[41]蒋戎.靺鞨参与营州事变的原因及其东奔[J].社会科学战线.2010(10).
Review o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ingzhou in Dalinghe River Basin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NG Yu-lang,CHENG G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Ancient Yingzhou(Chaoyang today)in Dalinghe River basin w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 hub to connect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the Northeast,and Northeast Asia with Central Asia.Either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Central Plains,or civilization of the Syr Darya River in Central Asia,or grassland civilization were well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with Chaoyang as a center.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in particular, Yingzhou,owing to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multi-ethnic development,had been an important political,economic,trade and cultural center of West Liaoning as well as Northeast China.Since the 1950s,a large number of tomb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Chaoyang area,more than 205, to be exact,by 2010.Thousands of burial objects unearthed from these tombs imprint brilliant and splendid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y.Yingzhou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dissemination,social progress,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The review of these fnding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the infuence of Yingzhou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alinghe River basin;Yingzhou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Review
K302
:A
:1008-2395(2013)02-0024-07
2013-02-17
王禹浪(1956-),男,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及区域史研究;程功(1987-),男,大连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