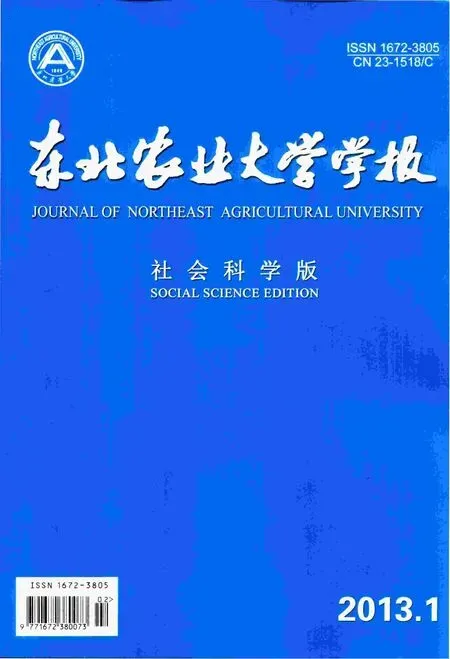浅析汉字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的途径
张 晶 金夏伊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汉字是表意文字,与英语等其他拼音文字不同,不能直接根据读音写出相应的汉字。因此,汉字对汉语学习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教学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学习者学习了半年汉语,仍然只能靠拼音来读汉字读物。可见,汉字的记忆和书写已成为汉语学习者的障碍之一。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理念和策略等还存在许多问题。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本文试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审视和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方法与走向。
一、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汉字是当代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仍在发挥作用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淘汰旧字,创造新字,以及字形结构发生变化之外,还出现了汉字体式的演变。历史上曾经形成多种字体,其中包括西周的大篆、秦朝的小篆、汉代的隶书、唐朝的楷书和为了书写快捷而产生的草书等等,传统称之为“真、草、隶、篆”。汉字字体由繁到简,还形成了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征的书法艺术。
汉字和中国文化是互相依存的,二者密不可分。汉字作为一种具有表意特点且历史悠久的文字,在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记载和传承着文化信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亦需要汉字的书面表述,如被译成多种文字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有了汉字的记载,人们才能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饮食文化和服饰特点等等。汉字作为工具,在表述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在漫长的使用和流传中,除了体式演变,汉字的结构和含义也在发生变化,变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以“昏”字为例,清代袁枚在《祭妹文》中说道:“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说文》:“昏,日冥也。”“昏”的本义是指黄昏。因为黄昏时分在古代是吉时,所以人们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传统中式夫妻结合的礼仪就被称为“昏礼”。《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就是说“昏礼”这种礼仪,能让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交好,对上可以告慰族中先祖,对下可以延续家族香火,所以君子把婚姻当作大事。这便是现在的“婚礼”。古代婚礼的基本程序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礼记·昏义》)。“昏礼”是继男子冠礼和女子笄礼之后的第二个人生里程碑。如今,中国人的婚礼虽然没有严格遵循“六礼”,但是大部分人仍沿用纳征、请期和亲迎的程序。“昏”字含义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传统婚礼文化的演变过程。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华文明之源泉。因此,要想学好汉字,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同样,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学好汉字。
二、汉字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汉字有独特的语音拼写系统,一字一形。因此也使得汉字难认、难写、难记、难懂。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学习汉字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第一,知道汉字读音,但记不住字形。也就是说,学生可以根据拼音读出读音,但是写不出相应汉字。第二,记住了汉字字形,但是不会使用。汉字系统庞大,存在同音不同字和同字不同义的现象,容易使学生混淆。如果在汉字教学中渗透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也可提高学习兴趣。
(一)将文化故事植入汉字教学中
在汉字教学中,将汉字本身的文化特性与所学汉字有关的文化故事相结合,不仅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汉字,而且便于学生深刻理解汉字的文化意义,加深记忆。
例如“喜”字。《说文》:“喜,乐也。从口,从壴,壴亦声。”“喜”字的本义是欢呼声。引申义为快乐,高兴。在生活中也常见“囍”字,而“囍”从何而来呢?相传北宋年间,王安石进京赶考,途中经过马家镇,见富绅马氏出联择婿,曰:“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第二天考试时,考官出联,曰:“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于是,王安石就用马家的上联对考官的下联,以考官的上联应马家的下联。结果既中了进士,又娶了马家小姐。他喜不自禁,挥笔写就两个连成一体的“囍”,让人贴在门上,并随口吟道“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从此,“囍”字便流传开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里,“囍”字仍然广泛应用。人们办理结婚、乔迁、生子等事宜时,仍是“囍”声不断,例如新婚之囍、乔迁之囍等等。又如“梅”字,可将它的文化内涵寓于讲解之中。“梅”“兰”“竹”“菊”乃是“花中四君子”。梅花常被人们看作是谦谦君子的象征,并为文人雅士青睐。一是因其花朵色淡香清,二是因其大多生于幽僻之处。例如,“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日黄昏”(《山园小梅》)等都是咏颂梅花的诗词。更有古曲《梅花引》,表现了梅花的高尚品性。此外,梅花有五瓣,被比喻为人生五福:寿、福、康宁、好德、善终。在“梅”字的教学中插入有代表性的诗词,加以声情并茂的讲解,这种情景交融的教学方法,不仅克服了汉字教学的抽象性,强调抽象与形象的有机结合,还使学生既记住了“梅”字,又学会了诗词。
通过向学生讲授汉字的文化故事,不仅可以让学生体会地道的汉字意义和中国文化,而且可以有效避免学生呆板、机械地记忆汉字字形和字义。
(二)引入汉字的基本构造法
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是汉字较常用的造字法。古代的象形字与其所表示的事物具有神似性,接近图画但并非图画,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符号。在汉字学习初期,学习者接触的一般是笔画少、字形简单的独体字①独体字一般不能再分为两个字,而象形字和指事字一般是单一的形体,因而象形字和指事字一般称为独体字。。利用这些特点,在教学中将展示象形字与讲解其中蕴含的文化知识相结合,是渗透中国文化因素行之有效的方法。
引导学生学会、记牢独体字。从汉字的基本构造看,很多笔画复杂的汉字都是由一个以上独体字构成。熟练认知并使用这些独体字,是进一步学习其他复杂汉字的基础。例如,古人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对大自然的探索找到用来代表“日”“月”“山”“水”“鱼”“木”等的符号,这些符号很容易让学生联想到字义。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会逐渐接触到笔画多、字形复杂的合体字(会意字一般多为合体字)。例如“从”字,是两人前后相随;“比”字是两人并列而立;“休”字是一人依木而憩。此类字根据字形就能判断出事物间的联系,即“以形会意”,是会意字造字法的一种。会意字的另外一种造字法是“以义会意”,如“光”“ 妇”“大”“炙”“孬”等。教授这类字时,可联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常识,从汉字的字形特征入手,加以分析。例如“炙”字,上部是“肉”,下部是“火”,形容将肉放在火上烤。这种有意识的汉字记忆方式,不仅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而且能让学生了解,是中国人擅长的形象思维创造了神奇的汉字。这与英语等拼音文字创造者的逻辑思维是不同的。
(三)结合偏旁部首讲解中国文化
“偏旁”是汉字构成的基本单位。偏旁中表示意义的部分称为“形旁”。基于汉字形旁具有表意功能的特点,在讲授汉字时,可以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对汉字偏旁部首加以归类分析。通过对偏旁的分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字义和字形。例如“材”字,左边是形旁“木”,凡是有这个偏旁的汉字大多与“木”有关,如“杆、杖、松、梅”等。其中“森林”或者木制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最典型、最易记的是以“木”为主的“森”“林”二字。古代认为女子貌美便是“好”。“女”是“好”的形旁,凡是以“女”为偏旁的汉字大多与“女子”有关,如“妇、妆、婚、媳”等。在线新华字典②见 http://xh.5156edu.com/html/323.html。上,以“女”为部首的汉字就有477个。古代有如此多与“女”意义相关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母系氏族”曾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汉字是表意系统的文字,但是形声字却占90%左右。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从发音上找到字间联系。例如,“朱”和“中”都是基础汉字,因此在教授新字“珠”“株”“蛛”“洙”“钟”“忠”“盅”“衷”等时,可以引导学生建立字音联系。
从偏旁部首入手进行汉字教学,介绍相关偏旁部首的历史背景,不仅能够让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望字生义”,学会根据偏旁部首识别汉字,起到举一反三的识字效果,还能让学生了解偏旁部首背后的中国文化。
(四)利用代表性繁体字,揭示字形蕴含的丰富文化
汉字产生于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其构成及发展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和探索客观世界及其自身思维的成果和心智轨迹。在中国历史上,从上古到西汉,官方的规范字体与现代的繁体字字体有显著差异。直到出现东汉盛行的隶书,才与现代繁体字的字形较为接近。繁体字流传数千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果能在汉字教学中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繁体字,对应现行的简化字来讲授,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苏州作为蜚声中外的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一直为许多外国朋友熟知和向往。苏州的“苏”字,繁体字写做“蘇”,由草、鱼、禾三个偏旁组成,原义是一种名为“紫苏”的草,象征鱼米之乡。苏州自古水网密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曾有诗句曰:“近炊香稻识红莲”(《别墅怀归》)“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送人游吴》)。
又如种子的“种”字,繁体字写做“種”。《玉篇》:“种,稚也。”从禾,中(重)声。“禾”指谷子,“重”意为“份量大”,“禾”与“重”联合起来表示“根部带土块的谷物秧苗”“待抛或待栽的秧苗”。种庄稼时,选种子一定要选大个儿、饱满、有重量的,由此产生“禾”“重”这两个字的组合。简化以后写成“禾”“中”,不仅失去原义,也是对这种优选法的遗忘。
汉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了独特的构形和表意功能系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文献典籍多以繁体字记载,和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繁体字的构形生动有趣,许多字体更贴近象形文字的本来意义,更便于学生对汉字字形和字义进行理解和记忆。所以在汉字教学中,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繁体字进行辅助教学十分必要。
(五)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千百年来,汉字和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彼此依托。因此要由此及彼,并举一反三地引出与汉字相关的文化典故,才能更好地向汉语学习者展现汉字和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使汉字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桥梁和纽带。
例如“纸”字。《说文》:“纸,絮一苫也。从糸,氏声。”教学中可引导学生联想制作纸张的过程——蔡伦的“造纸术”。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一系列工艺革新,改进了造纸术。蔡伦所造的纸,是现代纸张的起源。这种纸,因为原料易得,价格便宜,质量尚可,逐渐被普遍使用。为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又把这种纸叫作“蔡侯纸”。在教学中以“蔡侯纸”为切入点,引入具有浓烈中国元素的“笔”“墨”“纸”“砚”等书写工具,有助于学生学习与其相关的“毛笔”“黑墨”“宣纸”和“砚台”等文字和词组。讲授“毛笔”“黑墨”“宣纸”和“砚台”(即“文房四宝”)③“文房四宝”之说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虽然在历史上,“文房四宝”的所指屡有变化,但是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特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和歙砚。,还可延展出其与中国书法的关系。
在中国,“纸”并不是最早的书写材料。上古时代,人们依靠结绳记事。到殷商时期,出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就是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后来出现竹片和缣帛,替代甲骨成为书写材料。但缣帛太昂贵,竹片又太笨重,于是推动了纸张的产生。由一组关于纸张产生历史的故事,既引出了“甲骨文”和“竹简”历史的讲解,又涉及了“甲骨文”“竹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等充盈着浓重中国文化色彩的字词。可见,在文化故事里,这些枯燥、难懂、难记的字词被赋予了生命和色彩,立体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实现入耳过目、入脑入心的教学目的。这样的授课方式生动有趣,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能由此及彼,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贯穿于汉字教学中。当然,这样的授课方式也给对外汉语教师增加了压力。如何做到既将目标汉字向学生讲授清楚,又兼顾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并且衔接得当,是对授课教师的考验。
三、结语
汉字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浓缩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只是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迈出的“一小步”,要不断地探索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向汉语学习者展示、传递中国文化的内涵,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汉字难认、难写、难记、难懂等困难,使其真正学好汉语,成为汉语言文化传播的使者。
[1]毕彦华.浅谈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文化渗透[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
[2]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4]蔡振为.利用繁体字辅助汉字教学的尝试[J].基础教育,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