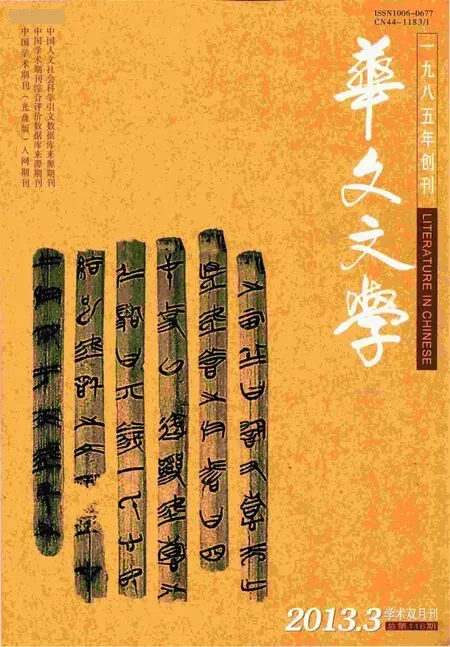打破新天:当代中国诗歌的英译①
[澳大利亚]欧阳昱
引子
2007年,我在堪培拉国立大学当住校作家期间,曾去堪培拉附近的深山老林间,拜访过一位隐居山林的澳大利亚青年诗人。此前,我们曾通话数次,他还为我的英文诗集《异物》(Foreign Matter)写过一篇书评。可能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堪培拉虽然市内一马平川,但一出城,就峰峦叠起、丛林茂密。我独自驱车两个小时,在山道上东拐西转,进入了云深不知处的境界,跑了不少弯路,通过几次电话,才找到他的住地。那个地方,用比他大十岁的女友的话来形容,是“放眼望去,方圆几十里不见一个人影。”习惯了中国稠密人烟生活的人,住在这种地方,可能未几就会发疯,但对于这个放着职业医生不当,独挑远离尘嚣,一味写诗的活法的诗人和女友来说,这可是金不换的人间仙境。可不,出门有四轮驱动的越野跑车,家里电视、电脑、电冰箱等各种电器设备一应俱全,随时可以上网,与全球沟通,还每天收到长期订阅的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自己种菜自己吃,自己制作肥皂自己用,自己接天上的雨水自己洗濯,唯一不需要见到的就是人,不似王维,胜似王维。太阳落山前,蒂姆,我的诗人朋友,抓起一把鸟食,撒在房前屋后,立时“哗啦啦”地飞来一群“嘎啦”(galah)(粉红凤头鹦鹉)。他一边喂食,一边对我解释说:“They aremyfriends”(它们都是我的朋友)。面对此情此景,我胸中升腾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
晚饭后,在他自己亲手盖起的形如庙宇的家中,我听他弹吉他,他听我朗诵诗,最后谈起了他喜欢的唐诗。他不仅把他搜集的几本英译的唐诗选集拿给我看,还告诉我说,平生最喜欢中国古诗。他的这种喜爱,让我想起接触到的几个澳大利亚诗人,对中国古诗都是一往情深,甘之如饴,不仅诵读不止,而且模仿有加,于是便告诉他,其实中国当代诗歌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毕竟一个古老的文化,从古至今是有着连续性的,而且有着新的变化。
最近,他来电告诉我,他已经买了数本当代中国诗歌选,觉得“很有意思”。③我也为他的这个新变化而感到高兴。
“为中国诗歌带来好消息的人”
最近,我译了一位来自中国,生于2002年的幼年女诗人(仅11岁)的一组诗,与其他当代中国诗人的诗混杂在一起,并未对她的年龄作任何解释,投稿给一家澳大利亚出版社,很快通过出版社审稿,决定出版,经过几次筛选之后,该诗人的诗有五首入选,除一位60后诗人的诗(她被选10首),她入选的诗占第二位。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推荐她诗的诗人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来自为中国诗歌带来好消息的人。”
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刺耳,仿佛我在自我赞美,自我欣赏,自我吹牛,就像这个非常自我的年代中,某些诗人特别喜好做的那样。但是,我想要说的是,除开别的不说,我的确是“为中国诗歌带来好消息的人”,因为每有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的诗经我翻译,在澳洲、在新西兰、在加拿大、在美国、在英国发表后,我就要一一寻找其通联方式,一一寄去样刊和稿费。不是“好消息”又是什么?!我好像还很少看到从瑞典文、希腊文、意大利文给我带来如此好消息的人。④如果有,我当然会喜不自胜,我当然会至少说声“谢谢!”惜乎当代中国,人们(包括诗人、包括学英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早已不会说谢谢了。⑤我本天真地以为,默默无闻地为陌生人做了好事,至少可以交个朋友,但事与愿违,译了诗歌,不仅成不了朋友,倒好像被自动划入了理所当然的“翻役”行列,成了自唾其面、自取其辱的“仆译”、“役者”。我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专译古诗,于2012年在澳门出版《二词其美:中国古诗英译集》,究其所以然,不过是因为当年翻译当代中国诗歌,遇到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说谢谢也不会说谢谢的中国人,让我一气之下,决定再也不译其诗了。
值此我的第三本英译当代诗歌集即将出版之际,我这个“为中国诗歌带来好消息的人”,正处于即将偃旗息鼓的阶段,不再准备带来任何好消息,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坏消息,很可能就此罢手罢休罢译,写我自己的诗、译我自己的诗,或只译不需要说谢谢的古人诗了。
缘起
1994年,也就是我的英文博士论文已经交稿,正待审稿结果的那一年的下半年,我在墨尔本与其他两位朋友丁晓琦和孙浩良合作,创办了《原乡》(Otherland)文学杂志,出版了第一期。办到第二期时,他们自动退出,我一人独办,这时,来自中国的稿件颇多,记忆中,来得最多的是一个名叫伊沙的人,既有小说,也有诗歌,我很喜欢,几乎期期选发。他的诗歌当时独树一帜,比较另类,凸显出一种与当代大陆诗歌迥异不同的诗风,也颇与我的诗风切近。这是我选发乃至选译的初衷。从他的投稿中,我慢慢开始了翻译。以我的直觉,他的诗,在澳大利亚这个涉“华”不深,依然沉浸在中国古诗状态的国家中,是能独当一面,开出一条新路来的。果不其然,1995年末,我给当时发稿最难,也最挑剔的一家澳洲文学杂志《烫》(Heat)投稿后,很快就有四首被选中发表(1996年),即《中国朋客》、《美国》、《蓝图》和《野史》,同时配有自己写的一篇英文序文。⑦值得指出的是,该杂志主编艾佛·印迪克(Ivor Indyk)本是悉尼大学英文系文学杂志《南风》(Southerly)副主编,因与主编向有龃龉,一气之下卸掉该职,自己拉起一杆旗,创办了《烫》杂志,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名声最响的招牌杂志之一。杂志初创期间,他是带着一股气的。我刚到澳洲不久,由于在这个白人国家亲身经历了很多歧视现象,诗歌中也是带着一股气的,故有人称我为“the angry Chinese poet”(愤怒的中国诗人)。伊沙的诗歌,在当时的中国很受排挤,也是带着一股气的。⑨正是这种气和气势,给澳洲诗坛注入了一种新鲜的力量。
随后,我翻译的伊沙诗歌连连得手,又在其他一些大杂志上频频发表,1997年共发七首,如新南威尔士文学杂志Ulittara 上发的《叛国者》和《我要的读者》,塔斯马尼亚文学杂志《岛》(Island)上发的《最后一个长安人》,汤斯维尔的文学杂志LiNQ 上发的《愤怒的收尸人》和西澳文学杂志《西风》(Westerly)上发的《英雄复活》、《车过黄河》和《假肢工厂》。由于我翻译的伊沙诗歌频发,我本人截至1997年已出版一部英文诗集,并在澳大利亚多家英文杂志发表了74首英文诗,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ABC的诗歌节目Poetica专门给我做了一个诗歌节目,其中并让我朗诵了伊沙的《车过黄河》,以及我翻译的两位澳洲华人诗人张又公和施小军的诗(包括我译三位的英文诗)。
其后,又于1998年在各刊连发7首,这在第一个中国诗人的澳洲发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五首发在英国杂志《议事日程杂志》(Agenda Magazine)上,还包括他一首最实验的诗歌《老狐狸》,里面没有一字,而是让人用显影液来显现老狐狸的真相。我之所以选中该诗,也因为我本人一直走的是先锋诗歌和实验诗歌的道路。请注意,我从一开始翻译诗歌,就没有把重点放在任何官方诗人或名声叫响的诗人身上,除了极少数之外,我对此类诗人从来都不感兴趣。不看,更不译,就是看了也不译。
我对诗歌的口味,并不仅限于伊沙一种。人在海外,对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口语诗和知识分子诗歌之争,也只是远观,而无近趣。我既喜欢伊沙那种野性勃发的诗,也喜欢欧阳江河那种智性洋溢的文字。更由于我长期浸泡在汉英之间,所以特别喜欢他在《汉英之间》那首诗中表现的张力和智慧,因此翻译了他两首,另一首是《手枪》,都于1997年发表在布里斯班的文学杂志《成虫》(Imago)上。
由此,我的英译汉诗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翻译发表的诗人有于坚(1999,2000),王家新(1999),张子选(澳洲1999,英国2001),杨春光(1999),余怒(2000),中岛(2000),张曙光(英国,2001),杨邪(澳洲2001,美国2002),于奎潮(2001),西渡(美国,2002),杨键(美国、加拿大,2002),侯 马(英 国,2002),海 上(2002),代 薇(2002),沈浩波(加拿大,2002),黎明鹏(美国,2002),马非(美国,2002),小安(美国,2002),阿坚(美国,爱尔兰,2002),凌越(美国,2002),车前子(爱尔兰,2002),牛汉(英国,2003)等。这些人中,后来还有几个发表在加拿大或美国,如黎明鹏和代薇。

古诗英译
从小我就喜欢古诗,父亲是我古诗的第一引路人。有时会在病中床头一首首地背诵给我听,也要求我一首首背诵。因此血管中流动着古诗的血液,早年开始写诗时,也是从古诗入手。还照此办理,在儿子小的时候,也要求他大量背诵,结果收效甚微,因为他最后生活在了一个英语国家,而且从事的不是文学。

与译当代诗歌相比,翻译古诗不存在说谢谢的问题。自己喜欢的,自己拿来就译。不用与他人合作(吾之性格,从来不与人合作翻译,永远是“地马行地”,独来独往,除了为提携学生合作翻译之外),自己译了自己算,拿到国际文学市场去闯荡一番,既测验了自己的能力,还赚得了不菲的稿费,且不用与前人共享。先人的财富,在自己笔下、键下,通过另一种语言而焕发了青春,用一句英谚来说,是“they would have turned in their graves”(他们如若有知,早就含笑九泉了),真乃赏心悦目,大快人心之事。我一向不喜奢谈光耀中国文化之类的大话废话蠢话,能做自己喜欢做又能做得好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必须的。这项工作,终于2012年在澳门出版《二词其美:中国古诗英译集》一书,而暂时划上了一个令自我满意的句号。
选诗和译诗
2005年后,我开始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翻译学院讲授中英诗歌翻译,一课英译汉,一课汉译英,交相辉映,往复其间。我的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属于80后,越往后越小,渐至90后,都是一些几乎一年看不了几本书,而且从不读诗,被我称之为“新野人”的人,正如我在《关键词中国》(台湾2013年即出)中所说的那样:
在三次诗歌翻译课之后,我的脑中终于产生了一个新词:新野人。

话虽这么说,但我也发现,这些“新野人”并不是没有思想、没有趣味、没有品味的。他们对古诗一致高度赞扬,对现代诗比较欣赏,对当代诗则毁誉参半,尤其是对离他们最近的80后诗人的诗,更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有鉴于此,我在每课之前,总是把入选待译的诗歌,抹去作者姓名,发给他们阅读并让他们选出最喜欢的诗来,作为翻译的对象。现以2011年7月5日的一堂课为例,看看他们是如何选材的。
这次选了7首诗,分别为多多的《在英格兰》,李笠的《旅行》,张枣的《镜中》,北岛的《乡音》,雪迪的《7年》,欧阳昱的《假人自述》,张耳的《山西情歌》和王屏的《你还在生气什么?》。由于拿掉了姓名,便移除了因姓名而可能带来的名人效应,包括老师效应(我必须说,有时候即使把我自己的姓名显露,也有学生不选的情况,我喜欢这种诚实,这是这个时代“新野人”的可爱之处)。

选诗的平民化
诗歌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它的兼具贵族及平民性。一首高贵得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写的诗,写成之后却能广为平民传颂,打动遥远到天边的陌生人,这就是它的最大特征。任何为了得奖,或为了得到学术界欣赏而有意把诗写得晦涩难懂的企图,都是与这个宗旨相违背的。这种贵族性并不表现在诗人在小传中把自己所得的各种头衔和奖项堆积起来,向世人昭示炫耀,而是直接通过诗歌语言本身,打动每一个并不认识诗人的人,像那些千年前的古人,打动跟他们毫无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一样。一个诗人就是一只不为任何人歌唱,也不为得任何奖而歌唱的鸟。你喜欢那是你的事,却并不是它歌唱的主要原因,甚至不是它要歌唱的根本原因。
正因如此,我在挑诗翻译的过程中,对文学造山运动不感兴趣,一向掠过名家,就像“非诚勿扰”节目中那样,直奔心动女生——对不起,我是说心动诗歌——而去,有名无名完全不是我的考量因素。实际上,那些有名者常常被我有意疏忽,他们自有关心他们的译者为他们建功立业,用不着我为他们劳神费力。
必须指出,我是一个每日读诗写诗的双语写诗者和读诗者。这没有任何骄傲的地方,这只是一个事实。这使我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大量诗歌,每每看到出自不知名诗人的好诗,常有一种听到好鸟鸣啭而不知其名的惊喜之感,就会马上复印,发给学生共享。我上翻译课有一个与人不同的做法,会当着学生的面,通过投影仪打在墙上,在电脑上进行现场翻译,逐字逐句讲解每个字词(包括标点符号),从中文进入英文的过程,完毕之后还让学生当场指出问题,不避错误(因为难免),也不避译不出的困难(因为难免),其要义就是通过现场翻译,展示一个译者的翻译全貌,通过这种方式,与学生达到真正的教学沟通,而采用此法翻译的诗歌,随后便进入投稿过程,如我原本不认识的一个诗人伍小华的诗,就是这样进入澳洲的,其全文如下:
一大片野花就围了过来
从故乡往西行,走着走着就有
一大片野花围了过来
带上它们的芬芳 带上
那些幽深莫测的念头。它们都
手提一小串露珠,和
一颗大大的心跳……
它们拦在路上。它们中的有几株
还被故乡吹来的风,刮得
侧过了脸去。那一刻
我才真正看见了乡村的羞涩。但我
怎样才能绕开它们,轻轻
拨出一条小路,但我不想用城市的皮鞋
伤着任何一株野花
我也不想被任意一株野花绊倒
但是,我的那颗刚刚濯净的心
还是在某一个微小的细节处
踉跄了几下……



一眨眼
已经二十五六
于是瞪大双眼不闭
直到深夜
眼泪兮兮
怕是再一眨
就老了
再一眨
就该死了
五岛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诗集中,就收入了这首诗。
选诗的澳大利亚化


我在读诗过程中,读到一首短诗,至为喜欢。诗人名不见经传,倒省去了替学生抹掉名字的麻烦,反正谁都不知道他是谁,直接读诗即可。其诗全文如下:
死亡像羞涩的门框
死亡像羞涩的门框
母亲只是多扶了它一会儿
它就矮下去、小下去
直到变成一个相框——
紧紧扶住了母亲



我选译的一首诗如下:

我问你爱我吗
你说
插入的时候
爱
拔出来的时候
不爱


何谓写诗写得好?一字尽言:真,所谓诗言真也。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写的诗,玩弄辞藻的居多,说真话的居少。不着边际的居多,以诚相见的居少。废话连天的居多,一语中的的居少。
我喜欢奥维德,原因之一是他真。比如,他坦诚他爱写淫诗:
我的《艺术》一书,是为妓女写的,它在第一页上,就警告说:生而自由的淑女,看见该书要当场丢掉。
然而,用该书大写淫诗秽句,却实在不算犯罪。
贞洁者可读到,很多不让读的东西。
……
但是,有人老问:干吗我的缪斯,老是荒淫无度,为什么我的书,老是鼓励人人都去做爱?
一个诗人不写淫诗,他还能算诗人吗?顶多只能算一个割了鸡巴的诗人。多么伟大而贞洁的诗人啊,我只能这么赞道。去死吧,一生一死都萎大的人!


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舔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俺怎肯把你的恩情负。欲要搂抱你。只为人眼多。我看我的乖亲也。乖亲又看着我。

不过,在澳大利亚这个向来具有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国家,对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文学(包括)诗歌,从来都采取一种排斥和抵制的态度。就在五岛出版社接受该诗集之前,我曾将其中一些已被收编的诗歌,投给一家大杂志,不仅被悉数退稿,而且,该刊一位知名不具的诗歌编辑,在我并没有问其原因的情况下,竟然颇带侮辱性地来信说:“all were terrible”(所有的诗都很糟糕)。好在澳大利亚这个诗歌空间,并不是他一人能够一手遮天的。
这本诗集入选的最年幼诗人是小女诗人乐宣。她的诗经诗人杨邪推荐,又经我再筛选之后,共有5首入选。据凯文说,她的诗非常“evocative”(引人共鸣)。仅亮一首如下:
孤独的马厩
马厩没有一匹马
马儿们都出去吃草了只剩下孤独的马厩
和马儿丢掉的干草
又简单,又简练,又隽永。读得我直摇头,是的,摇头,那是惊叹的表现。读了这样的诗,我向杨邪感叹道,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
出版和资助




翻译资助还有另一个方面,即私人资助。可以直言相告,我翻译的绝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是从来没有收取分文的。不仅不收,还要自掏大量邮费,向世界各地投稿,得了稿费,还要耗费时间寻找作者,张罗着把其中一半支付给他或她。如果听不到谢谢,(也的确听不到谢谢),那真是吃力不讨好。事实是,除了少数诗人之外,在大多数诗人那里,翻译从来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也许,此文是我的封译之作。但愿“译”长久,自有送来好消息的后来人。
结语

最后投票结果表明,他们一致选用“Breaking New Sky”(打破新天)作为这本书的标题,与我建议的“Breaking the New Sky”相比,仅仅少了一个定冠词“the”,他们那种深入骨髓的语感,通过少一个“the”字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再一次印证了我的微理论,即英文学到高处和深处,好与不好,全在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的把握上,而这种把握,是一个非母语者几乎难以企及但无论如何也要力图企及的。不过,这是后话,以后有空专章论说。
①因在华搜集资料困难,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黄梵、白鹤林、杨邪、梁余晶和陈颖等人帮助,特此鸣谢。
②顺便提一下,这个报纸的网上版,我在澳洲时经常去看,但回到中国,竟然被封掉了。想“翻墙”也翻不了,因为用在PC电脑上的“翻墙”软件,在我的苹果电脑上没法用。有知道如何“翻墙”者,请来信协助,尽管颇有助纣为“善”之嫌。
③其中有北岛和伊沙的英文译诗。
④多年前,瑞典倒是有一个,带着发表他译我诗的杂志到墨尔本来看我,我还请他和他夫人吃了一餐饭。
⑤这个乱象,以学英文的学生为最,通信来往中,从来不说“thank you”,不懂得最起码的礼貌。意下认为,不能全怪他们。教他们的老师,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⑦参见欧阳昱译伊沙“The Chinese Punk”,“America”,“A Blue Prin”and“Wild History”,with an introduction by Ouyang Yu in Heat(Sydney),No.2,1996,p.133-5.
⑧现已停刊。
⑨2012年年末,我在海南大学讲学,碰到一位来自西安的老师,吃饭喝酒时听他说,在西安曾有一位诗人朋友,如何如何地对什么都特别有气,我已经大致猜到,那人是谁了。讲完后我问他是谁,他说:伊沙。我“哦”了一下。
⑩参见欧阳昱译伊沙“The Traitor”and“The Readers IWant”,Ulittara,No.11,1997,pp.30-1.
⑪参见欧阳昱译伊沙“The Last Nan from Chang’an”,Island(Tasmania),No.70,1997,p.118.
⑫参见欧阳昱译伊沙“The Angry Corpse Collector”,LiNQ,Vol.,24,No.2,1997,p.35.
⑬参见欧阳昱译伊沙“An Hero Resurrected”,“The Train Journey Across the Yellow River”and“The Artificial Limbs Factory”,Westerly,No.2,Winter 1997pp.27-9.
⑭即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Papyrus Press,1995.
⑮有兴趣,并懂英文的读者可到这个网站听这个录音节目:http://www.abc.net.au/radionational/programs/poetica/4607072
⑯参见欧阳昱译伊沙“It’s So Bloody Difficult to Create the New”,Overland,No.151,1998,p.63,“Connecting the Dream”,“Small Cthe Rapist”,“A Tortuous Path Leads to a Secluded Place”,“A Poetical Discovery”and“Bashing up Wang Wei”,with an introduction by Ouyang Yu,Agenda Magazine(London),Vol.35,No.4,No.36,pp.244-247,and“The Old Fox”,Blast,No.37,1998,p.15.
⑰参见欧阳昱译欧阳江河“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and“The Hand Gun”,Imago(Brisbane),Vol.9,No.3,1997,pp.112-5.
⑱该诗集入选的诗人(含海外如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诗人)有阿斐、阿坚、柏桦、车前子、陈大超、代薇、海子、韩东、杜家祁、非亚、海上、何小竹、候马、胡哲、黄金明、黄翔、吉木狼格、贾薇、晶晶白骨精、李红旗、黎明鹏、凌越、陆忆敏、吕约、罗门、鲁若迪基、马非、马世聚、麦城、牛汉、欧阳昱、欧阳江河、秦巴子、盘妙彬、任晓雯、沈浩波、盛兴、石光华、施小军、宋烈毅、宋耀珍、宋晓贤、孙文波、唐欣、田原、王家新、王顺健、王小妮、王晓渔、西渡、小安、徐江、严力、岩鹰、杨键、杨克、杨邪、尹丽川、伊沙、于坚、于奎潮、余怒、臧棣、张洪波、张敏华、章平、张曙光、张又公、张子选、中岛和朱剑。
⑲入选诗人有代薇、杨键、黄金明和盘妙彬,如Dai Wei,“The Wind on the Window”,p.227,Yang Jian,“The Spring”and“Love in Life and Death”,p.203,Huang Jinming,“Sounds of the Earth Coming Back to Life”,p.44,and Pan Miaobin,“Green Grass Trodden by People Coming and Going”,p.227,Kenyon Review,Vol.XXV,No.3/4,2003.
⑳入选诗人有王家新、宋晓贤、非亚和宋耀珍,如“The Traveller”by Wang Jiaxin,“The Soil and the Letter”by Song Xiaoxian,“The Waking of Insects”by Fei Ya,and“Someone with Tooth-ache”by Song Yaozhen,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London),No.21,2003,pp.232-5.










在英格兰
多多
当教堂的尖顶与城市的烟囱沉下地平线后
英格兰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语声还要阴暗
两个盲人手风琴演奏者,垂首走过
没有农夫,便不会有晚祷
没有墓碑,便不会有朗诵者
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
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
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耻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
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
认出我的祖国——母亲
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
旅行
李笠
比黎明醒得早,我,一列在雾中
轰鸣的火车。变形的脸
用车灯同夜作爱的激情摇晃
一道充血的目光打开空荡的车站
鸟声用死囚的母语在窗外涂写
“我要回家!”的啜泣
在钟盘的雪地里爬行,那里
记忆之狼正噬咬着一个迷路的孩子
镜中
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乡音
北岛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7年
雪迪
在碎玻璃的碴上走路。
在不说本土语的城市里居住。
感染的脚,在自己的意志中走。
肉体后面的事物坚持着,让思想
完成。使手停在
黑暗突出的地方。语言
到达我们仍未到达的那些地方。
不断劳动。比一个精确的单词
更孤独。在本地的人群中:
比一种新的语言更坚强。
假人自述
欧阳昱
我姓贾
叫仁
我出生在一个假国家里
从小学会讲假大空话
长大干过很多假活计
在假肢厂制造假肢
在玩具厂制造假枪
在电影电视上拍摄假象
我还特别喜欢用假嗓子
哼唱革命歌曲
我吃过假药
我笑过假笑
我用过假钱
文革中我假死过
如今我摸过假乳
还玩过假阳具
我这一辈子最怕的莫过于
真刀实枪地争权夺利
我一家人都姓贾
上一辈子姓贾
下一辈子还要贾下去
我哥哥叫贾爱国
我妹妹叫贾美丽
我爸爸名字更奇
他叫贾胜利
就连我妈也姓贾
人家都叫她贾妈
我们贾来贾去贾到了一起
如今什么都能造假
假山假牙假面假寐假模假样
连猩猩也是假惺惺的
别说汉语好用假设
日语也要用假名
英语动辙搞虚拟
甚至于某些真理
也仿佛弄假成真
搞得我常常怀疑
我这副肉体
是不是假公济私
生我养我的那个国家
是否本来就是个假冒伪劣商品
山西情歌
张耳
你回来了
我不再出门
遍体抚摸
皮肤的记忆盛过心的叹息
黑鸟还会在我的黑头发中作窝吗,亲亲?
两种抚摸不是一种抚摸
你来了
我重新描画眉毛
镜子落满尘土
伸手去擦
连影象也擦去
我还能找回那对黑眉毛吗,亲亲?
两种表情不是一种表情
你来了
树叶竟全落了
于是在室内种花
没有阳光,草也能长
真是奇迹,亲亲
两种绿不是一种绿
你来了
我开始编故事
并唱给枕头一只只催眠曲
枕头也会闭上眼睛
甜睡不醒,并且做梦
我也能同样安睡吗,亲亲?
两种梦不是一种梦
你回来了
我在门口挂出
“油漆未干”
可这两种漆不是一种漆,亲亲!
你还在生气什么?
王屏
我想我应该感到幸运。
我没在胎儿期被打掉
或一出生就被丢进水缸里。
我没必要折断脚趾缠出三寸金莲
或挤压我的肝与肾以苗条我的腰身
我应该感到幸运
我没被塞到锈迹斑斑的船底,
自以为将前往自由国度,
却只得到被迫跳海的结局,
或蹲进墨西哥的拘留中心
等着被起诉传唤。
真幸运我不用担心被
拷上塑胶手铐遣送出境
头发还被喷成棕色。
真幸运我没被锁在海湾山脉中发霉的地窖,
晚上被强奸白天做工薪水少到不能再少。
是的,我应该感到幸运
我除了爱情与母性之外还有职业
我是个诗人,教师。而且正在修博士学位。
但我就是只讨人厌的野兽
因为我总是想用嘶哑的声音尖叫。
我该如何解释这无名的怒气
使我无法
喘息
每次我朝挂在祠堂墙上的祖先灵位鞠躬时
我就想尖叫。
它记录了王家五十代的男性祖先
但我的女性祖先的名字
却像蝌蚪尾巴一样消失了。
我尖叫,可我发不出声音。
所以我写下这母系的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