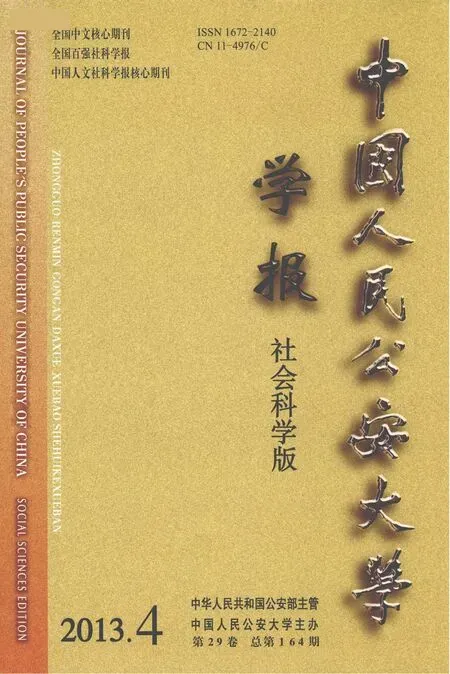伪证罪疑难问题探究
张 苏
(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作伪证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行为,可是,伪证行为被作为犯罪追究的却并不多见,这源于对刑法第305条伪证罪构成要件不适当的缩小解释,导致该罪处罚范围的萎缩。2012年修改的新《刑事诉讼法》已经生效(以下简称2012《刑诉法》),该法对证人制度作了许多修改、增删,涉及伪证罪的传统疑难问题,也引发解释论上的新问题,下文一并加以探讨。
一、污点证人、警察、被害人是否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污点证人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后,与国家追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提供证据,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对于一些隐蔽性强、不易侦查取证的刑事犯罪案件,利用犯罪参与者来证明犯罪,能够做到证据扎实、充分,这是查处和认定犯罪、有效打击犯罪的强有力手段,特别是在查处贿赂犯罪案件中,作用更为突出。按照对证人广义的理解,“证人指的是其陈述由法庭审查并加以评估的任何人”,[1]所以,由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被告人转化而来的污点证人,自然也可以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事实上,“污点证人目前在实践中主要用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贿赂犯罪、洗钱犯罪等案件。据资料显示,广西、云南、重庆等地的毒品案件,约90%使用了线人或耳目来查获、认定犯罪。”[2]但问题是,由于污点证人本人参与了犯罪,其证言会有别于普通证人的证言?本文认为,对于污点证人能否成为伪证罪的主体,需要区别对待,下列三种情形下,污点证人能够成为本罪的主体:(1)如果污点证人是警方派到犯罪集团或黑社会组织内部的卧底,或者是侦查机关的线人或耳目。由于其派到犯罪集团中的目的就是为了搜集犯罪证据,其实施的行为也并不同于一般的犯罪行为,因此,此类污点证人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没有问题,如果污点证人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可以成立伪证罪。(2)犯罪集团或者共同犯罪中,依法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参与人成为污点证人的。例如,犯罪人罪行较轻,或者是未成年人、从犯、胁从犯,或者具有未遂、中止、重大立功、自首和重大立功等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情形,由于其不同于本案所要追究的犯罪人,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成立伪证罪。(3)实施多个罪行,其中一个罪行可以免除处罚而转化成为了污点证人。例如,甲、乙、丙共同实施了贪污、挪用公款、走私普通货物等多项犯罪,其中,丙的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可以不予处罚,则丙就其走私普通货物罪而言,可以转化为认定其他人成立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污点证人,而丙所犯的贪污、挪用公款另外两项犯罪仍然要受到追究。丙如果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为甲、乙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罪隐匿罪证,丙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上述三种情形之外的所谓“污点证人”,由于其身份本质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证人,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我国2012《刑诉法》正式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那么,出庭作证的警察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呢?本文认为,警察出庭作证存在三种不同情形,只有在侦查人员出庭证明侦查过程中所知道的犯罪情况时,警察成为本罪主体;当侦查人员为了说明证据的取证方法而出庭、侦查人员取证方式严重违法涉嫌刑讯逼供而出庭的,侦查人员不是本罪的主体。关于警察出庭作证,2012《刑诉法》规定在第57条、第187条之中,其中,2012《刑诉法》第57条规定了在法庭进行非法证据调查时,有必要通知警察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①参见《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的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对此应细分3种不同情形:第一,侦查人员出庭证明侦查过程中所知道的犯罪情况时,其身份与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类似,如果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属于刑法第305条所称的“记录人做虚假证明”,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第二,案件的侦查人员为了说明证据的取证方法而出庭的,此时不具有证人、记录人身份,不成为本罪的主体;第三,如果侦查人员取证方式严重违法,或者涉嫌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其陈述的内容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其身份不属于证人、记录人,不是本罪的主体。2012《刑诉法》第187条第一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187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应当成为伪证罪的主体。此时,警察自然不是该案件的侦查人员,这是因为,警察如果在执行职务时目击了犯罪情况,就不再适合担任该案件的侦查人员,而应当优先成为案件的证人,因为证人具有身份上的优先性、排他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原理,证人的身份缘于其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在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身份具有不可选择性、不可替代性,既不能由司法机关随意指定证人,证人本人也不能放弃证人身份转而担任其他角色,此时,警察由于具有证人身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没有问题。
关于被害人能否成为本罪主体,笔者观点与通说存在较大差异,认为被害人可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应区分情形,分别对待。第一,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起诉,如果被害人为了放弃对被告人的追究,而为其隐匿罪证的,不存在对司法活动的妨害,没有成立伪证罪的余地;但如果被害人为了陷害他人而作虚假证明的,成立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第二,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公诉案件),被害人为了达成和解而为对方隐匿罪证的,被害人不是伪证罪的主体,否则刑事和解无存在余地。第三,在轻微刑事案件之外的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属于广义的证人,能够成为伪证罪的主体,按照对证人广义的理解,“被害人/告诉人、共犯/共同被告、其他偶然目击犯罪事件之人,均为证人”[3]例如,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犯罪既危害了公共安全,也侵犯了公民个人的人身安全时,如果被害人故意对犯罪事实作虚假陈述,使得案件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使被告人被不起诉、被宣告无罪的,被害人是可以成为伪证罪主体的。
二、伪证行为是否必须要求发生在立案之后
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通常认为,“所谓‘刑事诉讼中’,是指侦查、起诉、审判的整个过程。”[4]伪证行为只有发生在刑事诉讼中,才成立伪证罪,而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始,只有立案后,才认为已经进入了刑事诉讼。换言之,按照法律的文字表述,只有立案之后,行为人作伪证的,才成立伪证罪,如果刑事案件尚未立案,行为人故意作虚假证明的,不成立伪证罪。可是,这只是对《刑法》和《刑诉法》条文进行了字面的理解。法律是由文字写成的,解释刑法不能脱离刑法文字的含义,这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可是,如果根据字面含义得出的解释结论有悖“正义”时,便不能机械地遵循字面含义,而应当根据该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解释构成要件,否则,机械适用法律字面含义,结果反而有违刑法的正义。根据2012《刑诉法》的规定,刑事诉讼分为立案、侦查、预审、起诉、审判几个阶段,但是,对于“刑事诉讼”的理解不能表面化,不能一字不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对诉讼阶段的划分去理解刑法的条文,否则会使得应受处罚的行为逃脱刑法的制裁,使刑罚的功能萎缩。笔者认为,对“刑事诉讼”应当根据刑法第305条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行扩大解释,本文对伪证行为的理解是:作伪证产生的后果,对侦查、司法机关是否追究嫌疑人刑事责任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即为刑法第305条中的伪证行为。
本文认为,伪证行为不以发生在立案之后为前提条件,即使伪证行为发生在立案之前,如果满足了本罪的构成要件,仍然成立伪证罪。理由如下:
首先,立案之前的“审查”属于广义的刑事诉讼范围,具有法律上的根据。1997年《刑法》将刑法第305条中原来规定的“在侦查、审判中”修改为“在刑事诉讼中”,就是为了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此外,根据2012《刑诉法》第11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这里的“审查”是为了查明案件是否符合立案的条件,经过审查,案件如果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便应当立案,反之,便不予立案,很显然,“审查”活动是立案活动不可分割的部分,属于广义的刑事诉讼范围。
其次,将立案前的伪证行为纳入处罚范围,符合体系解释的规则。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成立该罪,也要求行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事实上,对此处的“刑事诉讼过程中”也做了扩大解释,在公司犯罪、涉税犯罪中,往往在立案之前,公司的法律顾问(事后往往成为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就会教唆或者帮助公司销毁、涂改、伪造有关凭证、票据,或者事先“培训”相关财务经手人员,一旦事发后做出“一致的”虚假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种行为当然会认定为犯罪,而不会因为其行为发生在立案之前,就当做无罪处理。
再次,对立案前的伪证行为不处罚,有违刑法的正义。行为人在立案之前作伪证与立案之后作伪证,其结果是,要么使得侦查机关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要么使得检察机关不起诉,或者使得审判机关做出无罪判决,立案前、后的伪证行为具有同质性,在本质上都妨害了国家对犯罪的追究,影响了刑事诉讼的进行,行为侵害了本罪保护的法益,都应作为犯罪处理,不应区别对待。事实上,许多伪证行为发生在立案前,例如,立案前的伤情鉴定、询问证人、贪污贿赂犯罪排查等,都可能出现伪证行为,伪证的结果会导致案件的进展,甚至将侦查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妨害了诉讼的进行,同立案之后的伪证行为一样,同样具有可罚性。
对伪证的存在阶段进行扩大解释,还有实践根据的支撑,无论是公安(安全)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院的自侦案件,还是海关缉私犯罪侦查管辖的案件,并不是有举报就必然立案,因为立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立案关乎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的自由和名誉,关乎国家司法资源的合理运用,必须慎之又慎。无论是涉及国家、社会法益的犯罪,还是涉及人身、财产犯罪的犯罪,立案前的初查都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必经阶段。例如,2011年,黑龙江省郑某清在满文出版物中记载了对某少数民族具有侮辱性的文字,并出版。接到举报后,公安机关十分慎重,首先对该案开展了初查(立案之前),侦查人员找到了满文翻译人员戴某光,请戴某光将该出版物翻译成汉语,但戴某光由于同郑某清系熟人,在翻译时便故意隐瞒了满文中具有侮辱性质的情节,在该证据的错误引导下,公安机关做出了对该案不予立案的决定,使郑某清逃脱了法律的追究,对戴某光的行为应当以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对“刑事诉讼中”做扩大解释,不将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包括到刑事诉讼中,则使得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使刑罚的功能萎缩。
总之,对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应当扩大解释,即使在立案之前作伪证的,只要伪证产生的后果,对侦查、司法机关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即为刑法第305条中的伪证行为。
三、对证人作虚假证明中的“虚假”应如何理解
刑法第305条规定了本罪的构成要件,在刑事诉讼中,行为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成立本罪。问题是,“虚假”应做何种理解,在外国刑法理论中有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对立。“主观说认为,虚伪是指所陈述的事实内容违反了证人的主观记忆(体验),或者说证人所陈述的内容与其记忆中的事实(体验)不相符合。”[5]客观说认为,虚伪是指所陈述的事实内容违反了客观的真实性。”[4]725在主观说与客观说之间,还存在折中说,“折中说认为,违反自己体验的陈述,在行为(作证)时能评价为违反了客观真实时,才成立伪证罪。”[4]726但折中说是建立在客观说基础上的学说,“折中说与客观说似乎没有重大区别。”[6]此外,“可以说主观说是从行为无价值论得出的结论、客观说是从结果无价值论得出的结论。”[7]因此,本文着重探讨主观说与客观说两种对立学说下对“虚假”的不同理解。
本文认为主观说存在如下疑问:首先,主观说根据主观罪过认定社会危害性,容易扩大处罚范围。我国学者常常脱离客观行为与结果,夸大主观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如有学者认为,“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意欲作伪证,其具有罪过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客观上看,行为人所作的虚假陈述的内容如与客观事实不符,行为人的行为当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即使阴差阳错而使其所作的虚假陈述的内容恰好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行为人的行为照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8]这是将伪证罪理解成了抽象危险犯,认为行为人叙述违反记忆的事实,存在着妨害国家审判活动的抽象危险,便不以客观事实作为基础,直接将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画等号,其结果极易产生主观归罪,有违法治原则。其次,主观说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按照主观说,证人应当原封不动地陈述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按照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陈述的,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也不是虚假的;反之,不按照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陈述的,即使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也是虚假的。主观说将客观上已经符合了客观事实的行为认定为作伪证,这不符合事实,但主观说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考虑到了行为的主观可谴责性,与其行为无价值的立场是相一致的。
本文支持客观说,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客观说判断“虚假”的标准更加符合事实。根据客观说,只有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才是虚假的;如果所陈述的内容在客观上与事实相符,便不能认为该行为妨害了司法活动或者具有妨害司法活动的危险。而主观说将在客观真实的描述,仅仅因为违反了证人记忆而认定为“虚假”陈述,使得伪证罪成为了处罚违反宣誓的行为了,可是,我国并没有证人宣誓制度,刑法也并不保护证人宣誓制度。第二,客观说能够合理限制处罚范围。司法实践中定罪通常的逻辑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性,然后判断客观造成的结果,常常用抽象的主观恶性标准,来替代具体的客观判断标准。按照这一逻辑,会得出如下结论:当行为人违反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做出与客观事实相符的陈述时,该陈述也会被认为是虚假的,而这一结论似乎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该行为和结果并不妨害司法活动,因而并不侵害伪证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应成立伪证罪,以主观说作为判断标准可能扩大处罚范围,反之,以客观说为标准可以限制伪证罪的处罚范围。第三,客观说与构成要件对故意的规制机能相一致。具体犯罪的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依赖于构成要件。故意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的认识、容认,即构成要件的内容,就是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因此,构成要件规制了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的陈述,其行为“无害”,不属于刑法中的实行行为,按照构成要件对故意的规制机能,客观上没有有害的行为及其结果,主观上如何能产生对该行为与结果的认识与容认呢?显然不可能产生,客观说与构成要件对故意的规制机能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客观说是在客观主义的立场进行判断的结果,关键是判断陈述的内容在客观上与事实是否相符,根据客观说,即便认为有“恶念”,也因为没有实行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联系主观内容考虑,虚假应是违反证人的记忆与实际体验且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如果违反证人的记忆与实际体验但符合客观事实,就不可能妨害司法活动,不成立伪证罪;如果符合证人的记忆与实际体验但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则行为人没有伪证罪的故意,也不成立伪证罪。按照这一标准,来判断下面的案件:苗某目睹了秦某杀人的过程,得知秦某被抓获归案后,秦某的妻子找到苗某,请求不要指认秦某,苗某允诺。警方请苗某辨认犯罪嫌疑人(同时将外貌与秦某相似的郑某平、云某德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由于苗某辨认错误,将真正的犯罪人秦某指认出来了。根据客观说,只有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才是虚假的,而苗某指出了真正的凶手,与客观事实相符,所以不是虚假陈述,其行为没有妨害司法,不成立伪证罪。如果根据主观说,苗某明知做出的陈述违背了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其陈述具有虚假性,意欲作伪证,主观上具有恶性,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认错人)而未能得逞,苗某成立伪证罪(未遂),其结果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客观的伪证行为和结果,何来伪证的故意,又何来伪证罪的未遂。如果根据客观说,将伪证罪理解为具体危险犯,即使苗某主观上有作伪证的想法,但由于客观上没有作伪证的客观事实,也不能认为苗某有作伪证的故意,其行为不会妨害国家的审判活动,即使有恶的念头,也因为缺乏客观行为与结果不认定为犯罪,充分体现了刑法自由保障的机能。
四、行为人教唆证人为自己作伪证的行为如何定性
行为人教唆他人为案件作伪证,行为人当然成立伪证罪的教唆犯,没有争议,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时,证人成立伪证罪也没有争议。争议问题在于,当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时,行为人是否成立伪证罪的教唆犯?这涉及行为人对自己案件事实作虚假供述时,如何定性。
不得不提及共犯的处罚根据,在共犯的处罚根据上,存在责任共犯说与违法共犯说的区分,责任共犯说认为,由于共犯使正犯者堕落,所以共犯者也应受处罚。不法(违法)共犯论认为,由于共犯者诱使正犯者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因而应受处罚。“现在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不赞成责任共犯论,一般也不赞成不法共犯论。”[9]目前,较有影响的是学说是惹起说(因果共犯论),惹起说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介入正犯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构成要件该当事实)。”[8]237之所以处罚教唆犯,是因为正犯的行为侵犯或者威胁了法益,所以教唆行为具有可罚性。
根据共犯处罚根据的惹起说,为了判断教唆行为是否可罚,首先需要正犯的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行为人教唆证人为自己作伪证是否具有可罚性,需要先判断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做虚假陈述的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行为人自己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作伪证的,是伪证的实行行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的行为,是伪证的教唆行为,实行行为的危害性应当大于教唆行为的危害性,举重以明轻,如果实行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教唆行为一般也不得作为犯罪处理。本文认为,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做虚假陈述的,不成立伪证罪,因而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时,教唆者不构成伪证罪的教唆犯。论证如下: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做虚假陈述的,该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刑法也没有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是因为,犯罪后逃避法律追究是人的自然反映,不能期待犯罪人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被公诉机关追究时,为自己辩护也是犯罪人的本能反应,不能期待行为人在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正是因为如此,刑法才规定了自首、坦白制度,作为对犯罪人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奖励。由于缺乏期待可能性的行为能够阻却有责性,所以,行为人教唆证人为自己作伪证的,不能认定为伪证罪。既然犯罪人为自己做虚假供述和辩解无罪,那么,犯罪人唆使他人为自己作伪证就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是因为,犯罪人自己作伪证是伪证的实行行为,是较严重的行为,其危害性一般应大于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的教唆行为,严重的行为不处罚,较轻的行为自然就更不应当处罚了。
解释论上的问题是,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将伪证罪的教唆犯作为妨害作证罪的正犯处理了,需要考虑体系解释规则对伪证罪构成要件解释的影响。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规定即“教唆行为正犯化”,这是否会影响对刑法第305条伪证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笔者对此持肯定回答。基于此,本文将刑法第305条中“行为人教唆证人为自己作伪证的行为”区分为两种情形加以探讨:(1)行为人教唆证人为自己作伪证,其采用的教唆行为属于以暴力、威胁、贿买指使他人作伪证,或者是同暴力、威胁、贿买指使作伪证的行为方式相当的,其行为应评价为妨害作证罪,以实现刑法条文间解释的协调。(2)如果行为人以暴力、威胁、贿买之外的方式指使他人作伪证,且该方式与暴力、威胁、贿买不具有相当性的,其行为便不宜评价为刑法第307条规定的“指使他人作伪证”,也不能评价为刑法第305条中的伪证罪的教唆犯,而应作为无罪处理。例如,行为人采用嘱托、请求等一般性的方法,请证人为自己作伪证的,不成立伪证罪的教唆犯,也不成立妨害作证罪。
[1]熊秋红.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之反思——以对质权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5).
[2]梁玉霞,杨胜荣.中国刑事诉讼法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142.
[3]林钰雄.刑事程序与人权保障[M].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230.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21.
[5]张明楷.外国刑法刚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25.
[6]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52.
[7]【日】高桥则夫.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M].戴波,李世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2.
[8]吴占英.伪证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J]法学杂志,2006(3).
[9]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