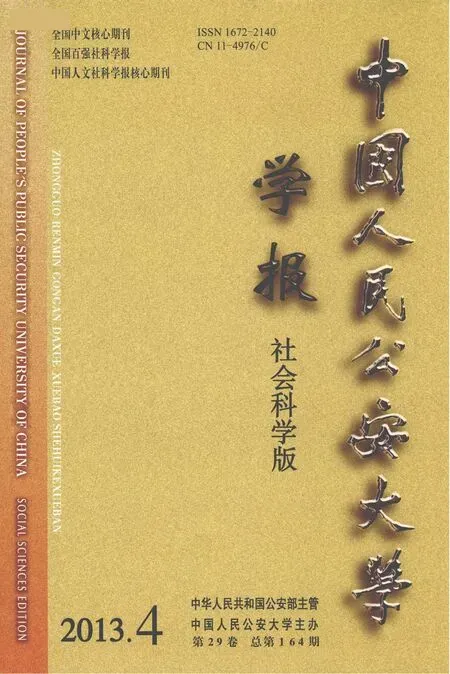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犯罪问题研究
鞠丽华,刘 琪
(山东警察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010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已经是新时期进城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在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不简单是一个年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这一群体不同于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特点。他们与农村的关系逐渐疏远,而在受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对未来的期望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亲近城市的倾向。①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基会《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的调研报告: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然而,亲近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仅是一种倾向或者愿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城市市民,他们的社会认同仍处于模糊化、不确定的状态。而这种社会认同的不确定性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的新特点
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理论,其核心是探讨社会类别化的心理机制,也就是探讨个人如何与一个或多个社会类别、社会群体建立心理联系[1]。社会认同包括四个过程,通过以下四个过程的分析可以了解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的特点。
(一)社会类别化
人类对于各种信息都要进行类别化处理,从而对所处的环境进行组织化和简化,以便更迅速和更好地适应环境。当人们认为某些因素之间的相似性较大,而另一些因素之间的相似性也较大的时候,就倾向于将这些因素作为两个类别分开,并趋向于夸大类别内的相似性和类别间的差异。这一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加重效应”(accentuation effect)。在社会生活中这一现象也存在,当某一类别的社会成员特征凸显时,人们会主动地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同一类别中个体的差异最小化。
从最基本的身份类别来讲,摆在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面前的身份类别有三大类,即农民、市民、边缘人(农民工)。他们在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认定时可从上述三项中作出选择(即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农民、可能认为自己是城市市民、可能认为自己既非农民又非市民)。尽管有学者指出代表边缘状态的“农民工”①本文中使用的是“进城务工人员”。一词带有歧视意义,建议停止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大背景下,不管是不是使用这一概念,人数达到2亿的“农民工”群体及与其伴生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我们当前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社会身份认同定位
在对群体类别进行划分的同时,个体也把有关自己的信息与这一划分相联系,因此形成对自己归属某一社会类别的定位。这一过程就是将自我与社会类别建立归属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认同的过程。不仅如此,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社会身份认同定位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即群体内偏向和群体外歧视。由社会认同所引起的给内群体成员较多的资源及正面评价的倾向,被称之为内群体偏向;相反,由认同缺乏而引起的给外群体成员较少的资源及负面评价的倾向,被称之为外群体歧视。②S.Otten,A.Mummendey.To Our Benefitor at Your Expense-Justice Considerations in Intergroup Alloca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ources[J].Social Justice Research,1999(12):19-38.转引自周晓红.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J].社会科学,2008(4):46-53.
在社会身份认同定位过程中,传统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数几乎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农民,而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则不同。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2]。虽然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他们也有强烈的倾向城市的愿望,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大多也不认为自己是城市市民,实际上他们的确也不是市民,农村户籍让他们无法享受市民待遇。来自西安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约11%的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是城市市民[3]。他们中的多数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打工者”或者“农民工”,这一比例能够占到34.5%,是传统进城务工人员的2倍多,还有约10%的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表示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2]。这些数据表明他们的社会认同处于双重性、边缘化和模糊化的状态。
这种社会认同的双重性和边缘化状态带来的结果是,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缺乏城市归属感。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是却经常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里。不仅如此,由于外群体歧视的作用,特别是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的歧视,他们时常感觉到城市人对他们的排斥。一项调查显示:近17%的进城务工人员经常或总是觉得“城市人(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而上海市这一数字达28%。尽管他们感到自己不属于城市人,也经常受到城市人的排斥,但是65%以上的务工人员表示,自己从来不觉得“在城市里打工低人一等”[4]。
(三)社会比较
将对应类别之间的各种社会信息进行比较就是社会比较。比较社会群体,特别是我群体和他群体,会更加明确构成“我们”群体中的成员具有的相似性,以及“他们”群体中的成员与“我们”形成的区别性。社会比较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我群体比他群体优越,即积极区分,这会满足群体成员的自尊和自我激励的需要;一种是我群体不如他群体优越,群体成员的自尊就会遭受威胁,群体间的偏见、敌意甚至冲突就会产生。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比较过程中,特别是在与打工所在城市市民比较过程中基本上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他们在城市干着脏、累、差的工作,工资待遇却远比不上城市市民;即使有些希望通过努力追求更好工作的进城务工人员,也由于主客观原因受到市场排挤甚至歧视而无法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就业机会;更有甚者给他们贴上“农民工”的标签。①农民工常常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素质低甚至脏乱差的群体。
(四)心理独特性
社会认同过程的结果是个体获得作为内群体成员、社会类别身份及社会角色导致的个体的独特性和与外群体成员的区隔性,成为个体重要的自我表征。同时,社会认同过程为个体带来共享的心理空间、认知表征、价值和社会规范。
如前所述,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并没有获得稳定的社会认同,因此他们并没有形成属于他们群体的一致的心理特性。即使是在同一城市、同一行业甚至是同一公司打工的务工人员,他们之间的联系、交流、共同利益诉求的表达也是相对较少的,也可以说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社会空间让他们进行开放性的表达和交流。然而与社会表达空间缺失相伴生的是小群体的大量形成和存在。这些小群体大都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如很多公司中存在的形式多样的同乡会、老乡会等。在这样一些小群体中他们归属和获得认同的需要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却是一种相对狭隘的认同。
综上所述,社会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社会比较的劣势以及社会认同中小群体的存在构成了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过程的主要特点。
二、社会认同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犯罪
心理是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犯罪与其来到城市之后心理的变化相关,特别是与其城市生活中遇到的社会认同问题密切相关。
(一)强烈愿望与残酷现实间对比形成的心理落差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有强烈的留在城市的愿望,这是他们与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相比十分明显的一个特点。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打工之后大多都会回农村置业、养老,而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则希望能在城市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中有55.9%的人,打定主意将来在“打工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也不再单纯是为了赚钱,而很大程度上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5]。
可以说,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是满怀着希望来到城市的,然而来到城市之后的现实情况却不如他们想象中的美好。他们一方面向往过城市青年一样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的欠缺,他们在城市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这一对比使得他们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落差。再加上年龄因素的影响,他们大多处于十几、二十几岁的年龄段,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抗挫折能力低,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困难重重的生活境遇,在享乐心理和攀比心理的作用下,在城市生活中很容易迷失自己,走上犯罪道路。
(二)社会认同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城市归属感缺失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认同处于双重性和边缘化的状态,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但是又没有获得城市市民的身份认同。虽然他们的生活空间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背景下,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自身和城市居民都不把他们看成城市市民。这导致了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的地理空间和心理归属的割裂,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却并不认为城市是他们的家。这种城市归属感的缺失直接来源于社会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
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缺乏归属感的心理状态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进城虽然完成了空间移居城市的转变,但是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处事方式等方面还或多或少与城市市民不同。再加上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较容易受到排斥,因此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不认同他们,他们自然就不以城市为家、不真正热爱和维护他们所生存的城市。不仅如此,在他们远离农村之后,原来束缚自己的乡村熟人文化、道德观念,到了城市后荡然无存。他们收入低下,不被城市认同,还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后,由于缺乏约束,一些人就容易产生犯罪的冲动或倾向[6]。这也是一些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遵纪守法,到了城市反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三)社会比较的劣势形成的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甚至导致人们诉诸犯罪的手段获取自己认为应得的财富。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向往城市生活,进城之后自然会和城市市民特别是同龄人相比较。显然,他们在比较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他们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工资待遇上却远远低于城市市民,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城市市民的歧视,被认为是“下等外来公民”。这种社会比较过程中的劣势必然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不平衡感,他们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自己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这种相对剥夺感会使他们产生情绪上的愤懑与不平,这种消极情绪如果不能及时正确地化解而长期积累,就会对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仇视的心态[7]。为了解决城市打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不惜采取铤而走险或者聚众闹事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财富和权利,从而促使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以至影响社会稳定。
(四)小群体中拉帮结派导致的不满情绪的放大
人都有归属的需要,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缺失相伴随的是他们中大量小群体的存在。各种同乡会、老乡会甚至帮派是这些小群体的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小群体中,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并借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在满足一定程度归属需要的同时,这些小群体的存在也会成为违法犯罪滋生的土壤。首先是小群体的狭隘性。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大都是以地缘、乡缘、血缘为规律分布的,即使是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同乡会。如果进城务工人员发现没有自己的同乡会,他的生存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被排挤或寻求不到照应,而内部的一些纠纷正是同乡会将其扩大的[4]。其次是小群体中不满情绪的放大。Smith等人的研究发现群体成员的集体剥夺感在他们对群体表现明显的认同时更为敏锐。①Smith H J,Spears R,Oyen M.‘People like us’: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deprition and.group membership salience on justice evaluations[J].Journal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4,30:277-299.转引自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3):475-480.如前所述,本身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市民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就存在相对剥夺感,在同乡会等一些小群体中,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会被夸大而变得更为强烈,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单纯的进城务工人员讨薪等事件在亲属、老乡的参与下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原因。再次是小群体中的胁迫、唆使和拉拢。调查表明,以宗族、地缘为纽带的进城务工人员犯罪团伙特别普遍,而且成员大都是“80、90后”的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对生活的追求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如果周围有违法犯罪的人员或犯罪组织的拉拢,特别是同乡的拉拢,他们选择犯罪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进城务工人员以地缘、乡缘、血缘相结合实施犯罪,或者某类犯罪、某个一定区域的犯罪以老乡为主,这是一种普遍的规律[6]。
三、市民化过程中准确的社会认同定位——预防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犯罪的根本方法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犯罪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他们的市民化过程。当然,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市民化,而应是在制度、权利保障基础上包括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在内的心理上的真正市民化。
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的构建是“以利益为基点,以文化为纽带,以组织为归属”[8]的。从构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的角度达到预防这一群体犯罪的目的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权利保障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建构
从本质上来讲,社会认同是一种利益共享。权利保障的不到位是制约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的根本原因。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劳动就业、福利待遇、教育培训、子女入学等问题上的权益保障还存在缺失或者明显不足。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权利诉求上已经远比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更为主动和强烈。他们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2]。这种强烈需求和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要想得到解决就必须要尊重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利益诉求,重视他们的呼声,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他们享有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
(二)城市文化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建构
文化包含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习俗,以及成为社会成员而习得的能力和习惯[9]。文化决定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因而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生存空间转变后,还面临着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由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年龄特征,他们在接受城市文化上比老一代要容易,然而也有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在转化过程中迷失自己。在城市打工,乡村的熟人社会和道德约束不复存在,而陌生的城市中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城市生活习惯[10]。这一改变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茫乃至失去约束。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加强对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人文关怀,使其尽快适应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如,组织适合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特点的文体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展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引导城市居民与务工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让城市居民真正认识和了解务工人员的内心世界等。
(三)组织归属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认同建构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人们通过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是人际信任的基础,而人际信任又是社会认同的基础和初级形式。因而组织在社会认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极其重要。
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打工的组织归属是明显不足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在城市打工面临困境时,既不愿回归农村又很少求助于打工地政府和其他正规组织,社会也没有专门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援助和支持的民间团体和机构。这一现实情况迫使他们只能求助于亲属或者老乡。而如果这一非正式渠道也无法解决问题的话,很多人就会选择铤而走险。
就目前而言,进城务工人员组织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现有的工会组织体系,把他们整合到工会中去;二是成立各种各样的自组织或群体[11]。鉴于进城务工人员自组织或群体作用的局限性,为了使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形成稳定、一致的社会认同,目前应着力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创新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同时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使得工会组织真正能够起到务工人员权益聚合、表达和维护的作用。
只有从上述三个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市民化,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身份上才能形成准确定位而获得城市归属感,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才会感受到公平公正而减弱相对剥夺感,在社会认同上才能打破狭隘的“三缘”划分而减少拉帮结派现象,从而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减少这一群体犯罪的目的。
[1]Tafel H,Turner 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M]//Worchel S,Austin W(eds).Psychology of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 Nelson Hall,1986:7-24.
[2]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6-21.
[3]郭科,陈倩.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状况的实证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49.
[4]安卓,王羚.“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我们渴望身份认同[N].第一财经日报,2011-06-23.
[5]刘俊彦,吕鹏.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R].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题研究报告”2007年第9 号,2007-06.
[6]歧视,让他们成为陌生人——访《中国法治蓝皮书》“农民工犯罪问题”撰写人靳高风教授[N].南方周末,2011-07-07.
[7]陆时莉.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心理分析及预防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11(7):277-278.
[8]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9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
[9]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
[10]吴玉军,宁克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J].浙江社会科学,2007(4):132.
[11]陈建胜,刘志军.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J].人文杂志,2010(5):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