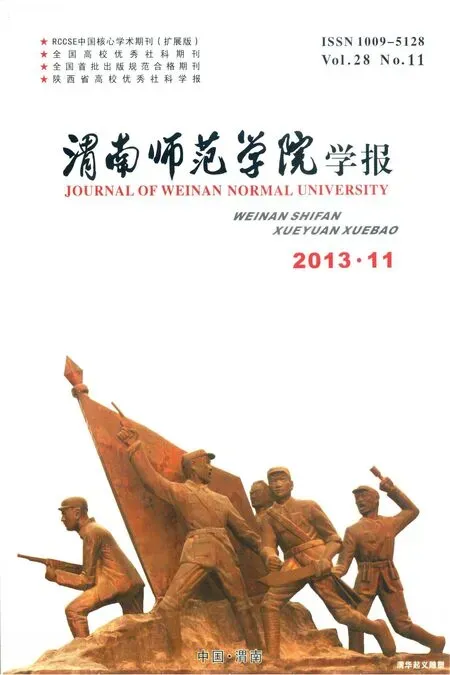司马迁昧于军事的影响——以李陵事件为例
吕 方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陕西汉中723000)
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学巨匠司马迁所受的“李陵之祸”莫不扼腕叹息,我们在为太史公掬一把同情之泪的时候,从未怀疑过太史公的正直无私、忠君爱国,然而他为何在李陵事件中作出有失偏颇的判断?他为何如此漠视李陵明显有亏于国家大节这一事实,而为之苦苦辩解?这一点似乎成为千古之谜,而学界对此所作的相关讨论有:认为司马迁不善于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明哲保身造成的;还有人认为李陵事件是由于汉武帝的私心,出于扩张的野心受阻而迁怒于人造成的;也有学者从司马迁对于李陵的主观预期与后来现实不符的角度来分析。[1-4]这些讨论实际上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疑问。有学者意识到此事件中透露出的认识论问题,试图将我们对此事件的考察引向深入。比如,孟祥才认为,司马迁错误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汉武帝。[5]遗憾的是,此文没有集中力量分析司马迁作为认识的主体,他的主观条件究竟对此事件有何意义与影响?张大可提到李陵事件中司马迁的主观过失,“李陵兵败降敌,成了叛徒,这个案是不能翻的。司马迁为李陵辩降,这个短我们也不必讳言而曲为之开脱。”[6]153他指出了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表现出的主观局限问题,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司马迁的主体条件在李陵事件的影响与意义。这是本文将要重点阐述的问题。
一、司马迁主体构成中的个体特色
根据史料所见,在李陵事件发生之际(前99),司马迁已经是一位社会游历丰富、学问渊博的成熟史学家。《太史公自序》载:“迁生龙门……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对于中原大地的山川地理、民情风俗、遗文古事都有了深入而感性的认识。而后他奉命出使巴蜀,“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7]3293。他的足迹遍及西南大地,到达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等省。这一经历无疑增长了他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状态的认知。并且司马迁还有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的记载,参与了封禅泰山,历北边,临瓠子塞河,祀后土,巡大江等恢宏、壮丽的事件。这些游历在《史记》中有生动、详尽的记叙。《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7]46《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7]1404《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7]1415《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7]1513《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7]2570
综观太史公的学术考察和社会阅历,这位伟大史学家的社会生活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广阔,但是很明显,其生活经历主要集中在文化民俗考察方面,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阅历则比较匮乏。《太史公自序》中对司马迁的家学、游历多次作了郑重而醒目的记载,我们发现他竟无一字提到亲历军旅生活的见闻记录。以太史公实录史事的一贯精神与手法,我们认为,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基本上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他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家学深厚、师承名门,但他缺乏军旅生涯的熏染。《史记》卷二五《律书》中透露出他对军事与战争的看法:“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7]1240他认识到战争具有平乱治暴的力量,将其比喻为昆虫鸟兽的毒针爪牙,是自卫的工具。很显然这是一种很表面化的直观认识,人类的战争毕竟同自然界的鸟兽争斗有本质的区别。当他把战争纳入人类活动中考虑,对军事的理解分别见于《五帝本纪》“轩辕乃修德振兵”[7]3,《礼书》“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7]1164,《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7]3305,《平津侯主父列传》“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7]2954。司马迁反对国家过分重视战争,认为礼义之德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战争观是继承儒家德政理念基础上的宏观理论认识。在先秦儒家的传统理论中涉及到军事思想。孔子同子贡谈论治国时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有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粮食、军事、民心这三样中,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孔子主张“去兵”[8]126。在孔子师徒论述的语境中,把民心与军事相比较,在治国思想上为了凸显民心的重要性而论,并非可以执著地理解为军事对于一个国家不大重要。或者可以说,太史公在军事理论的体悟与创建方面是较为平庸的,而且基本上没有将军事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考虑。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古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积累达到了较高水平。司马迁的前辈学者、军事家孙武深刻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1“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9]39孙武道出了战争之于国家的特殊意义,战争往往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军事的胜利在特殊时期是国家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较之前人,我们不得不说,太史公对战争与军事的认识显得过于浅白直观、书生意气和理想化了。而且,从先秦到汉初,军事文化有较为丰厚的积淀。《汉书》卷三○《艺文志》对此有全面的总结:“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10]1762-1763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古代军事思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那么在军事战争思想的时代认知积累上,并不构成对认识主体的负面影响。
社会经验是“造成主体意识结构的个体特色的主要因素之一”[11]149。太史公的社会生活阅历优势在于深厚的家学与社会文化民俗方面。他的社会阅历中缺少的是军旅生活的体验。太史公的社会生活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李陵事件的认识。以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和忠诚耿直的性格,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是他对这件事的切实的、全部的认识,他的话就代表了他对这一特殊军事活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太史公对军事生涯的隔膜和疏离,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李陵事件的认识和表达。
二、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理解和判断
李陵事件在《汉书》卷五四《李陵传》、卷六二《司马迁传》中有详尽的记述: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单于)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10]2450-2455
李陵出于“恶相属”,不甘居人下“为贰师将辎重”,自请“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作为贰师大军的策应之师,牵制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李陵冒险孤军深入,终于因“军无后救,射矢且尽”而全军覆没,兵败投降。
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站在客观与正义的立场上,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的观点分为三个层次展开。其一,他认为“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李陵一向怀有报国之心,“有国士之风”。李陵素有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而且是国内才能出众的人物。其二,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抑数万之师”,牵制了匈奴举国兵力。“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李陵在战争中负担过重,虽然失败降敌,但是杀敌过万,也可以功过相抵了。其三,李陵的投降不是真正的投降,“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10]2455-2456。他断定李陵暂时投降活下来,是为了找机会报效汉朝。
然而,事实没有像太史公希望的那样发展。汉武帝派“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公孙敖依据逮捕的俘虏之言,谎报“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10]2457。司马迁受到此事牵连,“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10]2456。司马迁被判“诬罔”罪,遭受腐刑。“诬罔”罪在汉律中是死罪。《汉书》卷六《武帝纪》“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10]187,栾大以神仙术欺骗汉武帝,被处死。卷七《昭帝纪》:“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斩。”[10]222“诬罔”,即欺君之罪。汉武帝得到的报告是“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而且,《史记》卷一○九《李将军列传》载李陵降后匈奴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7]2878。司马迁推测李陵投降为了“欲得当以报汉”,事态的发展使得司马迁的话成为欺人之语。《报任安书》说:“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10]2730又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10]2736对于李陵投降的事实,司马迁显然难以为自己当初的言论负责。就这一点,司马迁本人也无以辩白。有学考证:李陵败降匈奴在天汉二年十月。族灭李陵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司马迁被株连受腐刑亦当在天汉三年十二月。[6]150-152其后,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陵降敌有所反思和批判,“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7]2878。
李陵事件发生后,司马迁与群臣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群臣谴责李陵之罪,“群臣皆罪陵”。而司马迁竭力为李陵辩白,“迁盛言”[10]2455,显示出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理解与判断与大多数人不同,有着较强的个性色彩。
太史公对李陵事件的理解呈现出两大倾向。
首先,他忽视当下李陵兵败投降这一关键点,较多强调李陵的日常表现和兵败的客观因素。在李陵投降变节已然成为事实的七八年后,他回顾此事仍然说:“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他还竭力陈述了李陵失败的客观原因:“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10]2729他主张李陵的失败情有可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他的话隐含着汉武帝和贰师将军对李陵兵败负有责任。汉武帝也有战场调度不合理的地方。司马迁认为李陵失败的责任不在他自身,他在战争中承担了过多的压力是导致兵败投降的主要原因。
其次,太史公对战争与政治事件的复杂、险恶性质体认不足,是他理解判断李陵事件所表现出的另一个重要倾向。他不仅渲染了李陵的平素品德和失败的客观原因,并对李陵投降事件推测说:“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事实发展的结果证明太史公的估计过于乐观和轻率。李陵降后,匈奴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起初,太史公的意见对汉武帝有所触动。“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10]2457汉武帝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准备接应李陵回汉。然而,公孙敖在边境守望一年多没有迎到李陵,最后通过抓捕的俘虏之口,向汉武帝报告李陵投降后在教练匈奴兵,与汉为敌。尽管后来李陵向汉使者说明,教练匈奴兵的是另一位降将李绪。但为时已晚,汉武帝听到公孙敖的报告后,立即“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太史公也因此“遭李陵之祸”[7]3300,悲剧就此铸成。司马迁之所以认定李陵投降是为了“得当以报汉”,除了“诚私心痛之”[10]2729的义愤之外,主要在于他难以体会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个人的命运选择面临的险恶境遇。否则,“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这样的结论也不会轻易得出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军旅生活注定与胜败存亡、严酷斗争相关联。兵败投降向来为军法所不容。投降罪是先秦古老的刑名内容,“降北者身死家残”,军法对投降和战败逃亡的处罚十分严酷,不仅投降者本人处死,并株连整个家族。有学者考证认为:“秦汉军队严格适用这条军法以保障战争的胜利。”[12]投降罪由来已久,而且影响深远。汉律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二年律令》中《贼律》曰:“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3]133《敦煌汉简》中《捕律》:“亡入匈奴、外蛮夷,守弃亭鄣逢(烽)燧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降而贼杀之,皆要(腰)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14]256-257军事犯罪直接危及军队士气、军事安全和国家政权稳定。汉律对投降罪的量刑非常严酷,将此罪与谋反罪相提并论。由于投敌总是和叛国、谋反紧密相连,因此投降者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姐妹全部处以弃市极刑。李陵的投降行为已经成为事实。李陵成为一个触犯军法的罪人了。太史公为之竭力辩解,并不能使我们怀疑太史公正直的品格和忠诚爱国的政治立场。司马迁与李陵之间没有私交,他在替李陵辩护的时候没有党派的私心。太史公对汉律中载有明文的投降罪内容也很难说全无了解。有可能的解释是,因他的生活经验中缺乏军旅生活体验,才会淡漠了对投降罪的认识和理解。他的忠诚与正直使得他竭尽全力强调了李陵的无辜,等于为投降者的军事犯罪作辩护,损害了汉武帝的权威和整体战局的部署。因此,司马迁的言论在统治者的意识中成为别有用心的欺瞒,“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在汉武帝的眼里司马迁是有意歪曲事实,为了某种目的而为投降叛国的李陵辩护,于是才有了千古冤案——司马迁的“李陵之祸”。
三、司马迁的个体经验对认识李陵事件的影响
以上可见,司马迁疏于军旅的生活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李陵事件的认知和反应。也就是说,深厚的文史知识基础与几乎空白的军事、政治生活经验共同形成了司马迁特殊的主体意识结构。尤为突出的是,他昧于军旅生活的因素在认识李陵事件中发挥了致命的渗透力。在这一特殊思维意识时刻,司马迁的社会经验凸显出顽固的力量甚至压倒了其政治立场,导致其情感因素表现出偏离理智基础的倾向。“生活经验在单个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结构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特殊生活阅历的积淀,使认识主体在看待、理解事物时,“具有一种特有的体验色彩,发挥出其他认识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11]149。这一缺失导致司马迁在认识关乎民族大是大非的李陵事件上偏离了他原有的政治原则。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载汉武帝太初四年诏书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7]2917匈奴长期威胁着国家的安危,是司马迁生活时代汉帝国最主要的敌人和最强大的对手。李陵所参与的对匈奴战争关乎民族的尊严与国家政权的安危。由于对军事的隔膜,司马迁漠视、忽略军事战争中投降这一行为的实质意义。投敌总是和叛国、谋反联系在一起。军人的投降对军队的士气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损害了军事的利益,影响后续战争的发展,而且有可能泄露军事秘密、危及国家政权。正是缺乏这样的体认,司马迁只能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从常规意义上,根据一个人日常品德、作风、气质,以及遭遇事情的客观环境来看待、评议人物。当汉武帝询问他对于李陵事件的看法时,他的思维仍然被这样的主观经验所控制。他忽略了当下评价李陵,不是和平时期的普通人物品评,而是在民族矛盾高度敏感时刻谈论一个叛国的投降者,一个国家、民族、军队的罪人。他的主观经验这时发挥了顽固作用,促使他大力称赞李陵的为人,说他事亲孝,与士信,平时表现良好,经常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这次偶然作战失败有诸多客观原因,不能都算在李陵一个人头上。司马迁认为李陵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反映了他对战争中投降行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司马迁忽略了李陵战败投降这一军事上的耻辱和犯罪事实。他淡化了这个事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李陵已经投降的事实。他不能体会战败投降这一军事行为对一个国家的尊严、军队的信念,对国家后续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不能真正理解兵败投降的实质——对于军事、对于国家主权与尊严的致命性打击与侮辱。所以,他便不能明白,相对于这些而言,一个投敌者的日常表现、性格气质、兵败的客观因素是多么不值一提!司马迁也就无法认识到这时李陵兵败投降是多么不可原谅、不容辨白!他只是被自身的主观经验左右着,纠结于李陵事件的次要问题而挥洒着他的激愤与口才。
甚至,司马迁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轻率地凭直觉推断李陵是假投降,真正目的是“欲得当以报汉”。司马迁轻言军事的根源,在于他不能了解、体验军事活动中波谲云诡的凶险与严酷。李陵事件中“群臣皆罪陵”的态度,也包含着群臣对军事与军法的敬畏。群臣没有站在李陵的一边,太史公就认为他们纯属胆小怕事,“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10]2456。这显然是过于简单、表面化的判断。太史公与群臣对军事的内在理解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10]2729。“在一般认识活动中,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这是一种认识的常规。”[11]149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忠诚、耿直、成熟的史学家在投降罪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认识的偏颇也就不难理解了。
司马迁昧于军事是导致“李陵之祸”的主体方面的根源。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认知从反面证明:认识主体的经验条件在认识活动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警示我们反思,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主观条件的局限,从而不断地自觉提高认识个体的主观条件,加强主体修养。如果每一个认识个体最大程度改善主体知识经验水平,释放出巨大创造力,不断超越自身;那么,由这样的认识个体构成的史学家群体,可以推动历史认识的丰富和多元,不断超越前人,获得新的高度。
[1]夏中权.主体预期与客体结果相悖的悲剧——浅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性质及其思想基础[J].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6):97 -100.
[2]刘方元.关于司马迁“李陵之祸”[J].江西师院学报,1980,(4):38 -41.
[3]李蕾,谭翠娥.司马迁对李陵之降的辩护有失偏颇——读史札记[J].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6):71-72.
[4]李恩江.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J].郑州大学学报,1994,(6):17-23.
[5]孟祥才.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J].齐鲁学刊,1999,(2):82-86.
[6]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春秋]孙武.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新编诸子集成)[M].[三国]曹操,注.杨丙安,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2]赵科学.军法“降北者身死家残”述论[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0):211 -213.
[1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