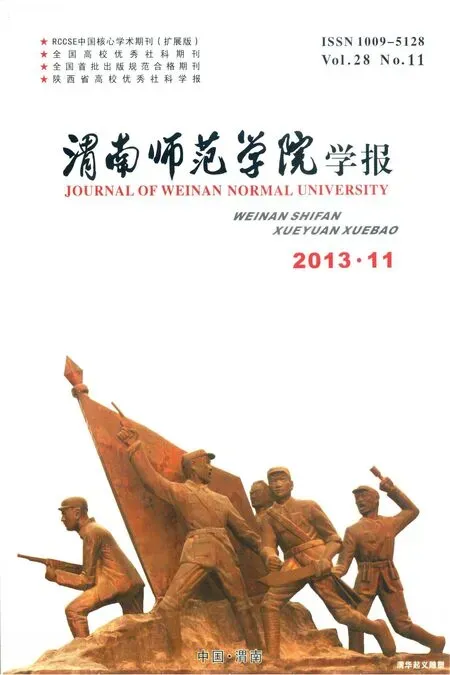《桃花源记》写作时间考论
刘书刚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巨大的作品之一,它开启了一个人们乐于不断向其回归的主题。同时,对这组作品的研究也已经十分充分,不论全篇的整体寓意,还是桃花源的地理考实,都有丰富详尽的考辩,并形成了一些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但是,寓言式的写作手法使得研究者在分析这组作品时有时又求之过深、失之穿凿,因此,继续讨论的空间仍然存在。本文试图将这组作品置于陶渊明一生思想演变的大致轨迹上进行考察,对其在陶渊明思想中的位置及其系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桃花源记》系年研究概述
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系年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作于太元、隆安之际,如梁启超说:“《桃花源记》及诗,不知作于何年,但发端称‘晋太元中’,或是隆安前后所作?”[1]148古直则将之系于太元十八年,云:“《桃花源记》为先生心中之安乐国,作记年岁无考,然记首特标‘晋太元中’四字,则必作于太元时矣。”[1]186这种观点今多不从,其论证亦不过依据《桃花源记》篇首“晋太元中”数语,未能深入探讨此文与陶渊明思想演变之间的关系,笔者不拟对其详加讨论。第二种看法是作于晋宋之交。如翁同龢曰:“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潜征著作佐郎不就,桃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欤?”逯钦立即依此将之系于义熙十四年(418)。[2]286赖义辉则以“晋太元中”标晋字,证此为晋亡入宋之后作品。[1]348袁行霈系之于永初三年(422),且云王瑶、逯钦立等说法“皆大致系年,且相差无几,难以详考也”[3]485。
《桃花源记》作于晋宋之际的说法目前较为流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即是记文中称桃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诗中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在习惯将文学作品与政治时事牵和在一起的批评传统中,秦世之乱很自然地被视为是对晋宋之际的政权更替的影射,而“避秦”也就被理解为陶渊明对刘宋新朝的拒绝。分析较为详尽的是黄文焕,在其解读中,文中的许多文字都成为这一主题的佐证:“此愤宋之说也。事在太元中,计太元时晋尚盛,元亮此作,当属晋衰裕横之日,借往事以抒新恨耳。观其记曰:‘后遂无问津者’,足知为追述之作。观其诗曰:‘高举寻吾契’,盖以避宋之怀匹避秦也。避秦有地,避宋无地,奈之何哉。篇内曰:‘无论魏晋’,而况宋乎?曰:‘皆叹惋’,悲革运之易也。曰‘不足为外人道’,叹知避之难也。”[4]277为这些只言片语阐释出如此丰富的意蕴,恐怕难逃附会之讥。
当然,对《桃花源记》的主旨有着另外的解读。特别是被黄文焕以一种不甚通畅的逻辑轻易带过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其中显示的超然洒脱的态度,很难让人认同这篇作品仅仅是为“愤宋”而作。马璞《陶诗本义》云:“其托避秦人之言,曰‘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自露其怀确然矣,其胸中何尝有晋,论者乃以为守晋节而不仕宋,陋矣。”[3]484他更多地将这一组作品视作是个人吐露胸怀、抒发志向的产物,而不是对由晋而宋的政治风波的反映。事实上,学者在阐发作品主旨时,往往强调不可拘泥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认为渊明的思想具有超然事外、贯通古今的穿透性,但是在系年之时又不能不摘寻篇中一二语句,将之与具体事件牵连在一起。在具体事件刺激下创作而充溢着超越性思索的作品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这种解读方式的风险也不能忽视,尤其是面对《桃花源记》这种有可能故意隐约其辞的寓言性作品时。
二、《桃花源记》的退隐思想
如何理解《桃花源记》寄寓的作者思想?应该从这组作品的整体思想倾向进行把握。诗文最为鲜明的特征是设置了一个对立的双方:山内与山外。这绝不简单是空间上的分隔,而是寄托了作者情感上的好恶、思想上的取舍。山外是秦以及继之而来的汉与魏晋,亦即此起彼此、延续不断的历代王朝,山内则是如王安石所说“但有父子无君臣”的聚落,它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可能只是以简单的血缘以及地缘关系维系的松散集体,以国家为主要形态的行政组织在这里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抵制国家形态的,不仅“避秦”这样的用语显示了它对国家的刻意规避,文章的结尾也表明它与国家的截然对立。“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显然不能视作是简单的迷路,在此作者借用了当时求仙访道故事的套路,使得桃源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待着发现的处所,而是一个具有主动选择其访客的能力的场域,因此,作为官僚政治代表的太守不得其门而入,实际是桃源对他的有意拒绝。
另一方面,应该对山内,亦即寄托了作者理想的桃花源的特征以及其中人民的生活状态略作分析。首先,渔人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随后遭遇的便是一片风景和美的桃花林。从空间上看,这片桃林是在山之外,更是在民众群居的部落之外,但这其实已经不再是世俗人间的场所,渔人行至此处已经进入到美妙绝伦的幻境,后来的太守探索此地之时,恐怕连这片桃林也已经杳无踪影。所以,这条溪水,这夹岸的桃林,以及这阻隔内外的山峦,都应该算作文章塑造的理想之境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不仅仅是充当进入山内的必由之径,它们本身就是山内民众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次是这群避秦之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农耕是他们基本的劳作操持,也是他们获得丰裕生活的物质保证,“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老少皆得其宜,足见此中淳厚的风俗、和睦的人情。但是,这种简单的设想恐怕不能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政治哲学方面达到了某种高度,它更多的是对一个摆脱了王税、逃离了国家干预的村落的描摹,仅此而已。概而言之,桃花源是一个山环水绕,其中民众以农耕为主要事业的所在。
因此,要判断这组作品的创作时间,更重要的是探究陶渊明一生之中哪个时段的思想状况与之吻合,亦即他是在何时对国家政治有如此激越的拒斥,对山林、农耕生活有如此强烈的追求。观其集中诗文,恐怕隆安至义熙初年之间的创作与这组作品的思想倾向最为合拍,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仕、隐问题是他着力思考的主要问题,告别仕宦、摆脱政治成为他越来越强烈的欲求,而他所向往的隐逸,也正是有着山水点缀的田园农耕生活。这一主题几乎在他此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体现。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林二首》其二隆安四年(400))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隆安五年(401))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诅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元兴二年(403))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兴元三年(404))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义熙元年(405))
所有的诗歌中都展现出一组对立:“园林”与“人间”,“林园”“耦耕”“衡茅”与“商歌”“好爵”,“高操”“平津”与“固穷”“栖迟”,“园田”“山泽”与仕宦行役,简言之,即使仕宦与园田的对立,这与《桃花源记》的基本结构正相合。作于元兴二年(403)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则将此种情绪表达得更为明显。第一首抒写了短暂的田舍生活带给他的巨大愉悦,“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非浅”。这使得他再次怀疑自己眼下的仕宦,重新思考人生途径应该如何选择。第二首更明白直接地描述了这种思想交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先师遗训虽要求孜孜以弘道为事,但在此方面自己已经无能无力,因此不妨耕种自足,而渊明在此设想的理想状态正是只与农人交往、不被行者打扰的乡村生活,这与桃花源中之世界也大致相同;巧合的是,诗中有“行者无问津”一句,而《桃花源记》中也出现了“后遂无问津者”的字眼。
义熙元年陶渊明终于辞彭泽令归隐,在可能为“预想之辞”[3]476的《归去来兮辞》中他再次设想了自己归隐后的生活:“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这里既有山水优游之乐,也有田间农作之事,与《桃花源记》记载约略相仿。归隐不久,他即移居园田居,也足见他长期以来念念不忘的归隐,就是融入乡村,进入一种以农耕为主,闲暇之余流连山水、寄意琴书的生活。《归园田居》五首即是对这种生活的实录,也正与“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大致类似。
三、《桃花源记》对待交游的态度
我们更应该注意陶渊明在归隐前后对待交游的态度。《归去来兮辞》中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可见在退隐之时,他对旧日相识采取一种十分决绝的态度,而对他们表示断然拒绝之后,他生活中的往来之人,就只有所谓“亲戚”以及“农人”了。这种想法在此时期的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说“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即设想了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上文分析过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也表现了对“行者问津”的排斥及与农人近邻的接触。在园田居时,他也确实实现了这种状态,《归园田居》云:“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云:“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归鸟》中云“岂思天路,欣反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都反映出对“故人”“昔侣”的有意躲避与“但道桑麻长”的邻近农人的和谐相处。而《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恰恰是一个“与外人隔绝”仅仅由农人乡邻构成的世界。
这些“故人”“昔侣”“行者”应该主要是指陶渊明在仕宦之时结识交往之人,但可能也不限于此。集中有《酬刘柴桑》一首,逯钦立、袁行霈诸先生并以为作于409年,而刘程之于402年归隐,则“山泽久见召”之事,当大致在渊明居于园田居之时。渊明拒绝其招隐的原因或者较为复杂,但诗歌中自称“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也并非虚泛的应酬之语,亲旧之情、天伦之乐一直为渊明所珍视。而桃花源同样并非隐者们离群索居之地,其中有着“怡然自乐”的“黄发垂髫”。另外,在记文之末,桃花源不仅拒绝了太守的探寻,也让高尚士刘子骥寻之未果。余嘉锡指出刘驎之采药入山见二石囷事与桃花源事相近,“盖即一事而传闻异辞”[5]773,因此,《桃花源记》可能是渊明以刘驎之故事为依据铺衍而成,其结尾处的刘子骥“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可能只是沿袭传闻,并无深意,不像太守之事为刻意寄托。但是,另外的解释是否全无可能?刘子骥可不可以视作是对刘程之的影射?别无他据,此处不敢断言。
不论如何,将自己的交往范围限制在亲戚、邻里农人之间,对其他的各类交游则大多拒绝、抵制,是陶渊明在归隐前后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态度,而这与桃花源的故意封闭、源内居处之人仅为农民恰恰一致。相反,在晋宋之交,渊明对归隐的理解已经有所改变。史称义熙十四年,潜征著作郎不就,当时亦似有劝之出仕者,因此,这完全有可能再次激起陶渊明对国家政权的拒绝情绪,但此时他已隐居多年,对农耕生活的甘苦也有了切实的认识,虽然乡村仍然是他的托身之所,但像《桃花源记》那样对乡村的美化色彩已经渐渐淡薄,如“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诗句即反映了他对稼穑艰难的感知。其晚年生活的贫困,对其心境也不能没有影响,这在其《咏贫士》等作品中表露无遗,而《桃花源记》笔调恬淡平和,全无此种情绪。更重要的是,晋宋之际,他对交游的态度与园田居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与村民野老虽然能够和谐相处,但毕竟无法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渊明难免有寂寞之感。
从渊明集中诗文看,移居南村之后的数年之间,是他隐居之后交游颇盛的一段时期。这些交游对他的隐居生活无疑是一种丰富,但周续之、庞参军、殷晋安等人渐次或出仕、或离开,又使他觉得能够如自己一样矢志归隐的知音难觅。因此,在他后期作品中,尚友古人之语屡次出现。如《饮酒》其二:“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六:“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其十一:“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其十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分别用荣启期、夏黄公、绮里季、颜回、张挚诸人典故。写作时间更后的《咏贫士》更为直接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后五首径取历来贫士之事吟咏成诗,而开宗明义的第一首则将他晚年孤独心境表露得十分透彻。因此,晋宋之际陶渊明并不像在园田居时,对几乎所有交游都一概拒绝,仅与村民野老往来,此时他更希望有能理解他固穷终隐之志的知音出现。桃花源中生活之人仅为农人,这与渊明园田居时的心态更为接近,与他晋宋之际的思想状况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四、结语
认为《桃花源记并诗》作于晋宋之际的另一依据为记文开端的“晋太元中”,从语气上看为晋亡后之追述。[1]347这一说法又与沈约《宋书》“(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等记载纠缠在一起,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沈约之说是否确然已是聚讼纷纭,“晋太元中”是否追述也未可一定。此文采用当时小说杂记之体,而此一体裁与史传关联甚密,因此详细记载时间,弄此狡狯之笔以郑重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何况,仅据此简短一句即断定其写作时间,也未免草率。
概言之,《桃花源记并诗》虚拟了一个与国家政权相对立的方外世界,这与渊明在隆安义熙年间对出处仕隐的思索与考量相合。渊明在归隐之前设想的隐居状态,即是决断一切交游、仅与村民野老往来,以农耕为主业、间或有山泽林野之娱的乡居生活,在其归隐后也移居到园田居,基本实现了这一愿望,而这与桃花源有山有水的自然环境、仅有农人聚居的人文风情相吻合。晋宋之际渊明的隐居生活早已发生改变,他对耕作之苦已有认知,与当地文士的交流也已成为其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寻求知己乃至尚友古人的情绪也十分强烈,而这些在《桃花源记》中并无展现。此外,唐长孺先生指出《桃花源记》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写成,而渊明与此传说接触的时机当是隆安年间在江陵之时[6]193,由此,这组作品很有可能是渊明假借传说故事、糅合退隐之思而作。因此,本文认为,《桃花源记并诗》应该作于隆安到义熙之际,亦即其归隐前后;而其文风婉丽平和,似更有可能作于其归园田居之初,亦即义熙初年。
[1]王质.陶渊明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杨勇.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