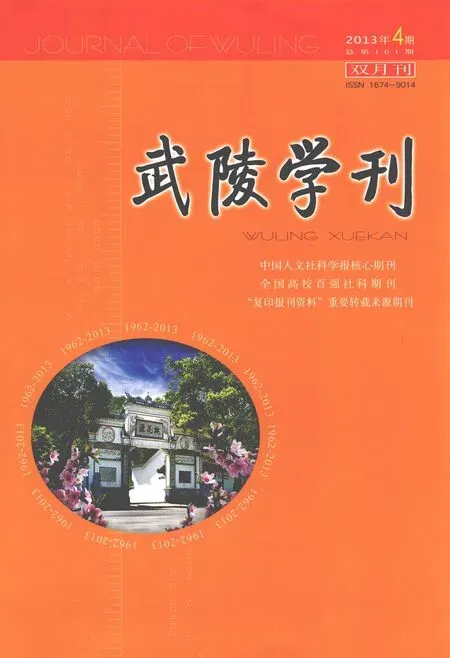陈云的国史观及当下意义
邱 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一 陈云的国史观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享年90高龄,革命和建设生涯长达70多年。他一生注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各项工作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在配合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给予了客观准确的评价,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国史观。陈云的国史观不仅在历史转折时期发挥了稳定大局、拨正航向的重大作用,在当下对于国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大局、全局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对待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党和国家的历史
古往今来,一切文明的民族和国家没有不重视自己的历史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是背弃自己的历史而走向辉煌的。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出现了一股打着清算毛泽东的旗号,极力贬低、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否定32年新中国历史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向。这是关乎全党利益、全民族利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大问题。对此,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坚定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299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299。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684,“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2]435。
在这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认识不谋而合。陈云主张,一定要敲定毛泽东的功过,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3]237-238以苏联为前车之鉴,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否定了斯大林,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以为明证。这一主张正反映了陈云国史观的核心思想,即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党和国家的历史,包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林彪江青两案的处理等,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着眼大局、全局,着眼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
陈云在1979年3月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3]237这是客观的认识。邓小平也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1]294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后来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原因有很多。陈云总结:“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4]274他说:“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3]237林彪、“四人帮”就起了很坏的作用。陈云的观点是,要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实际的结果区分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至于严重的后果,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而不能单纯地把错误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这个问题在今天,也仍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
事实上,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在“文革”后的短时期内,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突出他的历史功绩,并不容易。有的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一时不能客观理智地作判断;有的人不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容易错误地轻易地作判断;还有的人居心叵测,借以否定毛泽东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陈云力主:“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做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5]75陈云认为,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前提和基础。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陈云强调了五条:一是培养了一代人,一大批干部;二是正确处理了西安事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三是延安整风时期倡导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四是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是真心诚意的[4]284-285。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邓小平认为《决议》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文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1]307。陈云对《决议》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多次同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在谈话中表达自己对这段历史及毛泽东的看法,提出对决议起草的重要意见。据《陈云年谱》记载,他在决议起草期间关于起草意见的重要谈话有七次:1980年底同胡乔木谈两次,1981年初同邓力群谈四次,1981年3月24日同前去探望他的邓小平专门做了一次谈话。《决议》数易其稿,征求了近万人的意见(除党内人士,还包括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甚至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站在党的立场上,着眼大局和长远,最终给予了毛泽东科学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6]陈云在《决议》通过后,称赞“改得很好,气势很壮”[7]。
此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处理意见,也体现了陈云坚持党性立场的一贯的国史观思想。他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4]304当时有一种认识影响很大,认为“文革”主要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有人甚至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都是非法的,“文革”就是一场“反革命政变”。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都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的观点是,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是一个底线,不能让人产生党内存在残酷权力斗争的印象,这不利于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是一场政治斗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家野心家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很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场政治斗争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对这场政治斗争的处理,“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4]304。司法机关最终以“只审罪行,不审错误”的做法,严格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两种不同情况,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陈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又提到,“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3]381。对待1989年的政治风波,陈云坚持了同样的党性立场。他认为,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陈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4]369从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团结教育大多数。
(二)要实事求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力求全面准确地评价国史人物,客观稳妥地解决国史遗留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和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了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的路线上来,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对“文革”必须做出客观的评判,对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必须给予适时平反。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回避的,但绝非易事,必须要有正确的原则方法。陈云的一贯原则是:“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8]这也是陈云国史观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样的国史观原则方法,在转折的关键时期,陈云为全面准确地评价国史人物、客观稳妥地解决国史遗留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与否定毛泽东思想相对应的另一股极端倾向,就是神化毛泽东、教条化毛泽东思想,以“两个凡是”为代表。陈云主张实事求是。1977年9月28日,陈云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撰写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在开头即亮明了观点:“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4]441正确评价毛泽东,陈云的实事求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国史观原则方法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既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要客观地承认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否则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既要评判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功过,同时也不能忘记建国以前他的功绩,否则同样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陈云认为:“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4]2421980年11月上旬,他对负责起草《决议》的胡乔木讲:“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3]260同时,他主张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做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一,作为一个教训来说党中央是有责任的,没有坚决斗争,不能说整个党中央中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他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第二,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他说:“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3]260-261总起来说,陈云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是犯了错误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民主集中制,但是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是有责任的,地方上也有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结论,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建国以后32年党的工作中的错误,陈云也没有回避。他的观点是,“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但是一定要写得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4]283。邓小平也讲,“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成绩是主要的”[9],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0]。对建国以后我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它是一个新生的落后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的必经阶段的一面。正如陈云所说:“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4]242他在80年代末还指出:“‘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3]413
陈云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当中犯了“左”倾错误,但是评价毛泽东不能只局限于“文革”十年和他晚年的错误[5]75。他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发展地看待国史人物,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对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1981年3月,陈云同《决议》起草组的另一重要成员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他认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4]283-284
同时,陈云主张要在党内干部和青年中提倡学哲学、学历史,《决议》增加建国前的这段历史正好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毛泽东在建国前28年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哲学著作,代表性的有《矛盾论》、《实践论》等。陈云回忆,毛泽东三次亲自跟他讲过要学哲学。延安时期,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大好,需要休息,利用这个机会,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和毛泽东起草的重要电报,收益很大。他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陈云认为,建国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也离不开实事求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因此,他提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这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同样,也要学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理解建国以后的历史,不能准确理解毛泽东。这个问题,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有着更加深远意义的思考。陈云认为:“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4]285
此外,陈云还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建国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予以平反。这也是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国史观原则的体现和结果。他在60年代初就讲过,“真事说不假,假事说不真,真理总归还是真理,历史实践是会证明谁是谁非的。”[4]376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对“反右倾”运动时对许多干部的错误批评,陈云60年代就指出过:“对于那些犯了一般性质的错误,而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要恢复名誉。”[4]285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认为当时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如何看待“天安门事件”,一件是邓小平复出工作,这两件事是连着的。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指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4]230就在这次会上,还有领导同志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当其冲提出要平反冤假错案。他后来回忆:“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3]381陈云当时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4]232他列举了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陶铸、王鹤寿等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邓小平的问题以及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提请中央给以考虑和解决。陈云认为,对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4]233。对刘少奇案的平反,陈云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指出,对刘少奇问题、叛徒定性问题等,必须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不能拿现在的情况看过去。陈云认为:“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11]1522他主张,刘少奇冤案是党和国家的事情,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但是不能像“四人帮”那时那样,随便栽赃,随便定性,而要逐条甄别,重新调查。“要否认那些罪名,也让它公布于世,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让世人来检验。”[11]1521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共同努力下,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全会公告指出:“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12]经陈云直接提议复查和平反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还有瞿秋白、张闻天、萧劲光、马寅初、潘汉年、徐懋庸等。
二 陈云国史观的当下意义
国史研究,这里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性质来讲,国史研究旨在“为共和国立传、为人民写史”,是有着特殊的政治性与人民性的史学研究;从内容来讲,国史研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现实,既要关注历史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又要总结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国史研究中,能否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陈云的国史观恰为当下的国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依据。
(一)国史研究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真实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国史研究作为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其“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13]。应当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国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唯物史观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之一,它实现了人们社会历史观的彻底变革,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4],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旨在否定新中国历史(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以政治诉求为依据,片面引用史料,不尊重历史事实,任意歪曲历史,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对国史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任何人研究历史都不可能缺失历史观,任何历史研究的结论也都不可能没有立场、绝对的客观。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价值中立的。有些历史研究者声称没有立场,实际上,他们在“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非学术、非文化、非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加以排斥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原有宗旨,而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另一种历史观的支配”[15]。陈云国史观的当下意义在于,告诉我们研究国史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立场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大局、全局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对待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党和国家的历史,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史研究和国史研究者持有怎样的历史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要搞清楚国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国史研究为谁服务。知道为谁写史,才能写出好的国史。
(二)国史研究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的方法论,辩证地看待和研究国史事件和国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力求得出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结论
翦伯赞在他的《历史哲学教程》序言里提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16]国史,在时间断限上属当代史。研究离我们最近的这段历史会让我们发现,历史的舞台并没有那么高,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上面。但是,为什么同是历史的亲历者,对国史事件和国史人物的判断却会有巨大的差别?除历史观的迥异之外,研究国史的方法的不同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唯物史观的科学的方法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17]。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描述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8]李大钊在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指出,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19]。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陈云国史观的原则方法正是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的体现,即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国史人物、处理国史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国史,不是要一句一句地背诵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辩证地分析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力求得出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结论。
在已公开出版的陈云著作文献中,直接反映陈云国史观的内容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陈云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评价和对待国史人物,分析和处理国史问题,为当下的国史研究和国史研究者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理论与方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陈云年谱(一九O五——一九九五):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55-156.
[7]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101.
[8]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18.
[9]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2.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41-442.
[13]陈奎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大力开展国史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6):1-4.
[14]列宁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15]侯惠勤.略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J].历史研究,2008(6):4-8.
[1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3.
[17]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0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19]李大钊.史学要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