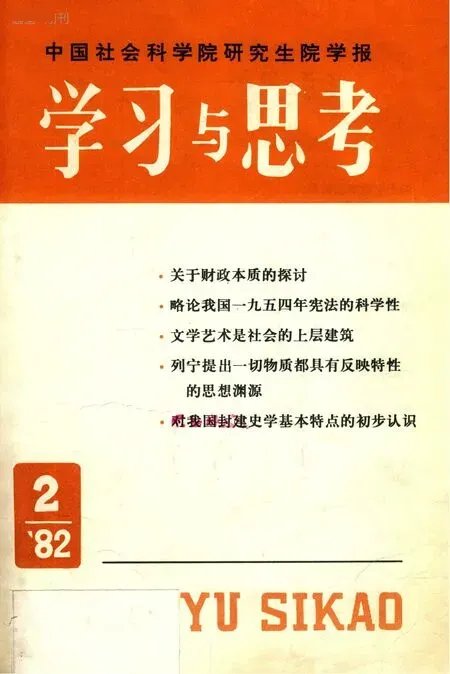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 周 静
我把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刘震云的《温故1942》,还有一本研究战后欧洲史的书放在一起读,找同一个问题的线索。这个问题是,底层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诉求和方式同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但我无法在这里回答好我的问题,哪怕仅仅从托克维尔的这本书着手。在这本书中,很多作为章节题目的惊心动魄的句子,越出了我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使得我从这本书里读出的疑问比获得的认知要多得多。我就说说我的疑问,跟大家讨论。
一、民众的第一诉求是平等吗
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人人平等”,几乎不是他们的第一诉求。比如“自由”这件事,是对不公表示申诉的权利。托克维尔在书里表述得很清楚,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订的许多规章制度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托克维尔就是在这判断的基础上,提问:“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托克维尔的答案是,“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我说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本身。”旧制度下的官员们,以及后来被涤荡掉的贵族,还有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没有料到他们“针砭时弊”并启动一些改良措施的方式本身,恰恰提示了民众的怨恨,激起了比求平等更不可遏制的行动激情。托克维尔说,“革命是在政治自由重新被人关注的时候发生的。这情形中政治自由是借口。”民众的要求从根本上是很实在的,仅仅是下一顿有饭吃,或者今天收税员不上门。
二、民众最需要的是改善还是安抚
在阅读中,托克维尔的提问始终非常精准。为什么旧制度下政府和精英阶层与民众那么不可沟通,为什么好心好事不被理解和接纳,以致革命不仅获得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
他讲到法国乡村贵族,也就是地主,在18世纪,离弃了农村。这是各种制度缓慢不断运动的结果。他选取了城市化这个角度,提出城市(主要是巴黎)势力的集聚,中央集权的成形,使得贵族地主在乡间彻底失去了政治权利,地方自由也随之消失。离开农村的还有资产者。托克维尔说,“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资产者就此与政治权力制度建立了联系。再有,“长期居住在农民当中并和农民保持不断联系的唯一有教养的人”,本堂神甫,也对安抚农民无能为力。就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卑劣的地方和优秀的地方一样,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然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激情,会马上意识到他们没有任何留待放弃或希冀保有的东西。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时期的法国阶层状况有这样的判断:“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他主要指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这样聚集在城市的阶层,他们坚持各自的利益诉求,都寄希望于各自的诉求能得到特殊照顾,至于公共利益乃至常理都可以放在后面考虑。他们就这样彼此隔离,并且同底层的人民隔离。进而,他要说明的是18世纪的法国,“资产者与贵族,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都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于是出现的情况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
三、不暴力的民众是多数还是少数
在那本讲战后欧洲史的书里,读到作者的一个判断,他说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欧洲旧秩序的终结”,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平静。他提到参与社会运动的民众有一个共同点——对暴力的厌恶。他的这个结论得自时代之风和民众追求的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在60年代的法国及欧洲学潮中就已明显。这是一代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是基础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与统治者辩论不感兴趣,对给他们提供一种不同的激进的统治方法不感兴趣,对意识形态的宣传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下而上的出头感兴趣。社会运动变成一场年轻人的嘉年华。就算是他们的领袖,欣赏的也是一种政治规范,有时候这一思想反映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有时候则反映在“公民社会”中。但无论如何,他们期待的现代生活仍然和当年、现在的农民一样,简简单单,实实惠惠,基本上就是一种常态。这是现代的年轻人对用暴力进行惩罚不感兴趣的原因。但刘震云和冯小刚估计不同意。
民众的戾气如何疏导,除了安抚之外,有什么其它有效力的途径。托克维尔在分析旧制度下法国社会阶层间“形同路人或仇敌”时说,“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自己的事务,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他的意思大概是阶层之间需要沟通,需要互相了解各自的诉求和各自的难处,需要一个平台来让他们说出和听到这些东西,毕竟,超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统一体不是一种社会常态。他指出阶层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正源于彼此隔膜继而彼此怨恨,他说,“当使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相互厮杀。”
读通全书不易,但找到该书的核心问题并不困难:专制、自由和平等三者关系。托克维尔在《前言》里定下基调: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