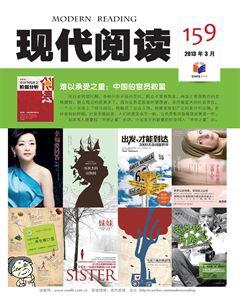田家英爱书
“爱书爱字不爱名”,是田家英在一首绝句中的自我描述。不爱书就不可能有自学成材的田家英,故而读书、淘书,是田家英工作之余的最大乐趣。毛泽东的部分书房在田家英的院子里,是和田家英爱读书、淘书,并帮毛泽东置办图书有关的。
所谓“淘”书,就是到古旧书店去购买他渴求的书。在北京逛古旧书店、书摊时,田家英有时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们。于是,孩子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如何忘我地扑在书海里,或扒在书架顶层,一格格地搜寻;或不辞劳苦,把一摞摞的旧书搬来移去,手上、衣袖上沾满灰尘。
每当意外地发现一本有价值的书时,田家英就会像稚童一样喜形于色。几乎每次淘书,都是抱着一捆书回家。由于常去搜扒,琉璃厂古旧书店的老师傅都跟他熟了。他的这一行踪,后来连毛泽东都掌握了。有几次临时有事找他,就让卫士把电话打到了琉璃厂。
田家英喜欢收集杂文一类的闲书,多达十余书架。闲暇时光,几乎都沉浸在书中,读得非常认真。他比较喜欢周作人的杂文,认为周的各类创作中以杂文最佳。他还爱翻简又文、陆丹林编的《逸经》杂志。正是通过这类杂书的博览,他了解到许多虽不见经传却相当重要的材料。从马叙伦的杂文集《石屋余沈》,他看到“四·一二”政变的诸多记载,得知蒋介石做“清党”决定时,会议记录竟是马叙伦。
他因为承担着为毛泽东置办个人图书馆的重任,自己购得的书,都先查看一下毛泽东那里有没有。曾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邓洁,知道田家英淘书的爱好,一次他们从没收敌伪的财产中,发现了一部乾隆英武殿本的《二十四史》,就问田家英对之有兴趣否。田家英马上想到毛泽东还没有,便立即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异常钟爱,时常翻阅圈点,直至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爱书、读书一向欣赏,曾戏言将来他的墓碑上镌“读书人之墓”最为贴切。亦因知其“过目成诵”的天赋,毛泽东喜欢和田家英闲聊泛论,从麻将牌的“中、发、白”各代表什么意思,到算命先生如何看手相,而且每次都有新话题。
田家英除了多读书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方家求教。有一次,田家英和孩子们散步,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一位算命先生,便向他请教。孩子们笑父亲迷信,田家英却说,“这里面有辩证法”。
由于喜爱读书、藏书,田家英还有一段和康生交往的逸事。
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与鉴赏水平,康生往往要争坐“第一把交椅”。他在诸如诗词、书画、金石、戏曲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他能画两笔国画,作画用名“鲁赤水”,向国画大家齐白石挑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康生因没有当上华东局第一书记,闹起了“政治病”。1956年在中国“八大”上又从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以致有点门前冷落。从此,他再度擎起揣摩领袖心态,和领袖身边的人搞好“关系”的法宝。一方面,他几次对旁人说如何佩服田家英的笔杆子,说田家英编辑毛泽东的文章,犹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一方面借田家英也有藏书爱好谬托知己,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家英。
据专家考证,明代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言》,世间仅发现过四部,其中两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人吉川幸次郎处。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而康生赠送田家英这部,为衍庆堂三十九卷本共二十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后为康生所得。
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自己的“康体”补了残缺的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本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两页,故按《世界文科》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墙往事——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秘书们》 作者:王凡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