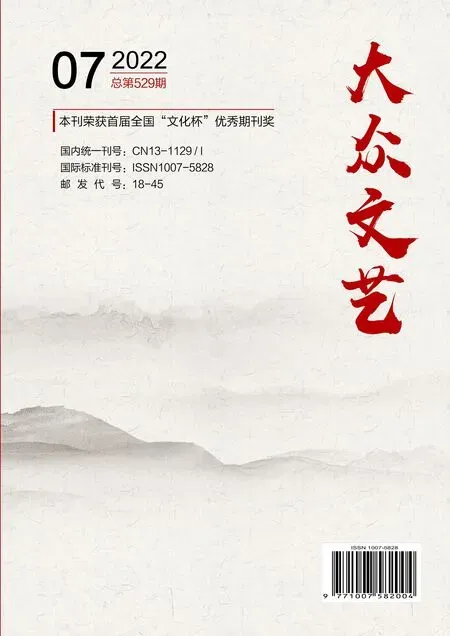论《桃花扇》非爱情剧
徐 阳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古典爱情名剧”,然而,随着学界对剧本的深层解构和不断探究,有学者指出“四大古典爱情剧”的说法仍有待商榷。《西厢记》描写的是纯粹、单一的爱情故事情节,被定位成“爱情剧”无可厚非。其实《牡丹亭》是否爱情剧也有待推敲。此外,关于《长生殿》的主题讨论亦是众说纷纭,然洪升在开宗明义的《传概》一出就指出:该剧是“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传概》)。作品偏于爱情的主旨一目了然,不容置疑。
与《长生殿》相同,《桃花扇》亦采用了复合型创作范式,形成了“爱情+政治”的二维复合模式。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出《长生殿》主题与《桃花扇》主题迥然相异的差别,这是由于作者完全不同的创作主旨造成的。
在南明覆灭、清朝取而代之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出自诗礼名门,久承老祖宗孔子之训的孔尚任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他想效仿“春秋笔法”创作一部政治历史剧。孔尚任最终选择了以传奇为史,“传奇虽小道……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桃花扇·小引》)他希望借助传奇的形式同样创作出如《左传》《国语》《太史公》的史学作品,把《桃花扇》写成一部关于南明王朝的历史剧。
黑格尔在运用“历史剧”这一名称时,把它界定为“向过去的时代取材”的作品,并把“维持历史的真实”作为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为了保证《桃花扇》的历史真实性,孔尚任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公元一六八五年,孔尚任前往明清对峙的聚焦点淮扬一带进行实地考证。明代末年,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吴三桂降清,清人乘机入关,后又挥师南下,大明王朝随之彻底灭亡。人民曾奋起抗击清军,结果招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尸横遍地。孔尚任观察了这些地方的劫后情形,搜集了很多关于南明的佚闻野史,也亲眼见证了官场的黑暗。孔尚任用了十年的时间广泛采集史料,广求逸闻,并证之“诸家稗记”,无不同者,方敢下笔。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对待素材、认真考证的做法正是因为他想将《桃花扇》写成一部《过南明论》,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对已逝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试想若只打算创作一部爱情主题剧,剧中的政治题材、社会题材都只是背景和陪衬,孔尚任则完全没有必要耗费如此的精力和时间来去搜集素材并进行考证,使剧中所写的南亲近事俱为“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先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
孔尚任曾多次重申,他是严格遵循历史史实加以创作,是在写一段关于南明王朝的政治历史剧。剧中涉及的大事,如明末复社的活动、崇祯自缢、福王登基、史可法死守扬州、江北四镇的内讧、左良玉兵变等,几乎都可以按年月考据出来,每一个事件展开之后都是一幅大场面。剧本上及朝廷天子,下至底层平民,各个社会层面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在面对改朝换代的历史趋势时的不同生存面貌都得以展现。将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连缀起来,几乎就是一部有声有色的南明亡国史。
虽然《长生殿》与《桃花扇》同是将政治和爱情交织在一起的题材,但是洪升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上关于李杨的题材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长生殿·自序》。虽对上层权贵、下层百姓的生活面貌在剧中也有所体现,但并不遵循历史事实,而是根据李杨爱情发展过程中的阶段需求作出的附带反映。这些都是因为《长生殿》是以写情为主旨,而非以言志为旨归,作为一部“专写钗盒情缘”的爱情主题剧,它需要的是浪漫而非真实。而孔尚任的期望是通过《桃花扇》展现南明政治历史面貌,使观众和读者“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使人们为之反思。它的定位显然不在爱情,因此,需要的正是真实、宏阔和深刻。
孔尚任不仅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桃花扇》的创作,对南明旧事进行了大量考证,主观上希望创作出以离合为皮相、以兴亡为内核的南明政治剧。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铺叙还是结构的安排,也都是统一于“兴亡”主题之下的。
对于人物的选择,孔尚任是慎重的。因为作者要写南明的覆亡,故不能不兼写南京、扬州、武昌三地。而“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恰好和这三地都有某种联系,是理所当然的局中之人。在确定《桃花扇》的女主角时,孔尚任从许多节烈女子中选择了侯方域文章《李姬传》的原型李香君。侯李爱情故事本来就委婉动人,再和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就显得更有光彩。孔尚任对侯李二人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式形象塑造,使文章的主题在错落的人物形象中不言而喻。
说到国家兴亡,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人与它似乎没有多大干系,最多只是充当“美人计”中的前台角色。但孔尚任却独辟蹊径,偏却让李香君卷进明末的政治斗争,展示了一个“巾帼卓识、独立天壤”的女性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不是青楼妓馆中的一名烟花女子,而是亡国浪潮中的一个“女英雄”,她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在国破家亡、生死荣辱面前,愿意用鲜血和生命实践复社“重气节、轻生死”的宣言。
在《却奁》一折,面对魏阉余孽阮大铖的利诱,侯方域动摇、暧昧,最终答应“即为分解”,到复社领袖陈定生、吴次尾那里去为阮大铖说情。而当李香君得知杨龙友送的妆奁酒席是阮大铖用以拉拢侯方域的礼品时,不禁怒气上冲,立即拔簪脱衣,掷弃于地,表现出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义无反顾的精神。李香君崇高的人格气节在《骂筵》一出达到顶峰,面对南明王朝的袞袞诸公,李香君颐指气使,怒斥群奸。“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骂筵》)这些詈词,把魏家的干儿义子骂得狗血淋头。这一切行动之始不仅是李香君内心对民族理想的执着,也源于秦淮歌妓对东林、复社的敬重。与其说她维护的是一种爱情贞操,不如说是维护一种政治贞操。孔尚任把视富贵财利如粪土的刚正之气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集中在一个供男人“怀中婀铘袖中藏”的小小玩物、一个流藩风尘的秦淮佳丽身上,不异于给了南明王朝的掌权者、中流砥柱们以当头棒喝。
在描写侯方域时,孔尚任一定是矛盾、犹豫和痛苦的。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孔尚任何尝不想写出一个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侯公子,与李香君成一对才子佳人、英雄美人,于明末政治浪潮中逆流直上!可是晚明王已经腐败糜烂到无可救药,生活在其中的人已经看不到王朝的未来和自己的出路。侯公子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的动摇和软弱,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保全身家性命时的畏惧和叛变也就合情合理了。当女子挺身而出,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血溅折扇的刚烈、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将一种悲壮的人格精神表达到极致,侯公子注定只能成为李香君辉煌人格的反衬,成为《桃花扇》千古悲剧中的一抹灰暗的底色。
《桃花扇》是一代王朝覆亡以及一个民族大悲剧的实录,除了李香君、侯方域,孔尚任还在剧中塑造了29个人物形象,昏庸无能、沉溺声色的弘光帝,奸佞专权、倒行逆施的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朝的田雄、刘良佐,心系朝廷却孤掌难鸣的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这些人物形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小民,既有文弱书生,也有勾栏艺人,共同成为南明王朝悲剧命运的见证者和承担者。孔尚任在用形象说明:这是一个毫无生气、毫无希望的王朝,其最终的覆亡正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撇去侯李情爱,南明依然要在这些人物的见证中走向不可挽回的灭亡,而如果无政治色彩的附丽, 侯李之爱仅仅是十里秦淮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风流韵事而已。在此意义上,情爱和兴亡的组合仅仅是一种表现的需要,这里的情爱不过仅仅是个透视社会的窗口而已。
除了用人物群像堆砌出南明末年的无法逆转的衰颓之势,孔尚任安插的纲领性政治主题在《桃花扇》的情节铺陈中也可见端倪。侯李的结合是因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的斗争促成,燕尔新婚的旖旎风光就布满了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两人的结合,不单是出于对才貌的倾慕,更主要的是对与东林党人斗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高尚品行的互相欣赏和对魏宦余孽之流卑劣行迹的共同憎恶,他们的爱情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的。而侯李的离别也是由统治阶级的内讧引起的。侯、李分离之后,以侯方域为中心,联系四镇争位;以李香君为中心,展现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局面。最后,国亡家破,侯李相会于栖霞山,双双遁入空门。因此,无论由离而合还是由合到离,侯李二人爱情的深化和升华自始至终都是伴随着政治斗争展开的。作者通过这种“表深层结构”,表面写两人的离合经历,实则将南明王朝内部矛盾的激化直至败亡的全过程寓于剧本深层。
事实上,《桃花扇》所反映的南明兴亡史并不长,只一年左右。但这一年却充满了各种复杂矛盾,有农民起义和封建政权之间的阶级矛盾;有入侵的异族统治者和南明之间的民族矛盾;还有南明王朝内部的矛盾;等等。《桃花扇》集中笔墨写了南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一方面是昏君福王以及只知倒行逆施的权奸马、阮等人,一方面是主张抗清的史可法,复社文人和下层人民等,两方面人物围绕着抗清卫国还是降清误国展开冲突,至于剧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冲突则很少,而侯李与其他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却很多。从剧本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仅在第七出《却奁》中有所表现。至《辞院》后分两线进行,主要写男女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正面冲突,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完全从属于政治斗争过程中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在一般的爱情主题剧,如《长生殿》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冲突较多,而男女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正面冲突很少。就《长生殿》上本所反映的剧情冲突看,有李杨爱情专一与不专一的矛盾,有梅妃失宠与贵妃得宠的矛盾,有忠与奸佞的矛盾,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乐中伏祸、乐极生悲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或为李杨二人之间的矛盾起伏笔作用,或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共同推动着李杨感情的深化发展,为“钗盒情缘”的主题服务。
《桃花扇》情节中最能体现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主题的在于它的结局。《桃花扇》大胆突破了以往生离死别或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创作模式,以大彻大悟的心态坦然面对江流云转的世事,结局可谓别开生面。侯生与香君,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一个是色艺双绝的佳人,经历了重重磨难,相会于栖霞山白云庵,本该顺理成章再续前缘,演绎一段才子与佳人风流旖旎的爱情喜剧,然“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而观者以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因此,孔尚任不惜改变历史事实,以大气派、大手笔、大写意打破传统结局,刻意安排了道士张瑶星点拨二人,“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风月情根,割它不断么?”(《入道》)二人遂如梦忽醒,相逢遗恨,断然撒手而去。孔尚任赋予了侯李双重身份,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爱情中的两个主体,而是被时代潮流卷进了政治浪潮中的两个客体。侯生等复社文人惨遭镇压,已无力担负起拯救国家和民族兴旺的重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已破败,家在何处?他们无法逃避爱情与现实政治、历史责任的矛盾,只能伴随着国家灭亡的趋势泯灭自己渺小的感情。孔尚任将自己面对历史兴亡时内心的无奈与悲凉寓于结局之中,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从而“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桃花扇·凡例》)
作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桃花扇》不仅在情节上胜人一筹,其巧妙的结构也历来为人称道。《桃花扇》“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非如旧剧,东拽西牵,便凑一出。”(《桃花扇·凡例》)全剧共四十出,可分为四部分。从第一出《听稗》到十二出《辞院》为第一部分,不仅叙写了侯李的相识、别离,还写到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斗争以及左良玉要移城就粮,其中专写侯李的只有四出,仅占三分之一;从十三出《哭主》到二十出《移防》为第二部分,主要叙写拥立福王登基,马阮奸臣当权,忠臣史可法遭到排挤,四镇将领内讧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有侯李参与,有的更是压根儿没有写到侯李;从二十一出《媚座》到二十五出《选优》为第三部分,主要叙写李香君为守住贞洁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事迹和南明王朝君王腐败堕落的生活;从二十六出《赚将》到结尾的《余韵》为第四部分,主要叙写南明王朝的覆灭和南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最终命运。从以上具体的场次安排可以看出,虽然《桃花扇》的事件和侯李密切相关,但他们的情感故事并不能构成《桃花扇》内容的全部。在整部剧作中,描写侯李感情的内容不到四分之一,有十三出二人并未出场。从出场的次数看,侯方域二十出,杨龙友十五出,李香君十四出,阮大铖十四出,作为女主人公的李香君的出场次数比杨龙友还少,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情感剧是不妥当的。
若将这些割裂的场次集中,就整体结构而言,即可清楚地看出作者让侯李缺席的深意了。《桃花扇》的整体结构布局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在《媚座》出总批中,孔尚任说:“上本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本之首,皆写偷安宴游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乱系焉。”(《媚座》)作者以生、旦的悲欢离合写南明王朝的治乱兴衰,巧妙地通过一把“桃花扇”,通过“赠扇”“溅扇”“画扇”“寄扇”、“撕扇”等情节,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情节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柄诗扇成为“离合”“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观众从侯李之间的爱情故事引导到广阔的政治生活中,完成了“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创作意图。
概而言之,无论是从人物、情节还是结构分析,《桃花扇》都不是一部仅限于男女之情的爱情剧。它以一柄诗扇,串演侯、李二人的离合悲欢,展现了明末清初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 揭示了南明乃至整个明朝覆亡的根本,具有痛定思痛的进步意义。然而,一些戏曲史和文学史却扭曲了《桃花扇》的本来面貌,把《桃花扇》单纯得定性为“爱情剧”,使这面忠于事实、忠于历史的镜子被误读,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得不到充分的挖掘。无独有偶,江苏省昆剧院近期上演的《1699·桃花扇》也将其处理成完全的爱情剧,不仅将大量集中表现侯李感情的折子“串折”演出,更是删除了堪称点睛之笔、集中抒发血满胸臆、泪渍泥沙的亡国之痛的《余韵》一折,对文本理解的错失至此,无怪乎舞台面貌失真,演出毫无风骨,置疑、批评之声接踵而至!孔东塘若泉下有知,当死不瞑目矣!
王季思《〈桃花扇〉校注前言》认为,《桃花扇》“一面尽可能得忠于事实,使读者不仅当作艺术作品欣赏,而且当作有切肤之痛的历史事件来看待,这是《桃花扇》传奇所以成为我国戏曲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戏的又一原因。”剧本中丰富政治性成分和深刻政治性寓意的展现对《桃花扇》爱情剧地位发出了有力的置疑。《桃花扇》只有被正名,其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被充分发掘。由此,中国四大古典爱情剧也许需要被重新定义。
[1]孔尚任著,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洪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萧善因.试论孔尚任的《桃花扇》.社会科学战线[J].1978年,第四期.
[5]邹自振.《双峰并峙的“南洪北孔”——<长生殿>、<桃花扇>比较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丛刊[J].2006年,第一期.
——对孔尚任《桃花扇》中道具“桃花扇”运用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