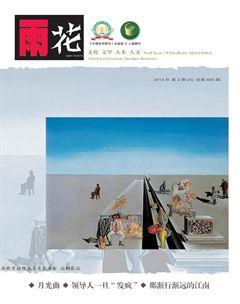苔色(外一篇)
陈元武
时光都被禁锢在那片绿意中了,何为禅—随意,率性而恬淡,随时而生随意而灭,这便是禅了。
木心禅师在森岗静心寺里的时候,特地在靠近卧房窗外筑一堵草墙——即竹篱笆墙上披络着各种藤蔓。秋末冬初的时候,藤蔓落光了叶子,只见竹片交织的篱笆墙上,参差浓淡的苔印,像一帧山水写意。木心喜欢绿的颜色,“唯四时之色,足以悦目愉心。”他喜欢苔藓之青,树叶的绿意是不长久的,如倏忽之风,随季而殒,那么,这种种意外,就是无常的提示了。木心喜欢苔藓的绿,不算太耀眼,却很耐久,并且永恒。
森岗在日本的东北部,那里的冬天是漫长的,万山凋零、雪野漫漫的时候,森岗只能看到蓝天和乌云,除之就是海雾,从山底下升上来,渐渐浸润了四野,森岗寺就淹没于一片沆瀣之间了。山间湿气一直很重,而苔藓就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冬天的雪掩盖住那堵苔墙的时候,木心每每去掸扫落在其上的积雪,而晨光到来的时候,山野里一片雾茫茫的,阳光仿佛是橙色的浓汁一样倾泻其上。“苔色于是愈来愈明亮起来,苔芽仿佛在一片焦枯的陈叶底下酝酿着重新萌出。我相信,倘若阳光再稍稍强烈一点,树上的雪就化为滴滴嗒嗒的水声,苔藓就绿成一片了。”他说的是一种假设。
四月底五月初,东京樱花开遍的时候,森岗的山也焕发出新的生机。木心的窗户挂着一卷明纸做的帘子,白天的时候收拢起来,帘绳下缀着小铜铃,他说,冬天的时候,风能够及时吹醒他的睡梦。因为冬天昼短,不可贪睡。晚间,四下阒寂,除了风和雪花飞舞。窗帘已经放下,屋里朦胧一片,屋外倘或有轻薄的月光,而积雪够深的话,那样,屋里就有一片清凉的雪光了,窗影就是明纸的颜色,那一片“朦胧的月色,多么宁静而美妙”。木心老年的时候,晚上眠浅,随时会被意外的动静惊醒。木心的夜里,有杜鹃的哀鸣,有不知名的夜鸟叫,他对弟子们说,瞧那些鸟儿,多么勤快呀。而春天到来之后,本来喜欢春睡的木心禅师却往往失眠了,他最为关注那堵竹篱笆墙的苔藓何时返绿。春天的午后,人本来已经倦怠十分了,而阳光照亮了那一片新鲜而美妙的苔藓。“一些微细的芽头,以及花苞都直立起来了,像喝足了清酒的酒徒一样兴奋。它在朝露之上跳着舞。”那时候的绿最为赏心悦目了,绿得宁静,仿佛亘古遗落的一片春意。
木心善于弹筝,茶道也是他的嗜好之一。静茶是在春末的午后进行的,静茶的参与者都身穿灰色茶袍,女居士则穿深褐色的茶袍,围坐在阶前的木几边。此时气温已经渐渐升高,夏天的影子越来越近了。茶是在寺后山上的茶园里采摘的,经过寺僧的加工,一片片绿意活泛的茶片在水盂边静静伫立着。水烧开后,木心要弹一首《春の曲》,是三叠反复的曲调,然后,那水盂里的水渐渐凉了,茶叶就可以放进去。一把竹茶匙搅动着,那水盂里仿佛就溶解了一片春色,绿意溶溶,绿得让人沉醉。木心说,茶道就是纪念春色的仪式,爱这春天,可是春天总是那么短暂而匆忙,而茶叶里收藏了这样的春意,使得我们可以时时回味。
禅茶比普通的茶道更为简单些,不需要吃那些茶叶渣子。真正的茶道是要吃光所有的茶汁,包括茶叶末子。那绿茶先焙得干脆,再捣成细末子,上茶时,茶叶末子搅到水盂中,成为浑浊的绿汤,那就是茶道了。木心心里的茶道就是苔色,茶汤绿意可人,清而不浊,绿而不腻。苔色是素朴的,茶味是微苦的,饮茶后,心里一片空茫,五内俱空,连思维也空得只剩下绿了,那种绿是刻骨铭心的。
松尾芭蕉是俳圣,也是一名执着的旅行者,松尾所处的时代,人们向往自然和率性的事物,旅行是僧人和俳人们最为热衷的事情。松尾的旅行却给他带来了忧伤和消沉的情绪,他越来越感觉世事的无常,春天短暂,而冬天总是那么漫长,道路总是那么艰难。松尾活得并不开心,远足的劳累让他身心俱疲,他抵达最后的驻足地大阪时,身体已经很差了,经常闹腹疾,便十分想念他的芭蕉庵和弟子寿贞尼,松尾是一个活在路上的人,走不动了,他的生命便告终结。“旅途罹病,荒野驰骋梦萦回(旅に病で梦は枯野をかけ廻る)”无比苍凉悲伤的俳句。在北海道漫游的时候,松尾芭蕉被厚厚的积雪所困,冬天多么漫长啊,他后来的游处都选在九洲等南日本各地,冬天不那么漫长,春天似乎更为曼妙。他酷爱的芭蕉树,只喜欢长在南方温暖的地方,而冬天的时候,这些树全都冻成枯槁的一堆,“睹芭蕉之憔悴,令人肝肠寸断。而樱花盛开的地方,积雪总是消融得迅速而干脆。”江户的松是美丽隽永的,那些松星散于四野,不高不大,如隐士般孤傲独立。京都的松太过富态,那是宫城外的松,是富商大贾们的松,没有气质。松尾所谓的气质大概就像他一样瘦弱、刚劲,饱经风霜而不失本色。
苔色大概就是松尾所谓的松的气质之色,苔藓在冬天的时候几乎隐没不见,枯燥的风和气候的寒冷会让苔藓成为一片片龟裂的碎片,随时会被风吹落,像尘埃一样飞扬。
木心的森岗寺外,处处是苔藓的印记,那简单的木栈道,竹篱笆墙,甚至是寺外的大树上,苔藓像一种心灵的扩散剂,随心或者无心,绿意沾染着视野,不需要知道春天何时发生,夏天何时结束。时光都被禁锢在那片绿意中了,何为禅——随意,率性而恬淡,随时而生随意而灭,这便是禅了。
每每看到木心的灰色僧袍的背影,就会想到他心里的那抹苔色,不管他走多远了,你还能看见。森岗寺外有一个牌子提醒游客:小心你的脚下,别踏碎一片苔色。
楮心未满
楮树,也名构树,树叶如心而残缺。过去,楮树皮是制纸的原料,楮树易蘖枝条,越砍越长。黄蘖禅师客居东林寺的时候,喜欢寺后山崖边的一片楮林,秋至而叶尽黄,随风片片飞。夏天的时候,楮实红艳如花,灿若桑椹籽。黄蘖禅师更喜欢楮树叶的形状——似心而未满,残缺的心形就是佛的一种暗示,世事无所遗憾,只有心之圆亏而已。楮树叶在提醒着佛子们,心永远是残缺的,万物皆有残缺,并无十全十美之事。佛教里有一个重要的数字就是七,从一到三,是芸芸众生世,而修行者则从三开始一直完善到了六,已属大不易,至七则满,满则涅槃,人就得往生了。世上有七种好,好音七个音阶,好色七种: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宝莲花,七种宝为金、银、玉、玛瑙、砗磲、玳瑁、珍珠。从来就没有像八、九这么美满的事情,更不用说十了。可是人们一生追求的不就是十全十美的梦想么?佛说徒劳,人们不信,继续挖空心思徒劳着人生。
楮树之美,在于它的不完整,它有叶似桐而材不济于琴筝,有枝蔓妙而形不济于修竹,能花而实,却无桑椹之美,擎如华盖而经不得风雨摧折。古人善于总结,于是,楮不上轮毂,实不上俎豆,就是说楮这种木材,是做不得车轱辘的,而楮实更是不上大雅之堂的。楮于是沦为草根一族,幸好,它还是有所取的,那就是楮树皮可制纸,并且是上好的宣纸。闽西连城一带原有古老的雕版印刷业,其印刷用纸必须是楮树皮制作的,它防虫防霉防老化,吸墨性均匀而稳定。楮树皮富含中长纤维,韧性强而耐机械磨浆。连城那里的制纸工艺也是古老的:楮树皮经过舂碾,浸淘,压榨和蒸煮后,就成为可用的木浆了,楮树皮富含鞣质酸,虫子不喜欢这样的纸质口味(麻涩大苦),而楮宣纸质细柔绵劲,适合做线装册页和绘画书法。
黄蘖禅师往往一青笠,一芒鞋,一竹杖,游于四境,他走得不远,就在山里转悠。躲避那些慕名而来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的滋扰,黄蘖禅师沿袭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圆顿止观”的观法大体,即允许对佛经和禅作各种阐释和援引。总体一点就是忘记身体,将身心融入自然。黄蘖禅师提倡僧人们要向自然学道悟道,他自己称是黄蘖树下弟子,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佛经历了雪山修炼和诸多磨难。光坐在寺里念念经是悟不了道、成不了佛的。诸方世界,十分婆娑,不是一言一语所能概括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而当时有的禅宗流派好大喜功,总是嘴里挂着圆满的觉悟二字,却不知如何去实现这些理想。黄蘖禅师不以为然地说,何曾看见月满天,何曾看见花满枝,春色须臾尽遁去,江天依旧水茫茫。他不提倡圆满和臻功极悟。明月一时圆后残,花朝才过满地绯,须臾青丝换白发,秋天倏然便到来。青案一枚菩提子,何日供养到天明?他是个哲学家,他所说的不圆满或许正是禅的最深奥义。楮心未满何处满,缸至满时水溢流。佛经里没有说过圆满二字,圆满何处去求来?
黄蘖禅师在世时,并未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以至于后来他东渡日本开创日本黄蘖禅宗一派,是对天台宗的发扬光大,至今日本奈良的黄蘖禅寺里依然香火旺盛。黄蘖禅师的即时圆满和顺世哲学影响了日本的许多人。
人生本来就是处处遗憾处处艰难的,人心圆满时,即真圆满,而世事是不可能圆满的,黄蘖禅寺外并无黄蘖,却有楮树满山。秋天,满山杏黄的楮树叶子,仿佛禅心菩提,那个心形的残缺,多么美妙。
印光大师十分景仰黄蘖禅师的德行和法倡,“旧年曾见黄蘖子,盘岩之上树婆娑,芒鞋竹杖谁秉持,非是心空何意空?”心空,则性空,性空则灵现,灵现则知佛意,是为禅法妙谛。近代另一位高僧弘一法师,虽为律宗长老,却实是禅宗大师。他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万般倏忽,一性天然”的天台宗法。随意而自然,是修禅的要谛,却不需要做作和伪装。真心空性空,佛性才会体现。而残缺是心空的第一步,如楮之未满,如楮之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