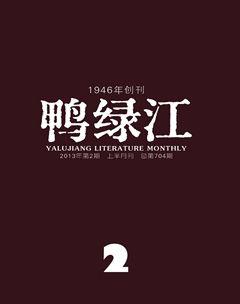蟋界风云
聂鑫森,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中文系作家班。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五十余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越南等国文字荐介到海外,出版过英文小说集《镖头杨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首届湖南文艺奖及其他文学奖。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说某某在某一行当技压群雄,往往称之为里手,也就是行家、内行的意思。这当然是一种泛泛的称谓,若落实到具体的行当,则又有另外的说道。围棋、象棋中的翘楚,名之曰国手。专门负责对死囚行刑的,称之为“刀手”,往往在三声追魂炮响过后,一刀下去,快如闪电,头断而又腻腻地连着一块皮,留得一具全尸。收人钱财,指名要将某人结果性命,取头颅如探囊取物的,谓之杀手。还有轿子抬得好的叫“轿手”,纸马活做得形神具备的叫“扎手”,泥水活操得漂亮的叫“砌手”,澡堂子里擦背擦得交口称赞的叫“擦手”……
俗语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还有一个行当:操虫手,不知诸君听说过没有?何谓操虫手,就是在鉴赏、饲养蟋蟀上名重一时,听蟋蟀之声,而知其体质强弱,看蟋蟀之形,而知其属哪个名品,一经他悉心调教,在一场场拼斗中,往往胜多负少。
在民国初年的湖南古城湘潭,可称之为操虫手的倒有几个。夏小满便是此中人物,不过,他的名号比其他人多了一个字,叫:操虫圣手。
夏小满从十五岁起开始给顾三爷当“操虫手”,一做就是五年。如今二十岁了。圆圆的头,亮亮的眼睛,一对卧蚕眉;身子骨壮壮的,厚厚的胸脯子把衣襟鼓得拍满。他常常觉得铁块似的腱子肉绷得很难受,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往外拱。在街上偶然看见年轻的女子,心就突突地跳。
顾三爷有一次很和气地对他说:“小满,你大了,该寻个媳妇了。”
是的,该寻个媳妇了。家里无田无产,爹娘又常年有病,靠着他每月把工钱捎到乡下去,谁愿意上门呢?想着想着,他就叹口气。平心而论,找这么一门职业不容易,吃住在顾三爷这里,工钱也不少,顾三爷待人又好,真的,有钱的人像顾三爷这样的太稀罕了。不就是侍养几条虫么?只有顾三爷这样的人家才雇请一个专人,因有雄厚祖业,这几个钱不在乎,大半辈子活得很是自在。顾三爷很会玩,会唱一口好京剧,会画画,会作诗,会看古董,对于玩蟋蟀更是痴迷到了极点。他很看重夏小满,说小满岂止是“操虫手”,简直可以称为“操虫圣手”。
夏小满是真正懂蟋蟀的。从几岁起,在乡间掏蟋蟀、养蟋蟀,又喜欢打听些陈年旧事,心眼又活泛,以致在那一块地方很有名气。他知道什么地方有蟋蟀,听一听声音就明白这头蟋蟀值不值得去掏。他只要看一看蟋蟀的颜色,青、白、黑、红、紫、黄,看一看蟋蟀的形体,就知道属于什么品种,一口就能叫出名字来,和尚头、五花斑、绣花针、寿星头、梅花翅、豆油灯、红沙青、紫黄虫……他懂得一整套侍养蟋蟀的方法,喂什么样的水,供什么样的食,怎样强壮筋骨,怎样坚固牙门。听的人惊呼:“这虫如此娇贵,谁个还敢养!”
深秋到了,寒气重了,夏小满将老盆换成新盆,新盆必盆底光滑,天天拭擦得洁亮如镜,蟋蟀在里面站不稳,只好走动,才不会因蛰伏而养成惰懒,筋骨便不衰老;另外,不断促其与三雌交尾,令其体内通窍,充满青春的活力。夏小满更绝的招数,是可以让蟋蟀顺顺当当活到春节,甚至可以在大雪天让人看到斗蟋蟀的奇景。
顾三爷的蟋蟀在古城的争斗中,威风八面,总是得胜的时候多。赌注虽有大有小,他却并不看重,看重的是名声。顾三爷玩什么都能玩出名堂来!
不知道为什么,夏小满顶喜欢看蟋蟀交尾。在顾三爷题写横额的“促织室”里,门关得紧紧的,他一个人蹲在一个盛着一雌一雄的大盆前。雄虫瞥见了雌虫,两片翅向两侧下方斜拉,使双翅磨擦,发出“嘀铃、嘀铃”的喜悦之声,俗称“弹琴”。雄虫听到这声音,急急地奔过来,紧紧相挨。雄虫先是不断地摇摆腹部,后腿插入雌虫下面,雌虫立刻主动地爬到雄虫的背上。这真是一件怪事,蟋蟀交尾竟是雄在下,雌在上。雄虫一边“过蛋”一边发出很快意的喊叫。
夏小满看得一身发热,然后,“呸”地往旁边吐一口唾沫,莫名其妙地骂一声“他娘的”,回到自己的卧室,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转眼又到了白露节。
古城各处开始斗蟋蟀了。
每到这时候,顾三爷就特别兴奋,酒也喝得特别多。他把家眷晾在一边,倒常把夏小满叫来同桌吃饭,一边喝酒,一边和夏小满说些闲话,脸红红的,哪里看得出他已年过半百了。
“小满,今年这几头蟋蟀怎么样?”
小满呷了一口酒,问:“什么?哦,顾三爷的蟋蟀头头帅气哩!”
顾三爷哈哈大笑。
“小满,你上次说到验证一条好虫,要看八个部位,即头、钳、脸、项、翅、腿、肉身和须;又说细分则有十二个要素,为虫形、虫声、虫头、虫眼、虫牙、虫项、虫翅、虫身、虫尾、虫小足、虫大腿及虫须,这须怎么如此重要呢?”
夏小满说:“三爷,一条好虫,生相俱全,配上一对美须,就显出了精气神,威武哩。双须要油黑光亮,长且灵活,搅扰不定,才是最好的。须有脆须、竹节须、鸳鸯须、卷须、结须、独须、蝴蝶须种种类别。”
“何谓脆须?”
“凡斗一次,须短去一截的,则称脆须。如果双须断得一般长短,这种虫可称上品之将,十斗则有九胜。”
顾三爷说:“此生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虫。”
“将来你会有的。”
顾三爷摇摇头,说:“玩什么都有个到头到底的,不可沉溺。”
夏小满有些疑惑地望着顾三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当操虫手五年了吧,细伢子长成大人了,该做一门正经事了。”
“三爷,当操虫手不是正经事么?”
“唉。你不懂。”
“明天去‘玉楼春茶馆么?每年的第一场开斗都在那里,看的人好多!”
“去。我顾三爷哪能不去。小满,明天带两条好虫去!”
“好的。”
小满一口喝光了酒,眼光有些散乱。
第二天,吃过早饭,夏小满端着蟋蟀盆跟在顾三爷后面,到了“玉楼春”。
“三爷,请您的安!”
“三爷,早!”
顾三爷彬彬有礼地应答着大家的问候,然后拣一张正中的八仙桌坐下来。
茶博士趋上前来,问:“三爷,喝什么茶?”
“君山旗枪茶!”
“好咧。”
夏小满一直站在顾三爷的身后,好像一个侍卫。
顾三爷悠然地品着旗枪茶,满口芬芳,说一声:“好!是谷雨前采的,味正。”
到十点钟的光景,店堂里一阵骚动,拥进一伙人来,打头的是个衣饰华丽的年轻公子,一进来就问:“哪位是顾三爷?”
顾三爷兀自品茶,好像没有听见。
那人径直走到顾三爷桌子前,说:“您可是顾三爷?”
“正是。”
“这就好了。在下叫王金成,闻说顾三爷有上等蟋蟀,特来领教,不知可否一试?”
顾三爷笑了笑,说:“王公子既有好虫,可否让我开开眼。”
王金成一挥手,有一黑脸汉子端上一只紫砂盆来,搁在桌上,小心地打开盆盖。
顾三爷眼风一扫,不过是一只极普通的“七宝虫”!
旁边的人也看清了,都一齐笑起来。
王金成说:“虽是一只无名小虫,但愿与顾三爷下注开斗,决不反悔,不知顾三爷是否赏脸。”
顾三爷不屑地说:“下什么注,你只管说。”
“一千大洋!”
“太少了。”
“二千大洋!”
“五千吧。”
“行。”
店堂里顿时沸腾起来。
夏小满悄声说:“三爷,何必下这么大的注呢?”
顾三爷装作没听见,说:“小满,双方验虫。”
夏小满把蟋蟀盆搁在桌上。
双方的操虫手互相验看蟋蟀,主要是看大小是否相差不多。
验过了虫,在另一张八仙桌上,摆开了一个很大的紫砂斗盆。斗盆是长方形的,两虫各占一端,用闸门关着。
顾三爷和王金成各站一边,手执斗草,等待公证人开闸后,好打草引虫。
顾三爷望望王金成,说:“王公子,你若犹豫,还可更改。”
王金成头一昂,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谁输还不知道哩。”
当闸门抽开,两虫抖须急蹿上前,鼓翅舞爪,鸣声尖锐如剑,刺得观者的头皮发紧。
顾三爷的是一头“正青”,刚要去咬那头“七宝虫”,竟一时愣住,威风顿减。“七宝虫”跳上前,疯狂撕咬,什么也不顾忌。
夏小满的脸别在一边,不忍看这惨景。
“正青”败下阵来。
顾三爷放下斗草,一拱手,说:“老夫认输。”从怀里拿出一张银票,递过去。
“再来么?”
“来又何妨。”
夏小满又将一头“五花斑”放人盆内。
不出三四个回合,又输了。
夏三爷再拿出一张银票递给王金成。
店堂里静寂如坟场。
顾三爷的上等蟋蟀怎么败得这样惨呢?真是咄咄怪事!
顾三爷对夏小满说:“走吧。”
他脸带着微笑,从从容容,潇潇洒洒。
回到家里,顾三爷便病了。他不是惜财,是丢不起这张老脸!
这一天傍晚,顾三爷把夏小满叫到床前,说:“我本打算斗完这场蟋蟀后,就让你回家去。你爹娘盼着抱孙子,你也该有门正经手艺。当操虫手不是长远之计,假若世道不太平,没有了这些有余钱剩米的人玩蟋蟀,这操虫手还有什么用。我给你准备了一笔钱,买几亩田,讨一房亲,好好去过日子吧。”
夏小满泪水猛一下溅出眼眶。
“别伤心。反正我也不打算玩蟋蟀了。我这辈子爱的就是这个面子,这个跟头我栽得惨。我很奇怪,那条‘七宝虫怎么会这么厉害?”
顾三爷闭上眼睛,觉得非常疲倦,再不想说话了。
第二天,顾三爷让管家给了夏小满一千块光洋。
夏小满对管家说:“我过几天就走,请你告诉顾三爷,我在城里还要办点事。”
五天后的一个中午,顾三爷在喝过一盅汤药后,觉得精神稍稍好些,便独自在花园中散步。园中的菊花开得姹紫嫣红,到处弥漫着清苦的气息,很好闻。他自感这段日子瘦了许多,腰间的皮带移过两个孔,而酒是无心品呷了,忽然得到两句诗:愁多旧带频移孔,病起新刍久覆觞。这可以作为七律中的一联,有了这两句,整首诗就好做了。
老管家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三爷,你胜了!”
“什么胜了?”
“斗蟋蟀胜了。夏小满以你的名义去和那王金成开斗,带着你给他的钱下注!”
“夏小满呢?这伢子!”
“死了。”
“怎么死的?”
“我刚才听人说的。夏小满验虫时指出那条‘七宝虫是由一种中草药喂养的药水虫,身上带着毒。公证人宣布上一场的赢家是你,并指令姓王的换虫开斗。开斗之前,先退回那两张银票。”
“那么说,此后的开斗自然是夏小满赢了?”
“是的。赢了后,夏小满喊道,‘是三爷的虫打胜了!是三爷的虫打胜了!”
顾三爷顿时神气上扬,双眼发亮,急急地问:“既然赢了,怎么小满却死了呢?”
“赢了后,那个王金成对夏小满说,‘你当初是应允了的,不拆穿这个西洋镜,事成后,付你一千大洋,你怎么翻悔了?你发过誓的,翻悔了就应该去死!夏小满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说:‘大丈夫说到做到!当初我一时糊涂,受了你的诱惑,我对不起顾三爷!然后一刀子插到胸口上,身子再往桌子上一伏,让刀插了个透穿,人就气绝了。”
顾三爷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上。
“快把夏小满抬回来!再派人去,把他的父母接到这里来!”
夏小满的丧事办得轰轰烈烈,顾三爷亲自为他点主、读祭文,然后,哭得死去活来。在灵堂前,他把那两张血染的银票,当纸钱一把火烧了。
夏小满的爹娘站在灵柩旁边,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顾三爷真是个好人哪!
此后,他们一直被供养在顾府。顾三爷虽说年纪和他们不相上下,却谨慎若子,小心地侍奉着这两个老人。
那些名贵的蟋蟀盆呢,早没了,早埋到夏小满的坟堆里去了。
责任编辑 郝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