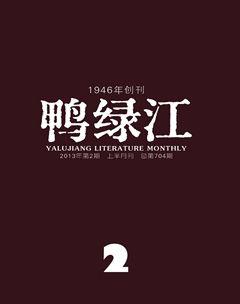中国新诗精神危机的成因探析
姚国建,男,中国写作学会理事,安徽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安徽省诗歌学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蚌埠学院写作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前,中国新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称为诗人的人越来越多,写诗似乎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随意,大量诗作通过报刊、民间诗刊、自费诗集以及网络诗歌等,如潮水般涌出。诗坛内热热闹闹,诗坛外冷冷清清,广大读者对新诗已由不满、失望到弃之而去。著名诗歌评论家孙绍振先生早在1997年就撰文《向新诗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以惊人的判断、罕见的口气警告一些人,如果继续“把任意性当作艺术”,其结果只能导致新诗的危机,必然让新诗“受到历史的嘲笑。”[1]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新诗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大,诗的面貌毫无回转的迹象,以致一些学者感叹:“诗歌病了。诗歌本身变得有气无力了,更严重的是迷失了自己了,找不到方向了。”[2]对此,任何一位热爱诗歌、关心中国新诗发展的人,都不能不在痛心疾首之余,开始冷静地思考:当前新诗问题的症结在哪?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关键的一条,就是新诗在进入社会转型后出现了新的精神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既有客观外在的因素,更有诗人的主观因素。为了更好地对新诗把脉问诊,寻求医治的良方,我们试图对新诗出现精神危机的成因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
从总体上看,造成新诗精神危机的原因既有诗的外在因素,也有诗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主要是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各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当代诗人、当代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诗人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存环境、精神状态也随之受到巨大的影响,传统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这场大潮中受到冲击,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日益商业化、世俗化、功利化、复杂化,人们一方面面临激烈的生存竞争,一方面又渴望迅速发财,一夜成功。许多人为了利益甚至不择手段,投机钻营。诗坛也不例外,这种外在的冲击使得很多诗人变得心态浮躁,欲望频生。不少诗人迅速弃诗而去,或投身商海,或改谋他业,或远飞异国他乡。即使是对诗歌不离不弃的诗人,也开始把写诗当作自己的副业或兴趣,他们很难做到处变不惊,潜心写作,创造出感动读者、足以传世的诗歌精品。而一些年轻诗人,则难耐寂寞,一门心思追逐时尚,寻求捷径,梦想以自娱自慰式的轻轻松松的写作,迅速加入诗人俱乐部。这是社会的变化促成了诗人观念的变化,也为他们的人生及其诗歌写作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第二,多元文化带来诗歌追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各种外来文化如潮水涌进,加上国内传统文化、各民族文化的全面激活,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深刻地影响到各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可以说,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培育和激活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艺术追求,大量时尚的、猎奇的、怪诞的、庸俗的、游戏的快餐式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作为感应最灵敏的中国新诗,在这场历史的变革期,更是以其活跃的身姿、强大的阵容、大胆的宣言、强劲的出击,一路呼啸,狂歌猛进,从而直接导致中国新诗面貌的变局。各种各样的诗歌宣言,颠覆了传统的诗歌观,多种形式、多种格调、多种品味的的诗歌作品令人惊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一些非诗的作品当然也充斥其中。
第三,环境宽松带来诗歌写作的自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更加宽松,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氛围日益浓厚,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采取了更加宽松、开放、理性的态度。管理部门再也不像极左年代那样,用政治的放大镜去寻找作品的疑点,以便扼杀作品、批判作者甚至制造一起又一起文字冤案。不仅如此,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民族文化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推动文化战略的实施,支持和激励我国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这是百年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和强盛的标致。中国新诗正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下获得了极佳的发展机遇。诗人的写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诗人的艺术主张、诗人的创作个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诗人的思想、情感和内心欲望都得到自由的表达。诗歌发表和出版的空间也较过去广阔和自由,各类民间诗刊极为活跃,各种自费诗集获得自由出版。即使诗歌鱼龙混杂,问题不少,但批评家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都是自觉地将这些问题置于学术语境,再也没有人因为一首诗、一本诗集或一种诗歌观而遭到政治的打压。可以说,没有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大量的新诗之花,就无法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开放。但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诗歌也泥沙俱下,呈现出丰富而芜杂、缺少精品与力作的态势。
第四,网络时代带来诗歌传播的便捷。比起传统纸质媒体(公开出版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网络时代以无与伦比的优势,为诗歌的传播打开了神奇的网络大门,只要鼠标轻轻一点,诗歌就以第一速度到达诗歌现场,出现在各类诗歌网站,进入网上读者的视野。这中间省略了纸质媒体的那种层层审阅和把关,使诗歌的发布、传播极为便捷,并且还可以借助网络媒体实现现时互动,开展诗歌的交流与讨论。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为诗歌的写作和传播敞开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很多年轻人顺应时代的潮流,纷纷搭上这种网络特快,迅速实现了自己发表诗歌、做一个诗人的梦想。当然,网络诗歌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很多人都忽视了诗歌艺术的挑战性和写作难度,降低诗歌的精神追求,把诗歌写作当作口语表白或简单的文字游戏,致使大量粗制滥造、毫无精神品位、毫无诗意甚至是文字垃圾的诗歌泛滥网络,最终使读者望而生畏,对网络诗歌产生厌倦和反感。
二
以上几点都是试图从外在寻找造成诗歌精神危机的原因,很显然,这些外在因素只有通过与诗人的主观因素相结合,才能对诗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这些外在因素本身从客观上为新诗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但如果有人对此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为诗歌到了一个可以不要诗魂、不要诗格,可以随意写作、任意把玩的年代,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造成对新诗的极大伤害。不幸的是,中国新诗在迎来了一个百年难得的发展机遇时,却恰恰被这些新诗的玩家们弄得失魂落魄,狼狈不堪。
可见,造成新诗精神危机的主要原因还在诗人的主观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责任感的缺失造成诗歌精神的下滑。诗人不仅没有抓住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机遇,把它转化为自己写作的动力、责任和使命,反而有意解构传统意义上的诗人角色,主张低姿态的向下写作,这本来也有利于新诗回归人本写作、真实写作、自然写作,但是,诗人在一致推进这种向下写作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诗人普遍降低对自身的要求,放弃诗人的社会理想和责任,直接导致了诗歌精神和诗歌品位的严重下滑。责任感的缺失具体表现在:首先,诗人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在他们看来,“责任”、“使命”这些都是过于宏大、过于虚伪的陈词滥调,诗人不必去理会。韩东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写诗就是写诗”,不必有其他更大的目的、责任和义务。沈浩波认为:“承担和使命,这是两个更土更傻的词,我都懒得去说它们了。”[3]在他们看来,诗人不必思考,不必做思想者,除了关心自我,竭力写另类的诗以突显自己外,不必过问人间冷暖、世道人心,不必把关怀底层人民、批判社会黑暗、呼唤公平正义、塑造人类灵魂、推动社会进步等等重任扛到自己肩上。他们放弃做一个严肃、高尚、有正义感、责任感的诗人,也放弃做一个品格纯正、充满热情、健康向上的人,而是以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做蔑视传统、反抗权威、解构崇高、拒绝文化、放弃责任、迎合世俗的诗坛急先锋。这就导致诗人精神境界、人格魅力及诗歌追求的下降,也直接影响诗人对写作对象的态度和感情。例如沈浩波的《乞婆》一诗:“趴在地上/一蜷成团/屁股撅着/脑袋藏到了/脖子下面/只有一摊头发/暴露了/她是个母的//真是好玩/这个狗一样的东西/居然也是人”面对底层一个卑微、可怜的生命,诗人没有一点同情心也罢,何至于用如此尖刻、鄙夷、谩骂的口吻,去嘲弄她,侮辱她。这是以前诗歌里从没有出现过的,读后令人震惊,充分说明诗人悲悯之心和人性关怀的缺失。这样的诗人怎么可能心系民众,写出感动民众的诗篇。正如谢冕指出的那样:“诗人只关心自己”,“于是民众也就自然而然地疏远甚至拒绝了诗。”[4]
其次,诗人放弃了写诗的责任。由于诗人放弃了崇高的诗歌理想和庄严的诗歌使命,他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都变得毫无顾忌,为所欲为。特别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他们已经自我降格,没有精神的底线。他们主张诗歌取消思想、取消意义、取消审美、取消价值、取消诗意等等,把诗歌追求引向语言实验、日常记录、肉体展览、欲望表达甚至“下半身”书写等等。在一些人看来,一切严肃的、重大的、沉重的、美好的主题书写,都是不可靠的、虚假的、骗人的、过时的,他们对此不屑一顾,极力贬低。他们认为“艺术的内容也是唯一的——形而下。”[5]他们如此对待诗歌,怎么能创造出高格调、高境界的诗?
再其次,诗人放弃了对读者的尊重和责任。一些诗人无视读者的存在,根本不考虑他写的诗对读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会顾及读者的接受度和容忍度。他们按照自己的诗歌设想,以一种随意、猎奇、游戏的态度对待新诗写作,既不会在艺术上呕心沥血、孜孜以求,也不会在思想内容上认真选择,精心提炼,力求以健康的精神、完美的诗境带给读者诗意的享受。他们以自己随手炮制的劣诗、伪诗或歪诗,来败坏读者的胃口,摧毁读者的期待甚至污染读者的精神。他们还容不得读者的批评,仿佛他们泼给读者一盆脏水,读者也得默默忍受。
第二,诗歌观的偏激导致诗歌内涵的平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诗歌观蜂拥而出,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群体大展”,一下子推出六十多个社团,各个社团纷纷亮出自己稀奇古怪的名称及五花八门的诗歌主张。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年写作”、“红色写作”、“个人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肉身写作”等等相继而出,不同诗派之间还就观点的分歧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应当说,这些诗歌观的提出,有利于打破“朦胧诗”所形成的诗歌格局,激活了新诗的创造力,形成多彩多姿的诗歌面貌,产生了一批新异的诗歌作品,大大拓展了新诗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这些诗歌观的提出,没有经过严密的思考、科学的论证及大量的创作实证,有的仅是某个代表人物为了标新立异所作的宣言式的表达,显得非常偏激或片面,这就影响到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写作时的价值取向,导致诗歌内涵的平庸。如从“非非主义”提出“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6]到“下半身写作”则延伸为:“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让他们去当文人吧,让他们去当知识分子吧,我们是艺术家,不是一回事。”[7]他们还特别强调拒绝思想、消除诗意,认为:“只有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什么叫作诗意,这个词足以让人从牙根酸起,一直酸到舌根。这个一点现代感都没有的酸词只能被那些学院派的冬烘先生奉为至宝。而对于现代艺术来说,取消诗意将成为一个前提。”“我们要让诗意死得很难看。”否定和排除了这一切后,他们把诗歌写作定位在一种“贴近肉身状态”的“下半身写作”,追求“一种贴近肉体,呈现的将定是一种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8]如果说,这些观点是出自诗人对僵化的意识形态、落后的文化观念、保守的诗学观念长期束缚诗歌的反抗,力求恢复诗的生命感、本真感,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这些观点本身把话说得过于绝对,为了强调自己的一点,却不惜否定一切,显然是极端偏激的。难道诗人及诗真的与“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等等脱得了干系吗?一些诗人在排斥别人的诗歌观,极力宣扬自己的诗歌观,并用各种办法推行同类的诗歌,不也是在进行自己的诗学思考,履行自己的诗歌职责吗?一些诗人挖空心思,用亵渎一切美好的语言,写着解构“崇高”和“庄严”的诗,不也是受西方文化及解构主义的影响吗?今天的人们对“诗意”的理解早已非常宽泛,取消一切“诗意”,诗还剩下什么,诗还靠什么来吸引读者,感动读者?诗人周伦佑也强调“诗歌是灵魂的事业”,难道“下半身写作”能将“灵”与“肉”分开吗?失去灵魂的肉体能带给我们什么?还有“诗到语言为止”“写诗就是为了写诗”(韩东语),“怎么写都是诗”,“诗语言,应如驴叫,怎么得劲怎么嗥”[9]其本身强调语言对写诗的重要性,强调诗歌写作的独立性,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实践中,有人误以为写诗就是语言游戏,就是玩语言,就是在语言形式上花样翻新,甚至用未经提炼的口语、大白话直接拼凑,忽视语言背后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等诗意的凝聚,这就导致有些诗徒有语言的形式而缺乏诗美特征和精神深度。何况真正的诗歌语言一定是与诗人的生命和灵魂息息相依,一定是发自诗人生命内部和灵魂深处的语言。诗人生命的方式和灵魂的向度直接决定着语言的生成。任何人以游戏语言的态度写诗,都注定写不出有生命感、有思想深度的诗。总之,我们认为一些偏激的诗歌观已直接影响到诗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容易使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反叛意识的支配下,一阵风似地倒向“向下写作”,忽视提升灵魂和凝聚诗意的“向上写作”,这就难免造成诗歌精神的整体下滑。
第三,心态的浮躁引发诗歌竞争的错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诗人也耐不住寂寞,他们心态浮躁,渴望快速成名,出人头地,而诗坛同样是充满激烈竞争的赛场,没有过人的精神修养、艺术禀赋,不经过一番辛勤的耕耘,是难有收获、难以脱颖而出、难以超越他人的。于是一些人便不在诗本身的竞争上下功夫,而是极力施展“诗外功夫”。首先,他们打出各种诗派的旗号,发表各种新奇的宣言,拉帮结伙,大造声势,用类似搞运动的方式,获得公众的注意;其次,他们无法创造出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作品,又想尽快戴上诗人的桂冠 ,便大写另类的诗歌,怎么出格怎么写,怎么引起关注怎么写(哪怕挨骂)。正如于坚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机会主义。对有些诗人,他觉得怎么能引起注意,怎么抢眼怎么写。”[10]他们追逐时尚,迎合世俗,以大量庸俗、粗鄙、低级的诗歌吸引一些眼球。“还有一部分新诗人不甘寂寞,搞起一些‘下半身写作,或者‘裸体行为艺术之类的创作活动,结果的确在社会上搅起一些水花——不过同时也招来不少口水。”[11];再其次,他们写文章,发表谈话,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诩代表新的诗歌流派,要取代原有的诗歌流派。他们批判别人,抬高自己,认为别人的诗歌观念早已落伍了,别人的诗歌早该淘汰了,企图以揭竿换代的方式,为自己在诗坛争得席位。如沈浩波就以“下半身写作”向“他们”派宣称:“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的时代开始了。”[12]而以解构思维写出《车过黄河》的伊沙,就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大胆和写作策略。他在《车过黄河》中把“列车经过黄河”与自己“在厕所小便”联系起来,以一种亵渎性的语言,彻底颠覆黄河身上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由此,他不仅获得了解构的快感,还无比自豪地宣称:“我为汉诗贡献了一种无赖的气质并使之充满了庄严感……我使先锋与前卫姿态变成了常态——汉诗的‘后现代由我开创……”[13]你看,用“身体”就能打倒“语言”,用一泡尿亵渎一次黄河就能获得一首颠覆传统的诗,还能开创一个诗的时代,写诗成名是多么容易,多么快捷。诗人朵渔也承认:“如果能够让人们谈论,这件事已经做成了一半,我是相信‘功夫在诗外的。”[14]可见,一些诗人由于心态浮躁,不是在正道上展开诗的竞争,不是在提升自己的灵魂、提高诗歌艺术质量上竞争,而是在做你过时我先锋、你下台我上场的竞争,这既不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诗人应有的气度和心胸。对此,诗人、诗论家郑敏早就告诫过青年诗人:“诗坛不是坟场,而是超越时间的角力场”,诗的竞争关键是“质量的优劣”的竞争,“每颗新星要多想如何增添天空的灿烂,而不是如何击落哪一颗已存在的星星。总是想着一个流派,一个代的诞生就意味着前者的死亡,恰恰是统治我们多年的一元化逻辑的翻版。”[15]
当然,诗的内在原因除了诗人主观因素外,也还有诗坛本身生态环境的问题,例如,在诗坛内部,有的人悄然离诗而去,有的人对诗的热情日益下降,诗歌界针对新诗出现的种种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不够,不少诗歌批评家也表现出对新诗的失望和冷漠,以致形成诗歌批评的失语,这些都使得诗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诗的精神品位和艺术标准,使新诗在一种放任自流、恣意生长的状态下,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精神风采和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综上所述,造成新诗精神危机的原因既有客观外在的因素,也有诗人的主观因素。外在因素对诗人的精神状态、诗歌观念、诗歌价值取向、诗歌写作方式、传播方式等等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使一些诗人难耐寂寞,在盲目跟风、追逐诗歌新潮中迷失了精神方向,导致诗歌精神的严重下滑。很显然,解决新诗精神危机的关键还在诗人本身。如果诗人能正确看待和把握外部因素的变化给新诗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并且能够明辨是非,通过自己的精神坚守和积极追求,将外部的某些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新诗就不会跌入精神的迷谷。阐明这一点,意在提醒当今的一些诗人,应赶快迷途知返,从读者期待、社会需求、艺术价值等层面,重新认识如何做诗人、如何写诗,进一步增强诗人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注意维护诗歌的精神品质,纠正诗歌的价值偏向,提升诗的精神境界。果真如此,中国新诗就一定能走出精神的困境,重获读者的信任和青睐。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AHSKF09-10D67)
注释
[1] 孙绍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星星》,1997年第8期,第66页。
[2]吴投文《当前诗歌症候分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4期,第107页。
[3][5][7][8][12]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下半身》创刊号,2000年7月。
[4] 谢冕《诗歌理想的转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6] 引自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84页。
[9] 徐敬亚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 于坚 傅元峰《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第135页。
[11] 黎志敏《诗学建构:形式与意象》,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165页。
[13] 伊沙《伊沙:我整明白了吗——笔答〈葵〉的十七个问题》,《诗探索》,1998年第3期。
[14] 朵渔《是干,而不是搞》,《诗江湖》创刊号,2001年。
[15]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413页。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