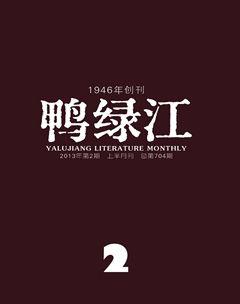远望长春为破颜
杨东阁,笔名程鑫,1932年生,吉林舒兰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接收沈阳的军事代表,沈阳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副主席,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厅主任,市委副秘书长。曾获中国民歌优秀词作家称号。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
郭沫若有诸多诗作传世,如《凤凰涅■》《女神之再生》,堪称精品。可深留在我的脑海中的,是郭老于1962年4月为“新旅”小友范政题的一首诗:“一曲洪波越海山,旅行小友忆新安,东风吹送人忘老,远望长春为破颜。”因由只有一个,范政曾经是我的领导,是我心怀崇敬的人物和悉心学习的榜样。
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接触到什么样的人,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其后续作用往往是巨大的。范政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占有重要地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成为我真诚向往的楷模,以至影响到我后来的人生。
1947年冬,我被组织保送到哈尔滨一所财经大专学校深造。一部中篇小说《夏红秋》刚好问世,一时“洛阳纸贵”,风靡东北。作者的名字叫范政。当时只知道他是《东北日报》的记者,心生仰慕,却无缘谋面。谁料想,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当时在东北工业部《东北经济》杂志编辑室工作,奉调作为军事代表参加接收沈阳的工业企业;范政则从东北毛泽东青年团哈尔滨市团部宣传部部长的职位上,调任东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沈阳办事处主任。
我第一次见到范政是很意外的。那是在接收沈阳的工作基本告一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们接收小组共有三名军事代表,只发给一张招待券,理应由首席代表王化民出席。可他因事脱不开身,便让我替代。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高规格的场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知名的高级首长。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委员张学思、王首道、陈郁等都出席了。这里面,王首道和陈郁是我们东北工业部的正副部长,张学思给我们作过报告,我自然认得出来,其他首长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招待会进行的过程中,我的眼睛不时地朝他们的座席张望。但见一位五短身材、白皙面庞,看上去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走近前去,只见一位首长站起身来,不知两人高声说了句什么,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场面令我十分惊诧:这位年轻人何许人也,竟然能同高级首长如此这般?这时同桌的一位知情者向我身旁的另一位介绍说:“那是伍修权,那个‘红小鬼是范政,十来年前伍修权当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时他们就熟悉……”“是写《夏红秋》的那个范政吗?”我睁大眼睛问。“正是他,一个‘小天才!”他以赞许的口吻调侃了一句。资格这么老啊,我有点不敢相信;见到了范政其人,和我想象中的可大不一样,原来这么年轻,心头笼上了一层诱人的神秘感。
不久,党组织把建立青年团的工作提上了日程,而这,需要由青年干部来做。我当时只有十七岁,受命从财经岗位转轨到建团工作上来,由此开始接触到了范政。那时,听报告的机会较多。在一次团干部大会上听他作报告,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记得他朗诵一般流利地背诵了毛主席讲的一段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要求大家,务求深刻理解,时刻牢记心头。接着,他联系实际,针对团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大的问题,说:“我们要为革命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而骄傲,却不要自恃清高。即使你水平再高,能力再强,那是你做好工作的条件,而不应成为骄傲的资本。况且有的人不过是一个大鼓,敲起来很响,肚子里空空;相反有的人有知识有经验,却深藏若虚,后者是可取的。”又说:“不要孤芳自赏。有的人看自己是朵花,视他人如草芥,老子天下第一,这样的人很难团结同志,到头来没有不跌跤子的;即使是朵花,在别人眼里也许是狗尾巴花,不会被人欣赏的。”最后,他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1948年‘五四青年节在哈尔滨成立的青年团,名称就是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我们肩上担负着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任重而道远。亲爱的同志们!青年朋友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吧!”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样鼓舞人心的报告,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记忆。
范政作报告,很受青年们的欢迎,每次都座无虚席。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鲜活生动的实例举证,聆听者无不受到教益。他言词诙谐,才思敏捷,口齿伶俐,一口北京话,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保尔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团干部,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在给青年作报告时常常引用。可是范政在讲坛上引用这段话时,犹如进入了角色,仿佛那是他心灵的独白,一边朗诵,一边作着手势,抑扬顿挫,慷慨激昂,震撼着听众的心扉,台上台下的感情融会到一起,那激荡人心的场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每次听他的报告,都认真速记,回头整理出来,向下传达,还不时地翻看。仅就作报告、讲话来说,我就极力地效仿他,视他为宣传鼓动家,心驰神往。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以及在许多团干部的心目中),范政就像一粒火种,走到哪里就会点燃起熊熊烈火;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一群群热血青年;又觉得他像一座高山,难以逾越;又像天上的云朵,可望而不可及。
我从事建团工作之前,经过大专学校学习,奠定了一生奋斗的政治思想基础。经过在东北一级机关工作和接收沈阳实际工作的锻炼,在各方面业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平。特别是作为军事代表接收沈阳,身穿军装挎着手枪,带着东野十二纵队的一个排的部队,接收沈阳第一砂轮厂,接着又接收工具厂,年纪不大,权威不小,身份在那里摆着,掌管人事大权,谁也不敢小瞧,工程师见我点头示意,三天两头给职工作报告,被聘为《沈阳工人报》《东北日报》通讯员,常有消息报道和诗歌作品见报;配有公务员围前围后地伺候,出入厂区大门,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啪”“啪”立正,可谓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现在回头来看,假设后来我就在这个圈子里转悠,也很难说会有多大长进。可从事建团工作以后,便有了别有洞天的感觉。总之,可以这样讲,在此之前,相对来说,我已经具备了一个高起点;而在此之后,则又有了一个高目标。这对于我后来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主客观因素。
1951年7月,我被调到沈阳团市委担任组织科长,范政时任团市委副书记。我为能够同范政走到了一起而感到幸运;为能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振奋不已。当时的团市委机关,包括《青年团员》杂志社、青年文工队和青年出版社,可以说荟萃了哈沈两市的青年精英。一部分是由包括范政在内的领导同志率领的从老解放区哈尔滨来的青运骨干;另一部分是沈阳地下党领导的青运系统的领导骨干。就整体而言,见识、能力和文化素养相当高。我来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实感相形见绌,可我并不自卑,只有自信,“春风得意”变为急起直追,而身边的范政就成为了我追赶的目标。过去是间接接触,心向往之,实则了解有限,经过一段直接接触,近距离、经常性地观察,才使我进一步全面地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范政,神秘感消失了。
被誉为“少年老革命”、“神童作家”的范政,知人善任,尤其惜才,工作勤奋,好学不倦,举止大方,性情随和;他的成熟,他的睿智,他的丰富学识和人格魅力,更加赢得了我的心。不仅认定他确为鲜见的英才,而且了解到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范政原名李万万,1925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延边市的一个被后世称赞的“红色家族”。由于他的聪颖早慧和勤奋好学,十岁便开始在《北平新报》上发表作品,接着成为该报儿童副刊的撰稿人和编辑。1937年2月,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的李常青(“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把年仅十二岁的儿子范政,送到周恩来和地下党领导下的少年抗日救亡团体——新安旅行团,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7年3月,在归绥(呼和浩特)曾代表“新旅”向傅作义将军献锦盾、献锦旗及慰问品;1938年为纪念多伦大捷为吉鸿昌烈士及抗日阵亡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他曾含泪宣读祭文;1938年10月,为解决团里的活动经费,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离汉口一百多公里的抗日前线,代表“新旅”拜访李宗仁将军。十三岁在兰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旅”的骨干;曾在“保卫大武汉”等群众集会上代表少年儿童作震撼人心的演讲;发表许多激励全民抗战的文章;十四岁时,随“中国救亡剧团”到香港、河内、西贡、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宣传抗战,作募捐演出;回国后,出版了五万多字的纪实文学《海外一课》,编辑《儿童抗战丛书》等等。
其间,受到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邓颖超、郭沫若、廖承志、李克农、伍修权等高级人物的赞赏;与陶行知、田汉、夏衍、艾青、欧阳予倩、洪深、金山、任光等知名人士广泛接触;曾同郭沫若多次联袂登台发表抗日演讲,从而结下忘年之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旅”因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范政受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和张爱萍师长的赏识。十六岁的他,担任新安旅行团团委委员、少年部部长,兼任《儿童生活》《儿童画报》的编委主任。在苏北的五年,使他成为“新旅”的领导骨干之一。
“九·三”胜利日寇投降后,他随黄克诚将军率领的部队回到光复的东北。离乡十载,激动万分,在肖华将军的鼓励下,创作纪实文学《阔别十年》,刊登在1946年2月的《白山》杂志上。先任辽东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后任《东北日报》记者(他的父亲李常青为《东北日报》社社长),1947年,只花十几天时间,便写出中篇小说《夏红秋》,声名远扬……
范政的非凡经历,令我肃然起敬;他的聪明才智,成为我心中的偶像;他的勤奋好学,成为我效仿的榜样。留心观察他的所言所行,对待和处理问题的领导艺术,常常以他做标杆来比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之处;不放过任何聆听他讲话的机会;珍惜同他的每一次接触,如饥似渴般地从他身上求取教益。
需要说的是,他身边聚拢着机关的许多干部,不只是我。这里边包括我的夫人马宏声。她直接接触到范政比我要早。1948年11月范政到沈阳后,为了培养建团骨干,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办“寒假青年学园”,他亲自担任主任,配张超、刘宾雁两位助手,从学生中选拔优秀分子。我的夫人当时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坤光女中读书,被选拔入园学习,加入了青年团,结业时被评为唯一的模范学员,受到范政的瞩目。她称范政为革命的引路人,有知遇之恩。从“寒假青年学园”结业后,便下基层搞建团工作,1951年7月被调回团市委机关。当时她剪着男士的超短发,泼泼辣辣,被范政称为“假小子”。范政说,他写的小说《夏红秋》里面的主人公夏红秋,小名就叫“假小子”,他很喜欢这样的性格。“假小子”和我初恋时,范政就鼓励她:“爱,是需要大胆的!”我的夫人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活泼好动。周末就在一起跳舞,打乒乓球,比赛掰腕子(范政身小力薄,掰不过我的夫人,可为了“照顾面子”有时故意输给他)。他朝气蓬勃,没有架子,处处同大家打成一片,从日常活动中,他的风度,他的做派,为人处事,言谈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可贵在有心,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他身上汲取经验和知识营养,自然获益更多更大。范政说过这样的话:“在知识的海洋里,要做一块海绵,尽吸一切对自己有用的营养;如果是一块顽石,即使在海洋里,它也会拒绝吸收哪怕是一滴营养。”我和我的夫人的共同点之一,就是要做一块海绵,而不做顽石。这也正是我们都能够从范政身上学到许多东西的重要内因。
有一次,我们同范政一道观赏京剧传统剧目《空城计》,我说,不读《三国演义》,恐怕对这一出戏不一定会有浓厚兴趣;他说,更可以反过来说,由于看了《空城计》,便引起阅读《三国演义》的兴致。接着问我读过哪些中国古典名著,我回答后,他说:“有道是‘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红楼梦》要反复认真阅读才行,囫囵吞枣是品尝不出真正味道来的。”又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累了无数的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些文学经典,犹如颗颗明珠,璀璨斑斓,光彩夺目,尽兴观赏,实在是最美的精神享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样丰富的宝藏,哪怕是浏览一下也好,否则是人生的一大缺憾。”还叮嘱我要读《中国通史》,说“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历史茫然无知,简直是一种耻辱。”听了这些话,真使我振聋发聩,如梦初醒,故而衷怀铭刻,殊不能忘。
记得又有一次我向他求教写作技巧,他竟开口问道:“你能说出二十位世界级外国文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吗?”我老实回答:“不能。”“不妨说说看。”他望着我,亲切地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和他的《母亲》,法捷耶夫和他的《青年近卫军》,托尔斯泰和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边想边说。他笑了笑说:“噢!都是‘苏联老大哥,其他国家的呢?”我沉思了一会儿,只说出一位——匈牙利的裴多菲,因为几乎人所共知他的一首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幼稚无知的我顿觉脸发红心发慌,真有无地自容的感觉,悔不该一知半解竟然讨教起写作技巧……他似洞悉了我的尴尬心态,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任何物质财富都可能为某个人所独有,唯有知识财富谁也无法垄断,是任何人都可以享有的。人既不要自满,也无须自卑,‘闻道有先后,认真多读些中外名著,就可以学到写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技巧,纯谈技巧怎么谈呢?若泛谈写作,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最后他说:“你要记住一句话,平庸和懒惰向来是一对孪生子。”我洗耳恭听,愧作殊深,心想,真乃诲人不倦,堪为吾师啊!范政对我的教诲,既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又使我受到深刻的启迪,促使我后来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对于丰富头脑,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提高写作水平,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范政于1953年被调到哈尔滨120厂任党委书记,1954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到长春任职。就他对我的影响而言,从1947年小说《夏红秋》惠及于我,到1948年11月接收沈阳从事团的工作接触到他,以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前前后后有五年多时间;从年龄上讲,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正是人生观逐步形成和奠定创业基础的阶段,他所给予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无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它使我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又有了更高的目标,产生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痴迷忘我的追求,以至有了日新月异的感觉,进而愈加充满自信、充满激情地向着更高层次攀登……。因此,我说“以至影响到我后来的人生”,诚为肺腑之言。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堪称五十年代沈阳青年楷模的范政,是影响了一大批人的。我只是其中之一。
范政于1958年,在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几年后,被摘掉“右派”帽子, 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热处理车间副主任。在此期间,他一面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一面以极大热情投入话剧创作。1962年,他带着剧作《五月的鲜花》(后改名《吉鸿昌》)特地进京向郭沫若同志求教。4月9日,郭沫若热情地在家里约见了范政。范政见到郭老真是百感交集。他把自己被划右派的事和所有心里话向郭老倾诉了出来。郭老豁达地鼓励他说:“人的一生总要不断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有所得益,经过这场风雨之后,要更健康地成长起来。”当场,郭老在洁白的宣纸上为范政题了“一曲洪波越海山”那首令他终生珍藏的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范政受到严重冲击。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愤然卧轨自尽,年仅四十三岁。
1979年8月27日,范政辞世十一周年前夕,中共长春市委为他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对他短暂的人生予以应有的高度评价。范政创作的话剧《吉鸿昌》由长春市话剧院排演,进京参加国庆三十周年演出获一等奖。……1999年鲜花盛开的五月,由长春市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合编的《深切的怀念——忆范政》一书面世,里边有《夏红秋》《吉鸿昌》等范政的主要作品和同志、亲人的怀念文章……
“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在圆民族复兴中国梦、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收笔这篇文稿,我远望长春,“破颜”自语。心想:范政亦当含笑九泉了!
责任编辑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