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历史及其叙述方式(节选)
《一九四二》:历史及其叙述方式(节选)
李玥阳: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一九四二》:历史及其叙述方式”。因为《一九四二》刚刚公映,这个电影应该说不仅仅是一部票房还不错的电影,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讨论的话题。因为《一九四二》不仅和我们当下的中国现实联系在一起,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向历史纵深处前进的途径,所以这也构成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我个人也看了一些资料,在我看到的这些资料里面——尽管是很有限的资料,但已经可以提供很多讨论的角度。比如有人探讨从小说到电影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过程中的对话和互文性等。还有人着眼于冯小刚的作品序列,因为他和刘震云有过多次合作,最早拍《一地鸡毛》,然后才转向喜剧贺岁片。今天,当他再转过来拍《一九四二》的时候,就可能构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关系。还有的人是从历史角度,比如194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后来对1942年的再研究再阐述等。当然更多还是从中国电影产业方面来讨论,比如这个电影的票房和华谊兄弟公司股票估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这些有限的材料和丰富的视角可以看出,《一九四二》是一个包含着很多有效问题的文本。我想各位老师一定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可能会提供出很多新鲜的角度,也可能在既有的角度中,进一步伸展。不管怎样,我都觉得今天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准备了两部分资料,一个是“《一九四二》:作为历史”;一个是“《一九四二》:作为艺术”。我写了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影片沉浸在对灾难、对生存痛苦的渲染之中,直至结尾仍然任由故事被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所笼罩,我觉得这种单纯的精神、生命和生存层面的观照,最终把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事件,部分地抽离出了历史,没有给人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展示出丝毫的希望。这是我对影片的一个总体感觉。因此我觉得影片对历史的叙述明显是片断式的,缺少大的格局,缺少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沦陷区和国统区,还有一个正在开创着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广大区域,即抗日革命根据地。当时的根据地也同样遭受灾害,粮食紧缺,加上日军“大扫荡”,生存也及其艰难。在这一时期,根据地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自救运动;在军事上开展反“扫荡”和敌后武工队工作;在文化思想上开展“整风运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一个饱受日军蹂躏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中国,这一点影片忽略了。如果影片面对惨痛的灾难,在思考灾难面前人的生存、生命问题的同时,在追问造成灾难原因的同时,能对苦难中国的出路哪怕做一点点尝试性探讨,也不会完全被沉重压抑和悲观的基调所笼罩。有人可能认为,通过探讨人的生命、生存的终极意义来结束影片,才显的更有普世感和艺术气息。但我觉得,生存永远是现实层面的生存,生命只有获得现实的物质基础才谈得上终极意义。艺术如果脱离了生活和历史的视野,不能给人以生的力量和希望的话,就无异于宗教和鸦片。因此《一九四二》在一定程度上是忘记了历史的历史叙事,不是真实的历史,更不是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应该是人在自然与社会的困境中获得主体的升华,应该是对社会历史某种必然性的坚定信念,所以我整体感觉影片充满痛苦、缺少希望,而且在艺术和文化层面上,这样一部影片,并没有太多当下中国所真正需要的积极的文化精神。
李玥阳:感觉王老师试图在被冯小刚已经钩沉的历史中,再钩沉一些被冯小刚遮蔽的历史。王老师似乎觉得这个电影存在抽离现实的问题,并且试图把这个电影再语境化,而再语境化的同时就发现了被无视的东西,比如说抗日革命根据地。

计文君(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看完这个电影,包括在观影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特别充分的情绪上的满足,虽然基本上是以流眼泪为表达方式,出来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还保持着那种情绪上的满足感。我在看《钢琴师》的影片时,也有类似的满足感。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眼泪到底是为何而流。我是河南人,我的至亲中就有1942年扒着火车去陕西逃荒才活下来的,我父亲也出生在1942年逃难的途中。所以我的眼泪里有个人因素,在我决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自己抒情了,给自己酝酿感动。当然电影中间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情节,比如说花枝临走之前和丈夫换棉裤,那个小女孩稚嫩的声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具有抒情的效果,虽然冯小刚整体上还是很克制的,没有刻意的煽情。抒情的是我自己,作为幸存者的后代怀想自己父辈祖辈的灾难时,流泪是正常反应。灾难是灾难,电影是电影。我回头去看整部电影,它的表达设置了很多视角,有神的视角,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这条线;西方的视角,外国记者的这条线;还有蒋介石的视角、河南军政各界的视角;官僚体系最基层的小人物的视角,如范伟演的伙夫,后来成了流动法庭庭长,最后成了汉奸的那个人的视角;然后是老东家和佃户的各自视角。主创们好像在做着一个努力,去还原真实的历史,但是整个看下来,我觉得适得其反。恰恰如刚才王老师说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忘记了历史的历史叙事”。在刘震云和冯小刚的创作过程中,历史成了传说,他们去采集这些传说,传说成了故事,然后将故事做了一个寓言化的表达,最后为我们讲了一个黑色的寓言。而在这个寓言里有一个视角无比重要,那就是当下的视角,电影通过灾荒中的饥民,表达出弥散在当下中国人中间的一种无助感。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我们讨论这个电影,千万不要把他的题材和电影本身给弄混淆。讨论它的题材,讨论这段历史,如何去面对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讨论电影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冯小刚和刘震云在今天要做这样一个表达?我看了央视的《面对面》,刘震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中国不是一个“神人”社会,而是一个“人人”社会,就是中国人唯一的依靠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一点点温暖和善意,就是最后那个老东家和那个小女孩之间展现的东西,这是刘震云能够寻找到的我们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今天同样是无依无靠,那么这个唯一的依靠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一点点善意,但是这个善意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现代商业文明彻底粉碎了中国古代依靠伦理和宗法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依靠人和人之间的温情,几千年下来基本靠道德和伦理来维系的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在当下的社会其实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再回到电影本身,那么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没有出路的电影,最后一点点温情也好,烛光一样的亮色也好,都是聊以慰藉。这个寓言他是针对当下,而不是针对历史说的。这是冯小刚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讲的,他说他愿意讲得很具体,他说妻子会问丈夫,你会卖我吗?儿子会问父亲,你会卖我吗?今天再遇到灾难,我们去依靠谁,相信谁?这个灾难也许不是饥饿,而是别的灾难。电影触及的是每个人心中的那种恐惧,我们当下最缺乏的恰恰就是那种信靠。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到底去依赖什么,信任什么,我们信任我们的体制吗?我们信任我们的社会吗?我们信任各种各样可能向我们提供帮助的社会机构吗?我们今天在不断地质疑红十字会,质疑各种东西,我们无依无靠。《一九四二》是一个针对当下而不是针对历史的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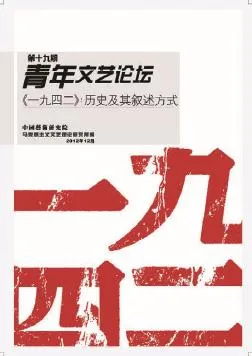

如果是这样,讲一个这样的寓言,说了等于没说,费了很大劲,花了很多钱,却没给我们一个稍有价值的指向。如果说我们能信靠什么的话,恰恰是需要从事精神产品制造的这些人为我们提供的。我们今天确实面临各种上层建筑建设的难题,但我觉得更积极的做法是尝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在《一九四二》里面,没有这种建设性的意见。
李玥阳:计老师和王老师的角度还不太一样,提供了一个历史之外的,或者说是把这个历史和我们当下语境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觉得这个电影在讲述一个关于当下的黑色寓言,而且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一个新的阐释方向。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历史回到当下,这个角度挺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当下”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问题。冯小刚近年来的几部电影,《集结号》是说组织不可靠,组织出卖了前线官兵;《唐山大地震》是母亲遗弃了女儿;《一九四二》又像计老师说的,每个人似乎都随时可能被自己的亲人出卖。总之,总是处在一种不安全感当中。冯小刚自己讲,他从90年代初就想拍这个电影,到现在已经接近20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很难说是“当下”。中国的情况,从90年代初期、中后期,到新世纪,到2008年,到今年,都很不一样。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至少从新世纪以来社会上比较乐观。所以,上面说的冯小刚的电影,可能和这一代人的创伤有关系。他们总是特别关注并不厌其烦地渲染所谓人性丑陋、阴暗、扭曲的方面,电影、文学都如此,文学上可能更严重一些,包括非常著名的作家。似乎在他们看来,如果作品中亮色多一些、能给大家以希望的话,就是“浅薄”的标记。就像《一九四二》那样,按照电影最后给我们展示的结局,影片中的那个族群,唯一的结局就是彻底灭绝。可历史完全相反。仅仅六七年以后,就诞生了新中国,这么有朝气的蓬勃向上、气象一新的新国家、新社会,是从哪儿产生的?和这个情况相联系的是影片中的刻意的回避。实际上这个电影还是有“大格局”的,层次很丰富啊,比如远在天边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至连“甘地绝食七天”这样的信息都刻意提到了,但恰恰又非常刻意地回避了当时就在河南周边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比如晋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和豫皖苏根据地,这些地方当时也受灾了,但情况和国统区、沦陷区完全不一样。丁玲在《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这篇文章里提到,当时的太岳区接收了20万河南难民,太行区接收了5万,另外别的资料还提到,当时陕北也接收了1万多灾民。也就是说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是参与到救灾当中的,而在影片中没有丝毫体现。实际上,任何光明的、有希望的历史内容,都搁不进那一代文艺家的叙事框架里面。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他们的叙事框架有问题?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计文君:我接着刚才祝老师的话补充一点。当时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也是有救灾行动的。影片中范伟扮演的伙夫,代表汉奸,他都出现了,显然这是一种回避。另外还有一个回避就是整个中国社会各界的救灾行动。常香玉在西安义演,然后买面往巩县拉,上海各界也有救灾活动。河南人不全都死在河南了,整个中国都有河南人,家乡受灾,整个中国,就像今天一样,肯定是要援助灾区的。虽然力量非常有限,有大批人死亡,但是河南受灾的报道出现在很多报纸上,社会各界都有反应,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在影片中没有提及。就《大公报》公布了消息,结果被蒋介石封杀了。影片对社会各界的努力没有丝毫提及。据说影片中原来有一句话,小说中有,是作者问他娘,是说饿死很多人的那次灾荒,他娘说我记不清楚了,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这样一个不做评论的叙事,其实是留着半句话,我觉得冯小刚是留着半句话,没说出来,等着看完电影的人去给他补充。

李玥阳:我也觉得是,很有共鸣。这个电影是从90年代初的刘震云小说改编的,从新写实文学的脉络衍生出来,但是已经过了20年,电影好像并没跳出小说的框架,就像刚才祝老师说的,是那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在小说里好像还提了一句,攘外必先安内,但在电影里就完全不见了。同时,今年的《白鹿原》也被拍成电影,也是一个挺好玩的现象,因为《白鹿原》也是那时候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而且把一个家族作为一个民族主体,《一九四二》不也是嘛,地主,要是在50到70年代的叙述中他应该是被枪毙的,但他现在是一个民族主体,是完全正面的人物。可能都是挺好玩的问题,当然我也没想清楚。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从小说《一九四二》到电影,变化还是很大的。如果说1993年刘震云创作小说的时候,叙述方式主要是多种文本混杂的后现代风格,对历史尤其宏大历史采用调侃、解构、戏谑的方式,结尾部分还不忘了摘录两则离婚启事来说明历史的荒诞性和日常化。20年之后,电影《一九四二》则完全拍成了一部悲剧或正剧,主创们反复强调这是一部民族史诗、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和灾难,而媒体也把这部电影称为“中国电影的良心之作”。我觉得,值得追问的是为何20年会发生这种叙述态度的变化。正如李玥阳老师提示的,2012年还出现了《白鹿原》的改编,与《一九四二》相似的是,9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说《白鹿原》依然在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的脉络中重构、瓦解、改写革命历史叙述中的中国现代历史,而电影则把《白鹿原》拍摄为一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史诗,可以说把解构、颠覆的历史再正面重建起来。
如果考虑近期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发现莫言、刘震云、陈忠实基本上都是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作家,今年他们又重新以不同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本身是有意思的问题。正如莫言刚在瑞典发表的演讲,也重述了一个带有他自己饥饿、创伤经验的当代中国的历史。我的基本理解是,新的历史书写开始回收、整编这些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新历史写作,以服务于新主流的建构。刚才祝老师、王磊都提到电影《一九四二》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根据地的“有意”忽视,电影中确实全景式地呈现了各种不同的视角,有灾民、政府上层与中下层、西方记者、教堂里的神父,甚至连日本人丢炸弹的视角都有,唯独看不见根据地,这种绝对的不可见和缺席成为当下拼贴新的历史记忆所必须的遗忘。借用影片的宣传语“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而新的历史记忆恰好又是建立在新的遗忘之上。有趣的问题是为何无法在全景式的版图中纳入共产党的视角,或者说,为何在民国一统的想象中无法呈现武装割据的根据地的影像?这或许就是历史书写和建构的基本规律,可见的影像以压抑其他图景为前提。

联系到《白鹿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九四二》也把中国呈现为一个乡土中国,一个有土围子围起来的村落。其中,白嘉轩、老东家这些乡绅或地主成为贯穿历史的主体,正如《一九四二》中所有人都死了,只有老东家活了下来,成为亲历历史的幸存者,是连接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桥梁,白嘉轩也是如此。而且他们都是父亲,这与五四到80年代启蒙逻辑中的文化弑父是不同的,这些电影在召唤一个老中国、老父亲的归来。
《一九四二》的上映,还让我想起另一个文化脉络。从2009年《南京!南京!》、2010年《唐山大地震》、2011年《金陵十三钗》、再到《一九四二》,不解的是,当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主流大片要呈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创伤与灾难?《南京!南京!》是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都由广电总局参与推荐。除了《唐山大地震》是当代史,其他三部都与民国抗战有关,其中《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都是呈现南京大屠杀这一中国现代史上最惨痛的记忆。这些电影有一个相似的功能,就是重建了一种新的国家记忆和民族想象,这种新的国家想象就是把当下中国想象为民国,或者说当下中国被民国化。现在有很多“民国热”、“民国范儿”的书,网络上也有很多“国粉”,问题就在于为何当下中国能够被“民国化”,而且是一种没有根据地、解放区的民国记忆?
《一九四二》一开始就借蒋介石的元旦讲话,把中国抗战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再加上剧中蒋介石要去缅甸访问、去开罗开会,呈现了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历史,也“恢复”了中国作为盟军的“国际”身份。近些年有很多作品把曾经遗忘的中国远征军作为国家英雄,不仅仅是抗战英雄,而且是“国家”的英雄。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国家记忆》,这本书的编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当时美国随军摄影师拍摄的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身影。有趣的是,在序言中编者很深情地说,以前中国人一直认贼作父,看到这些照片才找到真正的父亲。在美国找到自己的父亲这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文化表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当下会把民国想象为“国家记忆”,这里的国家又是谁的国家呢?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年一种新的主流表述就是重新指认民国为国家的代表,于是,《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中奋勇杀敌的国军是中国军人的象征,《一九四二》中忍辱负重的委员长和为民请命的河南省主席在内忧外患中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像90年代“分享艰难”叙述中的好领导、好干部。
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中有几个角色是相对固定的,就是受难的中国人、抵抗的国军将士、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士兵和作为拯救者的西方传教士和记者。可以看出《一九四二》对传教士、教堂空间的使用与《金陵十三钗》的呼应关系,还有《时代周刊》记者作为灾难的见证人,这些电影共同书写了一种新的国家记忆。在这种记忆中,中国人变成了被屠杀、被强奸的对象,他们是受难者和幸存者,对历史只能承受、认命和活着,这也是8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历史书写的惯例,人不过是历史的蝼蚁和牺牲品。在《一九四二》的推广宣传中有一款“蝗虫人”的海报,一个蒙着眼睛、张着嘴的人头、蝗虫身体的形象,这个形象源自1935年著名的现代版画家李桦的作品。这个作品也是一个蒙着眼睛张着嘴巴的被捆缚在柱子上的中国人形象,但从版画名字《怒吼吧,中国!》和呐喊着挣脱束缚的身体,可以看出版画和海报的差异。“蝗虫人”只是一个卑微的受难者、动物化的人,而《怒吼吧,中国!》则是在抗战背景下反抗者的代表,一个新的中国人的形象。
这种对中国人的想象,与整部影片没有表达出希望和未来是相关的。是没有希望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