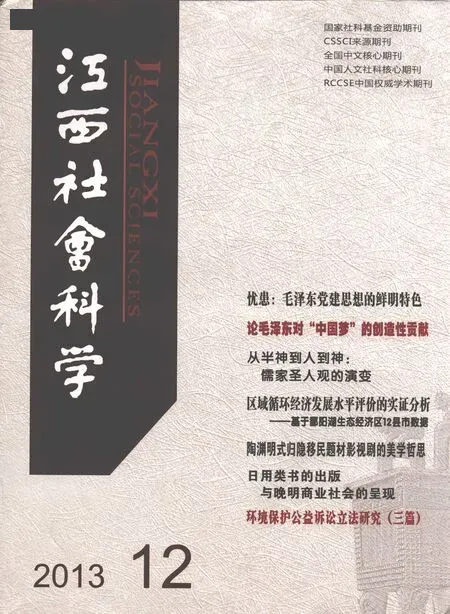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的立法完善
■高明侠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要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以流域水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的流域管理,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流域水空间是探讨流域管理的较新视角。流域水空间是指河流及其支流,和与之相连接的湖泊、湿地等各种水体,那些受洪水波及的洪泛平原和部分坡地及此范围内的地下含水层系统所共同占据的空间。[1](P316-319)流域水空间管理通过维护水循环、水资源自然可再生能力,进而维护流域水生态系统平衡。“水资源自然可再生能力是指通过水资源自然循环,水资源得到不断补充的能力。”[2](P277)水资源自然可再生能力,主要取决于降水量大小,而如果没有相关多级水空间调节,就会严重影响降水量,极大地增加水资源系统的脆弱性。“水资源调节完全依赖于工程性措施来解决是不现实的,应该研究水循环的自然过程,……显然,足够的水调节空间对水资源平衡与可持续性维持是极为重要的。”[3](P386-389)目前,把相关立法如湿地立法、水法、森林法等整合在以流域水空间为核心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如杨波等提出制定流域水空间管理法规和条例[1](P316-319),但并未提出制定哪些法律,学界仅有一些关于某种水空间介质立法问题的研究,如刘晓莉关于湿地立法的研究[4](P67),胡德胜等关于淤地坝之水的权利研究[5](P27-32)以及关于生态环境用水的研究[6](P1-45)、[7]、[8]等。本文将从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一、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立法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和理论基础之上,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主要涉及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正义理论等。生态学理论为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而生态伦理学、生态正义理论则是其环境伦理学及哲学基础。
(一)生态学理论
生态学的概念最早由德国人伊·海柯尔在1866年提出。早期的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与机理。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生态学,对系统内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和大气、水分等非生物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不同层次的全方位研究,强调利用生态学调整人类活动,进而调节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9](P3)这一点是与生态系统管理立法进而与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相契合的,因为这些立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去调整人的行为,进而调整人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而当代生态学已经超出了生物学的范围,涵盖海洋生态学、土壤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环境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等。
生态环境立法的特点之一是科技性,流域水空间立法及其完善,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才能很好地通过调整人类行为,从而达到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早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生态学必须完全统一到决策和立法过程中,人类法律的制定必须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因此,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也为完善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理论依据。
(二)生态伦理学理论
生态伦理学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主张以生态学为依托,强调环境伦理学应当以生态共同体的整体价值为标准,用生态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来改造和取代一些传统的伦理学原则和规范。包括以生态学为背景的“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和“深层生态学”。[10](P29)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mo1es Ro1ston)的“自然价值论”认为,自然价值是由自然物自身的属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结构生成的,强调在遵循生态学规律的意义上构建环境伦理学,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具有极高的道德意义。他认为应该把环境伦理转化为法律,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完全诉诸自愿践行的环境伦理学,是很难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的。
生态伦理学强调生态共同体的整体价值,主张用生态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来突破传统的伦理学原则,并使生态伦理法律化。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目的,是保护流域水资源自然可再生能力、维护流域水生态系统平衡和维持河流生命。因此,生态伦理学思想,同时也是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及其完善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
(三)生态正义理论
随着生态问题的出现,生态保护进入环境哲学正义探讨的范畴。有学者认为,在当下生态问题丛生的现代社会,生态正义在正义秩序中的地位应是“基础性”的,即我们应该运用生态正义去不断修正交易正义、社会正义。生态正义秩序顺序的安排为——自然公平(即人与其他物种的权利公平)、代际公平、代内公平,自然公平是一种“底线公平”,并随时以自然公平去审视和修正现行制度。[11](P172—173)正义概念关系到权利、要求和义务,与法律观念有着紧密联系。“由于正义概念关系到权利、要求和义务,所以它与法律观念有着紧密联系。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当人们提出正义要求时,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些要求则是向那些有权利凭借以制裁为后盾的具有拘束力的规范手段控制人们行为的人提出的。……正义的要求会在一个国家或其他共同体的实在法中得到广泛的实现,这也当然完全是可能的。”[12](P283—284)因此,生态正义必然要求我国的环境立法重视生态系统管理立法,它也是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完善的法哲学基础。
二、我国流域水空间现状及管理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流域水空间是多种空间介质的整合,每一种空间介质(例如湖泊、森林、湿地、洪泛区、土壤渗透能力等)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考察流域水空间状况需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水资源总量,二是流域水空间各空间介质状况。流域水空间的现状,也直接反映出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流域水空间的现状
流域水空间的核心指标是江河年来水量和降水量形成的水资源总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量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流域水空间的总体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全国水资源总量有减少的迹象,另一方面全国总用水量在不断增加。《201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3 256.7亿m3,比常年值偏少16.1%。从降水量、地表水资源总量到全国水资源总量来看,2011年的年均为1956年以来最少的一年,而全国总用水量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生活和工业用水呈持续增加态势。
我国流域水空间各空间介质也不容乐观。第一,森林水资源涵养空间不够,严重影响山地径流的调节与蓄留,不利于水资源的涵养与再生。根据《2011年中国林业基本情况》,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20.36%,只有世界平均水平30.3%的2/3,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8%,生态功能好的仅占11.31%,森林资源质量不高。第二,湿地面积比例太小,天然水库调节能力丧失,不利于水循环和水平衡。我国自然湿地仅占国土面积的3.77%,远远低于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现象仍很严重。第三,洪泛区方面,“由于来自生存的压力、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认识上的偏差,使人们对洪泛区进行了大规模无序的、不考虑边际效应的过度开发,导致洪泛区大面积减少,使区域水调节功能下降,水资源可再生能力受阻,水资源的赋存量明显减少,水资源系统平衡受到严重破坏。”[3](P386-389)例如,2011年全国有260多条江河发生超警戒线洪水,钱塘江发生1955年以来的最大洪水,与此同时,2011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1956年以来最少的一年。第四,盲目开采地下水使地下储水空间减少,从而导致地下水总量减少、漏斗面积扩大、水位下降等问题。《201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地下水资源量比1980—2000年平均值偏少10.6%,20个省级行政区共统计地下水位降落漏斗70个,年末与年初相比,浅层、深层漏斗面积扩大的各有11个。第五,土壤板结现象极为普遍,土壤孔隙率减少,其水库作用明显削弱,水资源调节功能及其可再生能力下降。
总之,由于流域水调节空间受到了破坏,极大地改变了陆地水循环方式,严重地影响了水循环和水平衡,致使流域水资源在补给、再生的时空上形成断点,明显降低流域水的自然可再生能力,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水资源的可持续性。
(二)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流域水空间管理没有直接明确的规定,但有相关的原则性和一些松散的具体性规定。原则性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水法》)第9条,“国家保护水资源,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植被,植树种草,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其他还有关于水生态系统保护、增加森林覆盖率、加强水土保持、保护湿地等几个方面的规定。
考察我国现行立法,其对于流域水空间管理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制度、有关介质的规划制度、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保护和增加植被措施制度以及蓄滞洪区制度等。例如,我国《森林法》对于超过批准的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等,均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分析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相关立法的缺位和相关立法内容的缺失
我国缺乏有关自然保护区制度和湿地保护的高位阶立法。自然保护区制度方面,现行《自然保护区条例》是关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行政法规,其他专门立法多为行政规章或政策性规范,缺乏高位阶立法。在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中,《自然保护区条例》“既不能起到统领其他相关法规的作用,也不能担当有效地和其他部门法律相协调的重任”[13](P44-45)。湿地保护方面,我国目前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门性的、高位阶的湿地立法,已有约40%的天然湿地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得到保护。换言之,我国尚有60%的湿地由于没有专门的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而使其保护工作受到限制。
一些相关立法内容缺失。洪泛区立法方面,目前其立法目的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洪泛区湿地生态保护方面的立法内容缺失,使洪水资源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流域土壤板结防治上,目前仅有一些相关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对土壤板结的防治措施、途径、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地下储水空间保护方面,虽然我国《水法》等有关于地下水保护的规定,但这不足以扭转我国盲目开采地下水的局势,导致地下水总量减少、水位下降、漏斗面积扩大等问题。
2.一些与流域水空间管理相关的制度缺乏或者不完善
我国缺乏流域水空间评价标准制度、流域水空间预警系统制度和流域水空间功能恢复制度等。对于违反用水总量控制制度所产生的损害流域水空间问题,目前缺乏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如《水法》第69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问题是,如果按照违法行为人的违法取水用量计算应当缴纳的水资源费已经超过10万元以上的,行为人可能非常乐意在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形下,每隔一段时间接受罚款一次。”[6](P1-45)
3.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的经济手段运用不足
在环境管理立法中,经济激励手段与行政手段同等重要。该手段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主要有收费、税收、价格等多种方法。“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作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利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公共决策者决不应该忘记激励,因为许多政策改变了人面临的成本或利益,从而改变了行为。”[14](P7-8)
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就是一种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然而,我国现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不少,如“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没有从基本原则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法律措施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没有得到清晰界定,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等规定缺乏明确性和科学性。另外,一些政策和法律规定落后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需要,如国务院在2006年公布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未将水资源保护补偿、水土保持纳入水资源费的使用范围等。[15](P76—78)
三、完善我国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的建议
针对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完善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
(一)制定完善更高层次、更高位阶的自然保护区、湿地、洪泛区和土壤方面的保护法
我国应制定更高层次的自然保护区立法、湿地保护立法、洪泛区生态保护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一是制定《自然保护区法》。我国应在整合各类型自然保护区专门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自然保护区的立法体系。二是制定湿地保护方面的专门性、高位阶的立法。我国在湿地立法中,可对美国湿地保护政策中“零净损失”目标所体现的严格保护湿地思路予以借鉴。“零净损失”(No Net Loss)目标是指任何地方的湿地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保护,转换成其他用途的湿地数量,必须通过开发或恢复的方式,得到补偿,从而保持甚至增加湿地资源基数。[16](P72-73)三是制定洪泛区生态保护法。在洪泛区生态保护立法过程中,美国重视洪泛区湿地生态保护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1979年,美国《国家洪泛区管理基本方案》增加了保护洪泛区湿地自然生态价值的内容。1993年美国《分担挑战——21世纪洪泛区管理》和《洪泛区管理评估》都强调了要考虑到洪泛区湿地的自然生态价值。四是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我国可规定采用适当的农用机械,以避免土壤紧实,在山坡地区尽量避免破坏蓄水的土壤覆盖物、保持森林和梯田等的自然土壤结构等,以防治流域土壤板结。五是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森林立法和《水法》,增加森林覆盖率和注重保护天然林。从生态学角度看,天然林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其他森林资源,对于维护水资源自然可再生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完善森林立法中,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荒野法》(1964)将一些国家森林、国家公园以及其他联邦土地划定为“荒野”和“原始地带”,建立了“荒野”系统。美国森林法规定的“无路创设权”,则赋予林业局ESCY在现有国有林中指定一些“无路的”区域的权利,规定在这些区域内不得修建任何道路,使这些区域获得与原始荒野同等重要的保护。[17](P65-66)我国在森林法修改时,可设置条款,禁止在天然林中修建与保护天然林无关的一切人工设施,并将天然林的范围确定下来进行永久保护等。另外,我国应完善《水法》,限制地下水开采,保护地下储水环境系统,充分利用地下水空间对水资源的调蓄功能。
(二)完善相关制度
一是完善用水总量控制和水位控制制度。加快制定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实施流域和区域取用水总量控制。在相关责任制度方面,胡德胜等认为除了建立和加强行政考核外,我国可以考虑借鉴马来西亚的违法行为人推定制度。[18](P387-401)
二是建立流域水空间规划制度、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流域水空间评价标准制度、流域预警系统制度和流域功能恢复制度。流域水空间规划制度方面,我国应在考虑水循环系统层次、生态环境层次和社会经济层次的基础上,分析流域水空间现状,预测其发展趋势,研究水空间控制单元划分及环境承载能力,提出水空间的总量控制方案,最后形成防洪控制工程、水资源土地资源利用规划、水土流失防治、河道生态修复等多方面多目标的规划方案体系,以满足该控制单元内的各个总量控制目标。[19](P54—55)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应强调从流域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和功能影响的角度进行评价,以保证流域管理法落到实处。流域水空间评价标准制度、预警系统制度、功能恢复制度是对水资源可再生性与维持能力进行评价,划分流域水资源风险等级,对受损的水资源空间系统进行预警、修复和保护,保障其健康运行,在充分认识流域水文系统特征和规律基础上,合理退耕还林、还草、还湿,保证流域有足够的水补给调节空间。[3](P386-389)
(三)注重经济手段在相关立法和制度中的运用
一是完善我国已有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将“受益者补偿”原则和“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原则,从基本原则的层面,细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各项措施,并且设置足够的程序性规定确保其执行和落实。[20]清晰界定各种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科学而明确地规定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15](P76—78)有学者认为,在完善包括生态补偿在内的流域机制中,我国应该以流域管理政务平台为抓手,建立和形成科学的政府管理机制、市场调节机制、社会参与机制以及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21](P37-39)
二是运用经济杠杆,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按期间制裁机制。目前,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经济处罚不科学,因此在违法行为人看来,这是“违法收益 >违法成本”,所以其违法行为层出不穷。[22]因此,针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考虑运用经济杠杆,通过建立或者完善针对违法行为人的按期间制裁机制,确保“违法收益 <违法成本”,让违法行为人得不偿失。[23](P165-169)
四、结语
水生态系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流域管理立法需要从流域水空间的视角,立足于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特点,以促进流域水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修复。针对流域水空间管理立法中的问题,我国需要制定更高层次的自然保护区和湿地保护等立法,或完善相关立法,完善或者建立相关制度,如建立流域水空间规划等制度,注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等经济手段在相关立法和制度中的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水资源自然循环,高效保护流域水生态系统。
[1]杨波,邓伟.初论流域水空间研究[J].地理科学,2006,(6).
[2]曾维华,等.水资源可再生能力刍议[J].水科学进展,2001,(6).
[3]邓伟,等.水空间管理与水资源的可持续性[J].地理科学,2003,(8).
[4]刘晓莉.中国湿地保护立法评判[J].求是学刊,2011,(5).
[5]胡德胜,等.淤地坝之水的权利问题[J].当代法学,2007,(6).
[6]胡德胜.生态环境用水法理创新和应用研究——基于25个法域之比较[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7]胡德胜.生态环境用水:国际法的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8]胡德胜.论我国的生态环境用水保障制度[J].河北法学,2010,(11).
[9]蔡晓明.生态系统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0]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3]马燕.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环境保护,2006,(11A).
[1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M].梁小民,译.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5]宦洁,等.以机制创新推动生态补偿科学化——基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陕南汉江、丹江流域的考察[J].理论导刊,2011,(10).
[16]张蔚文,等.美国湿地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03,(11).
[17]张小强.中美森林法比较研究及其对森林法修改的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05,(4).
[18]胡德胜,许胜晴.马来西亚水法中的违法行为人推定制度评析[A].高鸿均,王明远.清华法治论衡(第16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19]项祖伟,等.基于水空间的流域规划与管理[J].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6).
[20]葛剑平,孙晓鹏.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21]张锋,陈晓阳.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2012,(8).
[22]胡德胜,等.创新流域治理机制应以流域管理政务平台为抓手[J].环境保护,2012,(13).
[23]胡德胜.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按期间制裁机制的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 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