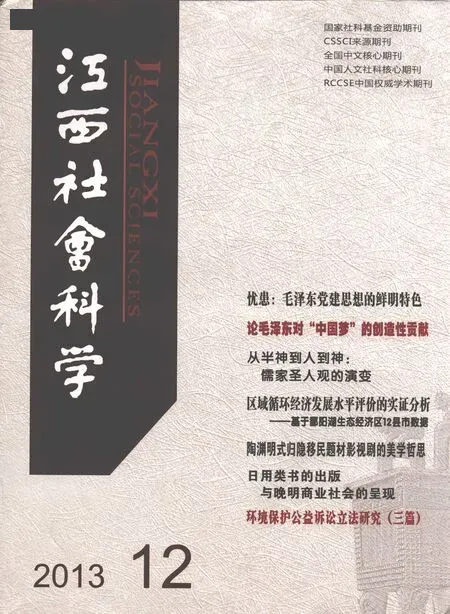原型批评视角下文学作品中“河流”的救赎意义——以《约檀河之水》、《施洗的河》、《阿难》为例
■孙胜杰
一、“河流”的救赎原型探源
从原型角度谈“河流”的救赎意义,不能避开原型不谈。“原型”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柏拉图,他指出原型是可感的万物之摹本,是原始模型,强调初始、开端。随后原型概念扩展到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领域。建立起科学的原型批评的是荣格,他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原型。“在神话学研究中它们(原型)为‘母题’;在原始人类心理学中,它们与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概念相契合;在比较宗教学中的领域里,休伯特与毛斯又将它们称为‘想象范畴’;阿道夫·巴斯蒂安在很早以前则称它们为‘原素’或‘原始思维’。”[1](P83-84)荣格通过这样的类比,对原型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说明,并指出原型是一种先天的“自主精神”,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是人类原始思维中共同的情结。文学原型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体现一个民族或人类共同精神元素的形象,是“具有生理基础的维度、心理体验的维度和文化模式维度的多维联系的精神文化现象”[2](P68)。
河流作为一种自然物象,转变为原型性意象,其历史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它是原始先民无数次对河流的感悟转化成的一种心理积淀,最终使人类对河流具有了普遍一致性的认知体验。文明始于河流,人们称古代文明为“大河文明”。两河流域成就了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长江、黄河哺育了华夏文明,印度河、恒河滋养了古印度文明。在以农业为本的国度里,因为河流与生命、与农作物生长的紧密关系而产生了对河流的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原始宗教的最初阶段是对“自然实体的直接崇拜”[3](P220),其中就有对河流的崇拜。这种河流崇拜逐渐成为根植于农业社会生活土壤中的自然宗教,影响到人类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艺、哲学、宗教等领域的方方面面。
河流来源于自然,它涤去污垢,还世界洁净;河流也是仙界与凡尘的交界,是人类和神灵交往互联的通道。人类跋涉渡河,为的是提升精神境界,慰藉精神和身体的伤痛。神话故事中,河流通常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传说中的伊甸园就是被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基训河和比逊河四条河流所环绕、滋润的园子。民间习俗中,农历七月初七,也称“七夕”。相传这一天,仙姬织女要下天河沐浴,天上的河与地上的河是相通的,所以河水都具有了灵气,这样的河水久贮不坏、驱邪除病。农历三月三,古称“上巳”节,主要活动是河中浴洗,“《后汉书·礼仪志》说‘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为大洁’”,又“《南齐书》说‘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4](P291)古人相信,在河边沐浴能祓除不洁与疾病,所以称之为祓禊。河流因为洁净的作用而神秘地具有了祛疾辟邪的功能。
河流的流动特性和清洗功能相结合,在神秘性的刺激下逐渐演变成了对灵魂的洗礼功能。中国古代文人自溺江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就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意思,当然历史上还有诸多贞洁烈女也通常以沉河的方式以期获得灵魂的洁净。在印度,佛教信徒死后把骨灰撒在恒河之中以求获得灵魂的永生;印第安人葬前也要用河水洗涤尸身,来获得死者灵魂的洁净。
《圣经》中约翰给耶稣施洗,施洗后的耶稣脱去俗气,以救世主的身份获得新生。洗礼“一方面象征着洗去原罪的污浊,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即将开始的精神上的新生”[5](P205)。新生意味着得到救赎,这个意义由“耶稣在井边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进所说的‘活水’这一词组特别地提示了出来”[5](P205)。有源之水,自泉涌出,循道而流,“不断更新自我,是一条无尽的河流”[6](P46),可见,这种洗礼的水是活的、流动的河水。所以,神话中,伊甸园中的四重河水在上帝之城中再度出现,在宗教仪式上则体现为洗礼。荣格认为,“宗教仪式、教义等等就是一种包含了圣秘体验的原型再现”[2](P193),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河流与基督教的洗礼仪式被作家用来表现作品主人公通过河流得到救赎,开始精神上的新生。
“原型象征一旦获得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它原初肇始的意义也许就会丧失。而随着文化背景的变化,还会获得其它的意味。”[7]在文学作品中,河流原型的每一次出现就如同进行了一次重构,将河流的救赎原型性象征的古老精神以新的形式进行激发,产生新的活力,在展示共同心理机制的同时,又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所以,现代人面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河流的救赎原型象征在作家的作品中反复被书写,只是具体到不同的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意义不尽相同。在《约檀河之水》(张资平)、《施洗的河》(北村)、《阿难》(虹影)文本中,河流的救赎原型象征意义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又有着不同的内涵。文本中的河流在表现作者的精神观念、传达作者的情感和心理因素的同时,又揉入了作者对本民族文化进行的思考。
二、救赎与新生:从《约檀河之水》到《施洗的河》
约旦河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他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的河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约檀河之水》(张资平)和《施洗的河》(北村)两部作品的创作年代相隔70年,历史时代背景大相径庭,但都同时选择了以施洗约翰在约檀河为耶稣行施洗的典故,也是对河流的救赎原型性象征的运用。
《约檀河之水》讲的是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韦先生和寄宿客栈老板的女儿被他叫作芳妹的女孩的恋爱生活经历。两人在没经家人允许的情况下,过了一段有实无名的幸福的夫妻生活。在韦先生到矿山实习离开的时候,芳妹发现自己怀孕。在姨妈的安排下,她到乡下待产,照顾她的医生是一位基督徒。在这个基督徒医生的影响下,芳妹意识到自己的“罪”。当然,这个“罪”不是法律上的罪,而是违背了神的准则,在结婚以前和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算作是奸淫罪,是对以后待嫁的丈夫和神的罪。芳妹最后选择了皈依基督教,她的想法和做法也影响到了韦先生。
小说结尾,男主人公韦先生最后的一点希望——他和芳妹的孩子夭折后,他的精神已经崩溃,“河流”——基督教中象征救赎的约檀河,再一次在教堂颂诗的歌声中出现,此时的河流代表着救赎。这个从认识罪恶再到承认被上帝赦免救赎的结局,让小说最后充满了基督教的思想色彩。这大概和张资平本人所受的教育经历有关。他13岁就进入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堂学习,经过了四年教会学校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很深。但张资平作为“五四”时期高举个性自由解放旗帜的“创造社”的发起人,他的创作也必定不会停留于宗教救赎意义的表达。《约檀河之水》中虽然韦先生通过歌声里的约檀河得到救赎,但作品的主旨仍是“五四”个性自由解放的时代表达。这从他后来的作品中对基督教会及教徒的阴暗面的暴露批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
张资平对基督教的宗教想象最多的是看到了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三天后复活的救主耶稣却被他忽略了。小说中出现在歌词里的“约檀河”只是作为“洗礼、除罪的一个固定象征……意义基本上是凝结的、单向度的”[8]。河流的流动能指在作品中没有表现,作品中韦先生的忏悔止于当下,愿意悔改被救赎后的书写戛然而止。
河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河水是活的,具有流动性,河流如果失去了流动性,那么它作为河流的意义也就终结了。无独有偶,在张资平发表《约檀河之水》的70年后,北村《施洗的河》诞生。《施洗的河》中的河流所承载的无论是绝望与救赎还是理想与罪恶,都与流动的水流一起绵延不绝。北村没有在作品中明确地说那施洗的河流就是约旦河,但在新约《圣经》里,施洗约翰给众人施洗的河流就是约旦河。《施洗的河》的故事也是围绕着罪恶与救赎的主题,流河所承载的救赎意义与基督教有关。
刘浪的罪恶好像一出生就开始了,他是在菜地里浇粪的母亲陈阿娇被父亲刘成业强奸的结果。当年刘成业拉上裤子站起来时说了一句:“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能操出个儿子,也是个臭蛋。”[9](P9)母亲和她的婆婆也为能打掉胎,想尽了办法,可是刘浪还是顽强地出生了。这也暗示了,刘浪执着的生命一生都要在洗除自己的污秽和寻求纯洁的救赎的征途中跋涉。幼年的刘浪在缺少温暖的家庭中长大,成人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开始不断地追求地位、名誉、金钱、权力、女色。他贩卖烟土、杀人越货,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放过,成为黑社会以恶抗恶的南方一方城镇霸主。在城市学校学得的医学知识非但没有让他知书达理,反而使他用更加残忍的手段来作恶。他有钱、有权,还有着富家少爷的身份,有知识、有声誉,但这些都无法满足他灵魂上的需要,他在精神上找不到依托,以致最后全面崩溃,万念俱灰。这时他乘船顺流而下,河水荡涤着他的灵魂,他在河流中反思:“如果当初我是一个医生,携着漂亮的妻子,我会过上一种平静的没有痛苦的生活。但让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没有如果,这一辈子,没有如果。”[9](P218)这个曾经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现在只能蜷缩在小船里,仿佛感到身体在一块块地破碎。与他的反思形成映衬的是河流:“河水在光斑中流动,这是一种不间歇的流动,当黑夜暂时覆盖它时,仍能听到河水清晰的流声,预备着迎接晨光的呈现。”[9](P239)刘浪在流动的河水中体验到了新生的冲动和对自由的渴望,在溺死前吸足了一口气,最后他得救了。被救上岸的刘浪,在基督徒的帮助下,放下心中的罪恶,接受河流的洗礼。刘浪得到了救赎,找回人性本原的真善美。
刘浪的生命如同昼夜流淌的河流,并没有因为被洗礼后而停留下来,他继续向前蜕变。刘浪承担了救赎昔日死对头马大的使命,在他的努力下,马大最后放下手枪,迷途知返。他带着马大顺流返程。船行驶在水面上,刘浪“第一次发现河水是如此清晰,它透澈得如同人本来有的面貌,让光进入水里,呈现出河里洁白的鹅卵石”[9](P240)。小说在《以西结书》的朗读声中结束,河流上的“歌声击打着水面,一切都是和谐的”[9](P242),人性得到了救赎。
这条河流本来没有名字,也充满肮脏,如果河水不流动就会继续肮脏,最后变得腐臭无比。北村运用了一种纯粹语意上的扭转,让河水在阳光之下,变成洁净生命的施洗的河水。刘浪的生命就仿佛河流一样总在不停地在向前流动,河流带走了脏物,生命曝在阳光的河流上,才不断地变化,纯洁、洁净、得救,就如刘浪可以抛下一切恩怨仇恨,去拯救仇人马大,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多次被羞辱后还依然坚持。
从《约檀河之水》到《施洗的河》,从张资平到北村,河流的救赎意义也更丰富、更复杂。对人性与罪恶的书写更加深刻细腻,不再仅局限于情欲的原罪里挣扎,而是关于物质、欲望、权力,揭示人性的奸诈、贪婪、杀戮、虚无的复杂生命情境。对于救赎原型,荣格曾这样阐释:“圣子基督本人便是‘重生的’,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他从水中再生,从精神上复活了。”[5](P101)河流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所以北村在小说中也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强调刘浪经过河流的洗礼被救赎的过程。北村不仅仅看到困在十字架上用鲜血洗净罪恶的耶稣,他更看到了生命的流动,被救赎的复活的生命流进了信仰者的灵魂中。他用基督教义来救赎罪恶的人们,用施洗的河流洗去刘浪身体和灵魂上的原罪。这条河对人们来说是救赎的河流,带有了上帝和诸神让罪恶之人获得精神与肉体的解脱的拯救任务。
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阿难》
在长江边长大的虹影是河流的女儿,几乎每一部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河流上面”[10],如《饥饿的女儿》、《K》中是长江,《阿难》里面是恒河,《一镇千金》和《给我玫瑰六里桥》中也出现了河流。《阿难》中的恒河是罪恶与救赎的象征,它承载着两家人的孽缘与劫难。一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另一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父辈们在“二战”时期结下的恩怨,随着恒河水流淌了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由他们的下一代人来承担。虹影通过恒河表现的也是“罪”和“救赎”的主题。
有“罪”的存在,才能有救赎。《阿难》中的每个人物都带着罪恶生存着,莫里森设计陷害了黄慎之和库尔玛,父辈的恩怨延续到了子一辈苏菲和阿难的身上,苏菲和阿难一直深陷在罪恶的旋涡里。作品中的“我”似乎以作家和侦查员的正义身份自居,其实也正陷入和丈夫的情感纠葛中,并且为了寻求解脱和孟浩发生了婚外性关系,无信仰主义者没有解脱赎罪之途,于是只能清晨走入冰冷的恒河。河水冰凉刺骨,“我”发出这样的慨叹:“人如蚁蝼,人的罪孽真的也是蚁蝼之罪。洗洗吧,都来洗洗吧。”[11](P209)
虹影在作品中想要借助宗教来涤除罪恶,河流是这种宗教力量的象征,“恒河西北岸,追求超脱凡俗生活的人,喜欢聚集在此地苦修”,他们相信“在这圣河中沐浴,就能涤去一生罪孽,灵魂变得纯洁”,印度教徒都渴望自己能在恒河边死去。“死后家人将遗体运来此处火化,骨灰撒入河里。火化要有钱买木材,没钱的,把尸体捆上石头扔入河里喂鱼。据说灵魂也能成正果,借此超生。”[11](P86)
“宗教的一端源于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惶惑,另一端通向他们对未知的探索;连接这两端的,则是一种永恒的拯救意识”[12](P160),而救赎的目的,最终要使人从“罪”的认知走向“罪”的反抗。通过救赎,人类的“罪感”才不会停滞于功利性的态度,才不会导致精神的长久委顿。虹影以宗教为依托,让河流成为解决矛盾冲突和摆脱虚无痛苦的手段,使河流成为具有宗教救赎意识的象征体,所以在《阿难》中处处体现着佛教的人生无常观,人物想要摆脱俗世间的恩怨情仇,得到救赎,走向恒河是唯一的途径。
河流真的能够轻易地洗掉人性的罪孽吗?是自我安慰还是真正的解脱?其实虹影自己做了回答:“我在这里是对宗教狂热的一种否定。河是存在的,宗教是可敬的,狂热却是人类永恒的悲剧。”[13]可见,虹影自己对宗教力量是怀疑的。
北村和虹影都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摆脱罪恶的束缚,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救赎,期待重生。《阿难》和《施洗的河》中的河流都代表的是原罪与救赎,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北村对宗教思想的态度是积极的,面对黑暗他是乐观的,而且也相信宗教对解救人类精神信仰的可靠性;而对于虹影来说,她对宗教思想抱着怀疑的态度,阿难和苏霏死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还是世俗的生活,唯一让我懂得的真理是玩世不恭,“睁开眼睛比闭上眼睛更能事事皆空”[11](P228),罪恶仍在继续。
赵毅衡在《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一文中认为,《阿难》的主题是流浪,写的是两代人的流浪故事。[14]流浪和逃亡不同,阿难从歌星到富商,在金钱的诱惑下,他犯下罪,来到印度应该是逃亡,可是小说中阿难尽管被人追踪,但他没有逃跑的欲望。人在竭尽现世努力的同时,难免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对现世的解脱,面对不可或缺的物质功利,他们既要投入自己,又力图超越自己。所以,此时的阿难反而更像无根漂泊的浪子,家国已失,金钱名利于他也已经厌倦,只想着自由流浪。
小说中阿难的流浪路线刚好和释迦牟尼与弟子阿难沿恒河传教以及玄奘游历的路线相一致,可是此时的阿难虽然流浪,但已经没有信仰。“有形的文明越是发展,人们就越能感受到丧失信仰的危险。有限的理性越是成熟,人类对终极的意义就越是关切。”[12](P203)所以如果想让这种有着终极意义的流浪的精神状态永恒,恒河的救赎是唯一的途径。
作品中阿难的人物形象扑朔迷离,人生状态总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其实,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大矛盾、大逆转的人生,阿难只是其中的代表。20世纪的人类离开了教堂,似乎又无路跨进天堂。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内在的而不是添加的悲剧性。它的症结,就在于迷失了原来那条通过服从和功利性的信仰拯救灵魂、解脱苦难的天堂之路。从阿难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代中国人很浓重的悲剧性的生命感,尤其体现在所谓的“精英”群体身上的精神分裂现象。
20世纪踏上现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的思想状态是处于信仰的真空地带。“卷入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最深刻的困境并不是经济或知识体系上的,那可以通过‘转型’来克服,而有一种困境既必然发生又无法克服,亦即对自身文化的不认同(或曰难以认同)。”[15]小说以佛教中的圣徒尊者来命名,是有深刻寓意的。尊者阿难最后得到救赎,“阿难”有着救赎的意义;另外,“难”字也可以指苦厄、灾难。小说中的阿难出生后就失去父母,他无依无靠,漂泊一生,最后走进恒河,一个“难”字穷尽一生。这其实已经不是个体的遭遇,可以说阿难的人生境遇代表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处境。“阿难是一个精神危机象征:这种危机,部分是他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个体的存在危机,部分则作为一种缩影,以反映置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厄难。”[15]小说中描写印度教徒在“大壶节”时,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来到恒河与神灵一起沐浴。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这样的宗教仪式可以使其去除身体、灵魂的罪恶和人生的灾祸,从而求得精神上的救赎。可是,对于阿难和辛格上校,他们两人是印度教的叛逆者而不是信仰者,所以靠宗教信仰是无法得到救赎的。但他们虽然背叛宗教却崇拜恒河,更渴望自己的灵魂不再漂泊,有家可依。
虹影以她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独特的悲剧性视角,书写了现代人无可回避的生存困境。在作品中,河流凝结着虹影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认识,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想象及文化立场的外在表现。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一切绝对价值,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颠覆的同时,也对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价值体系进行颠覆。那么,在一切绝对价值被颠覆、消解后,人们只有两种途径可以走:一是回到传统价值秩序;二是借助宗教,进入“终极信仰”。深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感受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的虹影,坚信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并非信仰危机,而解决的办法,并不是进入恒河或其他什么圣地所能解决的。中国人解决危机的途径是要回到自己原有的精神家园,进一步说,是要自我认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伦理和思想价值观要肯定、认同。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不管在哪里,都是长江的女儿,感觉自己站在河流的边上,祈祷着能有人来相救,“把命运彻底地改变”,可是后来发现救自己的人,“只能是我自己”。[10]虹影作品中的河流不但是生命救赎的象征,而且更有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东西方文化对立冲突的蕴涵,“河流来融合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原罪’,她还试图用宗教来解决跨文化语境下的思想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疑惑”[16]。作品中“救赎”意识的根源并不局限于宗教信仰,而更“是一种解救自我、超越悲剧的精神”[17]。
虹影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代表,享有一定的声誉,作品深受海内外欢迎,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的“跨越疆界”的生命体验,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使她对事物、人生的体验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带着这种独特感受和敏锐的眼光创作的作品拓展了文学作品中河流的救赎原型象征内涵,使河流增添了新的精神品质与内在品格。
[1](瑞士)荣格.荣格文集[M].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2]程金城.原型批评与重释[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3]卢红.宗教:精神还乡的信仰系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4]向柏松.中国水崇拜[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于弗.中国文化中的水意象[J].北方论丛,1998,(2).
[8]曾阳晴.两条救赎的河水——张资平《约檀河之水》与北村《施洗的河》比较研究[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1,(2).
[9]北村.施洗的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10]胡辙.解读虹影——虹影访谈[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2).
[11]虹影.阿难[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2]杨慧林.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3]关于流散文学、泰比特测试以及异国爱情的对话——虹影与止庵对谈录[J].作家,2001,(12).
[14]赵毅衡.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3,(5).
[15]李洁非.为何去印度——对虹影《阿难》的感思[J].南方文坛,2002,(6).
[16]李湘.论虹影小说的河流意象[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17]余文博.论虹影的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例[D].泉州:华侨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