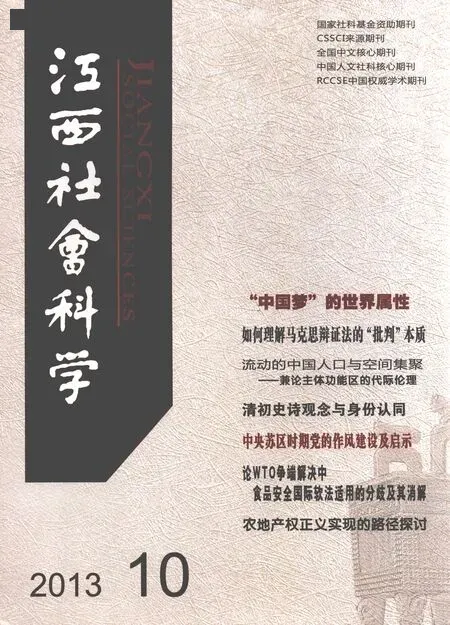清帝南巡与“江南三阁”
何 峰
清帝南巡与“江南三阁”
何 峰
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是清代江南地区的官方藏书楼,主要贮藏《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修建是南巡景观营缮事务日益成熟化的体现,修建之初作为帝王南巡行宫中的三处御书楼,主要贮存《古今图书集成》,但随着江南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及在清帝国文化系统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江南三阁”最终与北方四阁一样,获得贮藏《四库全书》的地位,并且成为江南地区三处公共图书馆,内藏典籍一定程度上可供文人士子借阅抄录。晚清数次战火纷争,江南三阁彻底被毁,典籍也多散佚,唯有文澜阁在清末得以复建。
清帝南巡;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四库全书》
何 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流动站博士后。(北京 100871)
清圣祖康熙皇帝和清高宗乾隆皇帝先后各进行了六次大规模南巡,从康熙帝1684年第一次南巡到乾隆帝1784年最后一次南巡,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南巡期间,两位皇帝优容江南士绅,大规模召试江南文人才子,在江南各地接收或收集书籍和名画,既达到了控制江南文化社会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以汉文化典籍纂修刻印为核心的国家大型文化事业储备了人才和资源,如《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的修纂。江南社会的文人和文献资源成为清帝王建立盛世文化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中江南文化社会彻底融入清帝国文化体系。至南巡末期,为彰显南巡胜迹、犒赏江南文化社会,清王朝建立了江南三阁,以贮藏盛世文化典籍。
《四库全书》藏于七处地方,即大内、圆明园、盛京、避暑山庄、扬州天宁寺大观堂、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镇江金山江天寺。前四处为帝都及陪都的宫殿或别苑,江南三处则位于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南巡的行宫。
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圣祖继统,诏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书,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彬彬向风焉。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1](卷一百四十五《艺文志一》,P4219)
颁赐书籍是帝王南巡的一项传统,彰显了帝王对江南文化教育的关怀。南巡早中期,江南三阁尚未修建,帝王多将重要书籍颁赐给江南著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如乾隆十六年(1751)清帝南巡,曾颁赐江南各重要书院“殿板经史”,“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2](卷三百八十四,乾隆十六年三月戊戌)。随着南巡对江南景观影响的日益增强,至乾隆中晚期,江南三阁建立,成为清中叶江南地区重要的国有典籍贮藏与传播之所。
一、“江南三阁”的建造与书籍收藏过程
扬州天宁寺行宫文汇阁和镇江金山行宫文宗阁应由两淮盐政衙门及盐商建造,初建时可能与乾隆皇帝向行宫颁赐《古今图书集成》有关。文汇阁修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南巡之前,“此阁成于庚子,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曾颁贮古今图书集成全部”[3](卷二十《文汇阁叠庚子韵》)。 文宗阁大概修建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778—1780)之间,庚子年南巡,乾隆帝有御笔:“前岁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于金山行宫,鹾臣建阁以莈,并请扁额,名之曰文宗阁,并御书‘江山永秀’额赐之。”[3](卷十六《金山四叠旧作韵》)文汇阁和文宗阁修建之初皆冠之以 “御书楼”之名,至乾隆帝庚子南巡时,方御赐“文汇”、“文宗”之名。杭州圣因寺行宫原辟藏经阁藏 《古今图书集成》,后改建为文澜阁,增贮《四库全书》。延丰等《重修两浙盐法志》载:“高宗纯皇帝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藏庋群籍,复念江浙为人文渊薮,宜广布以光文治,命再缮三分,赐江南者二,浙江者一,浙江即以旧藏图书集成之藏经阁改建文澜阁。 ”[4](卷二《图说》)《清史稿》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丙申,建浙江文澜阁”[1](卷十四《高宗本纪五》,P523),大概至乾隆四十七年,文澜阁方改建完成。[5](卷首)
北方四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和江南三阁,都仿造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规制建造。天一阁主要用砖石砌成,防火效果较好,在以木构建筑为主的中国古代,非常适宜做储书场所,且内部设置防潮透风。因此,乾隆三十九年 (1774)六月令寅著前往察看天一阁,以备仿建北方诸阁,作为贮藏《四库全书》的场所。“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与之相见,告以奉旨,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 ”[2](卷九百六十一,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丁未)乾隆帝有“御制文渊阁记”载:“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2](卷九百六十九,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乙未)江南三阁获颁《四库全书》之后,所贮四库典籍藏书规制、书架设置则完全参照文渊阁等北方四阁。[5](卷首)
文澜阁建于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行宫,“阁在孤山之阳,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文澜阁分藏《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阁建三成,第一成中藏《图书集成》,后及两旁藏经部,第二成藏史部,第三成藏子、集二部,皆分庋书格。凡四库书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册,为匣六千一百九十一。图书集成五千二十册,为匣五百七十六。总目考证二百二十七册,为匣四十”。[4](卷二《图说》)除内部藏书设置参照文渊阁等北方四阁的形制,文澜阁部分景观也仿造北方四阁建造,如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及杭州文澜阁都建有趣亭,乾隆帝 “御制趣亭诗”按曰:“御园之文源阁继山庄之文津阁而南屏以假山,俱有趣亭月毫,文津阁咏月台有米家范兼奇之句,兹文澜阁亦仿其式为之。 ”[5](卷首)
文汇阁建于扬州天宁寺大观堂旁,是扬州天宁寺行宫的组成部分,“御书楼在御花园中,园之正殿名大观堂,楼在大观堂之旁”[6](卷四《新城北录中》,P103)。《扬州画舫录》记载文汇阁藏书情况,“恭贮颁定图书集成全部,赐名文汇阁,并东壁流辉扁。壬子间奉旨江、浙有愿读中秘书者,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皆有藏书。着四库馆再缮三分,安贮两淮,谨装潢线订。文汇阁凡三层,莊莋楹柱之间,俱绘以书卷。最下一层,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畔橱皆经部,书面用绿色绢,中一层尽史部,书面用红色绢,上一层左子右集,子书面用玉色绢,集用藕合色绢,其书帙多者用楠木作函贮之。其一本二本者用楠木版一片夹之,束之以带,带上有环,结之使牢”[6](卷四《新城北录中》,P103-104)。藏书格局与文澜阁一致。
从上大致可知,江南三阁内部藏书规制 “仿文渊阁格式藏贮”[4](卷二《图说》),比较统一,一般为三层,下层贮《古今图书集成》及经部书籍,中层贮史部书籍,上层贮子部、集部书籍。
因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江南三阁初建时并没有打算贮藏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巡,高宗题扬州《文汇阁》诗:
皇祖崇经训,图书集大成。
分颁广流布,高阁此经营。
规拟范家制,工因商众擎。
亦堪匹四库,永以贮层甍。
按语为:“阁中贮分颁《古今图书集成》,此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为之。四库全书繁重,不能分贮各处,故只赐《图书集成》一部。 ”[3](卷十六)
最初,江南三阁所在建筑并非为颁四库全书而建,应是乾隆帝历次南巡,行宫营建日渐完善,有仿京城建御书楼之意,且基于对江南地区文化地位的认可,欲将康熙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御赐部分南巡行宫,当地盐政官员和商人即建楼以贮,并称之为御书楼,而浙江孤山圣因寺行宫则辟藏经阁藏《古今图书集成》。兴建江南诸御书楼时,四库全书基本编纂完成,然考虑到《四库全书》繁重,抄写不易,因此并未打算分贮江南,乾隆帝分别给扬州天宁寺行宫御书楼和镇江金山行宫御书楼赐名“文汇、文宗”,虽与北方四阁名称相为匹配,但诸阁并未获取与北方四阁同贮《四库全书》的地位。直至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方才改变想法,七月初八日谕内阁:“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所以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3](卷七十四《莌俊》)
乾隆四十九年(1784)南巡,高宗题《文汇阁叠庚子韵》:
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
遂以推行庋四库,况因旧有匪重营。
西都七略江干现,东壁五星霄际擎。
却待钞完当驿致,文昌永古焕重甍。
按语为:
此阁成于庚子,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曾颁贮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壬寅秋以四库全书分莈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者,均可按期蒇事。因思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愿读中秘书者不乏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敕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各贮四库全书一分,俾士子得就近观摩,并饬发内帑银百万于京师雇觅书手缮录全书三分,驿致莈阁,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3](卷二十)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颁赐给江南三阁后,江南三阁也获得了与“北方四阁”近似的文化地位。
二、“江南三阁”的文化功能
乾隆帝非常重视江南三阁的公共文化功能,要求《四库全书》藏于三阁之后,允许士子借阅,各阁委派专员管理。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谕:“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材,稽古右文之至意。”[2](卷一千一百九十九,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丁丑)江南三阁与北方四阁的区别在于:前四处所贮《四库全书》深藏宫中,秘不示外;而江南三阁则一定程度上对各地文人士子开放,原则上文人士子可以阁内阅览,甚至可以把书借出来,抄录传写,相当于清朝在地方上的三处以收藏中国文化典籍为核心的国家图书馆,在清代江南社会发挥了公共文化机构的功能。尽管因为借阅典籍须要事先声明,对部分普通文人稍显不便,但此间江南士大夫及地方官绅通过师承、游幕等途径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一些知名学者士绅如阮元、杨世沅等在遇到友人需要校勘古籍、考订文献时,也常介绍其前往江南三阁查阅资料。[7](《重刊乾隆句容县志序》)因此,对于有一定影响力和交游圈子的江南士人社会而言,江南三阁为乾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
嘉道年间,文人士子对“江南三阁”的利用还是比较频繁的。不少文人学子前往这三处地方观摩研习,一些专注于古籍研究的学者经常到阁中抄阅史料,考订经籍。文汇阁建成之后,“嘉道以来,人才辈出,或研究传注、羽翼经训,或咨诹掌故、明习典章诸子百家之说……今自李志所录外,甄录书目又得三百余种,区以义类,后之征文考献者,庶几兴起于斯也”[8](卷二十上《艺文考第十上》)。 乾嘉年间,江浙皖等地考据学兴盛,江南三阁应能为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文献条件。不少学者在编校古籍时以江南三阁所藏典籍为参照,“金山钱锡之府莍冲雅耆古,读书喜校勘文字异同。每恨若云氏书决择未当,又板毁殆尽,计所以重订,乃益出藏书,聚同志商莗去取,讨论真赝,反复雠对,民间乏善本,则准之以文澜阁本,或注案语,或系札记”[9](补遗《守山阁丛书序》)。 朱骏声,值文汇阁时,“曝书往读未见之籍,有得即录之”,“著经义数十种,尤邃于许氏说文,有说文通训定声三十二卷,嗣升扬州府学教授”。[10](卷十五《人物寓贤》)长沙府醴陵县人罗文谦至扬州拜会大学士阮元,抄录文汇阁藏书,详考两丁礼器、乐律,纂辑成谱[11](卷一百七十八《人物志·国朝人物四》)。一些民间失传的书籍被地方文人重新从 “江南三阁”中抄出,并继续流传。陆以莙曾抄录文澜阁四库本《续名医类案》,“钱塘魏玉横之琇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世无刊本,余从文澜阁借四库本录一部,凡六十六万八千余言”[12](卷五《续名医类案》)。一些州县编修地方志也常要到这三处地方查阅历史文献。道光年间,福建“宫保尚书孙公莅政之暇,以闽志间阙,与抚部韩公议设局三山,延聘文学之士任编纂,明年疏闻于朝,独慨文献零落,旧闻坠湮,因博搜前代载籍,近者假之士大夫,远者借钞于越中文澜阁及天一阁,于是桑梓遗文雅记往往颇出”[13](卷六《闽都记序》)。私家或普通府州县所藏之书毕竟有限,而编修方志,需要广搜前代资料,因此离福建比较近的“文澜阁”及“天一阁”可为之提供便利。清代许多士绅喜好编修藏书志,此举也得“江南三阁”之便,浙闽各地多用文澜阁版本,如陆心源《莚宋楼藏书志》、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等。
“江南三阁”作为国有图书馆,管理与借阅制度完备,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职能,备有专门的收掌、校勘之官整理收发图书,文澜阁“委员掌之,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借观传写,设档登注,勿令遗失污损,所以嘉惠艺林者至矣。夫前代书籍多藏秘府,牙签锦帙,外人莫得而窥,间有颁赐给借,已属仅事,如我朝之以四库缥缃津逮末学,莝莟福地,遍及东南,诚旷古所未有也”[4](卷二《图说》)。江南三阁的收掌之官多为文人学者,“文宗阁,江都汪容甫管之。文汇阁,仪征谢士松管之。汪容甫尝欲以书之无刻本,或有刻本而难获者,以渐梓刻,未果行而死。今容甫所管改为申嘉佑、吴载庭管之,申为笏山副宪之子,工诗”[6](卷四《新城北录中》,P104)。作为文宗阁收掌之官,汪容甫在四库典籍校勘与刻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终因“校勘文宗阁四库全书,往杭州借书”,因病“卒于西湖葛岭僧舍”。[14](卷七《人物志·儒林》)
即使对于文化发达、刻书印刷业非常繁荣的江南地区而言,将历史时期各代典籍汇纂在一起,此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孟森曾评价道:“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陟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 ”[15](P554)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杭州刊成《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时任浙江学政阮元曾有“跋”曰:“兹复奉命视学两浙,得仰瞻文澜阁于杭州之西湖,而是书适刊成。士林传播,家有一编,由此得以津逮全书,广所未见,文治涵濡,欢腾海宇。”乾隆皇帝荟萃全国文人的力量,并基于各代流传的典籍,完成四库全书的编纂,并使之拥有公共服务的功能,对于传统中国书籍借阅刊刻主要在小圈子里流传的状况而言,“江南三阁”确实可以满足广大知识群体需要。《四库全书》中的不少典籍,民间并无刊本或善本,清政府 “博采遗籍”,并将历朝深藏内府的典籍进行刊印,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尽管四库全书的编纂存在篡改事宜,难免有错漏,但对于资料获取非常困难的古代社会,“江南三阁”已经可以发挥地方核心文化机构的作用了。
三、晚清“江南三阁”的毁圯
道光年间,西方诸国入侵中国沿海地区,发起多次战争,中国沿海地区景观遭受创伤;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双方战火延及整个江南地区。康乾南巡期间建立的江南三阁在一系列战火中彻底被毁:“先是道光壬寅岛夷陷镇江,毁焦山三之一,及粤贼焚金山,则片瓦俱尽。今为合肥李伯相所葺,然十裁二三。”[16](卷十七《游金焦北固山记》)“咸丰癸丑发逆,陷镇江、扬州,文汇、文宗二阁毁,庚申九月淀园不戒,文源阁毁,辛酉十一月杭州再失,西湖孤山为贼踞,焚文澜阁,亦毁,七阁仅存三矣”[17](卷一《繛汋山房睉记)。道光壬寅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癸丑即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攻陷镇江、扬州;辛酉为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攻陷杭州。一系列战事致使江南三阁彻底毁灭,书籍多有散佚。阁毁之时,地方士绅和书院曾收杭州文澜阁残籍,“郡绅丁申、丁丙收残籍于兵火中,计得九千余册,借府学尊经阁尊藏”,后光绪年间,浙江巡抚谭钟麟重建文澜阁,“奏请颁御题扁额移庋于阁,俱复旧制,以昭慎重”[18](卷一《图说》),而文汇阁和文宗阁的书籍基本散毁难寻。
魏源曾经写过一封“与曲阜孔绣山孝廉书”,该信应写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认为镇江和扬州二阁太过靠近,且金山行宫在江中,不便文人士子前往阅读,而曲阜是先师故里,泮水行宫也是当地胜景,应将镇江分贮之《四库全书》改贮山东泮水行宫,以便齐鲁等地北方士大夫借录参阅,且曲阜深入内陆,可避免江南兵灾:
泮水为曲阜城中第一胜迹,旧属衍圣公燕游之所。自乾隆中建行宫,遂为官地钦工,终年封闭,茀为茂草,何不奏改为泮池书院,略加葺理。俾四氏子弟肄业其中,鱼藻与弦歌映带,人文必且蔚起。而四军官书七分,颁置江浙者三分,其金山与扬州相距四十里,而得两分。金山在水,中央人士无从瞻莡,何不奏请移金山文宗阁书一分于阙里泮池,建阁中央,敬谨庋藏。既可托于灵光文献之尊,为历代兵燹所不及,而齐鲁学士大夫亦得以借录官书,见闻日广,于国家文治之隆,大有裨益,此不可不陈者。[19](外集卷八)
晚清数次战争都发生在长江下游地区,南巡塑造的地域文化景观至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事后再看,魏源当时的建议确有道理。然而魏源生活的年代,清朝已过盛世,清政府疲于应付各类内外困境,再也没有能力像康乾时期有足够的精力来设置、调整及保护以诸阁藏书为代表的清盛世典籍文化工程了。
四、结语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臻于极盛的时期,其代表性事件之一即清政府对中国历代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以康熙时期的 《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代表,尤以后者为繁巨。为完成这一旷世巨制,清政府势必依赖文化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的江南地区,在两位皇帝南巡过程中,清政府充分调动和吸收江南社会的文化力量,主要表现在人、物等多个方面,使之成为清帝国建立盛世文化工程的重要力量。
江南三阁为后世所熟知,则因其是江南地区贮藏《四库全书》的代表性文化机构。然江南三阁初建时,并非出于贮藏《四库全书》之需,而是南巡皇家景观营建日渐完善及清政府开辟江南文化根据地的产物。江南三阁皆建于帝王在江南地区的三座行宫,作为帝王行宫内的御书楼,起初只是贮藏了体量较小的《古今图书集成》。但江南地区重要的文化贡献和影响力及江南士人对文献典籍的需求,最终使乾隆皇帝决定将江南三阁作为《四库全书》的典藏之地。这也成为清王朝在充分吸纳和利用江南文化力量后,对江南地区的一种文化 “回馈”,江南地区获得了与京城宫苑 (北方四阁)近似的文化荣宠,也拥有了此后帝王进一步向地方颁赐文献典籍的主要场所和空间,并且在地方政府及文人士大夫看来,江南三阁成为地方最高等级的权威藏书机构。
与北方四阁不同,江南三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有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功能,江南三阁藏书可供文人士子查阅抄录。乾嘉之后,江南地区学术考据风气盛行,文人士大夫文献考据兴趣浓厚,江南三阁丰富的典籍资源为此提供了便利。嘉道年间,江南三阁成为江南士人学者查询文献、校勘古籍、编纂书册的权威场所和学术空间。
然而,道光以后,晚清江南地区的数场战争,最终导致江南三阁景观建筑与藏书的毁灭。南巡政治影响下的江南三阁,其文化功能仅维系了半个多世纪。文宗阁和文汇阁本《四库全书》已散佚难寻,仅有文澜阁在光绪年间得以重建。在地方士绅的努力下,文澜阁本 《四库全书》几经周折,大致保存完好,成为清末地方政府和士绅挽救清盛世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成果。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高宗纯皇帝实录[M].清实录影印本(第9-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钦定南巡盛典[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清)延丰.重修两浙盐法志[M].清嘉庆六年刻本.
[5](清)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M].光绪二十四年钱塘丁氏嘉惠堂本.
[6](清)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乾隆)句容县志[M].光绪二十六年重刊本.
[8](光绪)江都县续志[M].光绪九年刊本.
[9](清)胡培莢.研六室文钞[M].光绪六年刻本.
[10](光绪)增修甘泉县志[M].光绪七年刊本.
[11](光绪)湖南通志[M].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2](清)陆以莙.冷庐杂识[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3](清)陈寿祺.左海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4](民国)歙县志[M].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5]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清)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清)平步青.霞外莣屑[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8](民国)杭州府志[M].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19](清)魏源.古微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王立霞】
K249
A
1004-518X(2013)10-01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