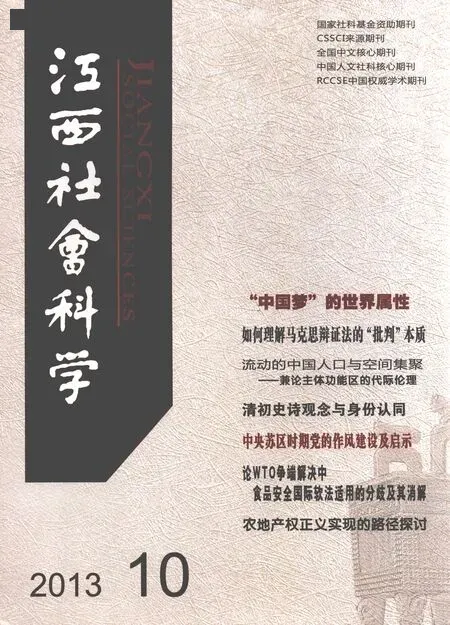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曲 蓉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曲 蓉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公共信任;道德信任;不信任;美德
曲 蓉,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浙江宁波 315211)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信任已然成为社会学领域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主题。这容易招致一个误解,即信任只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帝王的信任就被看作是王权合法性的伦理基础,孔子所谓 “民无信则不立”。英国思想家洛克也强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信任关系。可见,伦理学界对信任的关注要远远早于社会学界的深入研究。在伦理学领域,信任研究首先要解答一个重要问题:信任是一种美德吗?在本文中,这一问题具体化为,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培养的一种美德?
一
要回答开篇的问题,首先要回答公共信任是什么?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过公共信任的概念与性质,试图展现公共信任的复杂性。信任是一种与未知领域的行动相连的信念,而公共信任则是私人圈子外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特有的一种信任。公共信任是一种普遍信任,同时又包括对制度或价值观的信任;公共信任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策略,更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1]信任(公共信任)有无道德价值,这是信任研究中持久争论的主题。以卢曼、哈丁为代表的学者们坚持认为信任是一种策略,否认信任蕴含道德价值。卢曼认为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有效形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2](P10)哈丁强调信任是一种预测性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基于信任者对自身利益的预期。因此,信任是一个 “非道德性的概念”,应该与利他主义区分开来。[3](P270-271)另一些学者则在相对的立场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尤斯拉纳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一书中提出:信任是一种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一种乐观主义世界观。道德信任要求个体如同他人是可信的那样去行动,是不信任的对立物。[4](P19-22)简·曼斯布里奇认为道德信任是一种“利他信任”①,包括同情行为和原则行为。而奥弗认为信任的道德价值“不是出于轻率的习惯或因为这 ‘符合他的秉性’,而是出于一种尊重信任的道德责任感”[3](P47)。辜负信任者的假定和信念是不正当的。
信任在人类关系中普遍存在[5](《前言》P1),由信任产生的互惠是生物生存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3](P115)公共信任能够协调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加强与一般社会成员的联系,巩固日益分化复杂的社会系统,支持现代民主制度,维系社会良善的价值观。尤其是随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分化,公共交往日益频繁,对公共信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如果不能培养公民基本的公共信任的话,就会造成 “公共信任危机”,甚至会颠覆原有的高水平的私人信任文化。公共信任是有利的,是现代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就这一点而言,公共信任是有价值的,是值得选择的。但要证明公共信任具有道德价值,还需要证明在某个时间点上,即使公共信任不能为个体带来利益,也是应当选择的。
公共信任具有无可否认的道德价值,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相比之下,策略信任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果信任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信任就是好的行动策略;相反,如果缺乏风险保障或者缺乏收益的情况下,个体不会给予信任。换句话说,作为策略的信任,只有在有利于信任者的情况下,才能确立起来。而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和经验。公共信任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信任者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促进他人或公共的利益,或者为被信任者提供自由行动的空间和成长的机会。一位初登讲台的老师,一名毫无经验的医生,一项积极但未成熟的制度,等等,如果没有最初的信任是不可能获得成长、成熟的机会的。而且,为了整个社群的利益,公共信任者还需要坚信社会系统中各种社会角色能够履行自身的职责,各种精心设计的社会制度能够良好运行,社会良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信任需要信任者独自承担信任的风险,却没有任何收益。尤其在看似不可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使我国慈善组织和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如果不信任现有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当然可以减少信任者行动的风险,但在慈善事业中受益的人们将会直接感受到不信任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在缺乏风险保障的情况下,为了那些急需帮助的受赠者的利益,个体也应当信任现有的慈善组织及运行机制。②在这里,个体承担了公共信任带来的风险,个体的利益也可能招致损害,但这种信任有利于受赠者,也有利于现有不成熟的慈善组织和制度得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因而是有利于整个社群的。
公共信任还受同理心、善意的影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每个人既是施信者也是受信者,在申请工作、商业合作、初次与别人交往时,个体需要得到他人的信任。人类同理心要求每一位通过其他人的信任获得或者期望获得成长机会的人,首先应当去信任他人。“黄金规则要求的不是他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人,而是你期待他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人。”[4](P26)善意也会影响公共信任的确立。个体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会经历许多坎坷,会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会遇到 “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并不需要自己扮演警察或正义使者的角色,去裁判这个人是否有罪,而只需要给眼前有困难的人给予善意的帮助就可以了。简·曼斯布里奇认为:“当信任出于同情、或者出于意在对他人有益的某项原则、或出于坚持某一通常对他人有益的理想时,我将之称为‘利他的’信任。”[3](P271)由此可见,公共信任是个体的行动原则。正如尤斯拉纳所言,公共信任是康德所言的 “定言命令”而非 “假言命令”,信任他人并非是达成信任者愿望或可能愿望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是信任者的责任。只有公共信任才能作为“普遍规律”的行动准则。
二
就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而言,还需解决两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一是公共信任与可信性的关系;二是公共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信任问题研究者都探讨过信任与可信性的关系。支持信任具有道德价值的研究者认为信任有助于激发可信性,因而具有道德价值;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信任是对可信性的一种预测,是一种单纯的冒险。他们进一步强调,既然信任与对可信性的预测相关,那么,对缺乏可信性的人或事物给予信任就是盲目的、病态的。例如,卢曼认为,如果信任是一种道德命令,那么,人们就不能盲目付出信任,而只能在其应得的地方给出信任。[2](P103)换句话说,卢曼认为,所谓的道德信任是与对可信性的认知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与信任植根于不充分的认知能力相矛盾,因此,信任不可能具有道德价值。
事实上,公共信任与可信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对这一关系的充分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信任的道德价值问题。“高水平的信任是从高水平的可信性中产生的,并可能与高水平的可信性积极地互相影响。”[3](P285,注释1)当然,必须承认高水平的可信性对公共信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坚持法治运行,商业企业诚信经营,公共事业部门投身公益,公民个人信守承诺,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的诚信行为,有助于公民之间结成一种信任关系。相反,公民的背信行为、公共职能部门的弃责行为,破坏公共秩序和伦理关系,将造成公共不信任,甚至引发信任危机。
但也应意识到,公共不信任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可信性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争议不断的“彭宇案”引发了公众对老年人群体的不信任,此后发生的类似案件③更深化了这一不信任。人们由此推断,正是背信行为导致了公共信任危机。其实不然。大多数“碰瓷”案件为团伙作案的诈骗案,为什么为数很少的几个与老年人相关的碰瓷案件却会引发“公共信任危机”呢?这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相关,与法官依据常理进行司法推定相关,更与公众喜欢偏听偏信有关。④但其最根本原因与老年人的道德地位动摇及下滑相关。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体迅速扩大,这也导致了老年人与青年人在社会利益分配上必然发生矛盾冲突。而且,传统社会老年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而新时期青年人成为社会引领者,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下滑。这种地位下滑与典型事件结合起来,引发了信任危机。对老年人群体的信任危机可能是老龄化社会危机的一个表现,可信性仅仅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颠覆公共生活基础的不信任也在于当前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公共信任是信任者主动给予被信任者的一种好处,这种好处的条件,即要求被信任者通过自身的可信性予以回报。与此同时,这种回报是非强制性的,对被信任者仅仅具有道德约束力。而一旦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信任者就丧失了主动地位,如果被信任者滥用或背弃这种关系,信任者必然会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诚如前文所言,公共信任必须建基于利他主义基础上,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者既不可能基于被信任者的利益建立信任关系,也不能因此放弃道德上的主动地位。这种价值观的泛滥自然会造成“公共信任危机”。换句话说,可信性只是影响公共信任的重要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相反,公共信任还有助于激发可信性。我们都有类似的日常经验,在很难建立信任关系或缺乏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信任者以明确的方式 (语言或非语言的方式)向被信任者表明双方信任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信任的难度,要求被信任者避免失信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唤起被信任者的可信性。而后者如果滥用这种信任关系,则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能弥补或挽回。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公共信任激发的可信性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作用和影响,但这种看似鸿毛之轻能够撼动泰山之重。
大多数学者在讨论信任问题时都会不可避免地论及不信任。怀特认为不信任有两种:基本的不信任和程序的不信任。基本的不信任或者质问人的善良意志或者质问制度的基本目的和目标;而程序的不信任则指向一个人的能力或个人品质或指向制度的手段或方法。她认为无论是对个人或制度而言,基本的不信任都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力量。[6](P76-77)卢曼认为信任与不信任都能克服和简化可能性,都是合理的。不信任不只是信任的反面,也是信任在功能上的等价物。[2](P93,125)在所有反对信任具有道德价值的理由中,其中一个似乎特别充分,足以推翻全部关于信任具有道德价值的论证:既然公共信任与不信任都具有重要价值,那么,公共信任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道德命令。因此,我们接下来必须解释公共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说公共信任具有道德价值,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具有道德价值?
在探讨公共信任的复杂性时,笔者已经承认公共信任与不信任都具有重要价值,都是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公民积极参与、结成各种利益团体的心理基础,尤其是对公共部门保持警醒的不信任能够避免政治犬儒主义。而缺乏信任和不信任的话,公民很容易成为公共生活的“搭便车者”。[1](P59)诚然,公共生活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醒的不信任,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做出过多、过于美好保证的政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不信任的制度防范代理人滥用我们赋予他们的权力。作为一种行动策略,公共不信任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公共不信任仍然存在问题。从表面上看,公共不信任是对可信性缺乏的一种预期。实际上,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理性。诚如前文所言,“彭宇案”所引发的不信任是深层社会矛盾导致的结果。还有一类公共不信任是由日益发展的专业化服务和行业壁垒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在高度社会分工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专业化服务:政府代表我们行使权力,专家为我们提供知识和信息,商业企业为我们提供生活用品,学校帮助我们教育孩子。没有他们,我们只能退回到小国寡民、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与此同时,专业化也造成了行业之间的壁垒:对专业知识和充足信息的缺乏导致了安全感的丧失;几乎没有人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控制赖以生活的全部环境,也很难有效制裁外在环境中的失信行为,个体对生活环境的控制产生无力感。可以说,安全感的丧失和无力感的存在是公共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此外,如果将信任看作是对可信性的预期,包含了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期望,而信任者本身的期望或意愿超出被信任者的角色要求,由此引发的不信任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对不信任的研究并没有否定公共信任的道德价值,相反,它为公共信任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不可否认有大量违信行为的存在。就此而言,公共不信任具有合理性,有时甚至是更有利的行为策略。然而,只有公共信任才具有积极的力量,才具有道德价值。不信任的意义何在?公共不信任的价值首先在于提醒信任者公共信任是有风险的,背信行为随时可能发生。在意识到风险的情况下建立的公共信任才是理性的。其次,公共不信任也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程序存在的。民主制度、程序法、银行信贷、上班打卡等等都是作为制度和程序而存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既为公共信任提供了基本保障,又没有消减公共信任的价值,因为背信行为仍然存在,信任仍然需要信任者承认信任的风险。
三
要进一步证明公共信任是如同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美德,除了说明公共信任具有道德价值,还需要说明公共信任是我们正确行动的能力,是我们作为人特有的存在和行动的方式。美德是一种我们人道地存在和行动的方式,是我们正确地行动的能力。精神美德能使一个人显得比另一个人更人道或更优秀。[7](《前言》P3)
信任是一种与未知领域的行动相连的信念。当可信性显明时,信任没有意义;而只有当可信性无法验证时,信任才具有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常识以及风俗习惯有助于个体建构可信性。我们依据经验、常识以及风俗习惯就可以安心生活,而不必担心明天早上找不到地铁站,也不必每天都重新看地铁线路图。这里,建立在可信性基础上的安全感以及对生活的控制感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熟悉,是潜在的信任。相较之下,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更像是一个非经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风俗习惯被超越,常识和经验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可信性受到挑战,这时公共信任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仅仅依靠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难以建立信任。常识、经验以及风俗习惯的共同特点是稳定性,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恰恰充满了变动,要不要建立公共信任就成为个体的选择和信念。例如,我对货币的信心是建立在常识和经验基础上的熟悉,是一种潜在的信任;只有当其他人购买黄金以规避通胀风险,而我面临继续持有货币还是购买黄金的选择时,信任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公共信任超越了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是在我们的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行不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在可信性没办法验明、常识行不通的情况下,信任者将为自己的信任承担风险,几乎没有收益。在私人信任中,对违信行为的制裁可以通过持续的交往关系得以维持;而在公共信任中,信任者缺乏对违信行为的惩罚机制。这意味着当个体选择以信任的方式行动时,同时放弃了保护自己的主动权,将之交给了被信任者,给予被信任者甚至是那些值得怀疑的对象以行动的空间以及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公共信任是很难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公共信任是为他人或整个社群利益而非信任者自身利益所作出,必须独自承担信任风险的自主意志选择。这种道德信任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充分意识到世界的另外一面——充满了罪恶,了解人性善恶的两面基础上所保持的信念,坚信人性是向善的,世界是充满希望的,而且人类具有改变自己、他人和世界的能力,使之越变越好。用尤斯拉纳的话来说,这种信任来自于乐观主义世界观。[4](P98)
注释:
①也可称为“利他性信任”、“利他主义信任”。参见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郑也夫、彭泗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②据报道,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 “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国内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慈善总会和基金会接受捐款的数额减少,但社会捐款总量未发生明显波动。许多网友表示不再捐款,但个人身份捐款额波动很小。这也说明了我国公民的公共信任是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的。参见 “中国慈善组织近 3月受捐额剧降近九成”http://news.163.com/11/0826/04/7CBTAQ7A00014 AED.html。
③例如,有“天津彭宇案”之称的许云鹤案、“南通彭宇案”等。
④以“南通彭宇案”为例,摔倒的老人及其儿子根据路人提供的信息 “人被撞了,车跑了”,选择报警寻求法律帮助,而在人证和视频证据的帮助下,双方很快解除了误会。这里其实根本不存在“诬陷救人者”的情况。但是,媒体和公众宁愿相信这是一起因救人而导致的冤案,如果没有公交车上的视频录像作证的话,这将成为另外一起“彭宇案”。而这种造成救人者和被救者矛盾的根源正是公众缺乏公共信任所造成的。参见2011年9月1日 《中国青年报》“是我们误会了,我们不会做骗钱的事”。
[1]曲蓉.论公共信任:概念与性质[J].道德与文明,2011,(1).
[2](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M].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英)帕特丽夏·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M].朱红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7](法)安德烈·孔特 -斯蓬维尔.人类的18种美德[M].吴岳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赵 伟】
B824.3
A
1004-518X(2013)10-0027-05
科技部软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城乡统筹与农村生活形态变化研究”(2010GXS1D094)、宁波大学学科项目“现代社会发展与公民素养培育”(SZXW1012)、宁波大学学科项目“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好公民塑造”(XKW11D2016)